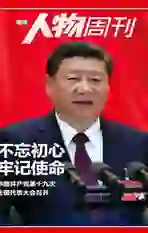仇晓飞我旁观我的画从过去回到未来
2017-10-28蒯乐昊
蒯乐昊
无论一个艺术家的风格和艺术语言如何嬗变,其个人经历、文化身份、国别传统,就像血液一样,始终难以被置换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图/佩斯北京提供

站在工作室里的仇晓飞看起来像一个梦游的少年,他个子很高,作为一个画油画的人也显得过于白净,四周整齐地堆着他那些大尺幅的画,大罐的颜料在升降机前排着队,陈设看不出个性。只有那些画面冲外的画布成为视觉会激烈捕捉的对象,大多是不合理的、冲突的、梦魇般的色彩和形状。“如果不画画,我是个极度无趣的人。”
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出门,只是常常做梦,他出人意表的动作,都在他的创作里。从央美毕业之后,他们一批人成为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青年艺术家,作品卖得很贵,很受藏家追捧,他本可以这样一路画下去,可是他却突然改变了方向和语言,像一条突然改变了坐标的船,向即兴和抽象的海域驶去。
从过去回到未来
“有点像在时间里面,你找到一个虫洞,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随着画画的深入,仇晓飞发现,时空上的环状结构无处不在,每天不停地重复,未来可能回到过去的某点,“今天中午12点的太阳和昨天中午12点是相接近的,如果比喻成绘画,这一点画出来的东西可能和离久远以前的一个时间点更接近。你嵌入的那个点不一定仅仅跟过去有关系,有可能跟未来有关系,有幻想、有幻境存在。”他把这种博尔赫斯在《交叉小径的花园》里隐喻的时空螺旋循环,提炼成了一条蛇的形象,环状盘曲,并且长了一张愕然的人脸。
绘画语言上的巨变,始于他自央美毕业第十年。在2012年之前,他还会做很严密的画稿,从小幅的草稿,到大幅的油画,类似一种誊写关系,“做稿你会考虑结构,考虑形象,考虑设置关系,这种方式都偏古典。但是,我所探讨的问题可能跟潜意识有关,是心理的一个瞬间。我画小稿的时候忽然捕捉到这一点,当我誊写到大的画稿,往往它就失去了,这种方式太间接了,慢慢我就发现,即兴的方式更适合我。”
转型是痛苦的,有大半年的时间,他没有画出一幅画来。只要创作,焦虑就无处不在。仇晓飞用长时间的审视和小范围的实验渡过了这段时间,第一幅转型之作《干叶》,后来在佩斯北京的个展上被挂在入门最醒目处,一个提纲契领式的开场。他记录下了当时的过程,他把半罐喷漆喷向画布,喷到一半的时候,粉红色的漆没有了,这是他不能预设的,只好换上蓝色、绿色的漆,在渐变中,新的空间关系诞生。
借读生
仇晓飞的父母都是所谓“红二代”,“文革”中被下放到哈尔滨,他就在那里出生,十岁左右才随家人重新回到北京。那时候的东北大工业还未萧条,尤其是哈尔滨,“洋气得很”,东方小巴黎,有着浓郁的异国浪漫情调,而北京却是另一番风貌,又大又土,“像一个很大、很大的县城”。那种开阔,对一个孩子来说,似乎也是压迫。母亲是单位集体户,父亲回京属于借调,仇晓飞上了北京的初中,但是却没有户口,“这在当时是一个挺严重的事儿,没有肉票,家里买肉就很困难,单位一时分不了房,那时也压根没有租房市场,都得自己想办法解决。”首都很大,但是对他们一家来说,都是“借”来的。借读生成绩好坏,不影响学校升学率,老师也就马马虎虎,如果考不上全国招生的高中,考大学也就没有借读生的份儿,为此父母日夜悬心。老师说,要不,你学俩特长吧,考上美院附中,那可就是半条腿跨进中央美院了。
仇晓飞一直记得他刚到北京的时候,父亲领他去看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对顾德新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好奇。等他上了美院附中,整个当代艺术的潮流已经开始了,他在那个时候看到王鹏、赵半狄他们的实验艺术,第一次看到装置作品。
到了央美,头两年基础课,“其实很无聊”,跟附中一樣,画石膏,画肖像,画风景和静物,但是,新潮文学、实验戏剧,包括摇滚乐在当时都能给予他们营养,告诉他们主流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那是一个信息平行涌入的时代,美术史在西方有其前后承接的脉络,但是对于仇晓飞来说,它们几乎是同步的,文艺复兴和杜尚、欧洲古典主义和波普在同一时间进入他的思维体系,“艺术史对于我们从来都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从视觉和经验来讲是混乱的、浪漫主义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几乎是他们这一代美术青年的共同记忆。两年后,仇晓飞进入刘小东工作室学习油画,当时刘已经是一位明星艺术家,“他不保守,比如我感兴趣装置,他也能说得上他的角度。他经常带画册来给我们看,给我们讲波依斯,而且他全世界地走,眼界广,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
记忆碎片的叠加
很多油画艺术家一旦弄上装置,就不再愿意回到架上了,装置艺术的直接、体量和力感,常常是传统的架上绘画所不能比拟的。但是仇晓飞却是个另类,学生时代和毕业之初,他的重心都在装置艺术上,最后却慢慢回归绘画。绘画因其冗长、亲力亲为的制作过程,变成一种心理释放的手段,成为个人疗愈的出口。
他曾经做过一组“样板间”的装置,“1992年我们搬进一个三居室,在定慧寺,老小区,单位分的房子,一直没有装修过,到了2007年,房子连墙皮都已经掉满地,实在不行了,得重新装修一下。家里那冰箱、电视都使了好多好多年,我爸妈还挺舍不得。”仇晓飞说,那就别扔了,都给我做成作品吧。满满一车拉到他的工作室,他把它们翻制成玻璃钢,在上面上色、描画那些家具和电器上的贴纸,“就是我小时候贴的那种,变形金刚之类。”在那个时代,每个人的家里都很像。
他发现他的创作方式有一点像编辑,用编辑的方式在处理图像。“在我的画面里面,一个很古典的方式和一个非常当代的方式、一种即兴的方式和一种构造的构图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我像在对待材料一样使用它们,有点像音乐家采样的大唱片,像科学家对待切片,或者像一个DJ在打碟。”endprint

3.女盗,2013-2015,木板,亚麻布,丙烯及油画,旧白瓷挂钩,塑料网兜,木球
互联网刚兴起时,对整个信息分享乃至图像生产都产生了巨大的颠覆,仇晓飞觉得,这些应该反作用于绘画上。他开始在网上搜索词条,下载相关的图形,然后在这些图形中寻找创作来源。比如他在网上搜索“与我的爱人和解”或者“疯人”,把截图汇总起来作为绘画的草图,那几乎是人类经验的通约,是在个人经验之上的合并同类项,但是又不同于达达主义的随机挪用。后来他发现,其实人的情感、思维、技艺,都是以相似的方式叠加和拼贴起来。就像他所欣赏的法国作家和电影人阿兰·罗伯-格里耶,他对电影最大的贡献,就是“对经验进行碎片化,同时对眼和耳这两种感官进行调控”,“焊接过去和现在,将它们完全融解在同一时间流中。”
几何体的性格
他画过一幅《悲观的暮年》,一边是蛇盘踞在彩色的地砖之上,另一边是黑白空洞的楼房前站着的中年妇人,被头顶的三角高帽子压得失去了面目。这是他在画自己的至亲。
他曾经专门关注过精神病患随手涂抹的图形,其中涉及大量的几何图案,“绘画从形象开始,最后又回归到形象。但其实我不算纯粹的抽象绘画,我的画里都有具象,空间具体的所指。比如说圆形,圆形在所有的绘画里它都不是一个稳定的形状,它是流动的,倾斜的,三角形则相反,它极度稳定,任何背景都不能够消解掉这个三角形,它始终跳脱出来。这很有意思,几何和心理、和你的意图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关系,几何体都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作用。”
仇晓飞的绘画受到极简主义的影响,但是他的展览或作品却往往有一个拗口的标题,似乎他总是不太信任可以轻易获得的东西,二元对立的,平行的,既此又彼的结构才契合他的价值观,比如《双摆》、比如《南柯解酲》:“一方面是梦,一方面是醉。梦和醉都是非理性的,梦有逻辑,有步骤,但是实际整体是荒诞的,醉是一个不清醒的状态,两者和谐又冲突。”他觉得这个世界有一个动力,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样,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协作,产生的动力使人得以直立行走,这似乎也昭示了一个心物二元的世界中最深层的驱动力。
他的另一个作品《山前木后山》,标题仿佛回文诗。最开始他画了一幅风景画,画中有三个虚构的木架子,画完他意犹未尽,又让木工师傅照着画中的比例,给他做了三个真实的架子,他把三个木架子的画,靠在真实的三个木架子上。“在审美结构上把自己抽离出来了,像一个旁观者,看着画在自己循环,让作品跟作品本身对话。”

3庙頂,2015,布上丙烯
单打独斗的十二罗汉
在央美的毕业生中,曾经有一个叫作N12的组织,囊括了当时非常活跃的12位青年艺术家,“之前可能八五新潮有过这种组织,后来就慢慢散掉了,然后就没有这种土壤了,艺术家们都单打独斗,很少以一种群体的方式亮相。”2003年前后正是中国当代艺术刚刚出现井喷迹象的时候,画廊业开始起步,N12就是在这种温度之下出炉的。“当时宋琨、王光乐他们几个人,就说我们组织一个展览,N12是一个组织方式,但是并没有共同的艺术宣言,没有彼此的约束和艺术语言上的协同,它不是一个艺术流派。当时的市场还根本关注不到年轻艺术家这个概念,仅有的几个画廊,比如说四合院画廊,做的都是方力钧、张晓刚这一代人。我们当时在中央美院位于王府井的一个陈列馆里做的展览,观众非常非常多,而且来的80%都是不认识的人,跟艺术行业不相关的人,那时候仿佛感受到了一种生态,非常旺盛。”
艺术行业趋于平稳之后,一切都变得不那么有趣。在展览上,永远是熟悉的面孔,像一个小圈子里自己人的游戏。这个是媒体,那个是藏家,这个是机构,那个是学院,展厅里出席的人就是一条完整而封闭的产业链。但在勃兴之初并非如此。2016年仇晓飞在纽约的佩斯画廊做个展,开幕时来了七百多号人,连展厅都挤不下,他有点吃惊,仿佛回到了当年王府井那个陈列室。
身份的寓言
仇晓飞这一代艺术家是幸运的,从毕业起就几乎没有体会过匮乏的滋味。“2002毕业的时候因为创作比较好,拿了一笔两万块的奖学金,在当时是一笔大钱,拿那个钱就生活了两年,到了2003、2004年就开始有画廊了,虽然开始的时候钱很少,除了买颜料、租房以外没有剩余的钱,但是也从来没有断过,最早的那些小画刘小东他们都买,相当于一种资助吧,最困难的时候,没钱吃饭了,就去考前班教教课,教几天就够生活了,我们真是相当幸运地赶上了好时候。”他和胡晓媛都是N12的成员,也都来自哈尔滨,毕业后双双成为职业艺术家,拥有各自独立的工作室,在创作上互不打扰。“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里是非常脆弱的,很谨小慎微地去维护自己的那一点点东西。那些东西也还在建立中,随时有可能倒塌。后来我们才学会了不置评,在过程中互相不置评。”
在今年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期间,佩斯画廊带来了仇晓飞的个展《问松柳》,亦被视为他转型之后风格日趋成熟的一次展览。仇晓飞说起他之前在纽约看到的一个罗马尼亚艺术家的作品,“他在影像中采访自己的母亲,母亲年轻时给领导人献花。当时他妈妈二十多岁,电视台采访她,没有录下声音,是一个配音给他妈妈配了声音。后来他妈妈已经五十多岁,他拿那个录像,重新去采访当年始末,他妈妈说,这是胡说八道的,这里边全都不是我说的话,但是他说,你看唇语,这就是你当年说的话。可他母亲完全回避这个事情。他在探讨身份文化的时候,你始终看到一个大屏幕上有一只手在弹奏钢琴,然后上面另外一个朋友也是另外一只手在弹奏钢琴。你会看到那个演奏的手,在停顿,在抖动,神经质地痉挛,这是一个一战时的作曲家,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他所有的音乐都是为独臂演奏者做的,但是后来的演奏者并不是独臂。他很巧妙,很有尊严地探讨身份的来源,而不是把身份作为标签来贩卖。这很高级。”这让仇晓飞开始反思自己,一个艺术家,无论他的风格和艺术语言如何嬗变,他的文化身份,他的国别传统、他的个人经历,就像血液一样,是始终难以被置换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