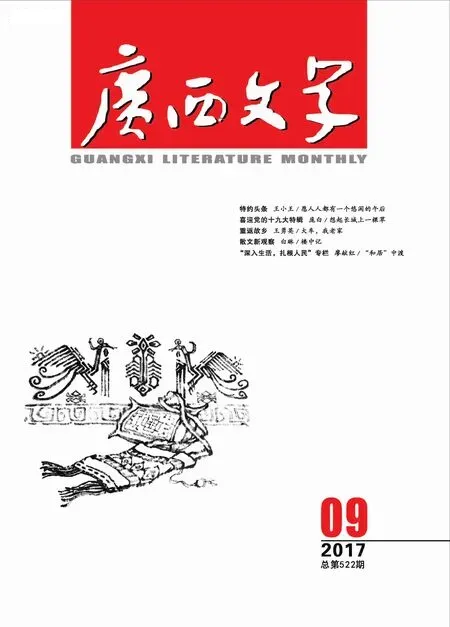大车,我老家
2017-10-22王勇英
王勇英/著
大 车
我的老家在博白东平,一个叫大车的山村。
初中离开老家到南宁读书,后来再转回东平镇中心校。高中阶段先后在南宁和博白就读,大学在南宁读,毕业以后在南宁居住。
学生时代,从南宁回东平老家还没通高速,坐班车走二级路要八九个小时,从南宁回老家,一路晕车,到了家,在山野中一走,吹一吹山风,喝几口泉水,精神就清爽了,而从老家到南宁,晕八九个小时到达之后,要两三天才缓过神来。毕业以后,每年春节、清明节这些传统节日,人多车堵,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要加入汹涌的回乡人潮,挤车回家。
现在,南宁到玉林有高铁,南宁到博白也有火车,回家方便了,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渴盼着回去。现在的老家,旧村老房古树纷纷倒塌,老人们陆续不在了,现在看到的老家是全新而陌生的,林立的高楼取代旧的村场,也占去原来的田野,人们纷纷从村子里搬出来,涌到马路两边,房子拥挤着紧贴着。山上几乎全是速生桉的鬼影,再无往昔那种林深木茂、山花野果的风景。
记忆中的故乡,就像照片上的这样:博白县内最高的玛肚嶂山稳稳地坐落在大车的尽头,左右伸出两条高耸的山带,把整个大车环揽在怀里,山带之中一片平野,土地肥沃,流水充足。村庄依次顺着山带挨在山脚处,也有一两个小村子,一两座古老的城堡坐落在田野之中。一年两季水稻,田野几乎常年都种着庄稼、蔬菜瓜果,只有十月禾收割之后,开春之前,大部分田野有短暂的闲落休整,闷一下冬,之后又是一片生机。
那个睡在记忆深处的故乡,静静的,万般美好。
在内心深处只有以前那个高山绿树,随处可见的瀑布、泉水、溪流,河里有游鱼小虾的家乡,只有那个青青稻田,有泥墙黑瓦,古老城堡与老树的家乡……
童年时的老村,每一条小巷,每一户人家,每一个人,他们的笑容,说话的声音,走路的姿势,甚至他们许多对话,我都记得。我总是有特别的能力,让眼前看到的那些高楼从视线消失,在同样的位置让过去的泥房老树、河流田野一一恢复。在那个时刻, 我就像一个拥有魔力的民间巫师,用意念和想象力在回忆的空间作图绘画,还原故乡。

大车20世纪80年代初的模样
厅 厦
我们村叫大龙田,客家方言叫起来就特别有趣:烫田或踏田,有些人的语气稍为特别些,听起来又叫“它田”,“它”字读去声,音尾拉得很长很长。
它田坐落在背夫岭脚下,山岭呈丰满的乳房状,树木浓郁,山上的树是全村公众树,私人不能砍,据老人们说关系到村里的风水,在这种风俗传统下,山头的树木得以保存。
泥墙瓦屋的一个大村庄卧在山旁树下,左右两边是田野,村前一条河流,然后又是田野。我们村隔着河流、田野与六一塘村相望着。
六一塘村,我们客家话叫起来就成了垒塘村,“垒”的客家方言发音跟装鱼的竹捞是一样的,每当说起或听有人说垒塘村,我便想到装满了鱼的竹捞。
我外公是垒塘村的,站在我们村厅厦大门前,就能看到在河流和田野那头的垒塘村,两个村子的厅厦大门远远地相向错开着。
客家话中的厅厦就是祖宗堂,也叫村祠。
据史记载,我们大车的客家人是古时候从中原迁来的, 由于中原战乱,自东晋年间开始先后有五次大举南迁。我们村的祖先从福建汀州迁江苏,再从江苏迁来。不知道先祖们经历多少艰辛曲折才走到这里,安居下来,形成现如今的村落风貌。
客家人的祖先是以家族的整体形式南迁,在漫长的南迁路中,族人们彼此团结、守护,客家人的骨血里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与群体意识,其他族群很难同化,因而客家人的传统习俗、文化得以完好传承与保护。
客家人有极强的崇祖传统,重视立祠、祭祖和修家谱等。在大车,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祖宗堂,里头供奉着全村人的祖先。祖宗堂是村里所有建筑中最大气的。但凡经过客家人的村庄,就算只有七八户人家的小村,就算住的是低矮的泥砖瓦屋,那个村庄的祖宗堂也会是最敞亮的,门头屋檐也一定会用上好的木材,透出气度,绝不会简单建就。
我们村是个大村,村里的建筑分布跟大车所有客家村庄一样,以祖宗堂为中心,各家民居左右排开。我们村祖宗堂左边的叫这片屋,右边叫那边屋,在祖宗堂后面靠近山脚处还有一处叫上高屋。我们村的祖宗堂应该是全大车最大气的,从厅厦大门到安放祖先牌位、供放香案的那一级殿厅,一共有四级殿厅、三个天井。大门之前不许起房屋,只有一块照壁,在最后那级殿厅和天井相接处,左右通有巷道,各通向上高屋和那边屋,从上高屋的巷道走出去,转一个弯也能通向这边屋,走到村外。在第一级殿厅和天井的左边有一条巷道,通往这边屋;在第二级殿厅和天井的右边有一条巷道,通往那边屋。其中第三级殿厅最宽大,长度也比其他长一倍半,通常村里人去世,棺材和尸身放在这一级殿厅,亲人们也陪在这里守孝,做法事。
祖宗堂既是祖先们灵魂的居所,人们在精神上有寻求护佑的依靠,但同时又有些害怕这里,天黑之后,这里安安静静的,小孩子一般不敢到这里来玩,民间传说,过世不久的人,鬼魂会从山上的坟地回来,可能会撞见。
在祖宗堂的左边,隔几间屋子的地方还专门建了一个叫花厅的侧殿,将近过世的人从家里搬出来,先放在花厅。花厅大门与厅厦大门并排着,一进门,有一个大大深深的天井,天井左边是一条露天巷道,天井右侧是一间很大的卧屋,大门大窗,光线充足,只是因为这里是安放将近过世的人的处所,又离祖宗堂的祖先有些远,听说牵引灵魂升天的白鸟就是飞到这里来引魂,平时少有人迹。只有谁家将有人过世,那家人才会有人来轮流陪守一两天,即使阳光再充足,这里也是生离死别的地方,充满了悲伤与阴森的气息。胆小的人,在大白天也不敢从这里走过,天色擦黑时连花厅大门外的空地都不敢靠近。
然而,在花厅天井尽头处却安放着一个大石磨,全村有几个大石磨,其中一个居然安放在这里。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做米粑,妇女们都要磨米粉或豆浆,人多时,人气就会把花厅的阴气驱散。我是在一次过节前跟奶奶去那里,才敢走进花厅看看,那里摆有一张木板、一张板凳。
也是那次我才知道曾祖父以前住在花厅旁边的房子里。曾祖父是有名的中医,关于他的传说有很多,爷爷、爸爸、叔叔还有村里的老人们经常说到关于他行医的各种故事。盛传秧地垌村有一个人的孩子病重,四处求医无果,那孩子的父亲抱着孩子来村里找我曾祖父,传奇的是那时我曾祖父已经被抬到祖宗堂的三殿厅。别人都是咽气了才放进棺材,他却与别人不同,要先躺进棺材里。混沌之时,那个父亲抱着快要病死的孩子来了。听说我曾祖父还没断气,只是先躺进棺材,便不顾忌讳,到棺材前来求曾祖父无论如何也要在咽气前给他儿子看看病。躺在棺材里的曾祖父临死前接诊这个病人,给他开出一副很猛的药,有大量石膏,这和以前诊过的医生所开的药完全相反,那个父亲慌了,生怕老医生脑子不清醒开错了药。曾祖父大喝一声,如果不用他开的这副药,那娃儿可能比他死得还要快。那个父亲按药喂下,病儿奇迹康复。这也成为曾祖父从医人生中的一大传奇故事。
然而,我从奶奶那里听到的关于曾祖父的故事却是另一个样子的。曾祖父过世前我爷爷和他的兄弟们轮流守护,奶奶餐餐送饭菜。奶奶瘦小,胆子也小,曾祖父脾气大,说话声音像打雷,又爱吃肉。奶奶说,一般快死的老人应该没有那么好的胃口,吃得不多,尤其是油腻的菜,可是曾祖父偏偏胃口好得不得了,餐餐要有肉,有一餐肉不够吃,便大声喝起来:“肉呢——这么少,我还没死。”奶奶模仿着曾祖父的声音。曾祖父这一喝可把奶奶吓得不轻,她端着空碗回去加菜,走到花厅的天井又听到曾祖父的喝声,吓得一哆嗦,摔了一大跤,爬起来赶紧走。奶奶跟我说这个故事时,曾祖父已经去世很久了,可她说有时候从花厅走过,耳膜响响,好像还听到曾祖父大声问她:“计煮好饭眠?得食饭眠?”(计:客家方言语气词;眠:吗)
我觉得曾祖父很有趣,一个医术高明、爱吃肉、声音大得像打雷、有时候脾气可能有点坏的老医生。还有,他的胆子很大,住在紧挨着花厅的房子里,不过,他是医生,救死扶伤,见惯各种生死病人,自然也就不怕躺在花厅里将去的人。
后来我从花厅大门外走过,都远远看到曾祖父住过的花厅旁边的那间房子,之后也不再那么害怕花厅了,终于有一天我自己一个人也敢从花厅的天井边走过。
花厅的那条巷道绕过石磨台,上几级台阶,就与一条小巷相连,一转就到我家楼前,再转就走到通往门楼的那条直巷。
村子中的巷道四通八达,彼此相通,且整个村子的泥房间间紧连相挨,门窗的朝向多数统一。在一条巷道中,往往是这样的景观:一路走过尽是人家的门口或一路走去全是高高的屋墙,门口不会特别大,窗口也极少,且小,多在墙头上方。

门 楼
古时候山里多匪,为了防匪进村抢掠粮食、财物,老家所有村庄几乎都筑有坚实的围墙,有钱的地主会筑高大的城堡,最有名的地主城堡有新城、老城、牛骨田。新城的城墙巨高无比,城墙面宽可以供一个成年人在上面躺着睡觉,这座城堡也是大车老家至今仍没倒塌的城堡。没那么富有的村庄便全村团结,用河石还有灰砂浆垒起高墙,筑一座村城,比如我们村。门楼的门关起来,祖宗堂的大门关起来,这边屋、那边屋还有上高屋几个巷口的门都关起来之后,村子又成为围墙之内的一座村城,村内四通八达,墙体屋瓦巧妙相接,在村中行走,不被月头(太阳)烤晒,也不被雨水浇淋,总之不用戴帽不用打伞。旱天不愁饮水,有几条山泉水也有溪水流经村中,雨季也淹不着,村里的水沟排水能力一流,再大的雨水灌进村子里来,转眼之间就能排到村外的田地或河流道中去。如有匪来,大小村门关闭,人们可以一两个月不出村庄半步。人们从高墙上的小窗观察村外的敌情。土匪也常带枪前来,以前村里有火粉枪,枪手队伏在窗前,必要时开枪还击,点射匪头。这种枪战打匪的故事,我只是从爷爷那一辈的老人口中听说。在我出生之时,已是太平之年,传说中村里所有的枪支全部上交政府。
各村不再需要厚厚的城墙防敌抵匪,人们开始嫌墙过高过厚,出入村子不方便,才从内往外破墙。
我们村的高墙也不例外地开始被人们推倒。
客家人的民居建筑多讲究风水,祖宗堂前多立照壁,再有一口有活水左倒右出的鱼塘。我们村的鱼塘前还有一个打谷场,打谷场有前门后门,还有高高的围墙,场内有一排房子,专门放粮食的。收割季,人们把禾谷收回来,拉牛拖碾脱谷,通常挑灯通宵,之后就是晒谷,晚上收回屋里放着,第二天太阳晒干了谷场再倒出来晒。小时候我们村里的孩子们绕着高墙走,捉迷藏、玩打仗,闻声而难得见人。可是,后来,村周边许多墙陆续被推倒,打谷场的墙也被推平,只留下低矮的墙根。祖宗堂前的照壁也被推了,印象中那照壁做工精细,雕有许多图案,是凝集了民间工匠们艺术精华的民间艺术品。当时的村民毁了多么珍贵的古物!记得那时我还小,站在已经被推平的打谷场附近的门楼上,远远看着一大群人在议论怎么推照壁,听到他们说祖宗堂大门前没有任何阻挡物才好,放眼看去一片开阔的田野。每每想起照壁,心疼,与祖宗堂一样,有好几百年,珍贵的古物,就这么被村里人粗暴地推塌。
门 楼
十多年前,南宁电视台去我老家拍我的节目,拍摄点就定在村里的门楼前。门楼可以说是最具有客家民居村庄建筑特色之处。那时村里的老人三六叔公说,门楼已有几百个年头。
门楼在村里是很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在客家人的村庄,祖宗堂、门楼是最重要的。祖宗堂是村里人灵魂的归宿,可以说是客家人精神上的圣地。客家人团结,一村人都是同一个老祖宗,同宗同根,其实一个村就是一个大家族,村也就是一个家,门楼也就是家的门。对于外出闯荡的人,从门楼出发,亲人在门楼送别,算是出门了。人们自远方归来时,踏进门楼就是回了家。出嫁的女子,客家方言有出门之说,也是踏出村子的门楼就从此作别娘家,嫁出去了。娶进来的媳妇,从门楼走进来,就叫进门,从此是这个村的人。
在老家,但凡去一个村子走亲戚,远远看村就先看到门楼,进村先从门楼进,离开从门楼出,才显得大方、光鲜、明朗。通常,门楼是村子人气最足的地方,闲时日里,人们坐在这里闲聊家常。夏天,门楼通风凉爽;冬天,门楼里头的空地搭几根老树头,从早到晚都有人来烤火,有专门来烤火的,也有路过坐下来暖暖手脚再继续去干活的。村里的老人们最喜欢坐在门楼里,边看孩子边做些针头线脑的活计。村里一对夫妇会生几个孩子,孩子长大再成家又各生一窝,当了奶奶的老人就得同时带看几个娃,每天忙着做虎头帽、小衣裳、布鞋子。老人面前多会摆一两张竹摇床,摇床底下安根滚木,还小的娃儿躺在摇床里,老人一脚踏在滚木上,轻轻来回推踩,摇床轻轻摇着娃儿。会爬的绕在门楼里,丢一个笨笨的木头人或一个手缝的粗布娃娃,小孩子们能抱着玩大半天。村里的孩子从小兄弟姐妹多,按照传统,大的都会带看着小的。就连家里养的土种狗也无比忠诚,守在小主人身边,小孩子要是去河里或水塘里玩水,狗要么咬着衣服拖回来,要么跑回大人面前吠几声报信。
有人来村,从门楼一进一出,大家就都晓得谁家几时来了什么亲戚,几时走,挑来了什么,又捎回了什么,清清楚楚。不从门楼走的,在众人看来就是在闪,闪着来闪着去的人定有见不得人的事,背后里要遭人嚼舌头。
小时候最喜欢在门楼里玩,人多,成群的孩子玩,天天像过节,还有很多大人在说古讲今,有听不完的离奇古怪事。妇女们买块好看的头巾,姑娘穿件好看的衣裳都到门楼里来展示展示,就连夫妻婆媳姑嫂之间的吵闹也爱摆到门楼里来,当着众人的面摊派,让众人听听、评理。有些夫妻打架,女人都逃到门楼才收脚,在那里有人帮着拦着,讲开了就劝和。
就连榨茶油都在门楼前面的空地榨,榨好了茶油在门楼前分。不榨茶油的时候,那个用一截两个大人手拉手才环抱得过来的大树掏空做成的榨油槽就摆在门楼内左侧厅,门楼栓杆、榨板、盖和木桩靠着墙依次摆开。门楼顶上还搭有一个棚,上面放些公众用的器材。大胆的孩子敢爬到上面去看,但是被大人看到肯定被责备,因为他们脚步不知轻重,跳来跳去弄落些灰尘来。
大人不喜欢灰尘,尤其是爱在中午太阳很好的时候烧水在家门前洗了头发的阿婆、妇女、姑娘们,她们到门楼来说话、吹头发,那些灰尘会落在她们洗干净了的头发上,拍打不干净又得重新洗一次。特别是那些爱甩两条大长辫子的姑娘,洗一次头发很费事,弄出灰尘来的孩子肯定不被轻饶,跑得快的只挨一下骂,跑得慢的被逮着,屁股上少不得挨几下。村里家家亲,对惹事精们随时能摆出辈分来代你父母教训一番。然而,孩子们却喜欢让木棚弄下灰尘来,我也特别喜欢,阳光从瓦顶的亮瓦片穿下来,抬头往上看,灰尘从那些阳光束中飘荡过时,像雾一样美,那不就是老人们讲古的仙境吗?我甚至期待从阳光染成彩色云雾的尘烟中看到仙人腾云驾雾而来呢。
从门楼进来的巷子,人多,热闹,但是记忆中,我曾经感受到过空寂无声的门楼和巷子。
四岁左右,有一天,天蒙蒙亮我就起来了。就要过节了,村里人都会在过节前的这一天一起打扫,挑水冲水沟,去河边洗锅碗。我喜欢过节,也喜欢过节前村里人一起为过节做的这些事。头一天我有了一把新扫把,八叔扎扫把时多扎了一把小一些的给我,交代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扫地。去年我只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没有机会拿扫把,今年如果表现得好,说不定我也能拿起水勺跟哥哥姐姐他们一起倒水冲水沟。冲水沟最好玩,村里有一首歌谣,就是在过节前冲水沟时唱的,大家一起用客家话哼着:“开啦啦——开啦啦——大家担水冲拉茶——”意思是,冲水啦,水声哗哗地流,大家一起挑水回来冲干净水沟里的垃圾。
我激动得早早醒来,拖着扫把,到门楼等着。心太急,盼天亮,就觉得大人们起得迟。在等待中,村子里安安静静的,我家的狗晚上不太睡觉,在二楼的阳台上躺着守家。那时它老了,睡眠比我奶奶还浅,我刚打开门板门,就看到它站在门前摇着尾巴,在我下床的时候它肯定就听到声音了,我们家二楼房间的地板全是木板,走路有声响。
老狗陪我到门楼,我坐在门楼左边的木门墩上,它趴在我脚边,抱着扫把玩了一会,然后就走到地坪那里,原来村里的狗都早早起来了。从门楼往前看,石板和大龙眼树外面的田野被晨雾盖着,往后面看,背夫岭上的山根本看不清楚树的影子,雾浓得很,都流到瓦顶上来了。那时候我很担心,如果雾不散去,太阳会不会就不出来?太阳不出来天就不亮?村里人都睡着不醒,今天怎么打扫?

从村中我家老楼往下看到的旧房子
那个早晨的寂静让我害怕,我担心村庄不会醒来而错过过节前的打扫。许多年之后,我再次感受到这种可怕的寂静,而那时,不是早晨,是中午时分……
2009年,有一天打电话回家,妈说,我家在村里的老房子后面倒了一堵墙,原来住在我家老房子的人都搬走了,不敢住。妈说,再下几场雨,说不定老楼就会全倒了,想回来看看,拍照就快点回。第二天我就回去。那时我正着手写弄泥的童年风景书系《巴澎的城》《弄泥木瓦》等。弄泥是我的小名,客家话的音译。这几本书是以老家客家文化为背景的,写我童年的村庄、故事。在我的小说中,我家在村子里的老房子也是重点之笔。
书里的旧房子处于我儿时的模样,只是,当我回到老家,眼见到它时,已经苍老得让我担忧,木梯被虫蚀得到处是坑坑洼洼,小心地走踏上去,到二楼的走廊站了许久。
小时候我和大姐、二姐住在二楼尽头的这间。外公经常躺在这个位置的摇椅上慢慢地荡着,哼着戏曲,时不时看看阳台前面的瓦顶,从瓦顶上的太阳光看天色,什么时候下楼去灶屋做饭、喂小鸡。我也经常在这里蹲下来,趴在砖栏的空格处往下看,跟别人说话。有一次我把头伸进去,出不来,家里人想尽办法也没能把我的头拉出来,卡了许久,最后我妈决定找人来拆砖。村里的工匠说,这可不好拆,要再去找水平更高的人看看怎么拆。家里人分头去找人,我趴在这里等着。那时村里有一个远嫁的阿娘带着姑父和孩子回来探亲,带回很多饼、点心,她娘家的人正抬着吃的挨家走,发给村里的小孩子们吃。小孩子们闻风而动。那时还没发到我家,看到好几个小孩子从楼下的巷子跑去,打听到有吃的东西后,我口水直流,叫他们等等我,一直收不回来脑袋的我居然在美食的引诱下奇迹出现,一缩,头就收回来了,飞奔去讨吃的。一直守着我的老狗也跟着我跑,远远见到我妈,她已经找到一个工匠来看怎么拆砖,妈猛地见到狗和我,惊讶不已。
回忆着这些往事,心里有些酸痛,楼下右边的那一排泥房,也差不多倒了。爷爷、奶奶曾经住的房子是一个门进,有一米左右长的窄同子巷,入里一间是灶屋,左右各有一间侧房,这三间房子留给了明叔,现在明叔一家还住在那里。窄同子巷早就倒了,旁边那间村里公众的碓房也倒了,堂弟们把老房子修缮过,其中一间单独开了门,婶带着小女儿住,另两间大堂弟和他老婆带一个儿子住。周边是一片断墙的屋地。
我家在它铺街另起了一栋新楼之后,全家搬出去,这栋楼留给爷爷、奶奶住。爷爷、奶奶住一楼尽头的那间,第一间做灶房,中间那间八叔借用,放些谷物。楼上第一、第二间明叔家借住,第三间宁伯家借住。原来我家的灶屋和柴房先是爷爷、奶奶住了一阵子,后来再由明叔和八叔各分一间去借用。
那时我家可能是全村,或者可以说是全大车住上楼房最早的人家, 也是房子比较多的人家,但是家族之间还因房子的事闹过很大的矛盾。
明叔借住我家的楼房许多年后,想要,叫爷爷去讨。有一晚,全家吃晚饭,爷爷喝了一点酒,跟我爸妈说房子的事,要我爸妈答应把村里的那栋老楼给明叔。村里那老房子的屋地原只有一间是兄弟分家时从爷爷、奶奶那里分得的,其他都是爸妈跟村里人买来的,爸妈意见坚决,村里的那栋楼不能给明叔,但可以借给他们住。爷爷当时很生气,他说我家在它铺街头有一间大药铺,这头又有一栋十几间的楼房,还有大院落,房子这么多,一定要把村里的楼给明叔。爸就是不让步,爷爷抡起一条板凳要砸爸,我和大哥二哥吓得直发抖。爸坐着,一动不动,跟爷爷说要砸就砸,反正不能给房子。爷爷最终放下板凳。

20世纪80年代初的全家福
我还记得,明叔要不到房子,很恨我爸,凡是见到我爸就说要杀了我爸。
有一次,堂弟三成病了,爸回明叔家给三成看病,婶抱着三成在屋里。明叔在门外我家原来的灶屋前磨一把刀,一边朝屋里骂我爸,等我爸给他儿子看完病出来就砍我爸。我在门楼紧张地看着明叔手中磨着的那把刀。婶子长得好看又善良,听着明叔这样骂我爸,心里也难过,只是不时埋怨一声明叔,不敢管,明叔的脾气压着她。
我爸给三成打完针,背起药箱出来,快步从明叔身边走过,飞快地穿过门楼往村外走。明叔一手提着篮子,一手拿刀,也快步跟着我爸,不停地说:“你以为我不敢砍你吗?”
但其实,明叔只是说说恶话吓吓而已。
下楼来时,我眼一花,仿佛还看到奶奶坐在木楼下面的灶屋门前。奶奶生前经常坐在这里,门前这里放着明叔的孩子,奶奶一边带娃一边看屋内灶里的火。以前我回来玩,从楼上下来,奶奶总是抬头看着我,微笑着,招呼我坐一会儿,她架在灶上的泥煲里炖有菜,夹一点给我吃。
愿时光倒流,还能回到那个时刻,只是,下楼来看,空空落落。
楼下三间房子的门关着,从窗口看进去,空空的。
那时我家开有一家药铺,爷爷一早就要在药铺帮忙抓药,晚上八点左右才回来陪奶奶住。
村里人都说,人老了半身入土,不怕鬼,可是那时已经将近七十岁的奶奶胆子小得很,怕鬼。看着夕阳光从楼前的瓦顶上一歪,拉一道暮色的阴影,她就赶紧吃晚饭,然后提着手电筒到隔壁大伯嬷家去。大伯和大伯嬷跟爷爷、奶奶年岁差不多,老人在一起有话聊。奶奶等到爷爷回来,在巷子里喊她,她才回来。爷爷给奶奶起了一个外号:阿惊。这个外号一直被爷爷温柔地叫了很多年,直到1993年春节爷爷去世。
1993年,我在南宁读高中,寒假回家那时听说爷爷摔了一跤,病中。我给爷爷奶奶买了袜子、长寿面。
我回来看爷爷,爷爷躺在床上,爸爸给他输液。
在爷爷过世前的那十多天,我白天都回来照顾爷爷,早上起床就回来,一直到晚上才出村回家。晚上轮到叔叔们来照顾。
为了防寒,在床底下放一盆炭,盖着薄薄的火灰,被窝里还放一只火笼让爷爷焐在怀里暖着。我要时不时摸摸火笼,如果火太旺,就要换一换位置,免得灼伤爷爷;如果炭火弱了,就要把火笼提出来,轻轻地摆动甩几下,让火炭表层的炭灰衣脱去。醒来,继续燃,否则,炭火会在炭灰衣的包裹下睡熄了。
有火烤,爷爷的脚还是不够暖,他穿着奶奶做的布筒袜子,不够厚。我把买回来的厚棉袜给爷爷、奶奶,他们都舍不得穿。我便给爷爷先穿上,他说很暖,但只是感受了一下袜子的暖之后便脱下来递给我:“搭到竹竿上放着。爷爷就要死了,不要穿坏了,新袜子,好好留着。”
“就是买给你穿的。”我固执地再给爷爷穿上。
我觉得爷爷不会死,我剥了一只橘子喂他,他全吃光了呢,胃口不错,怎么会死呢?而且我爸爸是医生,给爷爷下最好的药。可是,爷爷咳嗽吐痰的时候,咳很久,有时候痰咳着许久不清爽,也停不下来,咳得眼泪出来,有时候还有一口气要上不来的感觉。我用毛巾接了一口又一口痰,还要拿软的纱布伸进爷爷的嘴里帮他掏出吐不净的痰。那时候是慌乱的,帮爷爷摸胸顺气,又拍背助吐,感觉根本帮不上大忙。
有一天,爷爷躺久了,骨头痛,要坐起来。我扶着他坐起来,让他靠着床杆,扶着他的肩胛,隔着衣裳也能感觉到老骨头的枯瘦,突然间有种预感,爷爷可能会死的。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哭着说:“阿大(爷爷),你不要死呀——”
爷爷眼圈发红,他说:“爷爷如果不死,就享我老妹(对孙女的昵称)的福;爷爷要是死了,就保佑我老妹。”
那年大年初三早上,爷爷去了。
做一场大法事。奶奶不能到祖宗堂来,传统风俗,老伴不能去见过世的老伴,怕伤心过度会被一起带走。奶奶却好几次拄着拐杖悄悄从巷子里走来,每次她刚走到祖宗堂二殿的大门处,就被爸爸和八叔或我妈妈扶回家里去。奶奶每次被送回去了,又再悄悄走来。奶奶那么瘦小,一身黑色的布衣也显得过于宽大,那根拐杖都让我担心会不会太沉。好几次都是我先看到奶奶,她像纸片人一样被风吹来,突然就出现在二殿的那个门边,默默地看着守孝的人群。虽然隔着一个大殿和一个天井,有点远,但她的悲伤那么清楚,在阳光下乱飞着,就像她那头在风中乱飞的白发。
我们去寺庙行香,偌大的祖宗堂静静的,只有爷爷躺在棺材里。奶奶在这个时候终于成功来到爷爷的身边,还没完全盖好棺,她趴在棺材上,仍能看到熟睡般的爷爷。不知道奶奶在祖宗堂陪着爷爷待了多久,我们回来时,就看到她趴在棺材上,拐杖落在地上一边。我爸妈和叔叔他们很紧张,生怕她会哭着哭着就跟着走了。爸爸和八叔把奶奶送回家。

20世纪80年代初,小时候的我
爷爷下葬后,真正走了。
虽然我们家是一个大家族,人多,都陪着奶奶,可是奶奶看起来却是那么的孤单。其实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像爷爷那样陪着她。
我每次回去看她,都发现她蹲在灶边神游。她总是忘记爷爷过世了的事,餐餐给爷爷准备饭,在小桌子上总是摆着一碗饭,两副筷子。她自言自语着,细听,是在跟爷爷说话。
收假了,我回南宁上学。
转眼一个学期将过,周末二哥到南宁大姐家来。我回大姐家吃饭,听他们谈话,几次听到二哥说奶奶去世,我生气地更正,是爷爷去世,不要总是错说成是奶奶。二哥瞪着眼看我,大姐才说,奶奶去世的事没告诉我,我在学校上课,也回不去。春节时爷爷过世之后,紧接着在清明节近时奶奶也去世了。家里人没有告诉我,怕影响我学习。
当晚回学校,骑车从民族大道到桃源路,一路哭。我恨家里人的理由,我请假回去几天能有什么不可以?错过学习或考试仍有大把机会补,就算补不了,那又怎么样?奶奶这一走就永远不能再见了。
假期回家,放下东西就回村里的老屋,在门前站了一个下午。走廊那根竹竿上还挂着一只竹篮,篮子里还有奶奶放在那里的菜,已经风成菜干,干枯的菜叶在风中发出的声音,听听错觉为奶奶的声音:“十七转来哩(回来了)。”

老村门楼旁的旧屋
姑姑告诉我,奶奶将要走时总是看着巷口,以为能盼到我回来……
在2009年回想着1993年的往事,泪流满面。
我推一下门,居然是开的。
站在门口往屋里看,只有一些杂物。我还能还原爷爷、奶奶住在这里的物件摆设,左边有一张木柜,柜上吊着一根竹竿,搭一些衣物。右边尽头放一张大床,床挨着墙,有一眼后来才打的窗……
对于我来说,怀念亲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写下来,留在小说里。
从老屋出来。
巷子里静静的。
在门楼坐了一个多小时。门楼的门板和木墩早已没有了,老墙还在。村里大多数人都在村子周围起了新房,只偶有三两个人从门楼前走过。门楼内左侧还住着一个老人,门半掩着,无声无息。八叔也在村子外面人多的地方起有新房,给堂弟住,他和婶还住在门楼旁边的老屋。
后 记
去年春节,二哥搬进新家,回去祝贺。
我回老家,走进村子就是一栋栋新楼,楼下的空地上停有小车、面包车、摩托车。村里有钱人不少,各家起楼,不再像以前的老村那样有整体规划,新的高楼很多,显得凌乱,公众空地上有垃圾、积水。人们的新楼都做了卫生间,家用废水全都通往村外的河流或山脚下的溪流,甚至是村外的空地。
以前清澈的大河、小溪不见了,小溪成了臭水沟,河流变成窄小的小河,漂浮着垃圾,从猪场冲出来的各种东西,还有从村里各个人家里冲出来的东西……
再无鱼虾踪影!
从楼前楼后绕着走,再从一些推倒了的旧屋地上经过,艰难地回到门楼前。祖宗堂、花厅和门楼还在,客家村场的三大标志性建筑还在。八叔的那排旧屋也拆了,二堂弟年初三在旧屋地上起了新的楼房。

2016年春节,二哥在老家第一栋旧楼屋地上起的新楼
门楼看上去老朽不堪,禁不住担忧还能经受几年风雨,也担忧会不会被更年轻的后辈们抛弃——
这时候的老村场有一种让人心痛的寂寞。
时代的潮流有一股我们看不见的威力,把老村场冲击,曾经紧紧相连的各家单独独立起来,许多村庄的门楼已不复存在,村里每一栋高楼都有自己家的大门或阔气的院门。客家村庄以新的面貌到来,老的客家村庄即将死去。也许过不了多久,年轻的村里人再也不知道我们的村庄曾经有的泥墙瓦屋,曾经有的门楼……
我们必然要面对时代的发展,面对新农村的面貌,但我还是难免去怀念童年时的村庄。
终要承认,我是一个固执的人,在我的灵魂深处,童年时代的那个家乡才是我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