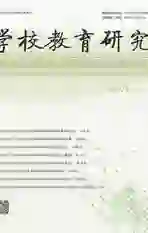《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文本解读中的几个问题之管见
2017-10-21刘朝京
刘朝京
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以下简称“《宣》诗”)是一篇极其出色的古风。但在教学研讨中,对其文本解读,同仁们却有诸多分歧。
其一是诗题分歧。
其二是有同志认为“《宣》诗”结构突兀、紊乱。
然而笔者看来,个别同仁如是云云的原因,一是对李白及其时代背景缺乏深度解读,二是对“《宣》诗”及其写作背景缺乏深度解读。
李白身世向来众说纷纭。笔者相信最新见到的一说:李白乃玄午门之变中被杀的太子李建成之玄孙。建成后人罪徙中亚,五世为庶。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35岁的李白结识了卫尉张卿,得以向玉真公主献诗。同时结识了贺知章。由此,自比管仲、张良、诸葛亮的李白,一步步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引荐,李白应召进宫并供奉翰林。
但李白很快看到了庙堂高端的危机与险恶,感受到了皇叔对自己的戒心。御用文人生活对于胸怀“直挂云帆济沧海”理想的诗人,渐渐成为精神的枷锁和对其政治品格的侮辱。极度而又不能轻易倾吐的内心矛盾与苦闷,使诗人选择了纵酒以自昏秽。与贺知章等人结“酒中人仙”之游,玄宗呼之不朝。尝奉诏醉中起草诏书,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以昏秽的外在表现曲折地宣泄内心的苦痛与愤懑。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两年后被“赐金放还”,被变相撵出了长安。诗人重新踏上了浪迹天涯的游历之旅。
“《宣》诗”作于“安史之乱”前两年的天宝十二载。从庙堂之高端到江湖之远角,诗人对盛世光环掩盖下的腐朽与罪恶,对盛世泡沫掩盖下的危机与蠢动,一方面有着深刻的洞察和大展宏图的才干与担当;同时又有不得不做旁观者的无奈。面对危如累卵的大唐江山,作为头脑清醒的天下名士和流落天涯的当朝皇室宗亲,诗人的担当是最强烈的也是最纯净的;不能做旁观者却又不得不做旁观者的无奈也是最极端的。这种担当的极端和无奈的极端,并存于诗人心中,猛烈地撕扯着诗人的灵魂,分裂着诗人的精神。这种伤到心穿、伤到心碎的痛苦,表现在“《宣》诗”中便是情绪的神经质般的狂躁,便是“倒放的蹦极”般的跌宕。
其三是有意见认为:“《宣》诗”不合“起承转合”的格律规范,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非主流体。这种声音其实包含了两层误解、一层无视。
唐代的诗坛,其实同时流行着“古风”和格律诗。这里的“古”和“今”,是站在“唐代”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说的。对今人而言,他们都是古诗。从《诗经》到南北朝的庾信,都算是古体诗。其后,古体诗日渐式微,逐渐消亡。但唐代之后的诗歌不一定都算近体诗。具体在于格律声韵之分。
唐代流行的古风与唐代以前的古诗又有区别。唐代以前的古诗是一种不讲究格律,也没有字数句数限制的诗体。唐以后,由于近体诗的产生,诗人为了将古体诗与新兴的格律诗相区别,便总结汉魏六朝古诗的写法,在某些方面加以限定,从而形成了唐代古体诗的固定模式。其结果就是把唐以前完全自由的诗体,变成一种处于格律诗与自由诗之间的半自由诗。“《宣》诗”就是这种古风中的名篇。
与古体诗相对的格律诗,则要讲求严格的格律和行文的规范。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对偶等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行文则必须符合“起承转合”的规范。
古风的行文并没有“起承转合”的规范约束。古风行文可以用“起承转合”模式,也可以用其他模式。
其四是有同志认为:“《宣》诗”的主题是消极出世的。
的确“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明白地写出了要泛舟江湖,换一种心情的打算。但仅仅是表示要换一种心情而已。并没有说从此就换一种活法:归隐江湖,放弃抱负,不再关心国家大事。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时光无法留住,生命在不可逆转地逼近终结。官场却依旧黑暗,才比管仲、张良、诸葛亮的诗人依旧怀才未遇、报国无门。纵酒似乎可以暂时忘却深入骨髓的痛苦,但酒醒时分,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又更加残酷地清晰呈现于眼前,更为剧烈的苦痛复又无可抗拒地来袭......这样的折磨,这样的苦痛,固然反映了残酷现实对诗人无情且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展现了诗人对理想坚韧而执着的追求。若是已经放弃了追求,则痛苦自会日渐消减;若是执着地追求而不得,则痛苦自是日甚一日。这是人类心理的客观规律,李白也不会例外。通过写极端的痛苦来表现追求的执着,这是反衬的笔法。
不高兴、不快活之时,一叶扁舟,放浪江湖。这是要遁世逃避,还是只是怡情一时?初读似乎无从考究。但细品之下,一个“弄”字却在笔者面前开启了一扇解读诗人隐秘心境之门。“弄”者,经笔者反复考证,有“把玩、赏玩、戏弄、摆弄”等相关意思,这里解为“摆弄”似乎更合适一些。“弄扁舟”之意应该只是泛舟消遣、赏景怡情。就像纵酒一样,只是消弭痛苦的一种手段。或者说只是换一种方式来消弭痛苦,改善心情。也可以说是换一种方式来换换心情。“弄扁舟”并不是要乘舟到化外之境或隐秘之所去隐居避世,也不是要以舟谋生,更不是要研究造船。并未表达要换一种环境换一种生活的意思。而且,既是“摆弄”,应不长久。心情稍好,心伤稍愈,极端的担当意识又会把诗人拉回到对政局变化的关注研究之中,拉回到实现理想的奋斗之中。哪怕伤得更深,痛得更甚。这是必然的。不如此便不是李白;不如此便不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天下名士;不如此便愧为当朝宗室之后。
诗人其后的生命旅程也对此做了完美的注脚。“安史之乱”后的第二年,也就是诗人写下“《宣》诗”后的第三年(756年),李白应永王之聘入其幕府,极力鼓动永王割据江南。永王兵败后,李白被流放夜郎。759年,59岁的李白获赦后立即顺长江而下,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早发白帝城》。那心境,那心情,不仅源于大赦的喜悦、江景的迷醉,更有对政治生命复活的无限憧憬。
综上所述,认为诗人末两句表达了消极遁世思想的说法明显武断,是缺乏依据的过度解读。“《宣》诗”主旨是表达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昏庸当权者的愤懑之情。基调是积极入世的。这,应该无疑。
以上便是笔者解读“《宣》诗”的点滴愚见。不当之处,恳请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