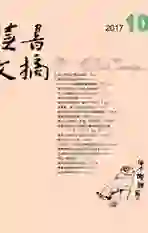梁启超与何蕙珍“情事”新考
2017-10-16陈忠平
一
梁启超在一九〇〇年二十七岁时旅居夏威夷,为当时追求爱国进步的保皇会宣传政治改良,并因此与檀香山年轻女郎何蕙珍相识相恋,但又终于未成眷属。这一脍炙人口的爱情佳话在学术界和大众媒体中都广为人知。在最新一本号称“最客观、最翔实的梁启超传记”之中,何蕙珍仍被描述为梁氏的“红颜知己”。但该书承认:“今天我们要了解她,以及她与梁启超的感情,似乎也只有梁启超写给妻子李端蕙 (蕙仙) 的两封书信以及他的二十四首诗作可以参考。”(解玺璋著:《梁启超传》,上海文化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60页)
实际上,梁启超关于何蕙珍及其爱情的记载既有渲染铺张和浪漫想象之处,有关学术论著或通俗读物对他的记载也有偏信、误解或者曲解。梁启超确实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到达檀香山 (The Hawaiian Star, January 1, 1900),但他直到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四日给夫人李蕙仙的一封信中才提到与何蕙珍的见面 (全信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163—164页)。由于此信是长期以来有关何蕙珍的主要资料来源,现对其中五点主要内容进行补充与考证如下:
第一,根据该信,何蕙珍是檀香山的一位华商之女,年方二十,精通英文,“喜谈国事,有丈夫气,年十六即为学校教师”。现存的中英文献记载何惠 (蕙) 珍的英文姓名为Ho Fui Jin,籍贯广东归善县,即后来的惠阳县 (《西美留学报告》,旧金山,《中西日报》 一九〇八年印,32页)。她的父亲为何广荣 (音译自Ho Kong Wing),在该市国王街一四〇一号开设广荣记 (音译自Kong Wing Kee);母亲谭树英 (音译自Tan Shoe En),蕙珍为其夫妇长女 (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August 11 and 15,1903)。美国政府于一八九八年兼并夏威夷之后,在一九〇〇年第一次实行当地人口普查,显示何广荣夫妇实际生有七子、五女。其长女Fiu Chin Ho显然即是何蕙珍。她在一八八〇年生于中国,年龄二十岁,职业为教师。但她在一九一〇年、一九二〇年及一九三〇年的人口登记中的英文姓名为Fui Jin Ho或 Pearl [F.] Hoe,将出生时间推后至一八八四、一八八六或一八九一年 (United States Census,1900,1920,1930)。但从上述何蕙珍已在一九〇〇年担任教师四年,并能翻译梁启超的讲演等记载来看, 她的出生年份应为一八八〇年。
第二,梁启超在该信中称他于一九〇〇年五月初的一个晚上受邀在何蕙珍父亲的店铺对中西宾客发表演说,由蕙珍担任翻译。在讲演成功结束后,何蕙珍与梁启超握手道别时表白:“我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梁启超当时不知如何答对,但此后“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在给何蕙珍送去照片后, 收到两把扇子作为回礼。
檀香山当地报纸确实曾报道梁启超于一九〇〇年五月七日晚在该市国王街一家华人店铺对中西宾客做长篇演讲,并提及他的翻译为该店主人的女儿Fu Shin,亦即何蕙珍。该报称赞她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少女,以其纯真和机智赢得了来宾喜爱 (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May 8,1900)。这一报道可以部分印证梁启超的上述记载,显示他与何蕙珍在这场成功的演讲之后互相产生了好感与爱慕之情。但是,即使梁启超单方面的记载也证明何蕙珍明智地表白双方已无可能结为连理,甚至无法再次相遇,因此仅仅希望获得梁氏的照片以作纪念。然而,梁启超却因此展开他在夏威夷的柏拉图之恋。
第三,梁启超该信又称在上述演讲半月之后,有一友人前来劝他娶一当地妇女作为英文老师兼翻译。梁氏听后恍然大悟,确信友人是为何蕙珍所托前来提亲。他以家有发妻、坚持一夫一妻主义及献身国家大事为辞谢绝,并主动提出为此女做媒。但友人称该女平日对于男子均觉得不足一顾, 已在数年前誓不嫁人。
就梁氏记载本身进行分析,何蕙珍是否曾托这位友人前来提亲或由后者主动作伐并不清楚。如果何蕙珍在数年之前就已下定决心坚持独身主义,此时突然主动转托梁氏友前来提出愿意委身为妾,似乎值得存疑。所以,此事是否表明何蕙珍对于梁启超的真挚热切、不计名分的爱情,尚待证实。
第四,梁启超在信中记载何蕙珍在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四日第二次为他的演讲担任翻译。他与何蕙珍因此畅谈良久,但他未敢触及友人提亲之事。何蕙珍也“毫无爱恋抑郁之态”,但她表达了追求个人教育、兴办学校、回国服务的愿望,并以基督徒的身份劝告梁启超入教。在两人握手分别时,何蕙珍又对梁启超表示:“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莫忘我,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以一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惟有先生。” 因此, 梁启超归寓之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落……”他的柏拉图之恋由此达到顶峰。
何蕙珍的这番举止也许确如梁启超所述,在托人提亲受挫之后仍然对他一往情深,并在镇静自若的谈话之后最终表白示爱。但何蕙珍自然大方的言行也有可能表明她对于梁氏五日之前与其友人的谈话毫不知情,所以并未表现出任何异常。她身为基督教徒并劝导梁启超加入该教,也似乎难以逾越当时教会坚持的一夫一妻的传统教义,轻易对一有妇之夫以身相许。何蕙珍在两人分手时的表白完全出自梁启超的转述,准确与否已无可考证,但其中的语意是指她等待梁氏召唤其回国办女学之决心不变,抑或向梁氏明示爱恋而又保持在初次见面的尺度之内,尚需更多的资料才能证实。
第五,在当晚激动难眠之际,梁启超挥毫兴笔,给远在澳门的夫人李蕙仙写去一封情思并茂的书信。此信主要内容已如上述,基本从他个人的观察、感受甚至想象出发,详细描述了他与何蕙珍的交往经过及他忍痛斩断情丝的心路历程,也显示了梁启超对于发妻李蕙仙的坦白真诚。梁氏坦率承认确实曾经萌发“因蕙珍谙习英语,將来驰骋于地球”的雄心,但他又理智地认识到娶后者为妾“揆之天理,酌之人情,按之地位,皆万万不可也”。所谓“天理”即是梁氏当时所提倡的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主义;“人情”则指他对于何蕙珍的恋爱、怜爱与敬爱,不忍将她置于小妾的地位;而他作为保皇会领袖的“地位”也使其意识到不能因此男女私情而影响当时席卷海外华人世界的政治改良运动。
实际上,梁启超这段爱情传奇在夏威夷的终结不仅是出于他个人在主观上的理智考虑,也是由于当时以一身承担梁家在澳门生活的李蕙仙在六月十二日迅速复信,威胁要将梁氏此事禀告其父。更为重要并被长期忽视的原因是梁启超所谓的“红颜知己”何蕙珍并未在他继续逗留檀香山期间采取任何追求行动或与他深度接触。梁启超在六月三十日写给李蕙仙的第二封回信虽然再次表示斩断情丝的决心,但也提到“近亦月余不见此人……今将行矣,欲再图一席叙话,不知能否也”(全信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64—165页)。
二
梁启超终于以理智战胜个人情感,以政治改良事业为重,将他对何蕙珍的感情埋藏于心底,显示了伟人的品格;他对于这段感情的自我发展、无奈结束及念念不舍也反映了一个年轻书生的凡人本性。这种个性的矛盾充分表现于梁启超离开夏威夷之后,在一九〇〇年十一月通过 《清议报》 (第六十四册) 发表的 《纪事二十四首》 组诗。这组诗歌热烈颂扬了何蕙珍所持的女权主义,对于感受到她的“独有青睐”表示受宠若惊。但他又表达了与谭嗣同烈士共树一夫一妻楷模的决心及与红颜知己何蕙珍归国兴建女学的憧憬,并惋惜在临行之际未能得到再度与后者畅谈、握别的机会。
曾经师从梁启超的冯自由后来写作 《梁启超之情史》 一文 (《逸经》 一九三六年第八期),声称保皇会领袖康有为将梁诗斥为“荒淫无道”。冯氏并称梁启超因在夏威夷试图向何蕙珍“乞婚”不成,“乃为情诗二十 (四) 绝以解嘲”。何蕙珍之弟何望此后随梁启超到日本学习,但因奉康党之命参与在广州的一次暗杀活动受到清政府通缉,导致个人身败名裂及保皇会的分裂。何蕙珍也因此与康、梁党徒决裂。由于冯自由早年师从梁启超时曾经遭到训斥,导致他与后者反目成仇,从保皇会转向同盟会,所以他的这篇文章也常为后来的学者斥为对于梁氏的人身攻击与党派私見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9页;解玺璋著:《梁启超传》,57—58页)。但冯氏的记载也并非无来由。
现有资料尚无法说明何蕙珍何时看到《清议报》所载情诗及做出了何种反应,但她至少可以从在日本跟随梁启超学习的弟弟何望处了解此事,并有可能因此知道梁氏在一九〇三年就已经接纳李蕙仙的婢女王来喜为妾 (后得名王桂荃,见解玺璋著:《梁启超传》,57页)。从何蕙珍在此前后表达的激进女权主义态度来看,她是否仍然保持了对于梁启超的恋情并愿意接受与王来喜一样的小妾身份是值得怀疑的。
何蕙珍在一九〇二年八月九日曾对檀香山的保皇会发表过一次公开演讲 (当地报纸在报道这一演讲时记载,英语演讲人是一位商人女儿Wai Chin,即为何蕙珍。她的中文翻译是刚从日本学习归来的弟弟,即以上冯自由所记述的何望)。何蕙珍的演讲号召华人妇女打破传统、争取解放,她抨击长期男性专制已将中国女性转变为玩物、家具以及没有灵魂、智慧与权利的贱民,她们因此与外界没有接触,对公共事务缺乏了解,甚至并不了解自己的丈夫。她的演讲特别颂扬了几位女权主义先驱,包括在广州学习医术后取得医生执照,并在义和团之乱时期开业行医的Chong Chock Kwan(Hawaiian Star,December 8,1902;旧金山,《中西日报》,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位女医生可能即是“持不嫁主义”,喜欢以男性自称的张竹君 (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 219页)。
不幸的是,何蕙珍的父亲在一九〇三年四十九岁时突然病故,她作为家中唯一成年的长女,成为遗嘱执行人和十口以上家庭的家长,帮助寡母照顾所有未成年弟妹 (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August 11 and 15,1903)。但是,这一家庭的不幸变故和沉重责任并未阻止何蕙珍继续追求她的女权主义理想。
三
最近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南温莎市所发现的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所遗留的文献中,何蕙珍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两封来信中讲述了她在檀香山所展开的妇女政治运动。当时康同璧正在北美协助康有为的保皇会发起组织保皇女会,号召通过宪政改革实行“男女同权”(见陈忠平:《保皇会在加拿大的创立、发展及跨国活动,1899—1905》,《近代史研究》二〇一五年第二期)。所以,她与何蕙珍取得通信联系并给后者寄去保皇女会的章程。何蕙珍在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回信中报告她并未照搬康同璧所送来的保皇女会章程,而是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个“华女合群”的组织,大概反映了当时盛行的合群进化思想。何蕙珍在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二日的另一回信中指出这个妇女组织的名称是当地保皇会 《新中国报》 主编陈宜侃 (宜庵) 帮助选取,但她在创建该组织时曾受到当地华人社区男女居民的共同非议。她的工作从少数妇女开始,通过演讲来宣传该组织的目标,并将其章程发表于报纸。这一组织很快发展到四十人左右,而且包括一些美国白人妇女。但是其中的会员大多还是文盲,并未意识到中国面临的危机。所以,她计划在筹集到足够资金后,为华人妇女开办一个学校,用知识带给这些妇女真正的快乐,以便最终达到救国目的 (该资料见Jane Leung Larson,“The Kang Tongbi Collection of South Winsor, Connecticut”, https: //drive.google.com/file/d/0By7Ajg4xYgVqUXFwbjlWNk0za0k/view)。
何蕙珍也一直追求她在一九〇〇年对梁启超表达过的个人教育计划,并为此在一九〇七年进入檀香山的瓦胡学院 (Oahu College) 求学,这使她成为孙中山的校友。该校实际是一所学制四年的高中学校,孙中山在一八八三年进入此校学习时刚刚十七岁,而且半年后就因信奉基督教而被长兄孙眉强行送回中国 (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香港中华书局二〇一一年版,227—229页)。何蕙珍进入该校时已经二十七岁,在该校从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学年开始一年级的学习, 但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学年未能通过三年级考试。于是她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学年重读三年级课程,并可能在该年 (她三十一岁时)肄业 (Catalogue of Oahu College,1907—1908,1908—1909,1909—1910,1910—1911)。
值得注意的是,何蕙珍学业受挫之时正是她的弟弟何望在广州参与保皇会 (其正式名称已经改为宪政党) 的暗杀、受到通缉的前后。何望在一九〇〇年随梁启超进入保皇会,在日本的大同学校学习,改名何其武。他后来凭借英语能力而受梁氏的推荐,协助康有为的其他弟子徐勤、陈宜侃在香港和广州办理保皇会的报纸,并因在日本接受过军事训练,被称为保皇会“大将军”。一九〇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晚,何其武受徐勤之命在广州与陈宜侃等人配合,亲自率领近十人的团伙刺杀振华公司发起人刘士骥致死。何在案发后受到清朝官府通缉,经日本逃回美国。由于刘士骥的被杀与其拒绝康有为的保皇会控制振华公司有关,康氏及其门徒梁启超、陈宜侃等也一并受到通缉 (赵立人、刘仁毅编著:《刘士骥之死——康有为集团策划的一桩血案》,中国影视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77—89页,406—407页) 因此,冯自由在上述记载中声称何蕙珍受此打击,与当时日渐蜕化的保皇党人分道扬镳,可能不无根据。
导致何蕙珍学业挫折的另一主要原因可能是她从一九〇三年父亲早逝后就开始承担的家庭重任。一九一〇年檀香山的人口调查报告显示她仍持独身主义,却是一个十二人大家庭的家长(head),与五十二歲的寡母、已经结婚的何望夫妻以及其他五个弟弟及三个妹妹同居一处。从这一人口登记来看,何蕙珍的职业已经不是教师,而是经营父亲所遗店铺的零售杂货商人。其他家庭成员中,大多均无其他职业,主要依赖何蕙珍经营的店铺为生。大概是由于她在发型和装束上仍然保持了当年梁启超所赞许的“丈夫”气概,人口普查官员竟然将她登记为男性。 她以一位年届三十岁的单身女性支撑如此大的一个家庭,其生活的艰辛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何蕙珍在一九一三及一九二四年两度从檀香山来到中国,希望与梁启超重续前缘的记载,充斥于网络。如百度百科“何蕙珍”条目即称她在梁启超一九一三年任民国司法总长时,从檀香山来到北京,欲结秦晋之好。但是,梁启超仅仅在他总长的客厅里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这使得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 编辑梁秋水也责备梁启超薄情,“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何蕙珍是否曾在一九一三年抛开支持全家生计的店铺而远访北京,尚须使用可靠的原始资料进行考证。即使此行确实,她是否仅是回国观光时顺道拜访故人?或曾向梁启超表示愿意委身为妾?
作者使用现有的一九〇〇至一九五二年间檀香山乘船旅客名单资料库进行搜索,仅仅发现何蕙珍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以英文姓名Pearl F. J. Hoe在檀香山海关登记,从海外旅行回到该市的记载 (Hawaii,Honolulu Index to Passengers,1900—1952)。据一九二〇年檀香山人口普查记载,何蕙珍当时仍然是八口之家的家长。她也仍然独身未嫁,但已成为一名邮局职员,与寡母及其他未婚家庭成员住在一起。在一九三〇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中,她只是一个四人之家的家长,仍然未婚,并未登记任何职业,仅与寡母及一单身的弟弟和离婚的妹妹同居。由此可见,何蕙珍已经逐渐帮助母亲将十人以上的弟妹抚养成人,在完成这一家庭的责任后,她回归祖国,希望重续当年与梁启超的爱情是有可能的。但是,根据上述檀香山乘船旅客的记录,何蕙珍实际到达中国的时间应该是在李蕙仙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逝世之前 (李氏逝世时间见解玺璋著:《梁启超传》,56页)。所以,何蕙珍的此次中国之行也有可能只是与李蕙仙逝世时间巧合。她在这一丧事之前或之后就迅速离开中国,并于十月二十一日回到檀香山,这也说明她在此丧变的短暂时间内与梁启超谈婚论嫁并为后者拒绝的可能性不大。
总之,本文的上述考证,只是对长期以来关于梁启超与何蕙珍“情事”的说法提出异议,使用海外有关资料试图揭开何蕙珍作为梁启超“红颜知己”的神秘面纱,并呈现出一位海外华人女权主义先驱者的政治追求与个人奋斗的成败及其为家庭作出的奉献与牺牲。她是否一直坚持激进的独身主义决心以至于拒绝婚嫁,或是在这一女权主义的坚强外貌之下一直为梁启超保留了温柔纯真的感情与永不泯灭的爱情,这也许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
(选自《读书》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