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与“新国画”体系的建构
2017-10-13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徐悲鸿与“新国画”体系的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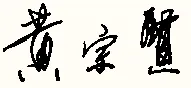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

20世纪是中国画坛涌动变革与重构激情的一个世纪。在中国画的变革过程中,西方美术的观念与形态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参照系。“中西融汇”是自“五四”以来喊得最响的一个口号,也是许多致力于中国画变革的人士依循的一条重要途径。20世纪前期,许多画家和画派在中西融汇的试验中已作了诸多努力,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中国画界的“新画派”(折中派)已在画坛上占有相当的位置。至20世纪30年代初,已有人对中国画的“变异”深感不安,感叹到:“即习于国画者,亦因趋时好而参用洋法,致现代的中国画,成为非驴非马。若以严格的眼光来评衡,南北百数著名之画士,可称纯粹的国画家者,简直不到三分之一,每与同仁言而痛之。”(郑午昌《现代中国画家应负之责任》,见《国画月刊》1933年第2期)可见,经二十余年新美术运动的洗礼,纯粹的“国粹派”在中国画界已不占主流。抗战的爆发,因环境和局势之变,许多中国画家不仅在艺术的功能观上发生了转换,而且也将中国画技法风格的变革与探索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徐悲鸿以写实精神改造中国画的探索,就是在这个时期取得了重大进展,构建了“新中国画”的基本模式,并形成了徐氏学派。
众所周知,年青时代的徐悲鸿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确立了求真求实的美术思想,他不仅在油画上始终如一地坚持写实主义,而且在中国画上倡导改良。他在25岁时写的《中国画改良论》中就明确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在徐氏看来,“西方画之可采入者”当然是写实技法。所以,他鄙夷因袭摹古和八股试帖式的笔墨程式,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在中国画创作实践上力求变革。他在人物的塑造上吸收西方素描法,增强明暗起伏感,准确表现人物的面部五官、四肢的结构比例关系,体现了他所坚持的造型第一、笔墨第二的原则。其人物画与传统画谱和古典名作中的人物造型大相径庭,更疏离了文人艺术“墨戏”的旨趣。因此,20世纪40年代就有人认为徐悲鸿对传统笔墨精髓缺乏深入体悟与研究,批评他的“综合中西的新中国画,则并未能真将中西两种绘画之优点综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同时具备两种之优点的作风,而只是教科书里的‘毛笔画’而己”。(白风《当代画家述评》,见《战时后方画刊》第2期)从传统文人画立场来审视徐氏中国画之笔墨,自然能见洞见其“不入流”的一面。但如若因他对文人画笔墨程式的疏远而认定其对传统缺乏了解是有失公允的。徐悲鸿青年时代在临摹古画上曾花过不少功夫,或许因个性所致,更由于“五四”美术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对文人墨趣不感兴趣,却对唐宋艺术却十分推崇。在他看来“吾国唐迄宋,为自然主义在艺术上最昌盛时代”。(徐悲鸿《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见《益世报》“艺术周刊”第45期,1947年11月23日)徐氏推崇自然主义,必然会将“师法造化”视为中国绘画最有价值的传统。在他的心目中,“师法造化”的传统和西方写实主义精神是相通的,将西画写实观念与手法糅合于中国画中,是顺理成章之事。所以他在为“吾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而感到兴奋的同时,也乐观地认为“吾国传统之自然主义有继长增高的希望”。(徐悲鸿《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用写实的手法改造中国画既是徐悲鸿的艺术观念使然,也是战争时期对中国画的吁求。对此,徐悲鸿也敏锐地意识到了,他说抗战中写实主义绘画作风“益为吾人之普遍要求”,他个人的艺术好尚与现实需求完全交融于一体。因而,他不仅自己在创作中加快了中西融汇的步子,创作了一批具有很强写实性的新中国画,而且还大张旗鼓地把西画的写生法融入中国画教学之中,建构中西融合的中国画教学体系。
徐悲鸿曾说:“以中国纸墨用西洋画法写生,自中大艺术系迁蜀后始创之。”(徐悲鸿1946年写为李斛画展)徐悲鸿的这一举措要比他本人的创作更具意义,影响更大。他以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为阵地,通过教学方式,结成了一个强大的写实主义中国画流派。中大艺术系迁至重庆以后,教学体制有所改变,不再按西画、中国画分科教学,而是要求学生中国画、素描、油画、图案、金石兼修。这种教学体制虽说是由中大艺术系的师范性质决定的,但是这为徐氏进行中西融汇的试验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在所有开设的课程中,素描一如既往地被视为最重要的基础课。徐悲鸿要求学生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也要坚持锻炼素描的基本功,他曾对学生们说:“要立志画一千张素描,一千张是言其多,意在必须在量中求质,其实是越多越好,所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最好是经常画,天天画,砍柴还不惜磨刀工,何况是搞艺术。”(艾中信《徐悲鸿研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版)他对素描课的重视是基于“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一认识之上的。在徐悲鸿看来,借鉴西方造型观念、素描方法不失为改造中国画特别是中国人物画最重要的途径,他极力鼓励学生们将写实的素描语言和色彩等西方画法与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即毛笔、宣纸和水墨)结合起来进行探索,并重点把李斛、宗其香两位学生作为进行中西融合试验的重点对象来培养。李斛曾当过小学教师,他的素描才能深得徐悲鸿赞赏,在老师的鼓励下,他有意识地将素描的造型方法融入水墨画中,并尝试用水墨临摹油画,逐渐形成了中西融合的写实性中国画人物新样式。李斛于1945年至1946年初创作的《嘉陵江纤夫》,可谓这种新样式的经典之作。作者将西画的造型方法在中国的宣纸上发挥得淋漓尽致。1946年春,李斛个人画展在重庆举行,徐悲鸿参观画展,颇感欣慰,题词赞叹:“以中国纸墨用西洋画法写生,自中大艺术系迁蜀后始创之,李斛弟为其最成功者。”同年徐悲鸿又为其题词:“中国画向守抽象形式,虽亦作具体描写,究亦不脱图案意味。李斛弟独以水彩画情调写之,为新中国画别开生面。”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也是在徐悲鸿的影响下,蒋兆和就开始在人物画上进行中西融合的试验,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只不过李斛的人物画是徐氏在抗战时期有意识全面推行中西融合式教学试验的产物,所以受到了徐悲鸿格外的推崇。宗其香也在徐悲鸿的影响和鼓励下尝试用水墨和西画技法结合的方式描绘川黔山水和重庆夜景,既不失水墨的韵味,又表现出光影的效果,给人别具一格之感。可以说,在徐悲鸿的指导下,抗战时期中大艺术系的中国画教学全面贯彻着西画的写实精神。担当花鸟画教学的张书旂也巧妙地吸收了油画、水彩和水粉的技巧,改变了传统水墨画的面貌。其花鸟画最大的特点就是所画花木禽鸟造型严谨而生动,敢于用色,甚至用粉色,墨色交融,相得益彰,画面活泼清新,被人称为写实主义花鸟画。张书旂的花鸟画深受徐悲鸿赞赏,并成为中大艺术系最为流行的花鸟画式样,杨建侯、苏葆桢等一批弟子承继其画风并予以发扬光大。担任山水画教学的黄君壁注重对传统技法的研究,但不一味摹古,而以师法造化为其创作的主要方式,并善用墨、色渲染,青绿法和水墨写意法兼而用之,创造了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得到了徐悲鸿的认同,并对学生的影响很大。

徐悲鸿 芭蕉麻雀 115cm×54.2cm纸本设色 中国美术馆藏 1942年
除了在中大艺术系施行中西融合的国画教学方式以外,徐悲鸿对写实主义中国画家都给予热情的鼓励。早年在南国艺术学院就接受过徐悲鸿指导的刘艺斯,在抗战期间一直坚持用写实的手法描绘普通劳动者的肖像。徐悲鸿鼓励他用水墨作写实人物的探索。1946年4月初,“刘艺斯画展”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展出了《后方流汗》《挖红苕》等一大批反映劳动者生活的水墨画,田汉在《新华日报》上撰文高度赞扬刘艺斯用中西融合的新中国画表现劳苦大众的艺术选择,并称刘艺斯在水墨画中融入光色的画法是受徐悲鸿的影响的。(田汉《向农民的道路发掘》,见《新华日报》,1946年4月9日)徐悲鸿也在重庆《新民报》发表《艰苦卓绝的刘艺斯》(见《新民报》1946年4月6日)一文,对刘艺斯的艺术探索表示由衷的敬意。
正是在写实主义美术思潮的激荡下,经徐悲鸿的推波助澜,以西画写实技法与传统笔墨相结合的新中国画式样,在抗战时期的中大艺术系和中国画坛确立起来,并成为中西融合的主流,其影响一直持续到战后乃至今天。
当年,画界对徐悲鸿的“新中国画”颇有微词,今日,对源自西洋的写实技法融入中国画的表现方式反思、抨击之声更盛。如若将写实视为国画变革的唯一途径,当然是浅薄之见,甚至是数典忘祖般的邪说。但是,“法无定法”,尝试不同的变法何尚不可。况且,百年来,中国画立足于内部变革或中西融合者都不乏成功之案例。如若缺失了徐氏学派,或许今日也会觉得遗憾多多。毕竟谁能否定写实因素的参与给现代中国人物画发展带来的裨益呢?
责任编辑:刘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