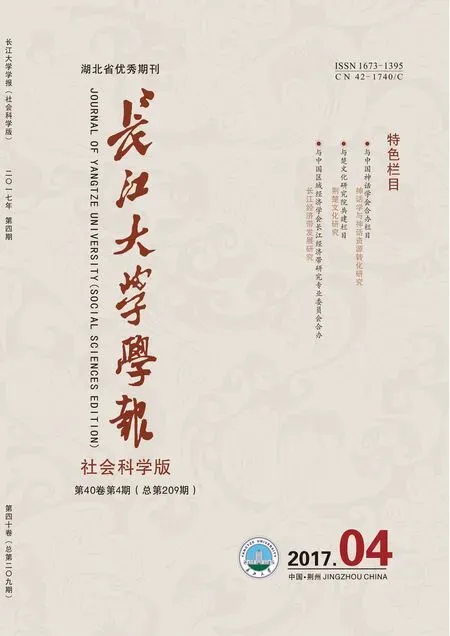少数民族创世神话史诗的非遗功能——以瑶族布努支系《密洛陀》为例
2017-10-09王宪昭
王宪昭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少数民族创世神话史诗的非遗功能——以瑶族布努支系《密洛陀》为例
王宪昭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少数民族创世神话史诗是人类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对瑶族布努支系《密洛陀》功能性母题的分解与梳理,可以发现创世神话史诗具有古老性、完整性、持续性和实践性,并由此发挥着民族历史的记忆功能、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承功能以及日常教化与行为规范等功能。创世神话史诗非遗功能的发挥,则需要积极推进与科学引导。
创世神话史诗;非物质文化遗产;密洛陀;瑶族布努支系
相对于传世稀少的汉族史诗传统而言,少数民族史诗具有数量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特点。其中大量的创世神话史诗则是许多少数民族发展过程中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文化瑰宝,诸如苗族的《苗族古歌》、壮族的《布洛陀》、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咪麻》、拉祜族的《牡帕密帕》、景颇族的《目瑙斋瓦》、彝族的《梅葛》《查姆》《阿细的先基》、德昂族的《达古达楞格莱标》、佤族的《司岗里》、瑶族的《密洛陀》等,均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鉴于这类史诗的独特性,本文以瑶族布努支系广泛流传的《密洛陀》为例,对少数民族创世神话史诗的若干非物质文化遗产功能作一探讨。
一、《密洛陀》功能性母题的分解与表征
本文所谓的“功能性母题”,主要指《密洛陀》作为特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内容解析而生成的具有文化功能意味的母题。瑶族是一个由众多支系组成的民族,一般将其分为勉支系、布努支系、拉珈支系、平地支系四大支系,这四个支系又分为若干个小支。瑶族历史上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在长期口传中,造成布努支系《密洛陀》文本存在一些异文,如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搜集,莎红整理的《密洛陀》(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桑布郎等传,蒙凤标、罗仁祥等唱,蓝怀昌、蓝书京、蒙通顺搜集、翻译、整理的《密洛陀》(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潘泉脉、蒙冠雄、蓝克宽搜集、翻译、整理的《密洛陀》(广西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蓝永红、蓝正录搜集、译注的《密洛陀古歌》(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张声震主编的《密洛陀古歌》(广西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不同版本在流传地、文本形式和叙事细节上存在某些差异,如潘泉脉、蒙冠雄、蓝克宽版本为14章,蓝怀昌、蓝书京、蒙通顺为34章;在具体表述方面,莎红版本中,密洛陀感风怀孕生下9个儿子,而蓝怀昌、蓝书京、蒙通顺版本中则是密洛陀感风孕生12对男女。这些外在差异并不影响研究者得出具有相似性的结论,如虽然不同版本叙述密洛陀生的孩子数量不同,但反映的都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期的母子关系。本文主要以蓝怀昌、蓝书京、蒙通顺搜集、翻译、整理的《密洛陀》为例,对《密洛陀》的非遗功能做一些分析。
该版本《密洛陀》采集于1983年,当时演唱者蒙凤标83岁,罗仁祥73岁,整理者标明这部史诗主要流传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巴马瑶族自治县、南丹县以及百色市的田东县、平果县等地。2011年6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只对非遗的性质、特点做了笼统的描述,对非遗类型的价值与功能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因此,对这类非遗作品的功能进行定位,就要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从国家非遗名录分类看,《密洛陀》等少数民族创世神话史诗均被列入“民间文学”范畴,从其内容的跨学科性、形式的多样性、传承的民俗性等方面看,它已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民间文学概念,是民族民间的综合性“文化”现象,其内容几乎涵盖了世界的起源、神的起源、万物的起源、人的起源、族的起源、自然现象起源、动植物起源、文化起源以及婚姻、战争、灾难、巫术等所有可以罗列的母题类型。在此,对照《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1](P3~19)设计的10大类型,对该史诗的母题作些示例性的统计与分析,见表1。

表1 《密洛陀》母题统计
从上表可以看出,《密洛陀》包含了传统神话叙事所涉及的所有类型。10大类型间又存在文化叙事结构的逻辑关系,形成了关于特定民族文化传统相对完整的记录。如W0“神与神性人物母题”是所有神话文本叙事中所关注的基本主体,《密洛陀》首先交代的女始祖神密洛陀的来历和她生育的12对男女神,构成了史诗叙事的基本框架。W1“世界与自然物母题”属于创世的基本对象,天地日月、山川河流等的产生,构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W2“人与人类母题”涵盖了“感生人”、“造人”、“孕生人”等多种人类起源方式。W3“动物与植物母题”则是人们关注自身之后,开始注意到动植物与自身的联系与区别。W4“自然现象与自然秩序母题”和W5“社会组织与社会秩序母题”,则是随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和社会形态的认识和把握,关注到自然界与社会生活中某些有规律性的东西,诸如史诗中的天地秩序、氏族起源、族体迁徙的思考等。W6“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母题”描绘了人类早期的“农耕制陶”、“弓箭发明”等物质文化以及“生活禁忌”、“丧葬习俗”等文化经验。W7“婚姻与性爱母题”记录了人类婚姻、爱情方面的生存体验,如史诗中的兄妹婚、人猴婚等婚姻形式,都是对婚姻、家庭与社会关系的有意识定位。W8“灾难与争战母题”则通过这些母题展现了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重大事件,无论是史诗中的疾病造成的生存恐慌,还是血缘之争造成的危机与不安等,都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W9“其他母题类型”主要是难以归为上述类型的其他母题等,如“巫术魔法”、“射日月”,等等。这些相互关联并具有一定逻辑关系的神话母题类型,可以从宏观、微观以及不同的时空视角审视人类漫长的历史,构建一个反映人类生存与发展历史的信息平台。
综上所述,《密洛陀》的非遗功能表现出四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是古老性。从内容上判断,该史诗产生于以女权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并兼及父权制的初步形成,传承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布努瑶原始神话时代。其中大量的神话原型具有民族古老记忆和原始经验总结的性质,反映出布努瑶早期自然崇拜、万物有灵信仰以及神人合一观念。二是完整性。从史诗的叙事关联而言,以密洛陀的诞生与业绩为线,集中呈现了天地日月的形成、人类与自然物的产生、大地山河的治理、稻作文化的发明、族体迁徙、安姓分宗、密洛陀续寿及病故、族内外的矛盾冲突等与布努瑶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事件,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三是持续性。在广西相对分散的布努瑶聚居区,大都流传着《密洛陀》,这部史诗也成为该瑶族支系独特的文化载体和根脉,其具体传承渠道除传统意义上的师徒传承外,还有聚会盘唱时的诗体传承以及还愿祭祀活动时师公的宗教性传承等。不仅有丰富的神话与传说叙事,在讲述语境方面,也有唱、诵、舞以及受众参与互动等形式。这些多元化的传承渠道及其神圣性保证了史诗传承的持续性。四是实践性。任何一项非物质文化成为“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具有相应的实践生态。从布努瑶民间民俗活动的田野调查资料来看,该史诗的许多母题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保留了相对稳定的生态,如节日祭祖、铜鼓崇拜、婚丧禁忌等,都可以找到与之对应的史诗母题阐释。
二、创世神话史诗的基本非遗功能
人类漫长的口头时代积淀出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创世神话史诗,这些史诗中的许多母题不仅是后世文化创造的丰富原型和用之不竭的武库,而且是具有明显文化记忆和记忆再现功能的活态宝藏。
首先,创世神话史诗对民族历史的记忆功能。许多民族的历史,特别是没有文字民族的历史,往往以口头史诗为载体,有研究者称其为“口碑史”。这些民族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一般由具有首领、巫师、艺人身份的传承人记录与传承。“历史不是客观经验的赐予,历史是神话。神话亦并非杜撰,神话是现实,只不过是在另一序列上,是比所谓客观经验的赐予更现实的现实。”[2](P16)《密洛陀》所有的章节都与布努支系的产生与发展密切相关,把该支系自神谱向族谱的演变描述得井井有条,如第15章“寻英雄归来”、第26章“布努人上山”以及第29章“迁徙分姓”展现了布努支系发展与迁徙的轨迹,在祖先的追溯中,与其他民族一样,将族源与神的谱系自觉联系起来。“祖先是人,也是神”的理念,不仅具有人类早期神话思维的基础,而且至今仍是人们表达祖先崇拜的集体潜意识。以此为前提,叙述民族产生与发展的神圣性与合理性,成为编撰民族史的一种基本套路。就此而言,这种“口碑史”的历史记录与传承功能也是其他文化遗产所难以替代的。神话史诗反映的历史往往隐含在看似荒诞的表象之下,史诗中密洛陀生的12个女孩用花蜡(蜂蜜)造人时,大姐包生育,二姐包采花,三姐捏人仔,四姐接孩来,五姐包养奶,六姐打扮孩。这种现象表明母系氏族社会中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工与协作。同样,史诗中叙述的大姐孕育12对男女,五姐闻声赶到,袒开她肥胀的乳房给孩子吮吸乳汁,则表明母系氏族时期婴儿由数个母亲喂养的原始共产主义生存方式。当历史跨入父系制时期,社会分工则进一步细化,如史诗中描述的密洛陀生的12个儿子,大哥管山,二哥管河,三哥筑路,四哥造林,五哥造雨管雨,六哥奔波报信,七哥管理兽禽,八哥造地种禾,九哥为万物安名,十哥、十一哥射日月已身残,十二哥除妖。这里几乎涉及到自然界与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正如马克思所言,神话“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3](P761)。当然,某些特定的背景下也不排除自觉文化创造的可能性。《密洛陀》中描述的婚姻现象同样表现出创世神话史诗的历史记忆功能。史诗中大量婚姻母题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婚姻形态,并与历史上的实际婚姻或婚配形式表现出高度契合。如果以婚姻史的自然进程为维度,可以归纳出如下多种婚姻形态:其一,无婚姻时代。密洛陀感风怀孕,孕生12对子女,属于母系社会时期尚未出现婚姻的蒙昧形态,人们意识不到男女结合对人类繁衍的作用,或者从本质上否认男性的存在,甚至在史诗描述中出现了婴儿出生时“是女就留着养,是男我们杀掉”之类的母系社会“女儿国”生存法则,反映出母系社会通过遮蔽男人存在来巩固女权统治的社会现实。其二,人兽婚。史诗中叙述一对不敢返回家园的父子在深山安家,住在岩洞中。儿子想繁衍后代,只好讨个丑婆(母猴)做妻子,并生育了7个儿子。从神话思维角度判断,此处与人结婚的母猴应该是以猴为图腾的氏族。其三,血缘婚。《密洛陀》中表现的血缘婚又分为单一形态的血缘婚和血缘群婚两种形式。如密洛陀生育的12对子女长成大人后,密洛陀就让姐姐和弟弟婚配繁衍人类,反映的就是血缘群婚。其四,族外婚。如密洛陀的后代分了姓、分了家后,芒多怀(人名)走到板升,在龙桃龙扬安家,那时男少女多,他就娶了2个老婆,与韦姓搭了亲戚,和罗姓成了亲家。同样,另一支的必经和必曼(2个人名)与族外结亲,娶了外族女。此外,《密洛陀》还涉及一夫多妻制和其他特定的婚姻规则,如阿赊(人名)迁住隆福一带,在那里讨了2个老婆。这种一男数女的婚姻表明当时社会已进入父系社会。关于布努支系兄弟共妻的婚姻规则也有记载,如密洛陀的后代格凤因战乱率7个儿子逃走时,7个儿子抛弃了丑陋的母亲。母亲放言:“你们要到山林生活,在那里繁衍后代。你们过了7代,能互相娶兄弟的寡妇。”诸多关于婚姻的描述,使我们洞察到一个艰辛的文明发展历程,也反映出母系氏族社会向父权制过渡的清晰历史脉络。
其次,创世神话史诗对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承功能。民间不仅是人们衣食住行的重要来源,也是滋生文化观念的温床和传递人生经验的大本营,民间生产生活的丰富性和世代相传的经验则成为人类文化创造的土壤。特别是相对于其他文化产品而言,创世史诗以其巨大的时间跨度和重要的民间文化地位,往往承担着一个特定族体百科全书的功能。由于其自身作为民族文化的普及性和神圣性,许多优秀的生产生活经验得以保护和传承下来,并且使后人从它带有隐喻性的叙事中感知到劳动的快乐与价值。如史诗中密洛陀生的女孩取花蜡捏人仔时,“一捏人的肝脏,二捏人的全身,三捏人的手脚,四捏人的头颅,五捏人的眼睛,六捏人的嘴巴,七捏人的耳朵,八捏人的鼻子,人头捏来两半分,两半捏好又合拢。两半眼耳各捏一只,鼻子嘴巴各捏半边。”这实际上是把手工制陶的经验借用到造人过程中,会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制作陶俑的工序。密洛陀在元些(地名)闹肚痛,在雅些(地名)患痢疾时,靠吃甜酒治好病痛。密洛陀还告诉后人,“卷土虫也好,它能制成药。有人耳朵鸣,用它能治好。”男孩患气喘病时,密洛陀喂他蜂蜜,结果“气喘渐渐消失,病魅慢慢跑光”。当密洛陀的儿女疾病缠身时,她派人“挖来千样草根,采来万种树叶,煮了12锅药水,给男孩灌药浆,给女孩洗药水,边灌边发咒,边洗边唱歌”,描述了通过中药配合巫术治病的情形。史诗中几乎涉及生产生活中的所有重大发明,如用松树制成弓,用柏树做成箭,把弓箭泡进蛇的毒汁里造毒箭。密洛陀受到“陈饭忽然变味,剩餐散发芳芬”的启发,蒸了12锅糯饭,并把树叶捶烂拌入熟饭,装进12个大缸盖严,存放120天后,酿造出酒;还有熔石炼铁做斧头,教人打柴、割草、翻土、挖地、养耕牛,等等。布努支系也正是依靠《密洛陀》提供的生存经验大纲,不断将更为细致的生产生活常识充实其中,使之从本质上具备了生产生活教科书的功能。
最后,创世神话史诗的日常教化与行为规范功能。许多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史诗之所以久传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本身在传承实践中具有其他文化产品难以代替的教化与规范功能。这个功能与一个民族或民族支系社会组织的自我管理的需要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史诗具有规范社会成员日常行为的律法性质。这种性质一般又与史诗的特定传播语境与公众化的群体认知不无关系。人的许多行为规范被巧妙地融入史诗叙事中,如在自然规则方面,史诗利用神话叙事解释了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关于日月运行的解释是,射日月后,密洛陀规定,月亮和太阳不得再结伴,每隔3年它们才碰一回面,每月月尾它们才有一次相望。在生产规则方面,密洛陀的儿子勒则勒郎规定,“种高粱别长出烟叶,种烟叶别长出瓜类。谷物瓜类要分开,种什么要分节气。”关于社会规则,密洛陀规定,“人类要分人种,人种要分民族。一族要有百家,百家要分百姓。”在具体生产过程中也制定了严格的秩序与规矩,如“狩猎各取所需。山民捉山鼠,人人安压石,各装得各取,不动别人的。”关于商品交换的诚信也有具体规则和范本,如密洛陀让四儿子雅友雅耶到远方的姨妈碟线原规(创造草木的女神)家买草木种,交了金银拿到种子后,对姨妈说:“密(指密洛陀)的金子你先保管好,密的银子你先别忙用。要是树籽播下不长,要是竹秧栽后不生,她的银子不能动。”碟线原规回答:“不生我退我姐的金,不长我还你妈的银。”亲属间的交易也遵循了丑话在前、诚信为先的规则。史诗还对日常纠纷提出具有判例法功能的描述,如有兄弟6人,叔父被仇杀,叔父家只剩一个孤儿阿帛。在为叔父报仇时,老六阵亡,五兄弟于是让阿帛抵命。显然,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依据和心理基础。无论是自然秩序的解释,还是社会规则的描述,其本质均统一于史诗的神圣教化功能,以高度的一致性维系着史诗在规范人们的行为时不可撼动的重要作用。
此外,史诗在创作方面也为后世提供了某些具有程式功能的范例。如史诗中对“12”这一数字的多次使用,如密洛陀生12个女孩、12个男孩,造日月有12对,造天梁地柱各有12根,天门12层,造物有12种、12千、12万,密洛陀丧葬时来了12个亲人,以后会繁衍成12个族支,等等。这类现象与其他民族的数字观念具有明显差异,一方面,在布努支系《密洛陀》叙事中有利于安排叙事内容和组织史诗结构;另一方面,也可以推测布努支系在数字观念上可能受到汉文化“天干”、“地支”或农耕历法以12个月计时的影响。
三、关于创世神话史诗非遗功能的发挥
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不是简单化地被保护,而是为了更好地激发对人类文化的再思考与文化复兴。事实上,非遗本身所具有的许多功能并不会通过自身发挥出来,而是需要有目的地去发掘与推进,并在积极推进非遗保护的同时,做好科学研究与学术引导。
首先,从“大文化传统”的高度对待创世神话史诗。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提出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他认为,“大传统”是代表着国家与权力,由城镇的知识阶级所掌控的书写;而“小传统”则是代表着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传等方式传承的大众文化传统。在文化批评中,不少研究者还将这种二元对立的分类做出变通性阐释,如与“大传统”对应的是“精英文化”,与“小传统”对应的是“通俗文化”等。对此,有研究者明确提出相反意见,“针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和多层叠加、融合变化的复杂情况,倘若既剔除孔子上智下愚二分法的价值判断色彩,也不拘泥于西方人类学家的雅俗二分结构观,可以把由汉字编码的文化传统叫做小传统,将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4]显然,后者的观点更具有学理方面的客观实践性。关于传统的“大”与“小”,是试图用量化的具象的概念去界定无形的抽象的事物,我们姑且借用这个移觉方式形成的概念,那么,首先要确定这个问题的本质。无论是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作为口头传统的文化都在文化实践中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就人类进程包括目前文化创作者和受众的人数比例而言,自然口头传统被称之为“民间文化”、“通俗文学”,无论是就人口覆盖面,还是日常生活的应用程度而言,都无愧“大传统”之称;相反,那些成为文献的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后生性、稳定性(保守性),其生命力往往需要口头传播,方能奏效。这种情况与人的生存层次极其相似,如现在有些文化人认为自己已经脱胎换骨,成了代表主流的知识精英,而事实上,世界性的文明化或工业化进程的相对晚近,造成绝大多数人接受文化的根源只能是民间,而精英们的衣食住行本身也是民间生态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就人的生存环境而论,城镇也属于民间范畴,而绝大多数人的文化交往手段并不靠书写,而是口头语言。因此,口头的“大传统”与书写的“小传统”之间,是孕育、催生与被孕育、被催生的关系,呈现出原生与派生的主客次序。依靠书写工具,尽管出现了口头叙事的文本形式,也往往会因为受众本身的局限性,在实际解读中出现变异。人类的绝大多数历史、文化观念、传统习俗均孕育、产生并流传于无文字时代,特别是对于无文字的民族而言,直至当今,绝大多数民众对历史、生产生活经验和重大事件的认知,仍来源于口耳,许多口耳相传的史诗母题,已积淀为后世赖以生存的群体无意识。由此可见,要真正理解各民族世代口耳相传的创世神话史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功能,就应该将其放在文化“大传统”的位置。
其次,积极引导和营造史诗传承的良好文化生态。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辩证的分析。在谈及对待文化的态度上,鲁迅提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对此,他还用了一个比喻,一个穷青年因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正确的方法只能是先“占有”后“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可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5]对待像创世神话史诗这类古老的文化遗产,也是同理。我们应该有分析、有选择地接受,既不能因为其中的许多观念显得陈旧过时就敬而远之,也不能不加思考囫囵吞枣般地全盘拿来。对其精华兼容并蓄,将其中与当代先进文化发展需求相左的因素作为人类文化的学术研究材料。另一方面,对非遗要做好生态培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和信息技术的全覆盖,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口头传统类非遗挣扎于传承人人亡歌息的边缘,其他很多遗产同样难以摆脱“只遗不产”的困局。要真正发挥创世神话史诗的社会功能,更应关注的是其内在的本质精神,而不是看似热闹的外在形式。以《密洛陀》叙事中突出体现的始祖信仰为例。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一个村落、家族或家庭,祖先崇拜,就主流而言,会起到聚人心、促人气的作用,所以,自古至今普遍存在的带有国家性质的公祭、国祭和私祭、家祭,都是这种传统文化功能的典型体现。对于一个和谐的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而言,不同层次的祖先崇拜又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同样,作为社会有机构成的任何一个族体,要提升自身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往往会通过追忆神圣的祖先来实现。既然任何一个民族的创世神话史诗都无一例外地将文化始祖的塑造放在核心地位,那么势必由此会上升为一种群体信仰,并会围绕始祖的事迹形成相应的节日和习俗。如布努瑶农历五月二十九日是“达努节”(又称“祖娘节”、“二九节”、“祝著节”、“瑶年”等)。关于节日时间的来历,蓝怀昌等搜集、翻译、整理的《密洛陀》中说,五月二十九日,各路神仙、子女庆祝密洛陀寿辰。而民间还有其他说法,农历五月二十四日清早,布努瑶女始祖神密洛陀率领蚩尤、神公(神农)众神出征时,家家户户在门外道旁设台烧香献祭,时至五月二十九日早上,即用一大团小米粑和七捆野麻祭密洛陀,共同庆祝瑶族五谷丰登和征战者凯旋归来。[6]虽然这一节日可能源于农耕自身的需求,但以上解释却无一例外地借助于始祖崇拜这一观念,这实质上反映了某些节日的自然现象人文化特征,是试图通过节日而强化特定的文化观念。那么,在有关密洛陀的文化节日的开发与利用中,是片面追求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还是让人们在切身的文化参与中重新对传统文化有所思考?两种选择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文化效果。祭祖类文化节日的引导与营造,其真正目的在于表达民族自豪感,使参与者从中获得自身的归属性定位思考,萌发或巩固人生的责任感,并对稳定社会政治与管理产生积极作用。
最后,通过古老史诗培育良好的民族观、价值观与人生仪礼。从主题表象上看,瑶族布努支系《密洛陀》似乎强调的是与其他民族、支系的“不同”,如果稍加分析,则不难发现史诗中所倡导的布努支系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和而不同”,或者说是自觉的“存异求同”。如关于女始祖神密洛陀的产生,史诗中的表述是“透明的水滴造化铁石龙”→“铁石龙变成了大龙”→“大龙变成了神仙师傅”→“神仙师傅吹气变成大风”→“大风造化了密洛陀”。从密洛陀产生的链条看,把“密洛陀”作为“龙的传人”,也属于合乎逻辑的推理。而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古老图腾,正是以龙为代表。如果有人认为通过此例确定“瑶族”与“中华民族”的关联性有些牵强,那么,史诗中明确叙述的密洛陀的孙男孙女婚后生的“头个是乡尚再尚,他就是布努老大。老二是布苗(苗族),老三是布关(汉族),老四是布羌(壮族),老五是布系(说广东话的汉人)”,等等,则是表明多民族兄弟关系不争的事实。密洛陀留下的遗言则成为全诗的要义所在。密洛陀临死前告诫子孙:“独树不成林,万树盖群山。兄弟和好,别人怕你如猛虎;姐妹不和,人家看你像笨羊。与亲邻和睦相处,别人对我们尊敬;和亲友断绝交往,你们就成一盘散沙。”“勤劳,山上的石头会变牛羊;勤劳,树上的叶子会变衣衫;勤劳,林间的花草也会开放;勤劳,河中的清流也会发亮。”“远客来到家,定要酒招待。别给人家吃白饭,别让人家喝清水。喝酒要有规矩,只许用碗不用杯。酒要给喝够,客要给灌醉。”毋庸讳言,人类文明进程并不是时间积累的结果,而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叠加和创新使然,特别是在突飞猛进的现代化与无所不在的快节奏正在不断排挤自我反思空间的当今社会,更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人类数千万年来保留下来的经验与生存智慧,也许这正是诸如创世神话史诗这样的非遗经典留给我们的真正有用的东西。
[1]王宪昭.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俄)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M].张雅平,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4]叶舒宪.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N].光明日报,2012-08-30(15).
[5]鲁迅(署名霍冲).拿来主义[N].中华时报·副刊,1934-06-07.
[6]河池市民委.广西河池市近40万布努瑶欢度传统佳节——祝著节[EB/OL].http://www.seac.gov.cn/art/2008/07/08.
责任编辑叶利荣E-mail:yelirong@126.com
TheFunction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ftheMinorityNationalities’theEpicofCreationMyth——TakingMiluotuoofYaoNationality’sBunuasanExample
WangXianzhao
(InstituteofNationalLiteratur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
The creation myth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s a non renewab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mankind.Through the decomposition and combing of functional motif of Miluotuo of the Yao’s Bunu,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epic of creation myth is ancient,complete,persistent and practical,and thus play the memory function of national history,the inheritance and function of production and life experience,as well as daily enlightenment and behavior norms and other functions.In a word,the fun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creation mythological epics needs to be actively promoted and guided by science.
the epic of creation myth;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Miluotuo ;Bunu of Yao nationality
B932
:A
:1673-1395 (2017)04-0014-07
2017-01-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160)
王宪昭(1966—),男,山东聊城人,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神话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