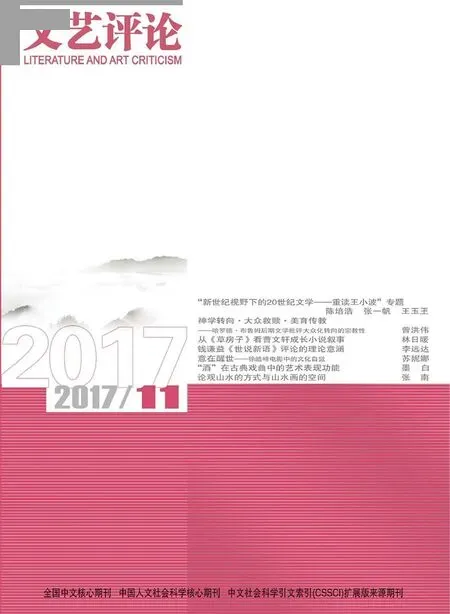史家抑或说家:钱谦益《世说新语》评论的理论意涵
2017-09-28李远达
○李远达
史家抑或说家:钱谦益《世说新语》评论的理论意涵
○李远达
明末清初的文史大家钱谦益对《世说新语》所发表的评论与众不同,很有启发性。可惜三百年来应者寥寥,学界尚未给予关注,值得清理与研究。他的评论主要收在《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九的《郑氏清言叙》和《牧斋有学集》卷十四的《玉剑尊闻序》这两篇文章中。文字虽不多,但提法却新人耳目:
临川王,史家之巧人也。生于迁、固之后,变史法而为之者也……史法芜秽,而临川之史志滋晦,此唐人之过也……而余则谓《世说》,史家之书也。(《郑氏清言叙》)①
临川善师迁、固者也,变史家为说家,其法奇。慎可善师临川者也,寓史家于说家,其法正。(《玉剑尊闻序》)②
钱谦益在文中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史家之巧人也”,“史志”与“史法”,“变史家为说家”和“寓史家于说家”,“奇”与“正”等,都很有理论价值。笔者试着透过这些观点,管窥钱谦益对史家与说家的态度,探究隐藏在文辞背后的历史幽微之覆。
一、“史家之巧人”
“临川王,史家之巧人也”是钱谦益在《郑氏清言叙》和《玉剑尊闻序》中都强调的一句话。这句话有两重意思:其一,肯定了刘义庆是史家;其二,刘义庆还是史家里面的“巧人”。问题是刘义庆为什么会被称作是“史家”?钱谦益是这样解释的:
夫晋室之崇虚玄,尚庄、老,盖与西京之儒术,东京之节义,列为三统。是故生于晋代者,其君弱而文,其臣英而寡雄,其民风婉而促,其国论简而刿,其学术事功迩而不迫,旷而无余地。临川得其风气,妙于语言。一代之风流人物,宛宛然荟蕞于琐言碎事、微文澹辞之中。其事,晋也;其文,亦晋也。习其读则说,问其传则史。变迁、固之法以说家为史者,自临川始。故曰史家之巧人也。(《郑氏清言叙》)③
钱谦益对刘义庆编纂《世说新语》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梳理与概括:首先谈刘义庆所记录的那个历史时代——晋代士人阶层崇尚清谈“虚玄”和“老、庄”,君主暗弱而好文,臣子英雄却缺少豪气,民风委婉而促狭,舆论简练而具讽刺性,学术、事功很不到位,玄学疏阔而不值得回味。钱谦益指出刘义庆准确地把握了时代,擅长语言描绘,将一代风流人物的真精神,真切地荟萃于言简意赅的文辞和小事里。刘义庆用晋代的文辞来描摹晋代的人事,并且改变了司马迁、班固的历史写作手法,用小说的方式来存史、著史,是从刘义庆开始的。换言之,刘义庆的时代适合用小说笔法,他顺应时代用小说存史,便成为了史家中的“巧人”。为突出刘义庆的“巧”,钱谦益还特别举出了后代“为续为补之徒”的“拙”:“代不晋而晋其事,事不晋而晋其文,譬之聋者之学歌也,视人之启口,而岂知其音节之若何也哉?”不用最贴合时代的语言对那个时代进行描摹,徒学其表,只能像聋人学歌,得不到其真精神。这种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后代续仿之作无论从史料价值还是艺术水准都无法与《世说新语》相媲美的原因。
有趣的是,与钱谦益切入角度类似,几乎同时而略早的王思任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世说新语序》中,王思任称赞《世说新语》是:“得晋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晋人之言于舌外,此小史中之徐夫人也。”④钱谦益称刘义庆是“史家之巧人”,《世说新语》是“史家之书也”;而王思任则说《世说新语》是“小史中之徐夫人也”。小史,是文言小说的一种雅称。也就是说王思任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世说新语》是说部中的翘楚。众所周知,钱谦益一生以史家自居,他曾自白道:“谦益,史官也,有纪志之责。”⑤他绝不会轻许刘义庆为“史家”,其中一定有他幽微的心曲。
二、“史志”与“史法”
钱谦益说刘义庆这位“史家之巧人”有着强烈的“史志”,又特别注重“史法”。笔者有必要研究一下刘义庆“史志”与《世说新语》的“史法”。唐初修《晋书》,大量采录《世说新语》,史学界早有公论。唐代刘知几的评论最具代表性:“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⑥他站在史家立场上,认为《世说新语》等书是记载“诙谐小辩”的小说,根本称不上逸史。如果哪部史书不慎收录了这批“晋世杂书”,那么只能是“虽取说于小人,终见嗤于君子矣”。不难看出,刘知几的矛头对准了唐初房玄龄等人奉命修撰的《晋书》。而钱谦益则将谴责的重点放在了房玄龄们不懂“临川之史志”。
钱谦益所谓的临川“史志”是将一代史事保存在琐碎的言语事迹、微文澹辞之中。这种“史志”,一方面是钱谦益认为主观上刘义庆有着强烈的存史愿望。另一方面也肯定了《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虽然,钱谦益不是第一个提出《世说新语》是“史家之书”的,明代黄汝亨在《世说新语补袖珍小序》中就已经提到:“《世说》,史家者流。而清辞玄致,似闺秀林逸,风流独擅。”⑦然而论证《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并对刘义庆的“史志”给予高度评价,还是体现出了钱谦益深厚的史学修养和独到的理论眼光。
与“史志”相关的是“史法”,钱谦益在评论《世说新语》时多次提及“史法”,尤其是“变史法而为之者也”。谈论“史法”之“变”,南宋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说得明白:“迁所纪五帝三代……然尚未有变史法之意也。至迁窥见本末,勇不自制,于时无大人先哲为道古人所以然者,史法遂大变,不复古人之旧,然则岂特天下空尽而为秦,而斯文至是亦荡然殊制,可叹已!”⑧叶适的说法提供了佐证:被后世奉为圭臬的《史记》,恰恰是“史法遂大变”的产物。这种对“史法”之变的认识偏重于宏观方面,而清代王鸣盛的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史法”之变的微观视角:
《晋书》列传卷第二十九……各传中叙事虽蔓衍无法,亦尚差可。其以八王特提出聚于一处,不似他王以同父者合为一篇,又其序次则以事之先后,不以辈行之尊卑远近,极得史法之变。⑨
王鸣盛是史学大家,他敏锐地发现《晋书·八王列传》不是把有亲缘关系的藩王放在一起,而是依照“八王之乱”发生的先后,依次以事相从,这种著史方法被王鸣盛赞誉为“极得史法之变”。应该说钱谦益评论《世说新语》是从司马迁、班固那里“变史法而为之者”,兼有宏观与微观这两方面的改变意义。宏观上说,《世说新语》的“史志”不同于官修的正史,既没有《史记》的发愤著书,也没有后世正史那种强烈的教化意味,只是记录了一代风流人物的真精神;微观上说,《世说新语》以类相从,专记琐碎细事、甚至只言片语,形成了与纪传体完全不同的“史家”文体。
无独有偶,钱谦益的晚辈蔡方炳在为朋友褚人获的《坚瓠集》作序时,也曾提到:“《世说》史法之变,斯集稗雅之遗,而其不诡于正则一,其可以解颐益智、适意陶情又罔不一,自稗编稗钞后续成异书一种矣。”⑩蔡方炳与钱谦益一样热爱《世说新语》,他们同样把该书认为是史家之书。所不同的是蔡方炳又为《世说新语》找到了《坚瓠集》这个同类作品。当然,在明清两代,说部地位很低,蔡氏的说法不排除附会史家,以抬高所序作品地位之嫌,不似钱谦益有自己一套论述脉络可循。
三、史家和说家的“变”与“寓”
“变史家为说家”和“寓史家于说家”是钱谦益《玉剑尊闻序》中至关重要的一对观点,它们互为表里,又有区别。前者评论《世说新语》,后者言说《玉剑尊闻》。需要澄清的是,在写作时间上,恰好以明清鼎革为界,降清之前所作的《郑氏清言叙》里,钱谦益将《世说新语》界定为“史家之书也”;而在晚年的《玉剑尊闻序》中,他又提出了“变史家为说家”的说法。钱谦益的《世说新语》评论在前后期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思想与明清鼎革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历代目录学家都把《世说新语》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四库全书总目》更指出:“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指‘纪录杂事’)。《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⑪然而刘义庆编纂《世说新语》的初衷与目的,由于文献匮乏,已不得而知。鲁迅先生根据《世说新语》中收录了《语林》和《郭子》,判断该书乃“纂集旧文,非由自造”,而据《宋书》认为“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⑫虽然编纂初衷不可考,但编选标准是比较容易考查出来的。刘强的《世说学引论》曾将《世说新语》1130条的出处几乎全部考出,我们从中可知,“杂史别传和志人小说中的言行逸事特别受到青睐,所占比例至少在全书的四分之三;正史和其它文献虽然也有涉及,但分量极小”⑬。刘强还提出“不能仅把《世说》当作一个‘史料汇集’或‘志人小说选本’,而应视作在有文献可征基础上的、有采有撰的‘二度创作’”⑭。
更为重要的是,《世说新语》还有诸如“网状结构”,对人物背景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省略与虚化,以及重“呈现”轻“讲述”的叙事方式等特征都迥异于史传传统尤其是正史的写作规范。钱谦益所谓“变史家为说家”的这种“变”,应该是一种质变。《世说新语》中有许多例子能证明这些观点,例如《言语》第二:
刘琨虽隔阂寇戎,志存本朝,谓温峤曰:“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今晋祚虽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于河北,使卿延誉于江南,子其行乎?”温曰:“峤虽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岂敢辞命!”⑮
根据刘孝标的注,这条盖出于虞预《晋书》:“峤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标俊清彻,英颖显名,为司空刘琨左司马。是时二都倾覆,天下大乱,琨闻元皇受命中兴,慷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峤奉使,峤喟然对曰:‘峤虽乏管、张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辞不敏,以违高旨!’以左长史奉使劝进,累迁骡骑大将军。”⑯对比可知,《世说新语》中删了温、刘二人的“背景资料”(55字),仅以“刘琨虽隔阂寇戎,志存本朝”(11字)叙述,体现了“删繁就简”的叙事策略;但是却把“使峤奉使”(4字)“敷衍”为刘琨壮怀激烈的劝使辞(43字)。压缩“讲述”使得这则故事基本上由对话组成,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格外鲜明。难怪明人陈梦槐评云:“琨语磊落扬厉。”⑰这种效果是史家叙事较为少见的,而说家色彩特浓。
从上面论述,我们知道钱谦益前期认为刘义庆是“史家”,与他的历史观有联系,而认为《世说新语》是“说家”表面上看是老生常谈,实则揭示了史家与说家之间界限的模糊,以及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郑氏清言叙》里有“习其读则说,问其传则史”这句话。典出《春秋公羊传·定公上》:“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何休注云:“读谓经,传谓训诂”。徐彦疏曰:“此假设而言之,主人谓定、哀也。设使定、哀习其经而读之。问其传解诂,则不知己之有罪于是。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⑱结合典故,钱谦益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读者对《世说新语》作文辞语言层面的解读,那么它当然是小说;但如果考究训诂,掌握其深层次蕴涵的历史兴亡与得失,那么《世说新语》便是一部史学著作。换言之,是“读法”决定了《世说新语》这部作品的本质属性,从而也成为了史家与说家相互转化的津梁。
钱谦益“变史家为说家”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世说新语》评论史上自南朝以讫于晚明关于该书性质的争论。他从历史学家的视角出发,提出《世说新语》是一部由史家刘义庆完成的小说作品。而史家与说家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可能,这种可能的实现取决于读者不同的阅读期待。
“寓史家于说家”也是《玉剑尊闻序》提出的一个有趣的概念。《玉剑尊闻》作者梁维枢,字慎可,真定人,钱谦益好友。顺治十四年(1657年),钱谦益为梁维枢《玉剑尊闻》作序,当然不免老友间的相互吹捧。但值得注意的是,钱谦益站在史家的立场上,否定了几乎所有的“世说体”续作,唯独肯定了《玉剑尊闻》。这部书一定有符合钱谦益欣赏的东西。
《玉剑尊闻》今存顺治甲午(1654年)赐麟堂刻本。书前有序三篇,引一篇。作序人和梁维枢自己对“世说体”的源流,前人笔记的得失,编辑该书的经过都进行了详尽描述,唯独对书名只字未提。连学识渊博的四库馆臣也不清楚书名的来历。⑲其实,“玉剑”就是“玉光剑气”的省称,同时代有一部明遗民张怡的《玉光剑气集》,曾参考过《玉剑尊闻》,表达了相近的主旨。⑳典故出自《晋书·张华传》。㉑在明末清初的士林生态大背景下,“玉剑”的隐喻义有二:一是“玉光剑气,终不可掩”,即大明气数未尽,一定能够复兴;二是“玉光剑气”,定不能掩:有志之士,共同奋斗,努力匡复大明江山。
了解了《玉剑尊闻》的隐喻,我们再来看《玉剑尊闻序》中的表述:
慎可善师临川者也,寓史家于说家,其法正。世之君子,有志国史者,师慎可之意而善用之,无惮筑舍,无轻奏刀。子玄有汗青之期,而伯喈无髡钳之叹,岂不幸哉!㉒
不难发现,钱谦益认为梁维枢是善于学习刘义庆的,它能够把历史的兴亡寄寓于小说的叙述之中。如果当世有志于修撰国史的君子,能够学习梁维枢的笔法,既不要与人讨论太多,浪费精力(当然也是躲避嫌疑),又不要轻率下笔,做好充分准备,那么刘知几“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的感慨就不必发生,而蔡邕被害前请求“黥首刖足”以完汉史的悲剧也不会重演。钱谦益连用四个比喻,含蓄地表达了他对当世史家的希望:用小说的形式寄寓历史兴亡的感慨,寄托故国的哀思。这种手法既能躲避日益繁密的文网,不致给史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又能完成修纂国史,保存文献的伟业,实在是一条正路。而从这个角度看,刘义庆编纂《世说新语》是用小说家笔法书写刚刚过去的当代史,既能够记录历史人物的语言神态,又能够传播一代文士的真精神,实在是“史家之巧人也”。
将明清异代作为历史背景进行考量,我们就会发现诸如“春秋笔法”、“习其读则说,问其传则史”等一系列思想资源被重新激活了。钱谦益熟读儒家经典,又有志于史学,“变节降清”的历史污点使他的后半生更加强烈地寻求存在的合法性。推崇《世说新语》,以及并不优秀的《玉剑尊闻》,无疑与这种身份焦虑有关。不过,当学术问题成为了实现政治抱负的思想武器,它的普适性与理论价值也会大打折扣。这也是钱谦益的《世说新语》评论在后世影响有限的重要原因。
四、“奇”与“正”
钱谦益将《世说新语》和《玉剑尊闻》对比,认为在史法的角度上说,前者“奇”,而后者“正”。“奇”与“正”也是一对有趣的范畴:先秦典籍里“奇”与“正”的用例有《老子》五十七章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㉓《孙子兵法·兵势第五》所说尤详:“三军之众,可使毕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㉔“奇”与“正”的观念多用于军事领域:“正”指的是与敌人正面交锋,后来引申为正面的手段,阳谋等;而“奇”则是出奇制胜的手法,引申为阴谋等。钱谦益文集中的用法与此相同,如《刘大将军诗集序》中的“余奇”㉕。在古人术数观念里,把握“余奇”,留有充分的战略余地,就能在关键时刻,出奇制胜。钱谦益用军事术语来比较《世说新语》与《玉剑尊闻》的不同,很有理论思维:《世说新语》以“晋文”写“晋事”,妙于语言,故能激荡人心,是出奇制胜;而《玉剑尊闻》典丽持正,体例严谨,描摹有明一代士风,风格平淡,持论平正,不失为良史。
关于《玉剑尊闻》的叙述风格,兹略举一例:
钱牧斋与文太清、王文水谭文左掖门下,各持所见,断断不相下,牧斋曰:“子亦知道家结胎之说乎?古之学者,六经为经,三史六子为纬,包孕陶铸精气结轖发为诗文,譬之道家圣胎已就,飞伸出神,无所不可。今人认俗学为古学,安身立命于其中,凡胎俗骨,一成不可变,望其轻身霞举,其能乎?”㉖
这段文字准确把握了钱谦益辩论时的背景,渲染了深夜阙下论文,“各执己见”的争鸣气氛。这些材料很可能来自钱谦益本人。其中“六经为经,三史六子为纬”的思想也能在钱谦益的文集里找到出处。即使在《玉剑尊闻》为四库馆臣所诟病为“肤浅”㉗的自注部分,梁维枢对老友钱谦益也持论平正,在表扬其“文才俊逸,亮直有风力,以是非为己任”后,注到“位至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起礼部侍郎、内翰林秘书院学士”㉘。是否有褒贬蕴涵于客观叙述之中,不得而知,然恐非“肤浅”所能概括。
结合前文曾讨论过的“史法”的问题,《世说新语》对“史法”的变,在钱谦益看来是“奇”;而《玉剑尊闻》将“史家”寄寓于“说家”,则是“正”,为清初有志于国史修撰的士人提供了一条可以效法的道路。这也就是钱谦益为郑仲夔的《郑氏清言》作序时大谈刘义庆《世说新语》的史学价值,而在晚年为《玉剑尊闻》作序时却将《世说新语》作为陪衬的原因。李庆西先生在分析《玉剑尊闻》的钱、吴等人序言时说:“梁氏‘寓史家于说家’之法,正好比今人所谓‘打擦边球’也。”㉙也许晚年的钱谦益意识到了:《世说新语》式的“奇”是不可学的,而《玉剑尊闻》式的“正”则属于可以学习的“史法”。综上所述,独具慧眼、志在存史的钱谦益对《世说新语》的评论涉及历史与小说的边界,二者是否能够相互转化等理论问题。他提出的“史家之巧人”,“史志”与“史法”,“变史家为说家”和“寓史家于说家”以及“奇”与“正”等话题,从史学立场出发的,指出了有志于国史者的“以说部存史”的向上一路,放在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考察,十分具有士人精神生活史意义。
①③⑤㉕钱谦益著,钱曾笺注《牧斋初学集》卷二十九,卷三十五,卷三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81-882页,第 881-882页,第997页,第920页。
②㉒钱谦益著,钱曾笺注《牧斋有学集》卷十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89页,第689页。
④⑮⑯⑰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会评》[M],刘强会评辑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27-528页,第55页,第55页,第56页。
⑥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6-117页。
⑦黄汝亨《寓林集》卷三[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36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4页。
⑧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4页。
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九[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页。
⑩蔡方炳《坚瓠集·弁言》[A],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清代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24页。
⑪⑲㉗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一,卷一百四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04页,第1225页,第1225页。
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2页。
⑬⑭刘强《世说学引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第39页。
⑱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十五[M],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第 8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6页。
⑳李远达《〈玉光剑气集〉研究》[D],北京大学中文系2014届硕士论文。
㉑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三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75页。
㉓陈鼓应注译《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0页。
㉔李零译注《孙子兵法译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27-28页。
㉖㉘梁维枢《玉剑尊闻》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218页,第216页。
㉙李庆西《〈玉剑尊闻〉及钱吴诸序》[J],《中国文化》,1995年第1期。
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晚明常奇观念的蜕变及其对文学之影响”(17CZW026)]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