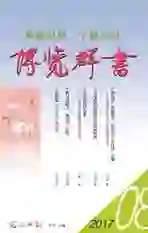文化大家间的矛盾与纠结
2017-09-26祝兆平
祝兆平
新中国的文坛上有那么一批人物,既曾经是才子作家,又是文坛领袖大咖掌门人。他们在历史上不是老革命,就是左翼文人,逐渐聚集到延安,执政以后,都是当然的文化官员,部级副部级的多得去,还有许多至少也是厅局级以上的文化官员。但他们在执政以后的几十年中工作生活的质量和幸福度如何呢?可以从这本由严平著的《潮起潮落:新中国文坛沉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中感受一二。
此书是陈四益推荐我读的,所以我读得很认真仔细,但却感觉越读越沉重,有时,竟有点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半年多的时间里反复看了多遍,感觉书中内容的信息含量太大太复杂,话竟无从说起,只好将书搁置一边,杂读其他各书消遣时日。
《潮》著一共写了八位文坛领袖掌门人物:周扬、夏衍、沙汀、何其芳、荒煤、许觉民、冯牧和巴金。
作者严平在改革开放初曾在文化部担任了多年的秘书工作,后又成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得以在时代大变革的背景下近距离地与那些文坛掌门人们接触和交往,长期的感受、观察、交往和了解(包括掌握大量的研究资料),甚至一起经历了某些人事的参与,使作者对有关这些大人物的人和事的了解与认识要比一般人知道得多。同时,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作者对这些人物个人的性格脾气、品行及内心精神世界的掌握和理解也要比一般人深入和透彻得多。
总的感觉,一是书中写到的八位文坛掌门人大多在长期不断地陷于为官和为文的矛盾与痛苦中纠结挣扎;二是这些文坛大人物的生存状态从未脱离过“左”与“右”的争斗。当然这些大多也是那个时代比较表面呈现的现象和事实特点。
书中除了周扬这个文坛总班头执政后每年写几篇讲话稿外基本上集中精力领会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和精神及不断搞运动,似乎无暇去为官还是为文矛盾与纠结,其他衮衮诸公基本上都多少存在着这样的矛盾和纠结。
沙汀与周扬相识于1930年,周扬担任“左联”党的负责人时,沙汀曾担任“左联”常委秘书,在白色恐怖时期,可谓出生入死,生死与共,但1938年他到延安后完成了《贺龙将军印象记》和《随军散记》等作品后,就提出离开延安返回家乡,提出的理由是妻子身体不适合,并不顾周扬的再三劝阻固执回乡。这次行为从此成为他的一块政治上的心病。“他经常陷于这种自责的痛苦中。那愧疚像一颗种子埋在他心灵的土壤里,随着岁月的绵延,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几乎伴随了他一生。”
“皖南事变”后的1942年,他奉命前往重庆参加整风学习,周扬再次通过何其芳带信给他,明确劝他重返延安。但学习了整风文件的沙汀本已很有些“羞惭”之感,读信后心情更加复杂。几天后,他还是在回信中说,反映落后生活讽刺和暴露,是不如歌颂党和党所领导的根据地重要,但自己不熟悉川北以外的生活,只能“退而求其次”。他再一次回到家乡,直到解放。
虽然在这期间他经历了躲藏追杀和逃避缉捕的危险,经历了贫病交困的潦倒,但他的大部分作品大都写于这两次回家乡的时间段里。
1950年,组织上调他从成都到重庆筹备西南文联,却被他以要搞创作的理由推辞了两次,直到第三次调令到,他才不得不前往履职。在革命年代,高层领导始终强调的是,党员作家,首先要你做好党员,才能做好作家。一个革命作家,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家,然后才能做好革命作家。可他老把作家放在首要地位。为此,在各次政治运动中,他不知作了多少次检查交待,也被批判了无数次,直到在“文革”中被彻底打倒。
到“四人帮”一倒台,他又被调回北京担任文化部下属的文学研究所所长时,他的老毛病又犯了。还是不想管事,不想做行政工作,一天到晚想到自己已经七十多岁,再不抓紧时间多创作些作品就来不及了,甚至为此产生了类似焦虑症的状况。老感觉在北京无法写作,因此就千方百计想着法子要把比他小近10岁的副部长级老弟荒煤调去当他的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自己老想着回到四川老家去創作。
沙汀调到北京后,作者看他不断地回四川,非常频繁地往返于北京和成都之间,非常疑惑他当时为什么决定要调来北京,曾经想当面问问他,但不知为什么虽然多次面谈却没有提出这个一直都揣测的问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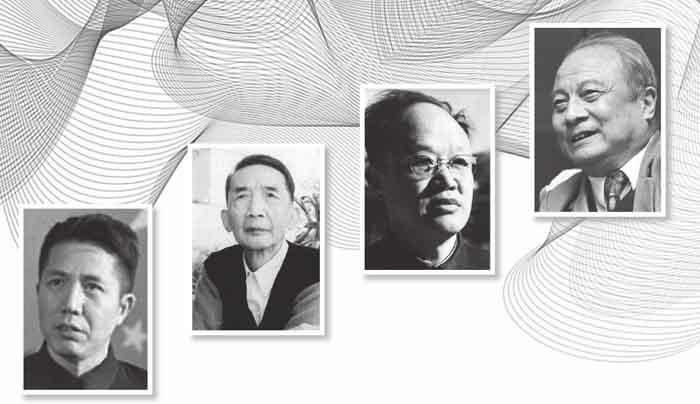
很多年后,作者才意识到,真正的理由或许就是他需要工作。和许多经历了十年磨难的老同志一样,能够重新为党工作是一种荣耀和责任。然而,从事情一开始,沙汀或许就隐约地感觉到了这其中隐含着的深刻矛盾。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作家,而作家重要的是作品,他知道自己内心更看重的是什么,不过,一个老党员多年培养出来的政治责任感让他把矛盾的另一面暂时淡化了。
这种矛盾与纠结挣扎几乎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到自己完全丧失了写作能力,这样的想法和矛盾和纠结都没有停止过。
同样的情况在何其芳、荒煤、许觉民、冯牧、巴金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和上演着。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往往在担任文坛重要职务时就挣扎于为官和写作为文的矛盾与纠结之中,而一被打倒批判时,又处于不要说无法创作为文,甚至落到连起码的人身安全和尊严都没有的悲惨境地。
巴金是20世纪30年代就成名的大作家。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他不属于延安一派的革命作家,没有去延安,却有不少文化青年因为读了他的文学作品而投奔延安。1950年他担任全国作协副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和上海作协主席。在新政漫长的岁月中,各种政治运动的连绵不断,到“文革”为最高峰,他被打入牛棚,受迫害到家破人亡的地步,所以长期以来根本没有进行创作的条件和环境(1973年从干校回到上海后,他已经开始偷偷地躲在一个不足三平方米的小屋子开始翻译外国名著)。而作为一个以文学创作为毕生追求的作家来讲,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事呢?endprint
1977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5周年纪念大会在上海展览馆举行,这是上海文艺界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大聚会,也是巴金11年来首次公开露面,他也见到了不少多年来未见的熟人。
从1978年底起,他应朋友之邀开始为香港《大公报》写随笔专栏,这激发了多年来压抑在内心的真实感受。从第一篇《谈〈望乡〉》开始,到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夕,他已经发表了三十多篇文章,从批判“四人帮”罪行,到批判封建专制和官僚主义,到对自己“奴在心”的深刻反省,称过去的十年是“可耻的十年”,呼唤创作自由,呼唤“讲真话”。
在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和全国作协会议上,巴金以高票当选为作协第一副主席,1983年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作协主席。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巴金已经进入了能够自由写作的境地,并渐入佳境,《随想录》的写作,是他进入晚年创作的一个高峰,但他的年龄已经进入“80后”了,他非常清楚时间对于他的珍贵,心里充满了紧迫感。进入80年代后,他许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最重要的除了写作,还想促成现代文学馆的创办。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但我更感觉到我必须退休了。不能再混下去。必须把该译的书译出,该写的写出然后死去,那有多好!”
此后,他多次通过不同的渠道向有关方面表述了自己这样的意思:1.辞掉作协主席,继续努力写作。2.希望作协抓一抓文学资料馆的工作。
同时,随着“文革”结束,复出后新生活的开始,文山会海也再次向他涌来,这让他倍感厌烦和焦虑,他不想这样度过最后的时光。他在给曹禺的信中说:“这半年来我一直在为多活、多写奋斗……现在我许多会都不参加了……今年起,我要为自己的最后的计划活下去。”这最后的计划就是除了已经完成的《随想录》等两部著作,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11部作品要去努力完成。
但他的作协主席的职务辞不掉,尽管已经是带有荣誉性质的。不仅作协主席辞不掉,茅盾辞世后的政协副主席一职也由他补上。直到最后,当他头脑还清醒时,曾多次表示不再担任政协和作协的职务,但已经没有任何作用。到他已经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愿望的时候,儿女们也多次明确提出父亲不再担任重要职务的意愿 ,但依旧没人理会,直到最终。
再说这些文坛大人物基本上终身陷于“左”和“右”的斗争漩涡难以摆脱。这里不说周扬、丁玲、胡风、冯雪峰之间的斗争故事,只举荒煤和林默涵之间持续了许多年的争执事例吧。
1981年9月,文艺界隆重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很不一般。起初,总报告的起草工作由荒煤主抓,周扬亲自拟定了题目“学习鲁迅的怀疑精神”,并多次和起草人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强调鲁迅科学民主大众的文化精神。报告写成后,几经修改送领导审阅,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认为没有战斗性,没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报告中提到的作家良知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表现,应该重写,并指定由林默涵挂帅。此时离大会召开只有十几天时间,原撰稿人退出,新的起草班子在林默涵的领导下执笔奋战。
愤怒的荒煤立即给纪念委员会主任邓颖超写信并转胡耀邦、习仲勋。
邓颖超的回复很快来了,认为报告写得很好,没有什么意见。胡耀邦、习仲勋也表示同意荒煤的意见。荒煤感觉,可能最终还要采用原来报告,当天就在日记中写道:“晚得通知仍修改周扬稿。”并立刻启动原班人马对原报告稿作文字上的推敲修改。同时,林默涵虽情绪不好,但也坚持指挥他的班子日夜奋战。
大会开幕前,王任重召开紧急会议说,现在有两个大会报告,大家讨论一下到底应该用哪个。经过争论,结果是王任重表示还是用原稿好,只要加上一段反对自由化的内容就行了。林默涵心存不甘,打电话给邓颖超陈述观点,还想争取自己重起一稿。而此时,离开会只有两天了。
书中写道:一直以来,在文艺界高层人士的分歧中,荒煤和林默涵之间的争论似乎格外针锋相对。荒煤最早发表(指“文革”结束后)的《阿诗玛,你在哪里》受到了文化部的一再责难;后来荒煤那些支持年轻人的文章被林默涵看作是跟在年轻人后面跑;荒煤对赵丹遗言的呼应被林默涵指责为没有立场;对《太阳和人》的意见被认为是错误观点,还有许多理论问题,以及用什么人的问题……荒煤绝不示弱,他最早指名道姓地批评林默涵,在文艺界公开他们之间的“分歧”;他在人性、人道主义以及如何看待新时期文艺等问题上一再和林默涵展开争论。
两人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你来我往,绝不妥协。但1992年文艺界举办荒煤文艺生涯六十周年研讨会,林默涵出席会议,他在发言中说:“当然,我和荒煤之间对某些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我们都是当面说,说过就算,并不影响在工作上的合作。”荒煤在答谢辞中回应了他的讲话,也算一笑泯恩仇了。
作者在这里又写道:“多年后再度回想他们的争论,让人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之初走过的艰难道路。”
再举个冯牧和贺敬之的事例。
馮牧和贺敬之有着几十年兄弟般的情谊。在延安,他们吃一锅饭,睡一个炕头,一起在鲁艺读书、一起开荒种地、一起散步在延河边。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共同工作在文艺战线,不仅个人关系甚好,两家人也交往密切,冯牧有件料子不错的大衣还是贺敬之夫人柯岩拿到稿费后给他做的。
“文革”中,冯牧和贺敬之彼此支持,冒着风险传递情报信息;“文革”刚过,他们也曾一起领导“文化理论政策研究室”,带领一批骁勇的理论家,为拨乱反正勇敢出击……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们却终因观点上的分歧不断产生芥蒂、隔阂、龃龉而至分道扬镳。
昔日老友在前进路上各自左右。他们不再有朋友间的串门,私人的往来,即便在同一个会议上碰面,也不愿坐在一起。一次,贺敬之在餐桌上遇到冯牧当着众人的面掉头而去。还有一次,一些人要编辑一套当代评论家丛书,有人提议应有贺敬之一本,冯牧欣然同意,却遭到贺敬之的断然拒绝。
他们就这样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陌路人,甚至扬言一方死了另一方绝不参加追悼会。可到1995年冯牧患白血病入院,当生死离别真的摆在面前的时候,贺敬之夫妇还是从天津找来名医为老友治病。事后,从小一直陪伴在冯牧身边的外甥女程小玲把情况告诉冯牧,身在病床上的冯牧沉默良久,叹息道:“我的这个老朋友!”尽管如此,直到离世,他也没有再见到自己这个老朋友。
冯牧去世后,小玲曾去探望手术中的柯岩,一见面,柯岩就把小玲抱住了。虽然身体虚弱但个性强悍的她嘴上仍旧不饶人,最后一次见到小玲时还埋怨说:“冯牧就是个傻瓜蛋!”
冯牧真是个傻瓜,一辈子书生气,不懂为官之道,侠义、率真、善良,不会计算得失利害,不多一两一钱也还要那么执着地,那么费心费力费精神地去争论去斗争,按某些人的聪明,那不是傻到了根上?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王蒙著《一辈子的活法》引用的一段话中的最后一句:“最后两边……谁也没比谁多斗出个一两一钱来……”真是感慨良多。
是啊,那都是那个时代的人和事了,且都往日是非已惘然。我想知道的是,现在还有谁如此真心真意、费心费劲地去争论,去斗争,为了一个观点,一种观念,一种理论,一种主义,一种责任,一种信仰,一种追求?
我想知道。
(作者系资深报人,评论家、藏书家、作家,曾获中国新闻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