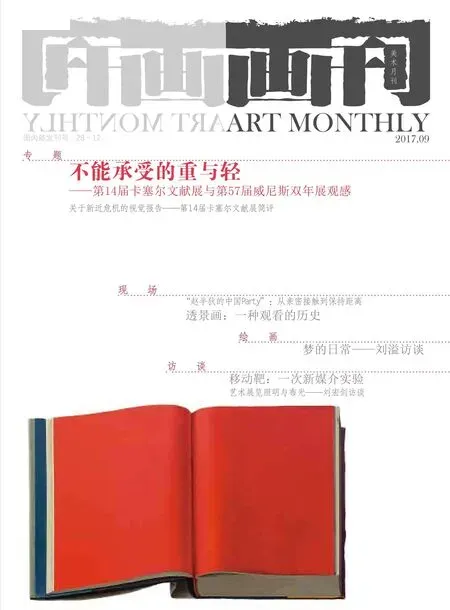不能承受的重与轻
——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与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观感
2017-09-25张晨
张 晨
不能承受的重与轻
——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与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观感
张 晨

《呼吸运动》 丹尼尔·克诺尔(Daniel Knorr) 2017年
2017年被称作当代艺术的“大年”。在这一年夏天,五年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十年一届的明斯特雕塑展、两年一届的威尼斯双年展,更有巴塞尔博览会等国际大展,让众多艺术从业者不得不踏上了欧洲的行程,也让国内的微信朋友圈被各大海外展览刷屏。
借着带领学生暑期考察的机会,笔者同时参观了第14届卡塞尔文献展与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同时在一次旅途中度过了德国的寒冷和意大利的暴晒,感受到两个国际艺术大展在策展理念、参展作品、展览空间等方面的特色与迥异之处。
一
倘若第一次来到卡塞尔,对于文献展学术、老派、严谨的刻板印象,在观展的过程中,会迅速被去中心化,甚至散乱、随意的亲身体验所取代。传统意义上文献展的中心——卡塞尔的弗雷德里希广场,自然集中着参加文献展的大部分艺术家,但更受观众欢迎的作品,则凌乱地散布在卡塞尔艺术学院以及经改造的老邮局、豆腐厂等30多个城市的角落。想要在这座距离柏林5小时车程的德国小城顺利观展,拥有一张文献展的导览图和一份对艺术的热爱显然远远不够,更需要的,是顺畅的网速、靠谱的手机导航、问路的语言能力和一双舒适的鞋。
产生这种观展体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来自本次文献展的主题:“以雅典为鉴”(Learning from Athens)。本届卡塞尔文献展的波兰策展人亚当·希姆奇克(Adam Szymzcyk)选定了这一主题,并第一次开辟了位于希腊雅典的分展场。据去雅典看展的朋友说,那里的展区多到令人摸不着头脑,甚至很多当地人都时常搞不清楚在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究竟是什么。而事实上,单只在卡塞尔的广场与小巷间穿梭,就已经让很多远道而来的观众迷失方向了。
基于“以雅典为鉴”的主题,在文献展的主要展区弗雷德里希美术馆(Kunsthalle Fridericianum)——18世纪由弗雷德里希·冯·黑森-卡塞尔二世建造,并以他的名字命名——集中展示了希腊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Contemprary Art,EMST)的收藏,也就是说,卡塞尔文献展的主体部分,这次几乎被来自希腊的当代艺术所占据。

《陌生人和难民纪念碑》 奥卢·奥圭贝(Olu Oguibe) 2017年
弗雷德里希美术馆一层中心位置的《跳房子》,来自希腊艺术家瓦拉西斯·卡尼亚里(Vlassis Caniaris)上世纪70年代的作品。主题源自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在大量移民的冲击之下,当时许多欧洲国家采取了关闭边界的措施,以保护本国居民的就业。而策展人选择这样一件将沉重的国际问题与轻松的儿童游戏相结合的作品,成功地使观众联想起今天欧洲的难民问题,也将艺术家早年的创作,巧妙地植入到当下的语境。也就是说,在策展人看来,历史从来不会淹没,从来都以幽灵的面目不断在当下闪现,并引发人们的思考。正如希姆奇克所说,弗雷德里希场馆的主题与目的,正是旨在“构建新的历史,同时挑战被普遍接受的历史”。如果走出弗雷德里希美术馆,仔细观看它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门楣,便会发现博物馆的名称“Fridericianum”,已被土耳其艺术家巴努·辛诺托鲁(Banu Cennetolu)的作品:《BEING SAFE IS SCARY》(安全是可怕的)的字样所取代。
如果说卡尼亚里的作品,因其主题与当下的关联性而能够被观众所理解,那么随着观展的深入,随着越来越多陌生而冗长的希腊艺术家名字与展签的袭来,观众的迷惑与不解也进一步加深。比如艺术家艾蕾娜·夫斯塔迪(Eirene Efstathiou)的作品《周年》(Anniversary),讲述的是1973年雅典理工大学爆发的学生动乱。由于缺乏对于作品信息的详细介绍,以及相关背景知识的隔阂,这样的本土事件对于远在东方的观众来说,确实难以进入,局外之感,由此产生。
如策展人所说,弗雷德里希美术馆展区的策展理念,在于唤起观众,尤其是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禁锢的艺术爱好者陌生的观看体验,促使他们在感性的层面,直接面对异国他乡的艺术家遥远的创作实践,引起脱离固有知识体系的好奇与反思,那么它的目的显然已达到。好在对于雅典来讲,作为古希腊民主政体的象征与美学化身的帕特农神庙尽人皆知,因此阿根廷艺术家马尔塔·迈纳士(Marta Minujín)耸立在与博物馆同名的弗雷德里希广场的《书之帕特农神庙》(Parthenon of Books),便成为了本次文献展地标性的作品。作品以10万本来自世界各地的禁书,建成神庙的式样,以一种不容置疑且回应历史的姿态,抗议着围绕言论自由的种种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走进这一书之神庙,会发现艺术家捆绑在多利亚柱式上的诸多禁书,甚至包括了当下流行与畅销的读物,如《小王子》《哈利·波特》《暮光之城》系列等,或许《哈利·波特》被列入禁书的原因在于对巫师法术的提及。这在此时此刻是难以想象的,但倘若换作欧洲中世纪的语境,抑或置于某个极权统治下的政府,却极有可能发生。也就是说,艺术家在此着意强调,重要的不是某本书或它的内容,重要的是围绕在其周围的一系列管制制度——只要禁锢言论自由的制度还存在,只要头顶仍笼罩着某种极端意识形态的乌云,那么任何言论、任何出版物、任何一句无心之语,都有可能随时被打入囹圄。
另一方面,作品的展示地点同样是值得注意的。1933年,纳粹德国正是在卡塞尔的这座广场上,在臭名昭著的“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运动”中焚烧了2000余本禁书。可以说,《书之帕特农神庙》不仅以对民主政体、自由信念的回溯与追寻,向雅典学习,更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在德国与欧洲沉重的过往中,以史为鉴。而在文献展上,与这件作品相呼应的,是罗马尼亚艺术家丹尼尔·克诺尔(Daniel Knorr)的《呼吸运动》(Expiration Movement)。克诺尔让弗雷德里希美术馆高耸的塔楼顶部,每天喷出滚滚的白烟,仿佛在艺术的展场透露着战争的威胁,更在同一意义上,指向了纳粹曾经在此的焚书活动。
有意思的是,克诺尔的这件作品因其难以被注意与理解的形式,常被观众所忽略,据说更有不明真相的当地居民频频向消防部门报警。同样因融入现场环境而很难被察觉的作品,还有汉斯·哈克(Hans Haacke)悬挂在弗雷德里希广场的标语《我们(都)是人民》[Wir (alle) sind da Volk],配以在博物馆屋顶放置的难民雕塑;以及位于卡塞尔的国王广场中心,由尼日利亚艺术家奥卢·奥圭贝(Olu Oguibe)树立的巨型方尖碑——很多观众可能把它当成了城市原有的纪念碑建筑,但只要凑近观察便会发现碑座的铭文,那是来自《圣经·新约》的一段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分别用阿拉伯语、英语、德语和土耳其语写就,再一次影射了欧洲的难民问题:卡塞尔这座德国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迎来了许多来自东德寻求庇护的难民,而今天,它与整个欧洲世界所面对的,则是来自非洲与中东,在他们看来遥远、隔绝、充满差异甚至危险的陌生人。
文献展上另一件不起眼的作品,甚至根本无法被看见。在卡塞尔城市的各个展区以及美术馆内部的空间,常会出其不意地传来一阵女性的窃窃私语,这是来自美国黑人艺术家波普·L.(Pope. L.)的声音装置《窃窃私语竞选》(Whispering Campaign)。在他看来,窃窃私语是一种极为日常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也让他决定把作品隐入现场的空间;而另一方面,作品中谈话的内容却极为政治,艺术家以此将日常生活政治化,或让严肃的政治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消解。波普·L.的另一件参展作品切实可见,是他自1997年开始创作的《肤色组计划》(Skin Set Project),位于弗雷德里希广场的另一展览空间文献展厅(Documenta Halle);他将一系列涉及种族问题极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用戏谑的方式镶入画框,如“黑人是沉默的,他们无法理解”(Black People are the Silence They Cannot Understand),“白人是上帝说话的方式,抱歉”(White People are God`s Way of Saying I`m Sorry),等等。
二
在卡塞尔的文献展厅,“以雅典为鉴”的主题与另一公共项目“身体议会”产生交集,这是由西班牙哲学家、策展人保罗·B.普雷西亚多(Paul B. Preciado)发起的项目,主张将文献展空间交给艺术家与观众,交给置身展厅中的每一具身体,并以一系列的艺术活动、行为表演、讲座与工作坊,伴随文献展的展期,不断讨论围绕“身体”的文化政治问题。在文献展厅中,艺术家安妮·维杰尔(Annie Vigier)与弗兰克·爱普泰特(Franck Apertet)便利用内部的空间结构,以斜坡搭建起舞台,令人联想起古希腊人参与政治、发表演说的公共场所,这一空间往往位于神庙广场之前,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集中体现。作品以舞台的空间延展,将“以雅典为鉴”的主题与每一位观众的身体发生关联,实际上,观众在观看展览的同时,也不自觉地进行了某种政治参与。

《书之帕特农神庙》局部 马尔塔·迈纳士(Marta Minuj í n)

《书之帕特农神庙》 马尔塔·迈纳士(Marta Minuj í n)

卡塞尔文献展现场

《寻找一个地方》 尼科斯(Nikos Navridis)1999年
另一方面,“身体”的概念也在此凸显。当代艺术中的身体,已不仅涉及具体的表象或物质性肉身,而更从性别、阶级、身份等角度,与文献展的政治主题发生关联。实际上,有关身体的哲学讨论,早已历经尼采、福柯、德勒兹、阿甘本的细数与思考,身体无论在历史与当下,在福柯看来,都是知识与道德铭刻的平台,是权力与政治纠葛的战场,因而,“生命政治”、“身体转向”等在今天仍是思想界热门的议题,尤其是,它又如此恰切地与本届文献展频繁讨论的难民问题相契合——面对来自非西方国家的难民,即便接纳国政府出台一系列对之进行教育、安置、规划与调节的技术手段,希望根除裹挟其中的恐怖主义威胁,减少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但每一个难民,终究携带着自己的身体,这一具具鲜活、实在的身体,对欧洲而言,一如阿甘本的“赤裸生命”,是权力悬置的真空地带。这一侵入的外来物,使固有、自洽的权力网络遭遇失语,难民的身体,也便成为了难以被讨论并消化的绝对陌生与差异化身;或如德勒兹所言,他们充满了鲜活而不确定的身体之力,埋藏着冲破固有权力体制的潜能和欲望。这样的身体对于掌权者来说,固然是危险的,是急需控制与规训的。而围绕难民的政策,同样为历史悠久,由古希腊绵延而来的民主政体带来危机与质疑。今天的欧洲乃至西方世界,极右与保守势力的抬头便是明证。
如果说,希腊的历史、欧洲的政治,为处在语境之外的文献展观众造成了障碍,那么身体,却是每一个人再熟悉不过的。恰恰是身体,构成了个人与政治的联结,也仍然是身体,被德勒兹等哲学家委以重任,抬高到冲破权力体制、去除政治边界的高原位置。或者说,身体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与艺术的概念近似,即通过身体,一如通过艺术,围绕艺术家的实践工作,新的思想与知识得以在展览空间中生成,新一轮的文化反思与抵抗活动,也在艺术与身体间被寄予希望——当政治难以被直接讨论,当语言的沟通遭到屏蔽与隔绝,文献展让观众重新拾起艺术的手段,找到它在今天的效用与意义。
正如卡塞尔文献展的标志:那只能将头歪到270度的猫头鹰所示,当代艺术在今天,代表的正是这样一种特别的观察方式:一方面,猫头鹰永远紧盯着眼前的世界,永远不会闭上双眼;另一方面,这种观察又是不同寻常的,是经过转化的,也即以艺术的方式接纳、反思并处理着现实。当代艺术也便从这个意义上,印证了阿甘本有关“当代人”的论断:在阿甘本看来,什么是当代?什么是当代人?便是那群永远紧随时代、永远凝视着时代的变动,同时又永远与它保持距离的人。惟其如此,他们才能不被裹挟其中,不被洪流淹没,才能捕捉并揭露时代的黑暗,而非肤浅的光明,体会并诊断时代的阵痛,而非娱乐至死。换句话说,什么是当代人?在阿甘本那里,便是尼采般不合时宜的人,是福柯所亲历的声名狼藉的生活,也是在今天,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家。
这种艺术与文化政治的联结,在文献展上也更为具体,以结合艺术史的方式上演。卡塞尔新新画廊(Neue Neue Galerie,由邮局改造而成)哥伦比亚艺术家比阿特里斯·冈萨雷斯(Beatriz Gonzá lez)的作品,呈现了一道被切割成两半的巨大帘子,帘子上编织的是马奈《草地上的午餐》的图像,明显地指向了艺术史书写与全球化背景下欧洲中心主义与精英主义的立场;而另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没能找到作品的展签及相关信息,这一现象在卡塞尔的展场极为常见),同样以东方挂毯的形式,再现了一幅幅欧洲艺术史名作:从戈雅的《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到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屠杀》等等,可以发现,艺术家所选择的画作,均与战争与杀戮相关。而这样的经典之作,在今天早已褪去了血腥的气息与震慑的效果,变为上流人士与知识分子玩味与欣赏的对象;但倘若转到挂毯的背面,便会发现,与正面悦目而流畅的图像剧烈反差的是,那里交错着因编织图像而外露的一团乱麻。在此,人们将战争娱乐化、将艺术的前卫性收编的手段再次被揭露,一堆难以辨认、粗糙杂乱的线头,使图像流于表面的唯美失效,同时,代表西方艺术史经典的名作,也在华丽背后的触目惊心中,松动了欧洲中心主义之于非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
三
结束了卡塞尔文献展的观展,笔者便经由杜塞尔多夫飞往威尼斯,准备进入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世界。并称为“国际三大艺术展”的威尼斯双年展与卡塞尔相比,其定位与不同自然涉及各个方面,单从二者的书店便可窥见一斑:卡塞尔文献展区的书店,被大量的哲学理论书籍占领,齐泽克、阿甘本、朗西埃以及福柯、德勒兹是常见的名字;而进入威尼斯双年展的书店便会看到,这些名字被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杰夫·昆斯、比尔·维奥拉、卡若琳·舍尼曼(Carolee Schneemann,本届威尼斯金狮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等当下流行的艺术家所取代。艰深枯燥的哲学书籍,与赏心悦目的新版画册的对比,或许是卡塞尔文献展与威尼斯双年展差异的一个缩影。
另一与文献展的直观区别,便是威尼斯双年展一直设立的国家馆展区。这让很多在卡塞尔错落的场馆间丧失耐心与兴趣的观众,欣然地找到了更为熟悉与明确的观展路线,对于每一届威尼斯各个国家馆的品头论足,也成为人们如同文化奥运会般的丰富谈资。
如果说卡塞尔文献展给人的印象之一,是其政治性的讨论有些过于直白,那么实际上,威尼斯双年展的俄罗斯馆,也几乎每届都在延续着类似的主题。俄罗斯国家馆的策展理念与审美旨趣,往往将视角集中在本国特殊的历史与政治问题的遗留上。在上一届国家馆中,艺术家伊琳娜·纳科霍娃(Irina Nakhova)将俄罗斯国家馆的外墙通体涂成绿色,以象征改革的决心与未来的前景,并掩盖了苏联政权的红色;在展馆内部,黑暗空间中不断闪现的蒙太奇投影,则细数着苏维埃时代惨遭清洗的人物,切换着被粗暴地画上红叉的一张张鲜活的面孔。而这一次,俄罗斯馆则以“世界剧场”为主题,选取了艺术家格里沙·布鲁斯金(Grisha Bruskin)配以歌剧音乐的雕塑装置,以及回收小组(Recycle Group)创作的新媒体作品。布鲁斯金用极简的白色雕塑,具象地再现了在双头鹰国徽的野心统摄下,由集体主义的劳动生产与激进革命所构成的特有的俄国历史,现场厚重的交响乐声,烘托了集权的肃穆与恐怖。而回收小组则将人的身体雕塑,囚禁在俄国至上主义与构成主义时期的白色形式之中,只有通过特定的设备进行观看,才能以热感成像的方式,解放内部鲜活的个体与生命。
如果说俄罗斯馆的政治性主题,可与卡塞尔文献展对历史一贯的沉重反思加以比对,那么本届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最佳国家馆得主——德国馆,则又贴合了卡塞尔“身体议会”的项目意涵。德国馆策展人苏珊娜·普费弗(Susanne Pfeffer)与艺术家安妮·伊姆霍夫(Anne Imhof)共同策划、发起的现场行为表演,以志愿者随机与观众进行互动、交流的方式,将身体的力量与角斗搬上舞台,阐述着与“身体议会”相近的“生命政治”议题。
但是,与对俄罗斯馆的评论类似,德国馆在获奖的同时,一样遭到负面的指责,如认为其语言过于直接、单一、老旧,以及围绕身体的本质主义展示等。由于带队观展的原因,我们到达德国馆时,遗憾地错过了行为表演的集中时间,原本人满为患的德国馆此时只余空旷的玻璃展厅。但巧合的是,在展厅中我们偶遇一位国内知名的艺术史教授,当向他表达了没能赶上表演的遗憾时,这位教授意味深长地回答:“没看到没关系,有时候也是好事!”语气像极了一位刚从卡塞尔过来的老左派。

威尼斯双年展之俄罗斯馆现场

《雕塑不能吃》 萨彭斯(Yorgos Sapountzis) 2017年
除德国馆、俄罗斯馆以外,日本馆同样延续了其在双年展上抓人眼球的视觉效果。第56届双年展盐田千春(Chiharu Shiota)以红线、钥匙与独木舟串联而成的巨型装置,以华丽震撼的外观吸引了大量观众,同时通过钥匙等承载温度的微小物件,传达着交流与沟通的情感主题。而这一次,岩崎贵宏(Takahiro Iwasaki)则以“翻转过来,那是一片森林”(Turned Upside Down, It's a Forest)为题,营造了一个微观城市与“里世界”的展览内景,一种德勒兹“褶子”式的巴洛克建筑美学:“褶子”的概念来自德勒兹对于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描述,在他看来,巴洛克艺术的繁复外观与幽暗内部之间,有着巨大的张力,它以一种弯曲、对折与盘旋的方式,打破了此前文艺复兴的典雅与理性,如同莱布尼茨的“单子”以不断运动盘旋的方式,穿透建筑的边界,剥开内部的空间,建立内外平台之间的连接。这一概念被艺术家用以重新思考现代城市的空间关系与规划设计,并把去除空间边界的努力,延伸到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时间贯穿,以及对于观众传统观看方式的颠覆。
在国家馆中作为主场的意大利馆,本次同样用对场馆空间的改造,展示了其时间绵延的国家历史。在艺术家罗伯托·库伊(Roberto Cuoghi)看来,意大利的场馆内部,既是一种巴西利卡式的教堂结构,也近似于一家工厂车间。展览现场怪异、复杂的气味,同样传达着有关场馆身份的流动与定义的不确定。因此,库伊在其中展示了其雕塑创作从构思、制作到生产、成型的全部过程。艺术家用循环可再生的有机材料,塑造了如同基督上十字架的图式性身体,同时像极了战争中惨遭涂炭的干尸,雕塑制成之后,随着展览时间的流逝,材料便开始了扭曲与消融的变化。在此,围绕材料的一系列由制作、融化到再制作的工业程序,与基督复活的宗教与艺术史主题相混杂,同时在工厂与教堂的空间错位间,让观众得以穿越战争与宗教、当下与过往的历史。
在双年展军械库展区毗邻意大利馆的,是我们不得不提的中国馆。本次中国馆在国内引起了激烈的口诛笔伐,但在威尼斯现场,却丝毫闻不到硝烟的味道;恰恰相反,带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剪纸、皮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吸引了不少国外观众猎奇式的驻足观看。平心而论,与其他国家馆相比,这虽是一次刻意回避现实问题的国家馆展览,并对于中国观众来说,透着满满的土气与山寨味道,但至少好过上一届国家馆,好过艺术家尴尬地与农民工及偏远山区的老人跳舞。这次中国馆的现场呈现仍是完整的(虽稍显拥挤,如同上一届威尼斯主题馆邱志杰作品的展区一样),而在语言上,汤南南充满诗意的黑白影像作品,同样受到不少观众的好评。
四
国家馆之后,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展,则在“艺术万岁”(Viva Arte Viva)的标题之下,设立了“欢愉与恐惧之馆”、“共同之馆”、“地球之馆”、“时间与无限之馆”、“艺术家与书本之馆”等几个分展馆。从名字便可看出,双年展与卡塞尔文献展共享着几个类似的题目,拥有着或多或少共同的目标。但不一样的是,正如“艺术万岁”欢呼式的口号一样,正如在双年展观众脸上轻松、愉快的表情一样,威尼斯双年展从来不像文献展那样,背负着太多的历史包袱,苦口婆心地劝说人们关心政治,并时常表达着悲悯与愤怒,而是更大程度地拥抱观众,更多地偏向一种即时性的互动与交流。
近几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获得金狮奖的艺术家,从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到安德里安·派普(Adrian Piper),均主张以现场的交流,传达作品的信息,这也反映出威尼斯双年展的某种趋势与趣味。而本届主题展,同样有艺术家李明维为观众缝制衣服的参与性作品《缝补计划》(The Mending Project)、大卫·梅达拉(David Medalla)向观众发出留下随身携带某件物品的邀请《缝纫时间》(A Stitch In Time)等。但值得思考的是,正如上届金狮奖得主派普的作品,她在主题馆现场邀请观众向自己的志愿者许下一句承诺“我永远言出必行”、“我永远不向金钱低头”、“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诸如此类,艺术家以郑重其事的注册程序留下观众的诺言,但似乎一旦离开现场,一旦时间流逝,很难相信今天的观众还会记得自己上次留下的诺言是什么,又会否在这两年间始终恪守——更谈不上艺术家本人的在意。
在这样一座热闹非凡、人流拥挤的旅游城市里,在这个夏天的岛上,各个角落同时发生的众多展览中,策展人似乎并不苛求人们记住某件经典的作品,艺术家也没有奢望自己会被写入厚重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威尼斯双年展这次没有展现出如卡塞尔文献展般严肃的姿态,而选择以一种互动式的轻松氛围,取悦着远道而来的观众或游客。在主题展的现场作品中,岛袋道浩(Shimabuku)将苹果的Macbook Air笔记本打磨、改造成一把可以使用的菜刀,关小将人们围绕米开朗基罗名作《大卫》的种种成见拍成引人发笑的MV,希拉·席克斯(Sheila Hicks)色彩绚丽的纤维艺术作品被争相自拍的观众所包围……轻松、愉悦、转瞬即逝,如同威尼斯的岛屿般浮动在表面的体验,可以说是本届双年展之于卡塞尔文献展的最大区别。
五年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显然是沉重的,也如外界评论所言,是过于政治的。很多策展人所选作品的政治主题,难免流于坦露与直接,演变为一种行动的口号,而失却了艺术的光晕。如同展区比比皆是的难民包袱与水泥管的临时住所,或者影像作品中被坦克追逐的艺术家本人。至于这样的“以艺术的名义”是否有效,即便在回国后问及看过展览的专业策展人与艺术家,都难以得到肯定的答案。有时甚至会失望地发现,他们的脸上仿佛也流露出如普通观众般迷茫与疑惑的神色,更不用说从世界各地涌来的年轻游客,可能只是想用不低的门票价格,换来在社交网络上的点赞罢了——又或许,展览宏大的主题与严肃立意,恰恰以一套完整的体制囊括了各色现象,也同时预料到它的观者群体。文献展正是以这一方式,尽可能地松动着消费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保守立场,而这样的展览,这样的欧陆左派思想与胸怀天下的知识分子情怀,也恰为我们所需要。
至于威尼斯,至于它与卡塞尔的区别,或许可以引用米兰·昆德拉那段著名的话: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消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No Pain Like This Body》 拉尼·迈斯特罗(Lani Maestro) 2010/2017年

《共同之馆》局部 弗朗茨·艾哈德·沃尔特(Franz Erhard Walther) 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