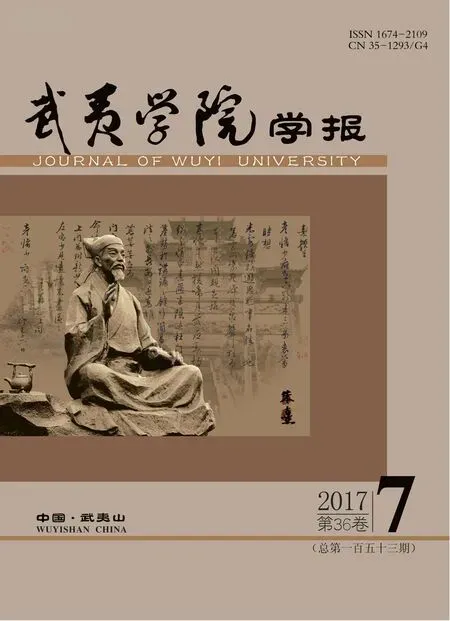殷商青铜器装饰中的政治权力思想研究
2017-09-20林汉铮李于昆
林汉铮,李于昆
(1.广东工业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30;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艺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1400)
殷商青铜器装饰中的政治权力思想研究
林汉铮1,李于昆2
(1.广东工业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30;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艺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1400)
中国古代艺术形式种类繁多,工匠技艺巧夺天工,尤其在殷商时期,青铜的装饰艺术发展出各种各样精美的形式。艺术形式的表达在于呈现视觉上的感受,更在于传达一个时期的文化特征,在以“礼乐”为重的宗法社会,其装饰纹样体现的应是势位至尊、器以载道、军权神授、乐以体政的政治权力思想。
政治权力;伦理等级;装饰;器物
在殷商时期的造物设计进程中,工匠所造之物都有着鲜明的等级次序,且所造之物必有其使用章程和制物法规。在《礼记·曲礼下》中记载,“凡家造,祭器为先,牲赋为次,养器为后”,“无田禄者不设祭器”[1],可见祭祀用的青铜器在殷商时期有着十足的分量,只有享受朝廷田禄者才能得以制造和使用。如此看来,青铜器不但是一件艺术品与祭祀品,更有着它的时代意义,在以青铜器为载体的装饰图形符号里,透析的不仅是艺术设计中审美的瑰丽,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权力思想的折射。
一、势位至尊
殷商时期的青铜器不再以使用为主要目的。“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2],大禹铸九鼎后流传于夏、商、周,寓意统治阶级得鼎者则问鼎天下。青铜器在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不再作为物的属性而从属于一般的使用物,而是以统治阶级的身份需求意向为一种政治权力符号的表征。“礼法”作为三代宗法社会的核心内容,统治者通过以器物的具体形态来缔结社会伦理关系,从而彰显造物与用物之规范。“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3]“礼”与“不礼”的区别在于尊与卑、老与幼、贫与富各有所等。人的社会秩序按照小至家庭,大至天下所“明分”,人的从属关系按照“礼”的规定所界定。青铜器的出现是为了明晰社会关系,奠定帝王统治的根基。
从商代青铜器装饰来看,以动物纹以及动物纹变体的纹样居多,而使用异化动物纹样为主的青铜装饰艺术,代表的是上层通天阶级的一个必要的政治手段。“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4]器物上变异的动物纹饰象征鬼神,这不仅能让民众知道神鬼的奸邪,也同时提醒世人近而远之,如此一来便能天地相协调,各得其所,上苍福泽万物。于是装饰纹样成为了人与神鬼之间的纽带,统治阶级通过对青铜器的占有和使用,来象征对权力尺度的把握以及对民众思想的规训。可见带有华丽装饰符号的青铜器并不是庙堂之上飨宴的奢侈品、点缀品,而是宗法社会权力意志的具体体现。
钺作为殷商时期的政治权力象征,诸多古文献中都有所记载。“(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5]黄钺为黄金所饰之钺,是天子所用至高无上之钺;“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6]钺在这里是军权和征伐权的象征。殷墟妇好墓中的一件青铜钺值得我们注意。妇好作为商王武丁之妻,在其墓葬中青铜钺的出现,代表了当时女性在政治朝局中还是享有一定的地位,并不像以后封建社会所强调的那样“男女有别,男尊女卑”。在妇好青铜钺的装饰纹样(图1)中可以看到,一对老虎以站立的姿态准备吞噬一个人,类似这种纹样题材出现在青铜器上也并不少见,如司母戊鼎、龙虎尊、神人双鸟鼓等。“虎,山兽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象形”[7],从字形上看,“虎”字的甲骨文[8](图 2)呈兽身人形双臂向前张开的站立姿态,与虎纹的形态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如果我们多加留意,商朝晚期的两件食人虎卣(图3、图4),也同样可以察觉其与食人虎纹、虎字甲骨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虎卣周身遍及纹饰,其造型是虎与人相抱的姿态,虎卣以足和尾部支撑身体,怀中之人朝虎胸前蹲坐,一双赤足踏于虎爪之上,双手伸向虎肩,虎欲张口啖食人首,其形态面目可憎,使人战栗。如果三者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应可以按“文字——装饰——器物”的逻辑关系加以分析。文字是文明的发端,文字的出现使得原始社会脱离了“上古结绳而治”的初级阶段,以甲骨刻画形式谱写国家的政治生活。当统治阶级权力稳固时,文字所承担的文化形态就进一步发展为看的装饰艺术形式。“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9]“物,万物也。”[7]有智慧的人创造出世间万物,而有技巧的人则遵循制造事物的道理和方法,这就叫做工事。工事以百工分职,百工所做之事又为圣人之所做。圣人在以政治教育的时代语境里就不再是神话中的先贤哲人,而是称帝王为圣,并连带着把许多文化事物的发明权归给他们。因此,纹饰这个文化事物的发明出现,并不表现以“无中生有”为逻辑起点,它是在“创物”的思维环节之后,直接从现有的文化形态中对社会意识赋予器物的形状。那些原创性的思维或智慧在以后一再重复进行的制造活动中不断地有所损益、有所变通,并且也不断实现了向制作性的转换。[10]所以,食人虎卣的器物形态就是在社会文化约束的前提下诞生的,事物的发明归功于统治者,而统治者又不断地加强统治思想。工艺匠人在受到严格的制作律令情况下,器物的形制就只能根据纹饰中所蕴含的权利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新的成器形态。这种装饰向器物的演变形式,无非是想借助于已知的文化经验和实践认识去指导装饰设计的具体方式,它首先是可以表现为对认知对象的模仿,再依照某种已存在的形象展开创造性思维运用,其次再根据形象之物所蕴藏的意义,来推行当时的统治目的。

图1 妇好铜钺食人虎纹Figure 1 Maneater Pattern of Fu Hao Tomahawk

图2 “虎”字甲骨文Figure 2 Inscriptions on ones or Tortoise Shells of Tiger

图3 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藏食人虎卣Figure 3 Izumiya MuseuMin Japan Collection of Ancient Small-mouthed Wine Vessel ofManeater

图4 巴黎塞努斯基博物馆藏食人虎卣Figure 4 Senusky MuseuMin Paris Collection of Ancient Small-mouthed Wine Vessel ofManeater
钺与食人虎纹结合本身就成为权力的代表,食人虎卣更是强化了王权等级分野的概念。对于器物与装饰的选择,是一个时代巩固政治权力的需求,它要求了对造物设计规范制约和题材选择。我们细心观察很难发现在殷商青铜器上有着灵动雀跃的植物纹样,活泼生动的人物纹样,这种形式扼杀了人与物之间流动的情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野性的狰狞美,通过狰狞恐怖的装饰形式强化了威严、等级、专制的时代情感,使得器物在其诞生之初就被深深地烙上了奴役与宰治的符号。为此,君之欲平治天下,必“天子者势位至尊,无知于天下”(《荀子·正论》)[3],只有统治阶级掌握了器物的尺度、用物的法规与装饰符号上所诉诸的政治语言,才能匡天下,通鬼神,正礼序,以此使庶民知神奸,晓伦理,唯宗法族系之独尊。
二、器以载道
青铜器作为殷商饮酒文化与神鬼宗教祭祀文化的产物,它的装饰纹样必然有依附于物质生产初期所承载的社会思想萌芽。古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1]之说,何谓之道,天道也。殷商原始宗教观念特征之一就是“万物有灵论”思想的存在并形成了多神崇拜系统。[12]殷商青铜器作为祭器,必定肩负着社会文化意义上的“道”,这种“道”通过青铜器本身以及纹饰来反映,它在被造之初就被赋予了强化伦理等级秩序合法性的含义。
一切民族的文化,都从宗教开始,都从天道开始。[13]殷商时期的天道是人类生存的周遭环境意义上的天道[14],是天人合一的初期阶段,它以纹饰反映神鬼,从而界定了统治者与庶民之间的鸿沟,以此强调宗室统治者与生俱来的统治地位。这又有别于战国时期的天行有常、君臣之道。由于生产力水平与认识的限制,这种纹饰意义上的天道,应被理解为殷商人对于自然环境中万物具有灵性的初期认识与神权崇拜。在这里天道无疑处于最高位置,是王道政治据以运行的正当性基础。如果说王道政治是对王政运行基本规则与法制安排的一套实践性方案的话,那么,“天道”就是对王道政治提供高级法背景的理论建构。可见殷商人崇奉鬼神往往是带有功利性与实用目的性,我们通过青铜上的装饰纹饰可以窥见,政治统治的目的在于借用民众对于物品上所传递信息的神秘感,以及上至先祖的绝对权威性的解读,以达到对民众的教化。殷商帝国的统治者把人们对上苍的畏惧与无知,通过器物本身以及器物上纹饰符号所传递出的视觉语言,转变为对君主的畏惧与瞻仰,这在无形中便构成了普罗大众对政治权力的认可。
三、君权神授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1]从中可以知晓殷商人对于崇敬神鬼的独特宗教文化,这种带有神话意味的“殷礼”便成为儒家思想中“君权神授”的早期来源,而后随着朝代更替以“天子”为上,“礼”的观念就贯彻了自古君主政治章程上的整个进程。我们可以从殷商青铜器的三大纹饰中解读帝王被上天所给予的权利。
(一)饕餮纹
对于殷商时期饕餮纹所传递出的政治权力思想,我们可以通过文物制度的沿用加以解读。有的人认为饕餮纹是对东夷集团蚩尤部落的崇拜,但由于历史悠久神话概念无从考据,那么我们不妨从二里头文化中的夏朝兽面铜牌,对殷商时期饕餮纹加以分析。从两个时期的装饰形态特点来看,饕餮纹(图5,图6)的造型有着惊人的相似,高高扬起的倒兽角,近心字形的脸庞,以及如出一辙的臣子眼。如此看来,当文化艺术作为一定物质形态出现时,它必定会延续着它的外在形式以及内在表达,通过而后的不同设计手段去塑造有别于它最早的范式。“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15],孔子在这里论述的目的,在于表达继承文化器物中所承载的礼制传统。艺术装饰作为可感知、可触目、可触摸的符号载体,就成为朝代演替中可沿袭炮制的一部分,工艺匠人们根据已有的图式进行设计、加工、完善。因此,二里头铜牌饰充当着自史前兽面纹到商周饕餮纹的传承中介作用,它们的造型和工艺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不仅是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而且是传承了信仰和神话。[16]不难看出二里头青铜文化与殷商时期的青铜文化是一个地方传统以及制度的繁衍。我们从历史的痕迹中,可以看见夏朝的铜牌中装饰纹饰已具备了某种神权政治的功能,张光直先生在其《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文章中曾说道:“在商周之早期,神话中动物的功能是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17],“或者说他们本身便是直接达成某种宗教目的、政治目的的工具”。[18]殷商时期的饕餮纹不仅在装饰外在的形式上延续了夏朝的艺术风格,而且也继承了装饰符号中的神权政治语言,这给予了殷商统治阶级以“君权神授”概念的正当理由,这种政治需求的继承与创新又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直接表现。

图5 二里头嵌绿松石饕餮纹牌饰(乙)Figure 5 Erlitou Taotie Pattern of Plaque setwith Turquoise

图6 殷商青铜器装饰纹Figure 6 The Shang Dynasty Bronze Decorative of Taotie pattern
(二)凤鸟纹
殷商人崇鸟尊凤,在殷商时期的青铜中有着大量的凤鸟纹。作为先祖继承关系的图腾,是指殷商人通过在青铜上描摹刻画,最终在祭祀时达到祭祀膜拜的效果。凤鸟纹的出现,是殷商先人与东夷族频繁交流以至族氏融合所至,亦或是殷商祖先本身就来自于东夷族,虽然各种说法众说纷纭,但通过纹饰的考察可以得出,殷商人的祖先确实与东夷族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先,从古文献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19]、“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20],都能看出殷商与玄鸟有着密切的关联。据考察,东夷族部落的聚居地在今天的山东渤海地区,傅斯年先生在其《夷厦东西说》中把商与夷归为东系,厦与周归为西系,东西对峙,他认为殷商的祖先为东夷族,王国维先生也在其《殷周制度论》《说毫》《说商》等文明确指出“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21]东夷族以鸟为官职,如五鸟官职历正、司分、司至、司启、司闭,可见当时东夷族是以鸟为图腾的部落联盟组织。《史记·殷记本》中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6]殷商的祖先殷契为简狄食玄鸟卵所生,殷人视玄鸟为己图腾,为其大宗,不无道理。总之,不管殷商祖先是否来自于东夷族,天命玄鸟的传说频繁地出现在当时殷商王朝中,而不是出现在早期的夏文化中,这本身就可以说明,殷商的先人与东夷或东方地区在文化以及活动上有着密切的交流,甚至能通过族氏的融合上升到了观念层次,最后通过物质形态的装饰纹样进而表达出族氏延续的思想。
其次,龙山文化作为远古的夷人文化,我们可以用龙山文化中的玉鹰纹圭与殷商凤鸟纹的比对,来看凤鸟纹与其渊源关系。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鹰纹玉圭(图7),造型是一只钩喙突出昂首挺立的雄鹰,其姿态朝上神情傲视,两翅呈松驰飞翔状,两爪微张。再反观殷商青铜器中的凤鸟纹(图8,图9),两纹纹饰嘴部都为倒钩状,在鸟类的嘴型中只有鹰是钩喙造型,图7、图9鹰爪部分同样都为两爪微张状。有学者持凤源于鹰说。如:“凤凰最早、最基本的原形是鸷鸟,一种鹰类的猛禽”。《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我高祖少嗥鸷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这反映了商部族对鹰鸟的崇拜,同时也隐含了鹰与凤的关系。[22]所以,殷商的凤鸟纹是在东夷文化鹰图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了后期便添加了其他的装饰造型元素,最终出现了不同种类的凤鸟纹。

图7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玉圭”Figure 7 The Taipei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of Jade Gui

图8 凤鸟纹Figure 8 Phoenix BirdDecorative Pattern

图9 凤鸟纹Figure 9 Phoenix Bird Decorative Pattern
最后,无论纹饰的起源如何,它最终归结于殷商祖先趋于时代的需求,对所留下物质文化遗产的沿袭,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当时统治者对于祖先的追根溯源与神鬼崇拜。原始民族的图腾意识有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当图腾崇拜转化达到 “人—图腾”合一的“神”的阶段,这一信仰就标志着现实的人本身也得到了升华,以致“神化”,相应的其社会结构也已形成了高出于一般社会生活之上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威。[23]殷商人对于鸟图腾崇拜是基于宗法社会的需求,在继承鸟图腾的同时,发展出凤鸟纹的更多形式,进而以装饰的手法表现权力的象征。
(三)夔纹
夔纹在青铜器中出现也是非常普遍的,夔纹常以对偶的形式对称出现在完整的兽面饕餮纹两边 (图10),要么就以两夔纹共同组成一组饕餮纹(图11)。夔为独体象物字,同夒。[8]卜辞中有“叀高祖夒祝用王受又”,又有关于夒的祭日卜辞“甲寅贞:辛亥酒燎于夒,三牛?”,“己已卜,其来夒,吏辛酉?… … 大吉”等,不难看出殷商人视夔为其高祖,那么夔纹依附于主纹饕餮纹旁,或单独组成一组饕餮纹,就显得合乎情理了。这样,夔纹就不再是艺术功能上的装饰纹样,而是作为高祖成为统治阶级与先祖的沟通之媒介。青铜装饰中的夔纹与兽面纹一样,应该与殷商时期的信仰有关。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对先祖的祭祀,达到与先民的对话,祈求祖先保佑,以得宗室之延续。

图10 置于兽面纹两侧的夔纹Figure 10 The Kui Pattern Both Sides of AnimalMask Pattern

图11 两夔纹组成饕餮纹Figure 11 Two Kui Pattern Composed of Taotie pattern
上海博物馆的商亚方罍是为祭祀历代先王后妃以及太子而铸造的祭器,周身的纹饰必定有其合理的排列方式。全罍由扉棱分割,在罍身铸有巨大的饕餮纹(图12),饕餮纹上方由一只牛头兽面纹和两只相对的凤鸟纹组成,下方饰以小型饕餮纹。罍的肩部(图13)由羊头兽面纹与相对的夔纹构成,颈部(图14)与足部(图15)都饰有凤鸟纹。从整体上看器物纹饰有着相应等级秩序上的排列,如果纹饰杂乱就毫无层次感,同时也会缺乏感染力。以饕餮纹为主饰,加以夔纹、鸟纹、龙纹等为附饰,这种布局结构渲染了凝重的氛围,同时也使画面均衡丰满、富有秩序。

图12 商亚方身拓片Figure12YafangJarBodyRubbings of Shang Dynasty

图13 商亚方肩部拓片Figure 13YafangJarShoulderRubbin of Shang Dynasty

图14 商亚方颈部拓片Figure 14 Yafang Jar Neck Rubbings of Shang Dynasty

图15 商亚方足部拓片Figure 15 Yafang Jar FootRubbin of Shang Dynasty
人类学家张光直曾经引用过吉德炜的一段话:“商代的宗教与商代国家的起源和合法化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都认为,‘帝’能够赐授丰硕的收获,在战争中给以神灵的保佑,商王的祖先们能代向‘帝’求情赐福,而商王们又可与祖先们进行沟通。因此,对先祖们的崇拜和祭祀就可为商王们的神权政治统治提供心理上和精神上强有力的支持。[24]由此看来,饕餮纹代表了殷商时期最高信仰“帝”,它上达天意,面目可憎,使人畏惧。夔纹代表高祖依附与“帝”的边缘,留白处施以地纹,以做主次陪衬。凤鸟纹居于最侧,以表殷商人图腾信仰。如此一来,装饰便构成了青铜器上的政治图景,通过不同的纹饰以神权、血缘、信仰维系殷商王朝统治者君权神授的合理性。
四、乐以体政
乐与礼一致袭于商,有所损益。[25]“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1],“乐”可以使天地相互协调,“礼”可使天地有序,乐的意义在于以和谐为前提保证礼的实行,器物上的纹饰不仅是对伦理秩序的体现,而且还是器物本身敲击所发出的声乐,使之达到与自然神明交流的途径。因此,“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装饰之道与政合。政治意义上的纹饰载体是统治者通过声乐作为疏达情感的表达方式,那么从统治阶级来看,青铜乐器就是一种合礼器、武器、乐器多种政治职能的器具。
“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1]礼乐是用金石等器物表现出来的,进而再通过声音传播,它用于宗庙社稷以及山川鬼神的祭祀,这些天子与庶民是一样的,“凡金为乐器有六,皆钟之类也,曰钟,曰镈,曰錞,曰镯,曰铙,曰铎”,故天潢贵胄以乐侑食,钟鸣鼎食。靡靡之音,不绝于耳。乐音在此时就成为道德情感的心声,它能协调上下至天下大同。殷商乐器以铙最为流行,象纹铜铙(图16)就是一件精美的殷商乐器,它虽然看似笨重,但制作却十分的精细。器物的上方开口两侧分别立有两只卷着鼻子的小象纹饰,钲部的主体纹饰是由两夔纹构成的巨大饕餮纹,器身粗犷厚重,纹饰繁缛精美。象纹出现在乐器上能给我们一定的暗示,通过殷墟卜辞“今昔其雨,获象”可以得知,在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期,祭祀求雨是祭祀中很重要的一项环节,从出土有关象的青铜文物来看,象在当时人的眼中应该是被视为比较珍贵的动物,因此这种动物纹饰具有一定的王权特殊性。然而,象属于热带动物,这又可以推敲出,在殷商时期中原地区环境应是属于炎热的气候,干旱对农业耕种有着强烈的影响,所以铜铙的一个功能就是在祭典上用声音以及舞蹈向上苍期许降以甘露,保国泰民安。声乐也与行军作战有着密切关系,《周礼·地官司徒·鼓人》记载:“以金錞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饶止鼓,以金铎通鼓。”[9]在作战时不同的乐器应有不同的用途,作乐时用金錞调和鼓声,行军时用金镯节制鼓声,在退兵时敲击金铙停止鼓声,发号施令时敲击金铎与鼓声齐作。铜铙,《说文》曰:“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庸。”[7]因此,殷商时期的铜铙主要用于军政的发号施令,并且由军中掌有大权者击奏。在考古发掘中,铜铙又主要集中在高规格的墓葬中,这就不难理解铜铙上常铸有恐怖的饕餮纹(图17),其目的就是为了威吓敌众,以及显示殷商军事集团军纪之严厉,并且还能以乐传达天子之意。“国之大事,在祀与戎”[4](《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与戎行都是通过乐来进行,礼藏于器,乐器本身的含义在于体现贵族阶级的身份,其等级越高者器物纹饰越加精美。同样,寓礼于乐,礼数愈多者为尊,其所享有音乐的权利就越多,所能拥有的乐器品种就越多。所以,装饰纹样是政治权力最直观的表达,它以乐符在亦或是不在场,体现出尊者为贵,明辨等列的礼乐文明制度。

图16 象纹铜铙局部Figure 16 The Part of Imitative Elephant Pattern Nao

图17 兽面纹大铙Figure 17 AnimalMask Pattern Nao
五、结语
青铜器作为当时社会阶层的分割符号载体,它在一定意义上承载了所谓“殷礼”的社会规范,统治阶级通过器物上规整的装饰纹饰向芸芸众生传达了不可触碰的威严。同时,装饰艺术形态还未从政治结构中剥离出来时,装饰就按照统治者的身份象征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当一个帝国消亡,再到礼乐制度的崩坏,使得强加在装饰艺术身上的政治形态枷锁得以冲破,装饰艺术便从制度规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发展成具有商品经济特征的装饰艺术,此时它的艺术形式是自由的、浪漫的,且无拘无束的。这意味着装饰形式不再单一地以礼乐制度作为成器装饰的终点,而是通过装饰艺术反映生活、自然、人文、动物等。所以从殷商青铜装饰艺术中看,其政治权利语言在于:第一,社会的伦理等级秩序不可僭越;第二,器物有其承载的王道,通过纹饰“铸鼎象物”予以表达;第三,君王的权力由神明赋予,血缘的正统以及通过对祖先的沟通,期以上达天听,使统治者“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故殷商时期的青铜装饰艺术是为政治权力的体现而存在的。
参考文献:
[1] 杨天宇.十三经译注: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9,724,476,468,476.
[2] 墨子[M].李小龙,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185-186.
[3] 荀子[M].方勇,李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300,287.
[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669-671,861.
[5]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3.
[6] 司马迁.史记[M].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63:95,91.
[7] 许慎.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10,53,709.
[8] 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120,135-136.
[9] 杨天宇.十三经译注:周礼译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00,183.
[10] 徐飚.成器之道: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122,125.
[11] 南怀瑾,徐芹庭.周易今注今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374.
[12] 王杰.殷商时期的原始宗教政治与神权决定论[J].北大中国文化研究,2012(00):49-65.
[13] 方克立,李锦全.现代新儒家学案(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607-608.
[14] 任剑涛.天道、王道与王权:王道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其文明矫正功能[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2):83-94.
[15] 张燕婴.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236.
[16] 叶舒宪.二里头铜牌饰与夏代神话研究:再论“第四重证据”[J].民族艺术,2008(4):86-95.
[17]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83:313.
[18]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97.
[19]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678.
[20] 楚辞[M].林家骊,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94.
[21] 张锟.东夷文化的考古学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0:163-164.
[22] 孙力.商饕餮纹新解[J].辽宁省博物馆馆刊,2008(00):68-110.
[23] 谢崇安.人鸟合一玉饰与君权神授:先秦艺术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三[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86-90.
[24] 张光直.商文明[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192.
[25] 李振峰.易代之际的殷商礼乐传承:以箕子、微子为中心[J].文艺评论,2014(12):61-65.
(责任编辑:陈 虹)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ower Reflected in Patterns in BronzeW ares of Yin and Shang Dynasty
LIN Hanzheng1,LIYukun2
(1.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Guangzhou,Guangdong 510030;2.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of Art,Guangzhou,Guangdong511400)
As is known,Chinese ancient art is of great diversity and wonderfulworkmanship even excels nature.Especially in Yin and Shang Dynasty,the crude bronze ware has developed into varied exquisite forms as decorative art.The expression of art forMaims notonly to create unique visual experiences but also to convey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dynasty.In such a patriarchal society mostly civilized with rites and music,political power are well reflected in the decorations on bronzewares.
political power;ethical classes;patterns and decorations;vessels;
J0
A
1674-2109(2017)07-0069-07
2016-10-28
林汉铮(1992-),男,汉族,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设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