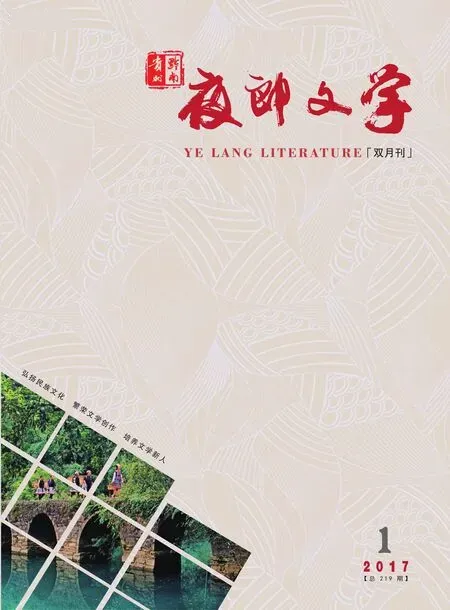我的母亲是棵洋槐树
2017-09-12蔡凤
蔡 凤
我不怎么喜欢洋槐树。你看着它满身的尖刺,就已经舍弃了亲近它的念头,六月天,满树的绿荫倒是乘凉的好地方,不过,这种树又极易长毛毛虫和洋辣子,不时掉下几条,令人浑身不愉快。
偏偏我的母亲,在弯七扭八的岁月里,浑然不觉地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洋槐树。她喜欢搬弄是非,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经生活磨砺仍熠熠生辉,她用这双眼睛防贼一样盯紧别人的不是,然后夸大事实四处传播。
我不明白我伟岸的父亲为何娶了我的母亲,他们是多么不匹配。
年轻母亲应该是带着无限期待,在旁人的羡慕中嫁给父亲的,当年的父亲满腹才华,风华正茂,俊朗洒脱,目光如炬,前程想来应该是繁花似锦。
父亲,则是带着凄然娶了母亲,他违抗了父母包办的婚姻,野了的心如无笼头的马,一心想驰骋在无际的疆域。论文韬,他才高七步;论武略,他能横马立刀,青春的热血激涌翻腾,小小的山村实在不是他的天地。能拴住他的,或许只有家庭,作为长子,奶奶把娘家堂侄女内定为儿媳并择了良日大操大办将其娶进了蔡家的大门。父亲百般反抗,婚后一年多不圆房,九龙山的杨矮子乘虚而入,女方在带人砸了嫁妆后跟着杨矮子过日子去了。奶奶又气又急,又羞又恼,包办不成,让父亲自己找个女人过日子,前提是自己找的就必须把心收了,过一个乡下人应该过的日子。
父亲是无意娶母亲的,我唯一的舅舅是父亲的中学同学,邀请父亲去他家,路上遇见母亲在放牛,芳年十六,梳了两个小辫,时值三月,远望人面桃花,父亲就那么远远望了一眼,连招呼都不曾打。就这一望,母亲铁定了父亲是去看人家的,催着她哥哥让父亲去提亲,父亲拒绝过,而母亲让人转告父亲“婚姻自古,戏男不戏女。”或许是这句话触动父亲,又或许爷爷奶奶催得紧,又或许同学情谊不可负,最后,父亲在苦楚中娶了母亲。这苦楚,苦在他结婚那天,决绝地对他母亲说:“妈,这回,是泡狗屎我也要吃下!”当妈的知道儿子性格,还庆幸儿子这回终于收心了。
这些过往,我的母亲或许并不知道,或许她假装不知道,她是欢天喜地嫁过来的,那时我家老祖公还在,家境还算殷实,很有地方影响力。尽管母亲个子矮小貌不出众,但能嫁给当时桐梓林蔡家作为长孙媳妇,对略有些爱慕虚荣的少女来说,内心的满足与喜悦让她无暇去构想生活的艰辛。
据奶奶描述,本指望有人管着父亲后,能少操一点心,谁知两人婚后一天吵得乌烟瘴气,后来进化为武斗,在坡上干活,只要听到满寨子鸡飞狗跳,那一定是两个又打起来了。

▲ 山水写生(国画) / 刘泉江
也许父亲曾容忍过,他是爱脸面的人,打女人这样的事实在令他无颜,而母亲不依不饶的性子让人难以忍受。女人哪里是男人的对手,挨打后的母亲常常破口大骂,像一只颤栗着尖刺的刺猬。
我非常理解我的父亲,因为我的母亲实在是个太会惹事的人,心眼小,爱挑事,不看事,还一天张家锅大李家碗小。以她的胸怀,想要驾驭一匹彪悍野马,怎么可能!
他们谁也改变不了谁,武斗升级为战争,每一次都两败俱伤,母亲越来越像洋槐树,浑身的尖刺让人敬而远之,但是,她硬是顽强地开枝散叶,把自己活成了一道风景线。她从来不在乎父亲爱不爱她,反正他已经是她碗里的菜,也不在乎别人的议论,前一分钟两个打得你死我活,后一分钟硬拽着父亲,两人一同背着娃娃赶场去了,五十多年打得死去活来,五十多年形影不离,因此也开创了蔡家“秤不离砣,公不离婆”的传说。
儿多母苦,那时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每到开学的时候,母亲总想方设法到处借钱筹备学费,也不知遭受过多少风言冷语,母亲从来不去计较,心眼那么小的母亲已经无暇去计较,她只想着她的男人是文化人,那么他们的孩子必须要有文化。为此母亲种过小菜卖,推过豆腐卖,做过黄粑卖,煮过甜酒卖……肩挑手提,一担一担抬去十多里路的街上去卖。小妹和老弟的大学费用就那样一分一厘地积攒,等熬到老弟毕业,母亲的肩膀长了厚厚一层老茧,肌肉长期被扁担挤压往下长,居然长成了一个大大的肉瘤,仿佛洋槐树的枝丫处突然冒出了一个疙瘩。
在卖菜的时候,她特意去认识了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据说两位女人个子差不多高,长得也相当。“看样子,她过得恼火,穿得还不如秦老二。”母亲向父亲描述她的所见,秦老二是我家下面的那女人,早年嫁给了一个麻风病人,好不容易跑出来嫁给了罗二公,罗二公满脸坑坑洼洼的麻子,秦老二在女人面前自觉矮了一头。父亲默默听着,间或抬头训导母亲嘴巴多,自家的牛马牲口都还没来得及拉上坡,哪里有闲心去管那么多。
听说那女人和杨矮子生了八个娃娃,大的是个女儿。她的一个儿子因生活寒苦参加黑社会组织“飞虎队”,专在桐梓林那段老路上抢劫,有次劫了军车上的物资,最后被枪毙了,就枪毙在桐梓林路边,那时我正好读初二,周一路过时,我特意去看了那滩血。殷红的血迹还在,我试图努力从中发现些什么,端详半天没有半点蛛丝马迹。
那时经常在桐梓林枪毙犯人,每一次围观的人比赶场还多,那一次,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正面相遇,八目相对,女人嘴角抽搐了几下,那男人羞愧地低下了头,父亲扭转目光,拉着爱凑热闹的母亲离开了。母亲有些幸灾乐祸,父亲有些低沉,说那是管教不严的恶果。
一次卖菜,那女人的女儿磨蹭着走到母亲身边,说:“叔妈,我一直有个疑问,不知该问不该问?”母亲欣然地说:“姑娘,有什么疑问,你尽管说。”“叔妈,从小我爸爸待我不好,别人说我是蔡家的,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平时爱嚼舌的母亲居然严肃的说:“姑娘,你不要听信那些谣言,你妈离开时还是清白的。不信,你回去问你爸爸……”一席话说得那姑娘展开了愁眉,后来她经常买两个油炸粑等着母亲,两人一人一个吃着摆龙门阵,母亲还偷偷带父亲去菜场,让那姑娘悄悄地看过父亲。
父亲年轻时,有个意中人,身材窈窕眉眼如画,和父亲两情相悦,怎耐对方家长说父亲脾气刚烈怪异死活不同意。这段情也就成了父亲心中的节,酒后经常忆起。母亲常在一旁默默地听,时不时冒一句“我要是你,一定要争取,你都没去争取,说明没得勇气。”
这段情,纠缠父亲若干年,母亲都一直不动声色,直到父亲垂垂老去的某天,母亲多方打听到了那当年眉眼如画如今也美人垂暮的妇人,并且安排了一场巧遇。当然,父亲早已不识当年黛眉,垂暮的妇人认出了父亲,告诉母亲,多年来梦中想着能见一面,如今见了,看见父亲儿女成群,只要父亲过得好也就没挂记了。等擦身走过,母亲才告诉父亲那刚才所见之人为谁,想来父亲应是百感交集,责怪母亲为何不早说,欲转身再去寻找,母亲淡然而答:“见了,你还不是认不出了!”父亲怅然若失,一路无语地跟着母亲回家。倒是母亲话多“这卢小碧,人老了,都还这样有看法,看来你还是没吹牛!”又牵扯岀父亲的记忆,又一路摆着年轻时眉眼如画的卢小碧回家。
了无心事的父亲开始觉得,我们的母亲,其实也挺好看的;开始为母亲的晚景操心,怕自己先走,我们苦了母亲;向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父亲开始担忧,深怕自己先走了母亲孤零零没个伴,担心母亲的性格不招人待见,反复提醒母亲少说话,担心母亲贪玩不按时饮食……
父亲走的那分钟,我们几姐妹哭得撕心裂肺,母亲本来正在厨房给父亲熬粥,听到我们的哭喊,飞奔过来,拉着父亲的手:“我的哥诶,说好的白了头,你啷个丢下我!”说罢,转身朝门框撞去,吓得我得大哥二哥脸都变了色,急忙将她拉住。
父亲走后的第七晚,母亲说她突然感觉屋里进了一股风,然后听到父亲的声音飘然响起“你不要怕,我现在变成了一股风,特意来看看你。你要好好活着,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
我的父亲幻化成了一股风,而我的母亲无意中活成了一棵洋槐树,满身的刺只出于自我保护,待到阳春三月,它什么时候冒出满树的洁白花穗,你真的不知道,但馥郁的花香让你不得不相信,洋槐树何止是树,原来它也是一种花。
而每一种花,自有它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