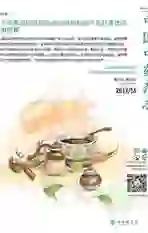中药制剂肝毒性的影响因素探析
2017-09-09刘莹汪刚仲青香吴豪宋捷封亮贾晓斌
刘莹 汪刚 仲青香 吴豪 宋捷 封亮 贾晓斌
[摘要]中药制剂作为中药发展及质量控制的重要方面,其安全性问题日益突出。肝脏作为人体最主要的药物代谢器官,中药制剂对其带来的药物损伤也首当其冲。笔者从中药制剂的原料药到成品加工等一系列环节出发,探究其与肝毒性之间的关系,剖析制剂存在肝毒性隐患的机制,为保证药物质量、临床合理用药以及开发出优质低毒的现代化中药制剂提供依据和指导。
[关键词]中药制剂; 肝毒性; 制剂工艺; 多维结构过程动态质控体系
Influence factors for hepatotoxic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s
LIU Ying1,2, WANG Gang1,2, ZHONG Qingxiang2,3, WU Hao1,2, SONG Jie2,3, FENG Liang2*, JIA Xiaobin2,3*
(1School of Pharmacy,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12,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New Drug Delivery Systems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8, China;
3College of Third Clinical Medical,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8, China)
[Abstract]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prepar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contr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security problem becomes more and more serious It is worthy to note that the liver, as the main drug metabolic organ, bears the brunt of the damage caused by TCM preparation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CM preparations and hepatotoxicity based on the processing chains from crude drugs to the end product Besides, the author hopes to clarify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hepatotoxicity of TCM preparations and provide basis and guidance for the quality control and rational clinical use of the preparations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CM preparations with high quality and low toxicity
[Key words]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 hepatotoxicity; preparation process; dynamic quality control system of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 process
中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治病防病史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近年来关于其毒性反应的报道也屡见不鲜,以何首乌为例,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关于何首乌导致肝损伤不良反应的报道[1],然而在2013年之前,我国含何首乌成分的中成药却在药物说明书上仍标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2]。可见中药制剂的肝毒性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未标毒,即无毒”的理念仍然存在。中药制剂以中药材为基础,从原药材的前处理到辅料、剂型、制备工艺、储存运输再到临床应用等多个环节均可导致肝毒性的发生,因而本文将从这些因素出发探讨产生肝毒性的机制。
1具有潜在肝毒性的单味中药以及复方制剂
中药作为中药制剂的原料从根本上影响其肝毒性的产生,其毒性的大小也影响制剂肝毒性的大小。我国对中药的研究是在传统中医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的,《神农本草经》里记载:“药有酸甘苦辛咸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3]。古代根据其毒性大小划分为上、中、下药,现代将毒性划分为无毒、小毒、有毒、大毒、剧毒。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凡药物云有毒及大毒,皆能变乱,与人有害,亦能杀人”[4]。强调了毒性药物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中药的不良反应涉及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造血系统、泌尿系统等多个系统,较常见的是肝毒性,牵涉单味药、中成药和中药复方制剂。近年文献提及的可致肝毒性的中药及其制剂的分类见表1。
某些传统认为安全无毒的中药在临床广泛使用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其肝毒性,如黄药子、何首乌、补骨脂、番泻叶、茯苓等[13]。临床常见导致肝毒性的中药,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认为有毒的中药,也包括传统认为无毒的中药,且以后者居多[9]。古代常凭经验界定中药的毒性,缺乏系統理论的证据证实,因此阐明毒性中药的作用机制对中药制剂的安全合理用药、减轻不良反应具有重要作用。endprint
2中药的毒性成分是制剂产生肝损伤的主要物质基础
肝脏是药物转化和代谢的主要场所,更是药物损伤的主要靶器官[14]。药物代谢大多都要经过肝脏进行氧化、还原、水解、结合等代谢过程,肝脏含体内最多的用来清除药物代谢产物的肝药酶,且多数药物都存在肝脏的首过效应,对其产生的损害不言而喻。药源性肝损害(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简称药肝,是指由于药物本身或其代谢产物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于肝脏或者由于机体特异质造成的对药物超敏感性或耐受性降低所引起的肝脏损伤[15]。临床表现从无症状的肝功能异常到急性和慢性肝炎,甚至肝衰竭、肝硬化、肝癌,程度不等[16]。由药物引起的肝损伤占美国和英国急性肝功能衰竭案例的1/2[17],超过80%FDA批准的处方药因其严重的肝毒性而出现黑框警告甚至撤市[18]。以往認为化学合成药是药物性肝损害的诱因,但据不完全资料分析,中药所致的肝损伤占临床药物性肝损伤的167%[19],在我国中药已成为药肝发病的首要原因。李海涛等[20]对医院40例中药致药源性肝损害的研究发现,中成药口服剂占40%,中药汤剂占30%,中药注射剂占20%,中草药外敷占10%。可见中药及其制剂引发的临床肝损害已不是新鲜话题,虽多为可逆性,但严重者甚至可引起死亡。
究其原因,从制剂的基础中药本身来看,中药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非常复杂,具有毒效的双重作用,物质基础是其发挥药效与产生毒性作用的依据。研究表明,引起肝毒性的中药成分主要包括生物碱类(吡咯里西啶生物碱、苦参碱)、苷类(强心苷、氰苷和皂苷)、毒蛋白类、萜类(挥发油、二萜和三萜)、蒽醌衍生物类、鞣质类、重金属类等[21]。宋秉智[22]对具有肝毒性的55种中药进行研究发现,含碱类成分的有16种,苷类的20种,萜类的8种,内酯类的3种,金属类的4种,蛋白类的3种,没有成分记载的10种。其中含有碱类、苷类成分药物肝毒性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成分类,可见中药的毒性成分是其产生肝损伤的主要物质基础。
3中药制剂肝毒性产生的机制
中药制剂产生肝毒性的机制主要包括2个方面,其中大多是由药物所含的毒性成分或毒性代谢物对肝脏的损害,其次机体的特异质反应亦能引起肝损伤。前者的肝毒性是可预见的,发病率高、与用药剂量、时间有关;后者没有显著的量效关系及可预见的生理机制,发生率低,仅在敏感个体中产生,小剂量也可使患者发生肝损害,潜伏期长。引起肝毒性可能的分子机制有:肝代谢酶代谢异常、脂质代谢异常、细胞内钙稳态失调、线粒体损伤、免疫反应等。
31药物对肝脏的直接损害机制药物在肝脏中的代谢经过Ⅰ相(氧化、还原、水解)和Ⅱ相(结合)反应过程,肝脏中催化药物代谢转化的酶主要分布在肝细胞微粒体,药物代谢酶(简称药酶)中最重要的是细胞色素P450酶(cytochrome P450,CYP),75%的药物可由它代谢。如含生物碱类中药千里光中含吡咯里西啶碱(PAs),PAs本身无毒或毒性较低,经CYP450激活后产生毒性代谢物吡咯,与DNA,RNA和大分子蛋白质等发生烷基化作用形成结合吡咯或与DNA交联,产生肝损害;还能与嘌呤和嘧啶碱基以及核苷形成加合物,或与细胞骨架蛋白actin加合,引起细胞凋亡,最终导致细胞损伤[7]。CYP酶对药物的代谢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对中药的影响表现为药酶诱导剂可使药物代谢加速,药效减弱;相反,药酶抑制剂可使药效增强,当中药与药酶抑制剂合用时,中药的毒性物质被吸收增多,肝毒性就增强。Shen等[23]研究雷公藤甲素对肝微粒体及肝细胞的毒性机制时发现,雷公藤甲素对CYP3A呈时间和剂量依赖性抑制,是CYP3A的弱抑制剂,造成了雷公藤在肝脏蓄积,增加了肝毒性。另外,CYP酶代谢还受年龄、性别、种族和个体差异、遗传多态性的影响等。
正常生理状态下,肝脏细胞比其他细胞具有更高的抗氧化剂水平,机体在生成自由基的同时活性氧清除系统也在消除自由基,维持体内自由基的相对平衡。肝脏细胞活性氧的增加及抗氧化水平的下降,引发氧化应激状态,导致细胞、器官功能异常。苍耳子的肝毒性与过氧化应激有关,当大量自由基产生后,打破了肝细胞内氧化与抗氧化平衡,抗氧剂水平的低下能够抑制谷胱甘肽还原酶系活性,形成过氧化脂质,从而损害肝细胞。同时脂质过氧化产物还可与线粒体蛋白、DNA相互作用,引起线粒体能量代谢障碍,导致肝损伤。肝细胞的受损会释放信号,启动免疫反应,激活非特异性免疫中的KC,NK,NKT细胞等,产生各种炎症因子如TNFα,IFNγ,加速肝损伤进程[24]。肝脏中谷胱甘肽(GSH)与药物产生的亲电子基、氧基等代谢产物发生作用,防止肝细胞发生损伤。但若服药过量,多余的毒性代谢产物氧自由基与人体内大分子物质共价结合造成脂质过氧化,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和Ca2+ATP酶,使Ca2+内流增多,破坏了钙稳态,导致肝细胞死亡。肝细胞线粒体正常状态下也能清除过多活性氧,保护肝脏,而细胞内大量涌入的钙离子转移到线粒体内导致线粒体脂质过氧化的产生,线粒体膜通透性转运孔异常开放(钙离子浓度过高所致),造成线粒体膜电位下降及线粒体膜完整性的破坏,释放促凋亡因子细胞色素c(Cytc)和凋亡诱导因子等,激活caspase级联放大反应,最终导致线粒体肿胀、破裂,肝细胞死亡。刘若囡等[25]研究发现中药黄药子破坏了体内氧化与抗氧化系统的平衡,使得氧自由基生成增多,Ca2+平衡的失调使细胞膜通透性升高,造成了线粒体膜电位下降,引起了线粒体功能障碍,电子传递链电子外漏率增加,细胞能量代谢障碍,启动线粒体依赖性细胞质凋亡通路,导致肝细胞凋亡。常见肝毒性中药及其毒性机制见表2。
32机体的特异质反应机制机体的特异质反应也是造成药物产生毒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包括代谢特异质肝损伤和免疫特异质肝损伤。代谢特异质肝损伤主要是CYP450的遗传多态性造成。遗传多态性是CYP450的一个重要特征,不同个体间肝细胞中CYP酶的量存在差异,对药物的代谢就不同,产生的毒性反应自然就不同。生首乌引起的肝损伤主要是轻中度的黄疸,并有家族同用均有黄疸发生的报道,说明病因可能与患者的遗传性肝脏代谢酶缺陷有关[5]。endprint
免疫特异质肝损伤又叫变态反应性肝损伤,机制主要有以下2条:药物直接与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形成药物MHC复合物获得抗原性,致敏T细胞产生T杀伤细胞和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ADCC)作用;中药及其体内代谢产物作为半抗原,与肝细胞内大分子物质结合成复合物,作为新的抗原刺激机体产生相应的抗体诱发免疫反应[34]。
33其他因素肝脏的病理状态也会影响到肝脏的代谢,如胆道梗阻、酒精病史、败血症、慢性病毒性肝炎等潜在并发症都会导致药肝的出现[35]。另外药肝还与患者本身的年龄、性别和个体差异等因素有关,如老年患者代谢减慢,肝功能较正常成年人低下,需特别注意用药的剂量和疗程,降低毒性反应。另外,也要注意合并、配伍用药等。
药肝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各种因素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中药化學成分复杂,物质基础尚不明确,探寻其肝毒性的机制更是难上加难,从动物实验到临床患者,从单味药到复方,运用各种“组学”技术寻找生物标志物,有望获得更为确切的发病机制。Huang ShanHan等[36]发现的定量构效关系模型对筛选中药活性物质中肝毒性成分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即使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中药制剂中往往含有一种或多种单味药,中药的毒性成分影响着制剂的肝毒性,运用各种方法减轻中药的毒性问题可以从源头上保证中药制剂的质量与安全。
4中药制剂肝毒性的影响因素
影响中药制剂肝毒性的因素除了中药所含的毒性成分外,药材的基原产地、种植条件、采收季节、制剂工艺、剂型与给药方式、炮制配伍、辅料、储存运输以及用药剂量、时间、个体差异等其他因素均能影响药效和产生肝毒性。
41药材基原与产地中药制剂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药材的质量,而药材的基原与产地是影响药材质量的关键因素。中药分布广泛,品种众多,多为植物药,其次是动物药、矿物药。同一品种不同产地的中药药效存在差异,《本草纲目》里记载有“凡诸草木昆虫,产之有地,失其地则性味少异”[37],《神农本草经》中也记载有“土地所处”[3],都用来说明药材产地影响质量,道地药材药效好。王秀坤[38]在考察不同产地千里光中PAs的含量及对小鼠的急性实验时发现,吡咯里西啶生物碱的含量河南>江苏>浙江>湖北>广西;小鼠致死率从高到低的顺序与该生物碱含量一致,说明不同产地的中药千里光发挥药效的成分也是其产生毒性的成分,产地不同影响着药效和毒性。再者,药材基原亦影响中药质量,2010年版《中国药典》收录的5种贝母类药材,基原共包括11种贝母属植物。中药入药品种混乱、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现象普遍。有调查表明,何首乌商品中有同科植物毛脉參和翼藝混做何首乌,黄药子和千金藤等明显具有肝毒性的中药也是何首乌常见的混用品[39]。又如菊科橐吾属多种植物的根或根茎(含有肝毒性吡咯里西啶生物碱)在西南、东北地区统称为“山紫苑”,常作为中药紫苑的代用品[40],由此造成的肝毒性毋庸置疑。再如广防己已在临床有肝、肾毒性的报道,若将其混作粉防己则会出现不可预知的肝毒性。可见保证中药材的基原与产地,避免误用是降低中药制剂肝毒性的第一步。
42种植条件与采收季节植物药类似于种庄稼,对土壤、气候、水分等种植条件和采收季节要求较高,影响药材的成分与含量。《本草纲目》[37]里“根叶花实,采之有时,失其时则气味不全”、“春采茵陈夏采蒿,知母黄芩全年刨,秋天上山挖桔梗,及时采收质量高”等,都说明了采收季节对保证药材质量的重要性。曹爱农[41]通过研究不同播种期对柴胡产量品质的影响,发现播种期对柴胡产量及有效成分含量影响差异显著,随播种期的推后柴胡产量先增后降,有效成分的含量呈增加趋势。植物不同药用部位有效成分或有毒成分的含量也不相同,如中药苍耳子在《南方主要有毒植物》里记载:“苍耳,有毒部,全株;以果实最毒;鲜叶比干叶毒,嫩叶比老叶毒”[42]。不同地理来源和不同药用部位的茯苓酸的含量具有显著性差异[43]。药材种植过程中应充分保证光照、水分、气候、土壤等种植条件。但随着我国农业的发展,有机磷农药和重金属残留成为制约中药种植的一大环境因素。导致环境及土壤污染的重金属主要包括汞、镉、铅、铬、砷等。中药中朱砂含汞,雄黄含砷,王大鹏等[44]通过对SD大鼠经口长期大量给予朱砂发现可引起大鼠肝脏汞蓄积,导致肝脏损伤。故降低土壤及环境中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和有机磷农药含量有利于减少药物的肝损害。做到“三分种,七分养”,避免农药、化肥的污染,严格参考中药材GAP标准进行种植栽培,保证中药材“安全、优质、稳定、可控”,有利于保证中药制剂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43制剂工艺中药的制剂工艺包括药材前处理、分离纯化、浓缩干燥等。据文献报道,艾叶挥发油的毒性与提取方法密切相关,用石油醚超声和微波提取法制备是没有毒性的,超临界CO2萃取和水蒸气蒸馏提取的挥发油则有一定的肝毒性作用,其中以水蒸气蒸馏法制备的挥发油肝毒性最大[45]。穿心莲注射液由于磺化作用,穿心莲内酯中的五元内酯环、双键、亚甲基以及羟基等的改变可不同程度地增减其作用强度和毒性,提示制剂的工艺可影响内酯的毒性[46]。采用恰当的制备工艺对降低制剂的毒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44剂型与给药方式剂型是药物应用于临床的形式,中药制剂是以中药材为原材料制成不同剂型供临床使用的,包括片剂、胶囊剂、注射剂等。药物肝毒性的大小与经过肝脏药物代谢的量及快慢有关。多数口服药物在胃黏膜上皮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之前在肠黏膜和肝脏被代谢,使进入体循环药量减少、药效降低的现象称为肝脏的首过效应。许多西药具有明显的首过效应,因此可以通过改变药物的剂型,使某些毒性成分避免肝脏的首过效应,从而避免肝脏中间代谢产物对肝脏的损伤,起到降低毒性的目的,如透皮贴剂、灌肠剂等。同一药物不同的剂型因在体内生物利用度不同,产生的药效与毒性反应也不同。动物实验中将具有肝毒性的栀子苷对大鼠分别进行灌胃、滴鼻、肌注,结果发现栀子苷不同给药途径在大鼠体内的生物利用度依次为肌注>滴鼻>灌胃,说明不同给药途径栀子苷的吸收率不同,毒性成分的吸收也不同,故引起肝脏毒性的程度就会有差别[47]。剂型与给药途径的不同会使药物毒性发生改变,影响着临床制剂的安全用药。endprint
45炮制与配伍炮制是用烘、炮、炒、洗、泡、漂、蒸、煮等方法加工中药,使药物纯净,增效减毒,便于制剂和贮藏。中药原料经过炮制才能制成药物供临床使用,炮制使中药制剂有别于其他天然制剂。明代医书《本草汇言》中记载何首乌“生用气寒、性敛、有毒;制熟气温,无毒”[48],可见生首乌有毒,制首乌由生首乌经炮制后毒性减小,制首乌醇冷浸液比生首乌醇冷浸液毒性小545倍以上,制首乌醇渗出液比生首乌醇渗出液毒性小627倍[49]。《本草便读》中“大抵生用则流利,制用则固补”[50],生、制首乌不仅毒性大小不同,治疗疾病的适用范围也不同。何首乌的炮制方法从简单的修制到黑豆等辅料蒸制、随后九蒸九曝制法,现代简化为黑豆汁蒸制[51]。古人云:“何首乌大能补益,全在蒸晒如法”、“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性味反失”,炮制方法不同、炮制太过或不及,造成肝损伤的程度也不同。王伽伯等[52]通过对大黄各炮制品高剂量组的对应分析图得知,炮制品的毒性低于生品,减毒作用强度与炮制程度相关。再如中药苍耳子,《本草纲目》记载其修治为“入药炒熟,捣去刺用,或酒拌蒸过用”[37]。《中国药典》2015年版规定:“取净苍耳子,照清炒法炒至黄褐色,去刺,筛净”,毒蛋白经水浸泡或加热可以降低其含量,从而去毒。临床上常因炒制时间不足、受热不均导致炮制不完全,引起中毒[53]。
配伍是中医用药的又一特色,根据传统中药配伍理论,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将药物以复方的形式入药是增强药物疗效,缓和毒性的重要途径。唐利宇等[54]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分析黄芪配伍雷公藤前后毒性成分雷公藤内酯酮含量的变化,发现配伍后雷公藤内酯酮的平均含量明显降低,说明黄芪配伍雷公藤后降低了毒性成分的含量,从而降低了毒性。炮制与配伍减毒是中药常用的2种减毒途径,其可能的机制见表3,4。
46辅料辅料是制剂存在的基础,包括填充剂、稀释剂、增溶剂、助溶剂、防腐剂、矫味剂、着色剂等,常见的有聚山梨酯80、乙醇、丙二醇、维生素C等,长期以来被认为无毒、无功效,有利于制剂成型、提高活性成分的稳定性和生物利用度、降低不良反应。但目前许多中药注射剂却因辅料引起了严重不良反应,如银杏达莫注射液、醒脑静注射液、参麦注射液等都含有聚山梨酯80,聚山梨酯80可引起肝毒性[62]。可见药用辅料与制剂的肝毒性息息相关,应该加强对药用辅料的管理,不断开发真正“惰性”的辅料,保证中药制剂的安全性。
47贮存运输目前中药制剂的质量控制多集中在药材原料和终产品的质量好坏上,相比之下,储运过程是质量控制中最容易忽视的环节。由于制剂产品从原料、前处理、生产工艺、剂型设计、贮藏运输到临床使用是个环环相扣的过程,任何一环出现问题最终都会影响终产品的质量,影响中药制剂的安全性。因此中药材须严格控制贮藏条件,注意光照、温度、湿度等,防止虫蛀、霉变、泛油、变色等变质现象,以防疗效降低,产生毒副作用。在贮藏中中药的黄曲霉素污染比较常见,日本学者对44种中药粉末调查发现,霉菌污染率高达90%,平均霉菌数547个/g。污染频度依次为青霉菌、黑曲霉菌、灰绿曲霉菌和黄曲霉菌。黄曲霉素是强致肝癌物,且霉菌污染具有普遍性不受品种限制[32],药物污染后会增大肝毒性的风险,更应该加强监测,保证贮存条件合格。另外,运输中应该注意包装的密封性,避免包装破损、污染、漏液等一切导致药物毒性增加的因素。
48其他因素其他影响制剂肝毒性的因素亦不可小觑。首先,从病人角度,应该加强用药知识的学习,严格遵从医嘱,避免因不合理用药导致肝毒性的发生。其次,中、西医医院的医生应各司其职,切忌西医师开中药方,而目前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再者,要根据中医药理论进行正确的炮制与配伍,注重君臣佐使,辨证用药,“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茸、枸杞子皆是砒霜”。辩证施治,因人而异,随症加减,因方而别,最大程度减少制剂产生的不良反应,降低肝毒性的风险。
5展望
中药作为天然药物被认为安全、无毒,在全世界广泛应用[63],其肝毒性已成为中医药发展的制约因素。要确保中药制剂的高质量与稳定可控,应认清中药材来源,尽量选用道地药材,在适合药材生长的环境中规范种植、采收等,运用新工艺、新辅料、新技术制成适宜的剂型,控制重金属元素及有害残留物等的含量在合理的范围,保证储运安全,进行稳定性试验研究,避免因储运条件不合格导致药品变质影响安全性与药效。另外,不良反应发生率与治疗过程、用药方式、剂型和用药剂量等密切相关[64],临床用药应减少或避免使用含肝毒性成分的中药,注意用药方式和剂量,加强对毒性药材如雷公藤等与中药材安全性相关成分的质量控制,警惕因性别、年龄、个体差異等造成的药物代谢差异。正确处理药物性肝损伤,一旦发生及时停药并采用恰当方式清除毒物,合并药物治疗,严重者给予人工肝移植等。最后,若天然药物的机制能够很好的被解释,更多的中药处方及制剂将会出现并被应用[65],再研究出一套不同于化学药物的符合中药制剂特点的质量评价模式来保证中药制剂的安全和有效,将有利于中药制剂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孙向红,纪恒胜,韩建香,等从何首乌致肝损伤看中药不良反应发生特点及预防措施[J]中国医药指南,2010, 8(34):21
[2]本刊综合被忽视的中药肝损伤[J]发明与创新·大科技,2014(10):15
[3]神农本草经[M] 合肥:黄山书社,2013
[4]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5]王学勤,李丰林,张维国中药药物性肝损害研究进展[J]亚太传统医药, 2015, 11(5):35
[6]焦云涛,高菁,任彬,等中草药肝毒性、肾毒性及对策[J]世界中医药, 2014, 9(1):124
[7]段永红基于文献的致肝损害中药品种分析[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4(9):950endprint
[8]中国药典一部[S]2010
[9]李秀玉,李超群,张志敏,等中药相关性肝损害研究——从理论到临床[J]转化医学杂志, 2015, 4(4):244
[10]王秀娟,许利平,王敏常用中药及复方制剂的肝毒性[J]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2007, 28(2):220
[11]周艳莉,杨毅恒中成药致肝损害401例分析[J]中国药物应用与监测, 2007, 4(4):6
[12]王京丽,周超凡中草药及其制剂对肝损伤的研究概述[J]中国中药杂志, 2011, 36(23):3371
[13]龚小慧,陈良良中草药所致药物性肝损害的原因及对策[J]湖北中医杂志, 2011, 33(5):70
[14]Hornby R J, Starkey L P, Dear J, et al MicroRNAs as potential circulating biomarkers of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key current and future issues for translation to humans[J] Expert Rev Clin Pharmacol, 2014, 7(3):349
[15]田梦曦,刘文兰肝损伤中药治疗研究进展[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17(4):125
[16]任美欣,孟庆华药物性肝损伤[J]临床荟萃, 2016, 31(7):713
[17]Wang Meng, Liu ChenXiang, Dong RanRan,et alSafety evalu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njections with a cell imagingbased multiparametric assay revealed a critical involvement of mitochondrial function in hepatotoxicity[J]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2015, 2015:1
[18]Chen M, Vijay V, Qiang S,et al FDAapproved drug labeling for the study of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J] Drug Discov Today, 2011, 16(15/16):697
[19]刘红杰,李天昊,詹莎,等四性、五味和归经对中药肝毒性预测价值的研究[J]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2015, 26(5):708
[20]李海涛,蔺爽,张景洲40例中药致药源性肝损害[J]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2016, 16(6):830
[21]黄道林,向娟,刘晓东,等药源性肝损伤中药的研究进展[J]海峡药学, 2012, 24(10):13
[22]宋秉智,施怀生肝毒性中药及其与药性和有效成分的关系——对55种中药肝毒性文献资料的分析报告[J]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1, 2(1):18
[23]Shen G, Zhuang X, Xiao W, et al Role of CYP3A in regulating hepatic clearance and hepatotoxicity of triptolide in rat liver microsomes and sandwichcultured hepatocytes[J] Food Chem Toxicol, 2014, 71(8):90
[24]饶跃峰,郑飞跃,张幸国药物性肝损伤的免疫学机制[J]中国药学杂志, 2008, 43(16):1207
[25]刘若囡,徐立,时乐,等常用皂苷类中药致肝损伤的毒理学研究进展[J]中南药学,2010,8(12):916
[26]陈宇征,吕文良中药导致药物性肝损伤的机制研究进展[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5, 21(11):1476
[27]谢玉兰,李秀惠,勾春燕,等中药致肝损害简析[J]中医杂志, 2016, 57(14):1258
[28]陈晨中药肝毒性成分研究进展[C]南京:江苏省药理学会学术研讨会,2012
[29]汪洋中药苍耳子的毒性物质基础及中毒机制研究[D]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2010
[30]昊霞,王忠震,林兵,等雷公藤毒性作用機制研究进展[J]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015, 35(16):1519
[31]方文君,谭兴起,胡永胜,等中药何首乌肝毒性物质基础及其毒性机制研究[J] 海峡药学, 2015, 27(6):41
[32]赵军宁,王晓东中药及植物药的肝靶毒性与安全性评价[C]北京:第二届药品技术审评研讨会,2003
[33]李丰衣,李筠,肖小河中药药物性肝损害的研究现状[J]中华中医药杂志, 2009, 24(3):265
[34]陈鹰翔,常铠麟,赵思伟,等中药导致药物性肝损伤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13(2):31
[35]Teo D C H, Ng P S L, Tan S H, et al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associated with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a review of adverse event reports in an Asian community from 2009 to 2014[J] BMC Complement Altern Med, 2016, 16(1):1endprint
[36]Huang S H, Tung C W, Fülp F, et al Developing a QSAR model for hepatotoxicity screening of the active compound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J] Food Chem Toxicol, 2015, 78:71
[37]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
[38]王秀坤千里光肝脏毒性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 2008
[39]马致洁何首乌肝毒性客观性、临床标志物及损伤机制的初步研究[D] 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 2013
[40]李大寿,艾远征中药致药物性肝损伤的原因与预防措施[J]中国实用医药, 2011, 6(28):251
[41]曹爱农影响柴胡质量与产量的关键因素研究[D] 兰州:甘肃农业大学, 2016
[42]广东省农林水科技服务站 南方主要有毒植物[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70
[43]Li Y, Zhang J, Jin H, et al Ultraviolet spectroscopy combined with ultrafast liquid chromatography an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for quality assessment of wild Wolfiporia extensa, from different geographical origins[J] Spectrochim Acta A, 2016, 165:61
[44]王大鹏,王莹,高显会,等朱砂亚慢性染毒致大鼠肝毒性效应[J]中国公共卫生, 2014, 30(6):743
[45]梅全喜,高玉桥,董鹏鹏艾叶的毒性探讨及其研究进展[J]中国药房, 2016, 27(16):2289
[46]郭志军中药毒性的研究进展[J]中国药房, 2011,22(15):1428
[47]方文娟,苗琦,罗光明栀子毒性研究进展[J]江西中医药, 2015,46(390):70
[48]倪朱谟本草汇言[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49]鄢良春,趙军宁,邱雄何首乌安全性问题研究进展[J]中药药理与临床, 2009, 25(3):77
[50]张秉成本草便读[M]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0
[51]崔鹤蓉,柏兆方,宋海波,等从古今炮制方法演变探讨何首乌毒性的潜在影响因素[J]中国中药杂志, 2016, 41(2):333
[52]王伽伯,马永刚,金城,等对应分析在大黄炮制减毒"量毒"规律研究中的应用[J]中国中药杂志, 2009, 34(19):2498
[53]张婷婷,鄢良春,赵军宁,等苍耳子“毒性”及现代毒理学研究进展[J]医学综述, 2010, 16(18):2814
[54]唐利宇,孟楣,张贺,等基于雷公藤配伍前后雷公藤内酯酮含量变化探讨其减毒机制[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2016, 23(8):87
[55]涂灿,蒋冰倩,赵艳玲,等何首乌炮制前后对大鼠肝脏的损伤比较及敏感指标筛选[J]中国中药杂志, 2015, 40(4):654
[56]曹玲娟,颜苗,李焕德,等雷公藤致肝损伤及与甘草配伍减毒机制的研究进展[J]中国中药杂志, 2015, 40(13):2537
[57]安靖,王耀登,盛昌翠,等苍耳子炮制前后羧基苍术苷和苍术苷的含量比较[J]药物分析杂志, 2013, 33(11):1910
[58]刘树民,姚珠星,张丽霞黄芪对苍耳子肝毒性影响的实验研究[J]药物不良反应杂志, 2007, 9(1):17
[59]陈莹蓉,杨水新中药肝毒性及配伍减毒研究进展[J]浙江中医杂志, 2012, 47(7):536
[60]李振华,鞠建明,华俊磊,等中药川楝子研究进展[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5, 21(1):219
[61]黄丽,常香云浅析大黄炮制前后的药理变化[J]内蒙古中医药, 2012, 31(16):46
[62]高英杰中药注射剂常用辅料的作用与安全性分析[J]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 2014, 14(7):640
[63]Teschke R, Zhang L, Long H, et al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erbal hepatotoxicity: a tabular compilation of reported cases[J] Ann Hepatol, 2015, 14(1):7
[64]王文萍,喻明,王丽,等中药新药临床试验不良反应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学术探讨[J] 中国中药杂志, 2015, 40(2):346
[65]Tsai C C, Kao C T, Hsu C T, et al Evaluation of four prescrip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yhMoYiin, GuizhiFulingWan,ShiehQingWan and SyhNihSann on experimental acute liver damage in rats[J] J Ethnopharmacol, 1997, 55(3):213
[责任编辑张宁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