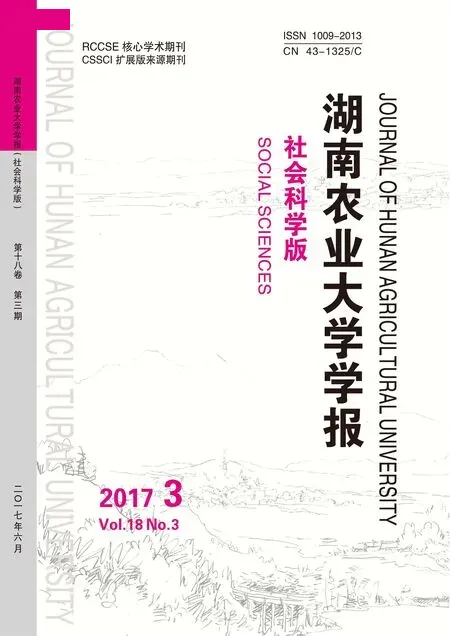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影响因素研究
2017-09-07肖云李波
肖云,李波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影响因素研究
肖云,李波
(重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在对重庆480个新生代农民工调研的基础上,基于社会-经济层面、社区-文化层面、结构-制度层面、感知-心理层面四个维度,构建并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解释变量中,影响力由大到小依次是交往程度、政策了解程度、政策评价、管理与服务参与情况、收入水平、挣钱后的打算、被排斥感、转移住处次数,其中,转移住处次数和被排斥感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余变量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为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区,应为其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搭建社区交往平台并促进其参与社区管理,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同时关爱和尊重新生代农民工以消除其被排斥感。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影响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①规模不断壮大,并逐渐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5年底,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7 747万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占六成以上[1]。与老一代农民工经济理性的务工动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偏向发展理性。大量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强烈。城市社区是农民工市民化的转换场域和日常生活依托的直接平台,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市,离不开城市社区这一载体[2],新生代农民工只有融入城市社区才真正融入城市。目前城市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还没有完全覆盖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还没有得到有效保障,社会生活还没有得到必要理解和尊重[3]。要实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的促进1亿农民工进城落户,需要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了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内涵,陈成文等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社会融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4]。关信平等提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主要包括就业市场融入、社会保障体制融入和城市社区融入等方面。而农民工各方面的社会融入,最终要通过日常生活的社区场域②来完成和实现[5]。
关于移民融入类型化研究,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是Gordon的“结构性、文化性”二维度模型,J.Junger-Tas的“结构性、社会-文化性、政治-合法性”三维度模型,以及H.Entzinger等提出的“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的四维度模型[6]。他们对移民融入的归因解释有三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人力资本归因理论主要强调移民个体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因素,如文化教育水平、劳动技能、语言技能、工作经验等对于移民融入的影响[7]。社会资本归因理论认为移民在流入地所具有的社会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及社会资源等对于其社会融入具有关键性作用[8]。制度归因理论则强调社会福利与保障、社会救助、子女教育、就业、住房等宏观或微观政策制度对移民融入的作用[9]。
在借鉴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主要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社会排斥等视角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最具代表性的三维视角是指经济、社会和心理文化融入三个维度[10-11]。李培林等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身份认同融入维度,并认为这四个维度之间存在着递进关系[12]。张传惠提出了社会制度、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三维分析框架[13]。王佃利和张军等借鉴H Entzinger“四维度”模型,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划分为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融入四个维度[14-15]。何绍辉则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与返乡适应层面面临的“双重边缘化”的境地,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融入、社区融入、心理融入与子女融入的城市融入新趋势[16]。
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大多数研究是从社会融入的宏观视角入手,而少有基于社区场域这一微观角度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问题。第二,关于城乡制度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较丰富,而对促进其融入城市的政策影响则关注得比较少。第三,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大多数也都是利用二元回归分析方法,不能从多角度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的影响因素。为此,笔者拟借鉴H.Entzinger的“四维度”理论模型以及张军、王佃利等的研究框架,从城市社区场域的微观视角,引入社区-文化因素解释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变量和模型的选取
1.变量选取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制度因素、社会支持网络和农民工主观心理因素等。经济因素主要体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城市融入程度也不断提升[17]。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收入越高,就越能够有充足的物质基础来改善自身生活条件并发展其在城市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缩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18]。在制度方面,由户籍制度衍生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管理制度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19]。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平等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以及建立在户籍基础上的以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20-21],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市民认同感,更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的步伐[22]。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主要取决于遇到困难能获得帮助的朋友人数,能够求助的朋友人数越多,他们的城市融入程度也就越高[17]。而相关研究发现,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意愿更为强烈,但他们与本地居民之间并未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23]。主观心理因素主要体现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自我认知。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越强,其市民化程度就越高[24]。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在行为习惯、文化素质等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并积极向城市居民靠拢,但是他们在城市中依然没有归属感,遭受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排斥[25]。
结合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的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关理论,将解释变量设置为四个维度共18个变量,社会-经济维度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形式、就业方式、收入水平、挣钱后的打算;社区-文化维度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的居住年限、转移住处次数、与社区居民的交往程度、交往意愿、对社区活动的参与意愿;结构-制度维度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民工融城政策的了解程度和评价状况、社区管理服务参与情况、社区服务宣传情况;感知-心理维度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的受尊重感、被排斥感、被关爱感、公平感和归属感,受尊重感指是否感受到社区居民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尊重,被排斥感指在城市务工是否有被排斥的感觉,被关爱感指是否感受到过社区工作人员的关心,公平感指是否感受到社区工作人员的平等相待,归属感指是否赞同“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一说法。以上变量选取是基于研究的便捷性,并不能包括四个维度的所有内涵。因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区融入程度的自评,为分类有序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4个特征变量。具体变量及赋值详见表1。

表1 变量的含义与赋值

表1(续)
2.模型选取
利用SPSS21.0统计软件,通过构建有序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相比其他方法,有序logistic回归充分考虑了结果的多样性和有序性,有效避免了将变量的多分类结果简单合并成两类所造成的数据失真的问题。
根据Mc Cullagh提出的方法,有序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表达式为:
η[π(≤)]=
=1,2,…,-1 (1)
由此形成的链接函数是累积概率的转换形式,其中累加Logit模型的链接函数表达式为:
ln= ln
= αj-(lil+…+kik)=1,2,…,-1 (2)
该模型实际也等价于:
π(≤j)=
=1,2,…,-1 (3)
其中,(=1,2,…,)表示分数组(自变量向量的行数);(=1,2,…,)表示因变量的分类数;(=1,2,…,)表示自变量的个数;αj为常数项(=1,2,…,-1);k为回归系数(若β>0,表明随着值的增加,更可能落在有序分类值更大的一端;β<0时,表明随着值增加,更可能落在有序分类值更小的一端);exp(β)为发生比率,表示解释变量增加一个单位给原来的发生比率带来的变化;σi为尺度参数(默认值为1);πij(≤)=π+…+π为因变量≤的累积概率;η[π(≤)]为关于累积概率π(≤)的链接函数。
三、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重庆城乡社区服务发展中的差异与社区服务体系的构建”课题组于2014年2月在重庆市所做的调查。重庆市于2010年7月发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在全国率先开展城乡户籍制度改革,赋予有条件的农民工城镇居民身份。截至2013年4月底,全市农民工已累计转户367万人[26]。《意见》的出台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全国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大背景下,重庆市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政策借鉴意义。此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对重庆市主城九区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入户访问,共计发放问卷1 600份,在剔除数据严重空缺和前后测试矛盾的样本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 413份,有效回收率为88.3%。本文抽取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问卷480份。其样本特征见表2。
四、实证研究及结果分析
首先将控制变量引入回归模型,得到基准模型1;再在模型1的基础上依次引入社会-经济维度、社区-文化维度、结构-制度维度的解释变量,分别得到嵌套模型2、3、4;最后引入感知-心理维度的解释变量得到最终的完全模型5。从模型1到模型5,Pseudo R2呈递增趋势,说明模型的解释力逐步提高。具体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2 样本特征

表3 新生代农民城市社区融入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表3(续)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表示参照组。
从完全模型来看,在考虑所有变量之后,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程度影响显著的因素有: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水平、挣钱后的打算、转移住处次数、与社区居民交往程度、政策了解程度、政策评价、社区管理与服务参与情况、被排斥感;其余预测变量在完全模型中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1.社会-经济维度的变量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对其融入城市社区程度的影响显著。从完全模型来看,与参照组(4 501元及以上)相比,月收入1 250元及以下组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程度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该组更倾向于选择“融入程度很低”,只有参照组的44.1%(exp(-0.819) =0.441);其他组虽有差异但是在完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与月收入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月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③的城市社区融入程度更低;月收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程度并没有显著性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挣钱之后的打算对其融入城市社区程度的影响显著。从完全模型来看,与参照组(在城市定居)相比,打算挣钱后回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程度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其更倾向于选择“融入程度很低”,只有参照组的50.2%(exp(-0.689)=0.502)。在表示喜欢目前居住社区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打算定居城市的(43.1%)比挣钱后回农村的(35.2%)高8个百分点。这表明打算挣钱后回农村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是将暂住的社区作为一个过渡的临时居所,难以形成对社区的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方式和就业方式在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两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影响不显著。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居住方式为自己租房(48.7%)和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41.4%),这两种居住方式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易产生“内卷化”趋向,难以判断自身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城市社区。而灵活就业(54.9%)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就业方式,缺乏稳定的保障和持续的收入来源,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社区的信心不足,融入程度认知模糊。
2.社区-文化维度的变量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务工转移住处的次数对其社区融入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转移住处次数在完全模型中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每转移一次住处,其社区融入程度将降低8个百分点(exp(-0.078)=0.92)。尽管新生代农民工转移住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变动,但这也反映了他们住所不够稳定会影响其社区融入。新生代农民工转移住处的次数越多,就越难以和社区居民进行持续交往互动和深入了解,使得自身始终游离于社区边缘,社区过客身份大于社区主体身份,难以较好地融入城市社区。
新生代农民工与社区居民的日常交往程度对其融入社区程度的影响显著。与参照组(交往程度很高)相比,交往程度很低和交往程度一般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程度在完全模型中分别通过了1%和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均为负,表明这两组更倾向于选择“融入程度很低”,分别只有参照组的21.2%(exp(-1.551)=0.212)和46.9%(exp -0.758)=0.469)。调查显示,52.9%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在城市务工期间与居住地社区居民之间的交往很少;当遇到困难时,85.3%的受访者都表示更愿意向亲戚朋友寻求帮助,其次是邻居(19.4%),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场域的交往具有内倾特征。与社区居民日常交往的匮乏导致彼此之间的陌生感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入基础的缺失,阻碍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区。
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的居住年限、与社区居民的交往意愿和活动参与意愿在完全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三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影响不显著。调查显示在现在小区居住不到3年的新生代农民工达79.8%,居住年限较短使得其缺乏与社区居民的持续交流,同时也表明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不稳定性,因此对自身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城市社区的认知比较模糊。而虽然有61%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愿意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但是由于其业余时间较少,加之因为户籍制度原因被排斥在社区管理之外,因此活动的实际参与度较低,活动参与意愿并未对其融入城市社区的影响产生显著作用。此外,交往意愿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影响在引入感知-心理维度变量后变得不显著,表明交往意愿的影响主要通过其心理维度变量表现出来。
3.结构-制度维度的变量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对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融入城市社区程度的影响显著。在完全模型中,与了解政策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不了解政策的社区融入程度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该组更倾向选择“融入程度很低”,是参照组的35.1%(exp(-1.046) =0.351)。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对国家政策越了解,自身掌握的制度信息就越多,从而能够做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决策和规划。而调查显示,有61.9%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了解政府有哪些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这一方面反映了社区对农民工宣传政策的效果不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的漠视态度。
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评价的情况对其融入城市社区程度的影响显著。与参照组(对政策评价很好)相比,对政策评价不好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程度在完全模型中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其更倾向于选择“融入程度很低”,是参照组的36.8%(exp(-0.999)=0.368);而对政策评价较好的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具有显著性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的评价高,表明其能够获得政策的帮助较大。而调查数据显示,对政策评价很好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5.7%,这反映了他们对于政府近年来针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政策的认同度低。除了他们不了解政策之外,可能的原因还在于政府政策在这一群体上的社会效应较低。
有无参与过社区管理或服务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程度的影响显著。与参照组(参与过社区管理或服务)相比,没有参与过社区管理或服务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入程度在完全模型中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该组更倾向于选择“融入程度很低”,是参照组的42.8%(exp(-0.848)=0.428)。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各项管理或服务,不仅意味着其自身心理形成了对社区的认同,也意味着主体成员的身份得到了社区的认同。然而高达86.6%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没有参与过社区管理或服务;在少数表示参与过的受访者中,参与较多的是社区服务(48.6%),而参与社区管理,如参加会议和参与社区选举分别只有10.8%和13.5%。可见,对最能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社区主体身份的社区管理活动,他们的参与度很低。
社区服务宣传情况在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该变量不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显著因素。调查显示,76.4%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社区工作人员未向自己宣传过社区的相关公共服务,表明城市社区管理的二元化状态仍然存在,新生代农民工未能及时获得相关的公共服务信息,使得新生代农民工难以明确自身融入社区的程度。
4.感知-心理维度的变量影响
在感知-心理维度的解释变量中,只有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的被排斥感对其融入程度的影响在完全模型中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与参照组(有被排斥感)相比,没有感知到排斥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融入程度较高”,是参照组的1.605倍(exp(0.473)=1.605)。由于生活惯习、家庭背景、成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少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社区,但是仍旧难以产生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感,难以与现代城市社区文化相融合[27]。调查显示,在表示没有感知到被排斥的新生代农民工当中,明确表示不喜欢目前居住社区的有8.5%,而在表示感知到被排斥的受访新生代农民工当中,这一比例有33.5%,比前者高出2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社区中感知到的排斥越大,自身对于社区的情感体验就越差,从而严重影响其心理上融入社区。
新生代农民工的受尊重感、被关爱感、公平感和归属感在完全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层次还较低,对他们而言只要能够有较好的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即可,与是否被尊重、是否被关爱、是否被公平对待、是否有归属感相比,他们更在乎自身是否被当作外来人员而受排斥,因此这些心理维度的变量并不是影响其融入城市社区的显著因素。
另外,在控制变量个体特征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对其融入城市社区程度的影响显著。与“本科及以上”参照组相比,受教育程度为大专的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程度在完全模型中通过了10%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表明该组更倾向于选择“融入程度很低”,融入程度只有本科及以上组的35.1%(exp(-1.048)=0.351)。而小学及以下组和初中组仅在模型1和模型2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高中组则不具有显著性。可能的原因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专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在城市生活具有较高的心理预期,期望与现实落差较大,造成其社区融入程度比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更低。而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预期相对较低,期望与现实的落差较小,因此社区融入程度与参照组相比没有明显差异。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程度的影响显著,未婚者比已婚者融入程度更高。未婚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程度的影响在完全模型中通过了5%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表明未婚者更倾向于选择“融入程度较高”,是已婚者的1.896倍(exp(0.640)=1.896)。相比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已婚者在社区场域内交往的同质化和内卷化倾向更强,日常生活以家庭为中心,社区交往半径较短,造成社区融入程度更低。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前述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程度的均值是1.92的情况看,大多数人认为自己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城市社区;数据显示仍有23.8%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融入程度很低,表示自己融入程度较高的仅有14.5%,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整体融入程度不高,这与现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从四个维度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的因素,结论如下:
第一,从社会-经济维度来看,经济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一般情况下月收入较高的经济来源较稳定,就业和居住也相对稳定,从而更容易融入城市社区,留城意愿更强烈。第二,从社区-文化维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居住地转移的次数越少,即居住地越稳定、与社区居民的交往程度越高,其城市社区融入程度就越高。双方交往程度越高,相互影响越深,新生代农民工同质内卷程度就会降低,主观上更能够将自己看成社区居民而不是外来农民。这样他们对城市社区的认同度和融入程度也随之提高。第三,从结构-制度维度来看,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有助于其融入城市社区。新生代农民工了解相关政策并获得政策帮助对其融入城市社区有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越了解相关政策、政策评价越高,越容易主动寻求政策的帮助,说明畅通政策传递途径十分重要。第四,从感知-心理维度来看,只有消除社会排斥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从内心感到已经融入到城市社区。在被排斥感、受尊重感、被关爱感、公平感和归属感等心理感受中,被排斥感对其融入城市社区的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而其他几种心理感受的影响则不显著。说明被排斥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刺激特别大,只要他们在社区感受到排斥,心理上就认为没有融入到城市社区。
此外,根据发生比率划分解释变量的不同影响程度,在完全模型中通过显著性检验的8个解释变量的影响力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交往程度、政策了解程度、政策评价、管理与服务参与情况、收入水平、挣钱后的打算、被排斥感、转移次数。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情况看,交往程度是他们最直接切身的感受;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和良好的评价是他们融入城市社区最有利的条件;参与社区管理是他们作为城市社区主体最直接的体现;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他们稳定居住和融入城市社区最重要的基础;挣钱后留城的打算是他们城乡之间最终的决策;消除排斥感是城市社区对他们最好的回报;减少转移住处的次数是促使他们融入社区有效条件。
根据上述结论可以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促成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稳定为其融入城市社区奠定坚实的基础。政府需要为初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营造良好的城市就业环境,使他们有稳定的收入,才能实现入城——留城——融城。应以社区为依托,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网络,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其人力资本存量,弥补其因受教育程度不高而造成的缺陷。同时通过财政拨款或社会募捐的方式,设立农民工创业基金,鼓励有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创业。通过多种途径促使他们增加收入。
第二,社区应为入城农民工搭建交往平台并促成其参与社区管理。社区作为责任主体,应积极搭建交往平台,通过定期组织开展农民工与社区居民都喜闻乐见的形式多样的活动,增加双方的交往与互动,避免其同质内卷。同时社区应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保障符合条件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选举权;还要按照社区农民工的比例推选社区居民会议代表,使他们取得社区主体资格参与社区管理,表达自身诉求。
第三,畅通宣传渠道、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的满意度。街道和社区要加大对目前和农民工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通过入户走访、发放宣传手册、张贴公告等方式对政策中的重要信息进行解读,或是举办社区知识竞赛,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的了解。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要有主动获取政策信息的意识,认识到掌握与己相关的政策信息的重要性,主动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社区公开栏等渠道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以获得政策的帮助。
第四,城市社会应关爱和尊重新生代农民工以消除其排斥感。首先,政府应该改革过去由户籍制度衍生的各种二元社会管理制度,在管理上不以户籍和非户籍人口相区分,平等对待社区内非户籍居民,尤其是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同等的帮助,消除政策和制度性排斥,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其次,社区工作者要主动关心社区内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同时通过“邻里互助”活动促进社区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融合,消除社区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排斥。
注释:
①2010年国务院在颁布的《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第一次从政策层面认可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随后全国总工会在《关于新生代农民问题的研究报告》中将其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
②布迪厄所提出的“场域、价值观念和文化资本”分析框架认为,社区场域首先是由共同的组织制度、价值观念和场域意识所构成的生活共同体;场域中的社区成员是具有精神属性和能动意识的人,他们在共同的社区空间中必然会形成属于“我群”的惯习,表现为社会经历中稳定的心理和行为倾向;场域中社区成员的文化资本主要指“非正式的习惯态度、交往技巧、语言风格和生活方式等”。
③据重庆市人社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重庆市2014年最低工资标准为1250元/月。
[1]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16-02/ 9/content_5047274.htm.2016-02-29.
[2] 柯元,柯华. 基于社区融入视角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J]. 农村经济,2014(8):105-109.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门户网站. 民政部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EB-OL]. http://www.mca.gov.cn/ rticle/zwgk/fvfg/jczqhsqjs/201201/20120100249568.shtml. 2012-01-04.
[4] 陈成文,孙嘉悦. 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6):66-71.
[5] 关信平,刘建娥. 我国农民工社区融入的问题与政策研究[J]. 人口与经济,2009(3):1-7.
[6] 梁波,王海英. 国外移民社会融入研究综述[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0(2):18-27.
[7] Robert Wuthnow, Conrad Hackett.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practitioners of non-western relig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J].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2003,(12):651-667.
[8] Alejandro Portes, Julia Sensenbrener.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3,(5): 1320-1350.
[9] Michael EFix, Zimmermann Wendy, Jeffrey SPassel. The intergration of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les[DB-OL].http://www.urban.org/publications/410227.html,2001-01-01.
[10] 张祝平.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认同与社会融入:浙江两市调查[J]. 重庆社会科学,2011(2):59-65.
[11] 悦中山,李树茁,费尔德曼. 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建构与实证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2012(1):1-11.
[12] 李培林,田丰.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 社会,2012(5):1-24.
[13] 张传惠.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调查研究[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3(6):988-993.
[14] 王佃利,刘保军.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框架建构与调研分析[J]. 中国行政管理,2011(2):111-115.
[15] 张军,王邦虎.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化资本支持[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3(2):43-48。.
[16] 何绍辉. 双重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调查与思考[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5):64-69.
[17] 王刚,陆迁. 社会资本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影响因素分析[J]. 广东农业科学,2013(24):185- 189.
[18] 肖云,邓睿.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主观判断的影响因素[J]. 城市问题,2015(4):91-99.
[19] 李强,龙文进. 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2009(2):46-54.
[20] 邱建均.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因素探析[J]. 群文天地,2012(11):281.
[21] 宁昊宇. 和谐社会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2(1):31-32.
[22] 邱爱芳.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因素与对策分析[J].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3):39-42.
[23] 张蕾,潘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构成及作用分析——以杭州为例[J]. 经济学导刊,2011(34):127-131.
[24] 张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2011(6):100-109.
[25] 刘玉侠,尚晓霞.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社会认同考量[J]. 浙江社会科学,2012(6):72-82.
[26]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大力实施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J]. 中国经贸导刊,2013(18):15-17.
[27] 李贵成. 社会排斥视域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J]. 理论探讨,2013(2):155-158.
责任编辑:曾凡盛
Study 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rban communities’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XIAO Yun,LI Bo
(Marx School/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480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ongqing, based on the four dimensions which contain the social-economic level, community-cultural level, structure-system level and perceived-psychological level, we construct and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ion into the city communiti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turn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having an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to the city communities from large to small is the contact degree with community residents, the extent of understanding the policies and evaluation,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munity management and service, the income level, the intend after earning money, sense of exclusion and transfer times. Among these factors, sense of exclusion and transfer times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and all the remaining variabl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To make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communities easier, we should create a good employment environment for them, build communication platform and promot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management, intensify policy propaganda, care and respec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sense of exclusion.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urban communities’ integr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10.13331/j.cnki.jhau(ss).2017.03.010
C912.82
A
1009–2013(2017)03–0056–09
2017-05-17
重庆大学资助项目(CQUMXZX201508)
肖云(1955—),女,重庆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