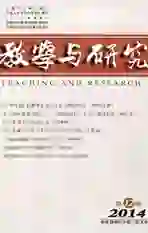民国初年开明专制论评析
2017-09-01邹小站
邹小站
[关键词]开明专制论;暴民专制;暴力革命;训政论
[摘要]对于开明专制论,学界一般比较注意其在清末提出时的基本主张以及思想界对它的批评,而较少关注其在民国初年的情况。梁启超等人在民国初年仍然坚持开明专制论,他们恐惧革命之后可能出现的暴民专制、忧虑革命再次发生的可能,希望依傍现有的政治权势,行开明专制,以向宪政过渡,但终为政治权势所玩弄。坚持共和民主立场的人士以及革命党人,对于开明专制有系统的批评,或坚持民主政治可以随时随地起步,或坚持应由革命党掌握政权以行训政。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12-0055-09
开明专制论是梁启超在清末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在清末立宪派和社会稳健人士中比较有市场。立宪派大体上属于社会的中上层,多少有些产业与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对于秩序的彻底崩坏深怀戒惧之心,对于以暴力革命改变现存社会秩序,历来持反对态度。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又使他们担心秩序的破坏会为列强干预中国政治,乃至瓜分中国,提供机会,故对于根本破坏秩序的暴力革命,畏如蛇蝎,避之唯恐不及。他们渴望通过政治革新来挽救危亡,同时又深知,中国缺乏政治革新的一些基本条件,尤其是国民程度不够。他们认为,国民程度的提高需要在和平的环境下逐步进行,暴力革命本身不能直接提高国民程度。因此,他们希望现有的政治权力能够实行开明的统治,逐步推动社会变革与政治革新。这就是开明专制论在中国产生的基本背景。
清末的革命派即曾对开明专制论提出批评,他们的批评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从排满革命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清王朝是个异族政权,不应当对于这样一个政权寄予希望。革命派认为,立宪则国民平等,必损害满人的特权地位,因此掌握清朝实权的贵族集团,不可能实行立宪,也不可能实行以立宪为前途的开明专制。同时,即便清王朝能开明专制,能立宪,也不能实现民族主义,即建立一个汉族主导的近代国家的目的。总之,无论清王朝能否立宪,能否开明专制,都要反对。二是从开明专制的可能性进行批评,认为开明专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道德与知识,靠不住,专制就是专制,不可能开明,不可能通过开明专制提高国民程度。梁启超则以德国、日本通过开明专制而实现立宪为例,证明开明专制之可行,又指出,满汉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满人已经汉化,满人汉人共为大清臣民,在实现国家富强、国家近代化的目标上,有共同利益,囿于狭隘的排满主义立场而否定清王朝开明专制的可能性,是感情刺激所致,并非理性思考所得。应该说,双方各有理据,也各有局限。
对于清末的开明专制论,学界多有论述,但对民国初年的开明专制论,以及围绕开明专制论的争论,学界的论述相当单薄。以笔者所见,只有徐宗勉等著《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一书,于此有简要的论析。不过,该书侧重于思想界对于开明专制论的批评,而对于此期开明专制论的实际内涵及开明专制论者的立场与策略,论述略嫌不足。本文试图系统地梳理民初开明专制论的基本思想主张及其政治立场,并述思想界对其批评。
一、开明专制论者忧惧暴民专制、推崇尚贤政治
梁启超在清末即提出開明专制论,以与革命党的革命论相抗衡。在清末,立宪派将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民国建立后,他们又将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与清末时担心暴力革命略有不同,民国建立后,他们最担心出现“暴民专制”。在民初宪法问题之争中,原立宪派反对极端之民权说(即国民的广泛参政与国会大权),担心这会导致暴民政治。他们担心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政治,则社会中上层因为人数少,在选举中处于劣势,导致多数之社会下层在选举中占据优势,最终损害社会中上层的利益。梁启超认为,极端的多数政治极有可能损害少数社会精英的利益与幸福,极易为少数野心家操纵而成为野心家争权夺利的工具。康有为称,政治取决于多数,“在理为公理,在势为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其实行,必赖社会上少数有道德、有知识、有财力者以为维持,否则必流于暴民专制。“夫天下富者少而贫者多,贤者少而不肖者多,智者少而愚者多;如必从多数以为治也,则必淘汰其贤者、智者、富者,而选用其愚者、贫者、不肖者,则奈之何其不流为暴民之乱政也。”中国不顾实际条件,强行共和政治,结果所谓共和、民权、平等、自由者,不过十数万之暴民得之耳。不过暴民之魁首得之耳。直斥中国的共和政治实为暴民政治。吴贯因则直接称平民政治、多数政治为“众愚政治”,说中国不顾条件欲行多数政治,其结果必为“众乱政治”、“众恶政治”。
开明专制论者之所以反对暴力革命,是担心暴力革命之后,社会下层乘革命之机,以暴力手段剥夺社会上层的地位与财富,更担心疾风暴雨式的社会财富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会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与社会上层的强烈反弹,从而引发内战。一旦如此,就会有强有力之人物乘人心思定之氛围,实施专断政治。而强有力人物的专断统治又会引发新派人物,以及在前次革命中得利而在专断统治中被打压的社会阶层的反弹,出现新的暴力革命。于是社会就会陷入革命与反动反复交替的局面。法国大革命后出现的暴民专制与专断政治辗转反复的情境,让他们不寒而栗。而德国、日本以现有政权的开明统治逐步推动社会变革的模式,让他们艳羡不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希望现有政治威权,有序地推动社会变革,自然就会呼唤开明专制。民国初建,革命党人以民国功臣自居,意态骄横,在一些地方也出现过火的打压原立宪派的暴力行为,这似乎印证了立宪派对于所谓暴民政治的忧惧。而同盟会一国民党在各地方的扩张,尤其是其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更使原立宪派担心政权会控制在原革命派手中。于是,他们即采取先联合袁世凯以打压同盟会-国民党(即他们所称的“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的策略,然后再试图在秩序稳定的情况下,改造袁世凯,引导政治上轨道。章士钊曾分析开明专制论的社会心理基础,他说,革命之后所以出现专制政治,除革命后混乱的局面需要借助专断手段进行统治之外,专制的出现,还需要相应的社会心理基础。法兰西革命之后的大乱,就与那里偏激的社会思潮有关。革命之后,社会思潮易趋于两个极端。一派人为暴民,他们挟一“民王”(peuple-roi)思想,即唯民为王、主权在民之意,误解主权在民的理论,以人民主权的名义滥用多数的权力,侵害社会少数的利益,乃至彼此之间各以人民自居,各以国民公意的名义压制、征伐对方,结果大祸以起。另一派则为纯正温良之士,实心爱国之徒,他们有见于暴民之专横,无法自救,于是在自由与生命财产安全之间,选择后者而抛弃前者,专制者就乘这种思潮而起。纯正温良之士的这种思想倾向,就是开明专制论的社会心理基础。但此种心理大抵为一时激愤之感情所驱,人们激于动荡的时局,希望有强有力之人物起而收拾局面,又希望此强有力人物能善用专断的政治权力。但一旦专制者掌握权力,人们就再难以平和的手段控制他,“社会心理所需专制之量,与其运用专制之方,一入专制者之手,遂乃漫无底止”。于是,反动以起,所谓温良之士又转而希望暴民出来推翻专制统治。于是,革命与专制交相出现,社会乃陷入长期的动荡。近代中国的所谓温良纯正之士,多期望政治革新,以救危亡,但又恐惧暴民政治,故希望避免暴力革命。他们自身力量孱弱,缺乏组织,不能承担政治革新的重任,又缺乏可以依靠的推动政治革新的力量,乃试图依靠现有政治权势,一面维持秩序,一面行开明统治,进行社会政治革新,以顺应世界潮流与国民要求政治革新的意愿,从而避免革命。这就是开明专制论的基本考虑。endprint
开明专制论者强调,欲确立宪政必须经过开明专制,中国革命之后必然会经历开明专制一阶段。吴贯因称,“政治欲革专制而为立宪,必循正当之轨道焉,而依次以进行,乃能抵于立宪之域,若躐等以登,则其结果往往反于其所期待……政治之革专制而为立宪,由儋次序以获得焉,则其宪政常收美满之效果,若夫大破坏以获得焉,则常立宪政治其名,而暴民政治其实,而暴民横决之结果,遂以行促专制政治之中兴,此必至之符,无可幸免。”他认为,革命之后,必秩序大乱,而革命元勋以“有功民国”为攘夺权利之武器,依附草木者腹削百姓以自肥,甚至借社會主义之名剥夺富民,于是所谓共和幸福只有少数“暴民”得享,暴民专制之祸甚于洪水猛兽,于是人们就渴望有强有力者出现,以武力铲除暴民而出民于水火。同时,国会腐败,议场秩序混乱,议事效率低下,议员又贪利奢侈,败坏天下之廉耻,国人遂“视议员如禽兽,听其自生自灭”,不再对国会抱期望,“使政府而师克伦威尔之手段,以铁骑蹂躏国会,则国民亦浮白称快,谓议员死有余辜已耳。”这就必然会导致专断政治。李其荃也说,“一国家由专制进为共和,设其改革之方法、程序,不儋乎政治轨道,而由革命躐等以攫得之者,其国必不靖,乃至革命再见,其势不得不促政治之折人专制者,实天演公例之无可俸逃者也。”他们还只是说,开明专制是以革命革新政治的必然现象。更有人则将开明专制视为一切国家由专制进于立宪都必须经过的阶段。
除希望维持秩序,依傍现有政治权势,推动社会政治革新之外,开明专制论还与中国的尚贤政治的传统有关。如《时报》上一篇鼓吹开明专制的文章所称的,中国政治原理原以尚贤为原则,故欧美之平民政治非东洋所能梦想。《礼记》“礼运篇”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选贤与能”,这实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追求,中国传统的文官选拔制度,其目的也就在选贤才治国。这与近代政治追求体现民意,追求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有重要区别。同时,庚子以后,国家主义盛行于中国思想界,持国家主义立场的人们认为,政治之第一目的在求国家之富强,民主政治也好,专制也好,开明专制也好,都只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工具。他们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有效能的政府来恢复秩序、应付内外危机,推动国家发展。而中国国民程度不足,行平民政治,则其所选出之代议士多难称优秀人物,难当参与国政之大任,难以承担以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推动国家发展的重任,平民政治在中国既难以立即实行,又不符合中国亟需强有力的政府的现实需要。所以他们认为,若能选举出有为之大总统,则与其将积极推动国家发展的责任交予“发言盈廷,事权不一”的国会,不如交给有能力之大总统。他们希望国人“不必汲汲博平民政治之美名”,而当“抱定一尚贤政治之目的”,假若选出的总统为大有为之人,“则一切均假之以大权,俾其有所展布”,以“造成一强国”。他们看中的所谓贤能之人就是袁世凯。开明专制论者对于民选的议员则嫌其德智不足,对于袁世凯则信其贤能,与他们担心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会引发所谓暴民专制有关。他们心存开明专制之念,希望行政的权力能对同盟会~国民党占多数的立法机关形成制约,防止“暴民专制”。此如草灰蛇线,有踪可寻。
二、开明专制之梦的幻灭
梁启超在清末即鼓吹开明专制,民国建立后亦心存此念。还在1912年2月,梁启超就曾致函袁世凯,为袁献策,说“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1913年初,他发表《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一文,论欧洲何以能够建立近代立宪政治,其中即说,欧洲各国的近代立宪无不经过一段开明专制时期,这是因为近代立宪政治需要国民有相应的智识、能力,需要养成国民尊重法律、严守秩序之风,而这些都要经过训练才能具备的。通过开明专制训练国民,此国家之天职,“有国家者所最贵也”。同年6月,在二次革命即将发生时,他又发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阐述二次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呼唤强有力的统治秩序,隐晦地表达对于开明专制的期待。提倡开明专制,是梁启超在政治策略上依傍袁世凯一派势力,在政治方案上主张强有力政府的重要原因。民初思想界都清楚梁启超的这种取向。因此,当袁世凯解散国会时,坊间曾传梁启超支持解散国会,倡导“军政五年”之说。梁启超遂不得不发表宣言,说报纸所说他主张五年不要国会或解散国会之说,“纯属断章取义”。他的本意是,大总统及国务院在近年内能负责任,有不要国会之魄力,便可暂且停止或解散国会,否则须赶紧维持,使国会不生不死乃非鄙人所赞成。但有人就不相信他的解释,就在他发表此番宣言之后不久,谷钟秀坚持说,当国会解散时,梁启超“曾倡行军政五年之说”。
除梁启超之外,在袁世凯解散国会,直接实施专断统治之前,吴贯因也数度鼓吹开明专制。1913年5月,他指责“今之醉心西风者,不问国民程度之如何,骤欲求多数政治之实现”,实际上以多数为治,只是“众愚政治”。其鼓吹开明专制之意图甚显。8月,他又说,“外稽他国之成例,内审本国之国情”,认定二次革命后,“中国必有若干年焉为专制政治中兴时代,经此时代乃能进于立宪。”同年10月、11月,他又称,共和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他说,中国数千年以君主国体为立国之精神,一旦改行共和国体,必有种种的不适应。一是政制选择有困难。行总统制,则有武力争夺总统大位之危险,行内阁制则内阁更迭频繁,不能得强有力之政府,以进行国家建设。二是国会腐败。“共和政治之下,只有腐败之国会,而无健全之国会”,并以第一届国会为例,指责国会贪利、捣乱、滥权。三是不能得良善之宪法。共和国体之下,“人民鸩毒于民主之说,其制定宪法常力谋限制政府之权力,毫不予以活动之余地,因之易惹起反动”。
袁世凯解散国会后,心存开明专制之念的人们,眼见袁世凯大权独揽之局已成,乃从鼓吹开明专制转为希望独裁者实行开明专制。丁佛言称,“民国二年,政争叠起,议会虽成,宪法未定,袁大总统奋其铁腕,取消议员、停止国会,制取开明,政尚专断,爱国之士,救亡心切,舍经从权,望风而治,有如饥渴”。然而,在所谓的“暴民”被清算之后,渴望开明专制的人们发现,事情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样。当局纯以力治,致使国家危机四伏,前景堪忧,于是,他们乃不断地呼吁袁世凯“急行开诚布公,明白宣示其专断政治之施行时间与实行立宪究以何时为开始”,以释群疑。然而袁世凯不但不从开明专制论者之请,且一意孤行,直往个人独裁与帝制复辟之路狂奔而去。于是,渴望开明专制的人们,乃怀疑袁世凯是否会行开明专制。1914年5月,也就在袁世凯颁布袁记约法之后,李其荃发表在《中华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很典型地表现了他们的这种心态。文章在论述由专制而立宪,必然经历开明专制之后,对于开明专制之前途表达了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说,“今日袁大总统之开明专制,既因第二次革命以激成之,则此后吾国人如能以强毅正大之对抗力与之相抗,岂惟不危及共和而已,又可利用之辅助之提携之,以渐进的方法,导之于改革之正轨。若然则此后必有若干年焉,行科德达(即coup d'etat,一般译为“苦迭打”——引者注)之政治,而袁大总统亦遂为克伦威尔,经过此时代始能进为真正民主立宪之国家,而为今世之华盛顿、东亚之美利坚。而不然者,法兰西之覆辙相寻,是非吾所敢知也。”又称,民国已经建立,各国已承认民国,断不至出现帝制复辟。似乎对开明专制有信心,以华盛顿望之袁世凯。另一方面又说,“吾国人处专制压力之下已久,民主之观念素薄,服从之根性甚深,被动者多易为握权据势者所愚弄操纵”,“权势常操纵于少数人之手,而又无强有力之政党以峙其前,而督其后,不幸此少数人连为一气,斯难抵抗是也。夫民气也,政党也,皆国民对抗政府最强毅最正大之势力也,而今俱无可恃矣,环顾现状,宁不悚惕。”似乎又对于开明专制之实行没有信心。不过,他又不愿意抛弃对开明专制的些许幻想,故又说,也许天佑中国,政局从此稳定,革命党不再革命,从而刺激当局之进一步独裁专断,那么进步党人或许可以因势乘便,养成强毅正大之对抗力,造成有团结力之民气与强有力之政党,从而可以积极与政府抗衡,并可以利用之、辅助之、提携之,以渐进于民主立宪之正轨。endprint
因为恐惧秩序之破坏,因为幻想开明专制,对于袁世凯之专断政治无一能满意的原进步党一系的人们,就处在坚持革命的革命党人与坚持独裁政治的袁世凯之间,彷徨失措。他们一方面反复劝告袁世凯,不刷新政治,则无由消灭革命党,反会催生越来越多的革命党;一方面又反复劝告革命人,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没有革命的资格,当前情况下,零星的军事冒险与空言革命的激烈言辞,只会为当局的专断统治提供借口,为其出卖矿产、铁路、大借外债提供借口,而无助于实际。他们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赦免革命党人,让他们有公开活动的机会,另一方面希望革命党之稳健派与进步党人联手,对于袁世凯的专断统治构成某种制约。但革命党与袁世凯似乎都不接受他们的意见,一方坚持暴力革命,一方坚持专制独裁,开明专制论在现实中已经破产了,政治的趋向已然要么是野蛮专制,要么是暴力革命,似无中间道路可走。
开明专制论者强调秩序优先,强调国家政治之目的首先在求国家自身之富强,担心暴力革命造成反复的动荡,希望以和平的方法循序渐进地为政治革新准备条件,逐步提高国民程度,希望政治革新的风险可控,自有其道理。他们对于暴力革命易引发革命相续、暴民专制的担忧,也有历史前例可据。然而他们的开明专制理论,他们依傍现有政治权势的政治品格,却为袁世凯利用,成为其专制独裁所凭借的社会基础之一。章士钊批评称,开明专制论,倡于前清,其始倡者确本无邪之思、至诚之意,但其流毒所至,则酿成前清伪立宪与民国伪共和两大恶剧,铁案如山,毫不可摇。从清末民初的政治实情看,这不算冤枉开明专制论者。
三、思想界对开明专制论的批评
对于此期的开明专制论,思想界多有批评者。批评者多从开明专制不可期,有之唯有专制;开明专制不可能提高国民程度的角度进行批评。
批评者指出,专制就是专制,不可能有开明专制。章士钊分析专制制度的根本特性,指出,专制制度之下,最高统治者一人独揽生杀刑赏之权,由其股肱心腹及一整套官僚系统去执行政令,而人民则无参政机会,无正常表达意见之渠道,对于当局之施政无表达喜怒之渠道,对于最高统治者及官僚无正常黜罚之道。此种体制下,“令之所在,或为成规,意之所在,始为所欲”,真正起作用的是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非法律。官僚无不以揣摩人主之意为行动之指针,由此必然造成国家纲纪法令的虚化和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集聚,从而引发革命。“专制之效,首在民怨,民怨既众,乱象四萌”。一旦有事,则专制统治者一人孤立于上,而臣僚作鸟兽散,“土崩瓦解,理有固然”。这是专制制度固有之“自贼性”,不改变专制制度,就不可能去除其“自贼性”,欲专制而开明,绝无可能,“开明者,本不可期,有之厥惟专制”。专制而开明有两个前提:第一,要有所谓至强至辨至明的圣人,对于国家政务、官僚系统以及民情民意等等有全知全能之能。然而,“人类生而不全者也,全者非彼能思义之物,则民之秉彝虽有等差,未能绝远,备德全美,信乎未能”。第二,最高统治者,必须无任何好恶。要使自己的威权不被臣僚侵夺,而造成威权下移;要保障国家法纪不沦为虚文,使臣僚从国家之法纪,而无从刺探、逢迎人主之意;要使人主真正做到“至辨”、“至明”,而不为臣僚所蒙蔽,人主必须“去好去恶”。但人主亦为有血有肉之人,就必有好恶。上述两个前提不成立,开明专制论从根本上就不能成立。章士钊对专制制度弊病的分析,入木三分。但他对于开明专制论者津津乐道的德国威廉二世时期、日本明治维新的“开明专制”及其成效,没有进行评析,所以他的批评并不能服开明专制论者之心。
开明专制论有一基本假设,即认为统治者心智高于被统治者,是所谓的先知先觉者,而一般国民则有如儿童,心智发育尚不完全,需先知先觉者去训练、去保育;又假设统治者为稳固统治、实现国家富强,会顺应潮流,主动推进改革。张东荪从人类人格平等、心智同等的角度,否定开明专制论的这一假设。他说,近代政治是“惟民主义”,即人民以自身之能力运用其政治。惟民主义立基于“人格观念”,即认为个人皆有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能力,个人与个人平等,个人与国家平等,皆有同等之人格。“夫各人民皆有同等之人格,有同等之发展力,有同等之自觉心,互相承认以求进步,则固不必有首出庶物之圣人,以一人之力为万众之谋,如园夫之治草木,草木之茁长繁盛,皆必待园夫措施之功,奪其自然发育之机,而一一代庖焉。故新式政治之精髓,不在求有贤良之人,拥之以为君后,知言者且谓贤君之害于自由,乃更盛于无道之君。换言以明之,近世政治之第一义惟在反对专制主义。”由此,张东荪提出了判断政治良恶的标准。晚清以来,国家主义在中国思想中占据相当的位置,持国家主义立场的人士,强调国家有自身之目的,政治之第一任务在实现国家自身之目的,即国家之繁荣发达。政治之良恶,首在其能否发达国家,一切政治制度的选择,一切政治行为的判断,均应以此为标准,而个人自由权利、个人能力之发达则被放在国家利益之后,也主要从其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角度论证其价值。开明专制论者即以此为标准,认为以尚贤为骨髓的开明专制就是适合中国的良政治。针对这种思想倾向,张东荪提出,所谓良政治,“不外乎能启发民志,使聪明才力皆得自用,情感利害咸足自安。……使全国聪明才力之最高量得以表现于上,全国情感利害之最低度得以相安于下。”“使人民有自然发展机会,自由运用之作用。”也就是说,政治良恶之标准,不在它能否实现国家富强,而在个人之聪明才智能否得到发挥,个人能否自我实现,社会之各种利益情感能否调和。此系对盛行于清末民初的国家主义政治理念痛下针砭。
开明专制论者坚持认为,国民程度不足以立宪,必经开明专制才能培育国民程度,才能和平有序地确立宪政。于此,朱执信指出,开明专制不可能训练国民,使之具备立宪国民资格。所谓国民程度,无非智识与道德而已。道德之进步在社会之自体,只要政府不奖励不道德而破坏社会之纲维即可,从来不见专制能促进社会之道德的。至于智识,则包括教育与经验。就教育而言,立宪国民所需要之教育,与专制制度相冲突,专制统治者必限制立宪观念的传输。即便专制者不限制立宪观念之传输,允许国民接受立宪观念,那么“其民将信其所受教而恶政府乎?将尊政府而以其教为非欤?抑以为教育者政府所奖,而为教者又短政府,遂以怀疑而两置之也?”至于经验,立宪的经验来自立宪政治本身,“以经验之缺乏,而言程度不足,则正当疾蠲除专制,而取立宪,然后可以得立宪之事实陶铸其人民。人民既得与政治,乃有经验可言。以无经验之故,而不使参政,则终古不参政可也。”“立宪国民不患其程度之不足,其在不足之日,亦惟先行立宪可养成之,非可以专制进其程度。”“专制之结果,虽至良好,而以促进人民程度论,尚不及立宪之最劣者。”他又指出,专制所以会损害国民能力,就是因为它不承认国民个人能力的发挥为社会发展之基石。古代的专制政治,其能得治,在治主放任,少干涉闾阎细事,故其妨碍人民能力之发展尚不甚深,而今之鼓吹开明专制者,鼓吹干涉政策,欲事事干涉保护,这必然萎缩国民之能力,养成国民对于政府之依赖,不可能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应该说,他的批评颇尖锐,是开明专制论者难于回答的。章士钊也指出,即便至明至辨的圣人,即便专制而能开明,专制制度也不可取。因为专制统治,一切政事都是由统治者包办,一般民众没有参政机会,故“专制之政,无论其文明达于何度,要于养成民力、增进民德、开发民智,无几微之实效,而况乎达于其所谓文明,又恒在万不可得之数也。”“宪法之不完全,任至何度,惟若准斯法也,国民之多数可以自由意志定其政略,则以衡之最开明而博爱之专制政治,其为优越至无垠焉。何也,立宪政治,进取者也,富于生机,专制政治,停滞者也,几于死体。”章士钊将民主政治看作一个可以随时起步、逐渐扩大、逐渐发展的制度,不认为民主政治必须具备何等国民程度才能实行。他说,凡一个国家能够存在,能够治理,必有其官僚系统,必有一定的社会精英,民主政治可以首先在官僚系统与社会精英的范围内实行,由他们按照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来运作政治。民主政治首先只能是精英的民主政治,然后在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训练民众,逐渐扩大民主的范围。而不是先由先知先觉的统治者来训练国民,然后再施行广泛的民主。与开明专制不同,有限的精英民主在其实施过程中,并不排斥一般民众对于政治发表见解,不限制思想言论自由,而思想言论自由本身就是训练民众理性看待问题的最好途径,这就可为民主范围的扩大准备条件。endprint
对于开明专制论所称,以革命求政治革新,必引发开明专制的说法,戴季陶的批评颇有意思。他说,革命之后,野心家所以得复出而行独裁政治,并再引发革命,主要原因是,专制统治既久,人民养成苟安目前之习惯,举国家之大权付之帝王一人,唯日望明君良相为国民谋幸福,使暴君污吏得肆意妄为,内生虐政,外召强敌侵凌,迫不得已,而后起而革命。革命之后,人民亦难改苟安之习惯,不谋自掌政权,而欲将政权交付给所谓贤明之政府,或期盼开明专制,欲政府代人民谋福利,遂使专制再现。要避免革命之后再出现专制与革命,确立共和立宪,则革命党人在革命后必须自掌权力,以革命党的政权,推动政治革新,而不能以为旧政权一推翻,革命的任务就已经完成,而将革命之后的建设委之于他人。他批评开明专制论者期望开明专制不过因袭国人“苟且偷安于虐政之下”的旧习。戴季陶此说是对辛亥革命没有按照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进行的批评。四、开明专制论与训政论之比较
甲午战败之后,革新政治以拯救危亡成为时代思潮,思想界普遍认为,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在政治制度的腐败落后,非从速革新政治不足以拯救危亡。政治革新无非和平改革与暴力革命两途。但政治革新思潮突起时,中国经济、社会、教育、思想文化的变革还很不充分,政治革新无论取哪一种途径,都面临着社会条件不足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思想界主要有两种解决思路,即开明专制论与革命程序论。
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即认识到中国缺乏建立近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不可能在暴力革命之后,直接建立民主政治,在革命军起之后,需经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才能进人宪法之治。这就是他的革命程序論。孙中山对中国经由革命逐步建立近代民主政治有系统的思考,这是他高出于一般革命党人的地方。但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革命党,革命程序论并没有为广大革命党人所接受,加上革命党势力有限,武昌起义后,革命党并未能控制局势,因此,中国即在军法之治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就直接进入宪政试验。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认为辛亥革命未能确立共和政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革命党组织涣散,党的领袖缺乏权威,二是革命没有按照革命程序论进行。因此,他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入党必须按指模,并宣誓服从党的领袖,又重新解释革命程序论,将革命分作军政、训政、宪政三期,强调革命党人取得政权之后,并不能直接进入宪政时期,必须经历一个由革命党独揽国家大权,唯革命党人有公民权,由革命党训练国民的“训政时期”。与辛亥革命前相比,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特别强调革命党的作用。孙中山的训政论与梁启超等人的开明专制论,在解决政治必须革新而社会条件尤其是国民程度不足的问题上,思路颇为相近,即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训练国民。两者的区别是,开明专制论者恐惧于秩序的破坏,又缺乏可资利用的实际政治力量,乃欲假借现有政治势力中之最强者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革命党人则不认为现有政权有推动政治革新的意愿与能力,欲以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然后由新政权推动国家建设,提高国民程度,进而建立宪政。历史的进程则是,欲因人成事的开明专制论者,往往为人利用,最终为有力者抛弃。李大钊评论称,民初的“缓进派”有一开明专制、贤人政治的梦想,“既欲实现其专制其质、共和其皮之玄想,遂恒寻势力之所在,以为倚附利用之资。迨其既受结纳,谋尽开明之责,负贤人之任,则又为官僚所忌,格而不容。”李剑农批评梁启超,“梁先生生平有一根本毛病,主张不能持久,恒倚强力所造成之事实为转移,换言之,则惟依傍强力为政治上之生活,强力之正不正,不暇问也。因是,其政治上之主张,无往不为所依傍之强力所格。其终也,则其所主张徒以供窃据攘夺者之牺牲而已。”对于此派势力依傍强权的特性说得很到位。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与各级地方议会,大力推动专制集权的时候,此派人物始反思其假借官僚腐败势力以排挤“乱暴势力”的政治策略,欲联合、吸纳革命党之稳健势力共同限制袁世凯的独断政治,但护国倒袁后,此派势力又故态复萌,重回利用官僚势力排斥革命势力的老路。而革命党在历经挫折后,夺取了政权,有机会进行训政。开明专制并非不可能,但需要开明而有威权的统治者,这可遇而不可求,同时当社会发展程度不够时,如何使统治者开明,也是开明专制论无法解决的问题。训政论也并非不可行,它的困难是,如何使大权独揽的革命党,忠实于宪政理想,最终自觉地还政于民。不过,在训政论中,革命党是公开地宣称要以训政为走向宪政途径的,这就为要求落实宪政的人们提供了发表意见与政治活动的空间。
近代以来,中国人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与英勇的奋斗。民族复兴与国家社会现代化以及政治制度的现代化紧密相关。对于政治制度现代化,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有过艰苦的探索,他们当中不少人都认识到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寻求实现政治现代化之路。革命程序论与开明专制论都属于此种探索,都各有其价值,各有其局限,也都为后来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开明专制论者依傍强者的政治品格,并非其个人品格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资产阶级还很幼稚的社会条件造成的,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
[责任编辑 李文苓]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