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抛弃郭敬明?
2017-08-31曾于里
曾于里
改编自郭敬明同名小说,由流量明星郑爽、陈学冬主演的电视剧《夏至未至》,有些静悄悄地结束了。即便是暑期档的热门档期,湖南卫视这样的优质平台,以及电视剧黄金时段,《夏至未至》的收视成绩却始终在1%左右徘徊,话题量也逊色于同期的《我的前半生》《楚乔传》。郭敬明这张王牌,似乎越来越不顶用了。
自2002年成名以来,一直到最近激起舆论风波的丑闻之前,郭敬明一直顺风顺水,即便有作品抄袭等劣迹,但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小说在市场中的爆红。2013年,郭敬明敏锐地步入影视领域,他的“小时代”系列拍了四部,总票房近20亿元,赚得盆满钵满。直到去年的《爵迹》,郭敬明终于马失前蹄。这部投资超过2亿元,有吴亦凡、王源、陈学冬、杨幂、范冰冰等众多流量明星参演的电影,最终票房不足4亿元,严重亏损。《爵迹》败北并非偶然事件,它只是郭敬明帝国倒下的一张最醒目的多米诺骨牌。
种种迹象早就表明,哪怕没有这次的风波,郭敬明在青春文学、青春影视领域的市场地位正在被撼动。2016年,由郭敬明监制的《是!尚先生》,遭遇了收视率和口碑的双重滑铁卢;同年,由郭敬明成名小说《幻城》改编的电视剧,3.6亿投资+郭敬明大IP的噱头,但收视率从开播时的1%左右,到播出结束已跌到0.5%不到。至于郭敬明曾经笑傲多年的图书市场更是彻底失守。根据开卷图书的数据,2013年度他不仅坐拥前三甲,前30名里他独占6席;2014年度,他只有两部小说进入,并排在末位;从2015年开始,郭敬明的小说就跌出了年度排行榜了……
即便郭敬明仍是个大IP,但他也正在被市场抛弃。究竟是谁在抛弃郭敬明?他的市场地位为何不保?
郭敬明的忧伤美学
郭敬明是许多80后、90后的青春记忆,他们都曾在校园时代里追捧过郭敬明的小说,不少人还是郭敬明的粉丝。当时的郭敬明为何能够在80后、90后那里形成一种垄断性的影响力?
根本原因就在于,郭敬明的小说本质上是一种忧伤美学,而这一忧伤美学,击中、迎合了当时年轻读者的一种忧伤情绪。80后、90后是独生子女一代,10多年前刚好都还处于青春期,还在为高考备战。独生子女的孤独、高考的竞争压力、市场经济的人际疏离和成王败寇、时代的高速发展与落后的恐慌、多元价值指标下的无所适从,以及青春期天然的多愁善感—使得这些少男少女的情感呈现出一种忧伤的症状。

以郭敬明为代表的忧伤青春写作,刚好契合了他们的情感需求,郭敬明一系列散文和小说的共同主题就是忧伤。比如成长的困惑与忧伤(《爱与痛的边缘》),学业的忧伤(《天亮说晚安》)、青春恋爱的忧伤(《悲伤逆流成河》)、友情背叛的忧伤(《夏至未至》)……总而言之,就像《悲伤逆流成河》中的一句话说的,“那些叫做悲伤的情绪,像是成群结队的蚂蚁,从遥远的地方赶来,慢慢爬上自己的身体。一步一步朝着最深处跳动着的心脏爬行而去。直到领队的那群,爬到了心脏的最上面,然后把旗帜朝着脚下柔软跳动的地方,用力地一插—哈,占领咯。”
值得一提的是,郭敬明的忧伤美学背后,是“我是孩子”的逻辑,也即“我是孩子”是忧伤美学的合理性基础。在郭敬明的作品中,“我是孩子”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我是一個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会仰望天空的小孩,望着那个大太阳,望着那个大月亮,望到脖子酸痛,望到眼里噙满泪水。这是真的,好孩子不说假话”,“我总是以一种抗拒的姿态坐在客厅墙角的蓝白色沙发里,像个寂寞但倔强的小孩子满脸的抗拒和愤怒”……
郭敬明将自己设定为一个单纯的、寂寞的、倔强的、真诚的孩子。孩子之所以忧伤,是因为外界施加在孩子身上太多太多的压力,是因为孩子的纯真与尔虞我诈、虚伪、残酷的成人世界是相对立的。“我是孩子”不仅将忧伤合理化和“崇高化”,并有效地构成了逃避责任、拒绝承担的理由和借口。因为我是孩子,“一个永远不肯长大的孩子也许永远值得原谅”,我可以堂而皇之地拒绝责任的承担;因为我是孩子,所以我任性做什么都情有可原,“我是个小孩子,大家不要欺负我”。
对于80后、90后忧伤情绪的击中,以及逃离欲望的迎合,便是郭敬明长期屹立于出版市场的秘密。
没有人永远需要郭敬明
近几年来,郭敬明的忧伤美学,为何影响力大大削弱?
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与郭敬明的作品一起成长的80后、90后,已经走完了他们的青春期,依照联合国的标准,他们甚至已经是“中年人”了。他们不少人已经到了而立之年,青春期的忧伤、成长的困惑、高考的压力,早就成了过去式,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更严峻更务实的生存问题:工作、房子、车子、结婚、孩子……此时他们回顾青春期的忧伤,难免觉得当时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郭敬明的“我是孩子”式逃避责任的逻辑,在80后、90后这里再也行不通了。青春期的他们,之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挥霍和任性,是因为他们尚有父母的庇佑,有人替他们遮风挡雨;如今他们已踏入社会的洪流,他们是自己的依靠和庇护所,以“我是孩子”做借口逃避责任,显得幼齿、可笑且不切实际。
没有人能够永远长不大,没有人永远处于青春期,因此没有人永远需要郭敬明。
但郭敬明曾颇为自信地说,“没有人永远需要郭敬明,但永远有人正需要着”。在他看来,虽然有人正走出青春,但永远有人正走入青春。话虽如此,但郭敬明是否想到问题的另一面:永远有人正青春,但是否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是一样的?
如今的青春文学和青春影视市场,主要被95后、00后所掌控。他们的成长期面临着与80后、90后一样的压力,但一个本质性的不同是,他们生活的“软环境”不一样了。95后、00后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们获取信息、表达情绪的主要方式不再是郭敬明式的青春读物,而是更为丰富、更为便捷、更为多元的互联网,他们在互联网上构建起了独属于他们的表达体系、审美体系乃至价值体系。
虽然很忧伤、压力很大,但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一定是“悲伤逆流成河”,很可能是吐槽,是表情包,是“丧文化”;他们的审美标准,也不再只是刻板式的忧伤、柔美、细腻的文字,也可以是简单粗暴但笑点十足的表情包,是满屏密密麻麻的弹幕,是二次元。更根本的是价值体系的变化,在80后、90后那里,高考等压力的背后仍旧是一种成功至上的单一标准,但多个调查结果显示,在95后、00后这里,他们不以成功为鹄的,他们追求生活方式的多样化,他们热衷于“小确幸”和“小确丧”……
当一代人的青春发生了变化,这证明了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仍停留在原地的郭敬明,还能够跟得上步伐吗?
青春不再只有一副面孔
郭敬明的青春故事,除了忧伤以外,另一个关键词,就是狗血。
郭敬明的另一部小說《悲伤逆流成河》正改编成电视剧,并由郑爽、马天宇主演。《悲伤逆流成河》出版于2007年,曾创下可怕的销售记录,一周销量突破百万册,三天后即名列中国图书销量当日排行前三。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易遥生活在上海贫困的小胡同里,父母离异。母亲做暗娼养家,生活艰难粗鄙,动辄打骂她。幸运的是还有朋友齐铭。在易遥暗淡无光的成长岁月中,齐铭是她的精神支柱。可是,因为齐铭与易遥走得很近,唐小米屡次恶意陷害易遥。易遥的包容无济于事,她只能选择以毒来对抗恶,齐铭却因此而疏离了易遥。
事情有了很多变迁。易遥和热情开朗的顾森西走到一起,而齐铭搬出了胡同,和顾森湘走在一起。故事似乎开始云淡风轻起来。只是最后的几千字又有了“惊天逆转”。唐小米对易遥的报复意外导致顾森湘的死亡,所有人都以为是易遥做的,包括她深爱的齐铭,和深爱着她的顾森西。易遥最后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跳楼自杀,而齐铭因为错怪易遥也自杀去世。
在2007年,笔者也是第一时间买来小说,应该承认,在当时这是非常新鲜的阅读体验,因为小说中描写的那种残酷狗血的青春故事,在大陆青春文学中非常少见。只是在2017年的今天,95后、00后还能够从郭敬明的忧伤书写中获得同样的体验吗?
2013年赵薇执导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开启了青春电影市场的“黄金时代”,一下子青春电影成了市场的香饽饽,一系列青春电影扎堆上映。但无论是《致青春》还是后来都大卖的《同桌的你》《匆匆那年》《左耳》,它们走的路线都是郭敬明的忧伤狗血路线,堕胎、劈腿、车祸、死亡……观众一开始还照单全收,只是当忧伤狗血的青春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大银幕上上演,观众也会审美疲劳,他们很快察觉到这一类型青春电影的“虚假性”,它虽然戏剧性、冲突性有余,但真实性不足,并不符合多数人的青春体验,观众再难以从中获得共鸣,忧伤惨痛最终获得的是“拙劣狗血”的评价。因此到了2016年,《致青春2》《夏有乔木 雅望天堂》等走忧伤狗血路线的青春片纷纷“扑街”,无论是票房还是市场反响都远不如预期,这预示了走这一老路的青春片已到了强弩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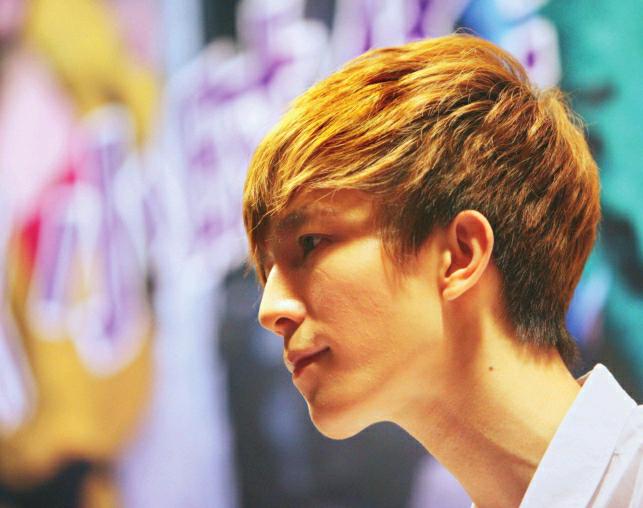
郭敬明终究来晚了一步。直到2016年前后,根据他一系列忧伤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才纷纷播出。但忧伤狗血早就不再是青春的唯一面孔。如今的95后、00后青睐的反倒是小清新式的,明媚阳光或舒服自在的青春书写,比如《我的少女时代》《最好的我们》《春风十里不如你》《闪光少女》,在这些青春故事里,有更真切、更多元、更与时俱进的青春体验,也能够真正引起他们的共鸣。
旧的粉丝正在流失,却没有及时跟上新的粉丝的需求,郭敬明的商业帝国风光不再。他显然高估了自己,没有人永远需要郭敬明,也没有人永远“正需要着”他。如果他没有及时调整市场策略,那么他注定成为过去式—虽然这似乎不是一件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