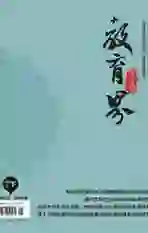浅析英美意象派诗歌的意象张力
2017-08-31曹晓安
曹晓安

【摘要】意象派诗歌兴起于20世纪西方诗坛。意象派认为诗歌语言要简练,以达到更好地筑“象”言“意”的目的。诗歌中的“意”重在体现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情感,并由此唤起读者的共感共鸣;“象”则充分借力视觉与听力想象,构筑张弛有度,可闻可感的审美之象。文章集中选取部分重要意象派诗人的诗歌作品,探讨其诗歌“意”和“象”的张力美。
【关键词】英美意象派诗歌;意;象;张力美
【基金项目】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翻译文学与文学翻译 ”(项目编号:GD16WXZ26)之系列成果之一。
若论及现代诗歌的格局,首当提起意象派诗歌。1912年,意象派开始活跃于英美诗坛。意象派诗歌一如加工精致的艺术,在语言的精确使用、形象与隐喻的准确构筑、韵律的走向流动与自由等诸多方面,都独辟新径。意象派代表庞德认为,诗歌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诗歌本身具有强度(intensity)(朱徽,1990: 36)。 故本文围绕“意”和“象”两个要素,探析意象派诗歌意象的张力美。
一、“意”之张力美
此“意”为情美。一首诗,其美的本质源于情,而张力之美也在情中迸发。在构筑诗之美的因素中,诗情被视为第一因素。意象派认为诗歌的创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诗人对外部世界获得深刻的认知和感受后,将这种主观情感转化为客观物象。郭沫若亦论述:“诗的本质专在抒情。”(谢文利,1989:43)而并非所有的“情”都可言美。诗的情美必须是情真意切。只有可被作为审美和表现对象的情感,且按诗的规律通过艺术的加工上升为客观的物象,方可成为诗,并产生美的效应,进而喷发张力。此类情感绝非单纯心理层面上情绪宣泄而获得的快感。再者,可被作为审美对象的高级情感能通过艺术加工而成为审美客体都必须经过理性的分辨力和思考的沉淀。正如庞德所说:“一个意象是瞬息间呈现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complex)。”(黄晋凯,1998:132)庞德虽然推崇情感对于诗的重要性,可是这种感情都是思考后的产物。盲目情感宣泄的作品,并非诗人人格力量和创造力的体现。意象派的诗学主张更多体现在 T·S·艾略特的《艾兹拉·庞德:他的诗韵和诗》中,他对庞德情感观点做出这样的评论:“庞德对这种自由诗的运用显示其艺术家的气质,但他把自由诗看作是传达思想情感工具的同时并非达到狂热而盲目的程度。”(Ezra Pond, 2002:128)只有当“情真”时,通过理性的沉淀所呈现艺术的状态才是诗人基于对生活深刻体验和透彻理解后生成的人生態度,也只有这样的真情“意”,才能创作出富有灵魂的作品,进而服务于构筑有张力美的“象”。意象派诗歌对“象”的构筑多数是表现诗人对某一事物的真实观察和思考,产生浓浓的情“意”,进而用凝练的语言来表现出所感物体,且这种“意”极具质感和精练,因此,其抒发的情感也让人回味无穷,细细品来,总会感受到诗人丰富的情感,这种情感的丰富就是“意”之张力。以H. D.(Hilda Doolittle,1886-1961)的诗作“The Pool”(水池)(H. D.,2002:80)为例:
Are you alive?
I touch you.
You quiver like a sea-fish.
I cover you with my net.
What are you-banded one?
寥寥几笔,作者却别具匠心。H.D.注视着一水池,平静毫无波澜,内心幡然涌现出一个问题:“你是否还活着?”而H.D.并非只是对水池发出感叹,那水面折射出的影像就是诗人本身,故而诗人是在对己发问。然而,诗人内心却希望打破这股平静。她揣着试探又期待的心,触碰了下水面。水面的动荡,倒影在水里深深浅浅地刻划,让她觉得自己像海里的鱼,被自我投放的网束缚着,颤抖着。此刻,H.D.内心一股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情感似是要从胸腔里蹦出,而这种酝酿的情感,经过凝练的语言形成了张力极大的“意”,在被阅读和理解的过程中再将它构筑成“象”,此“象”恰恰是情感意志的代表,可为现实的,亦可超于现实的。该诗从表面剖析似乎只有一个“象”。其实不然,深入地领悟之后,还有一个超于现实的“幻象”在水中倒映,“意”是“象”的内涵,“象”的外延与内涵完全取决于“意”的张力。H.D.使用了“象”的叠加方法,比如,一方面写实的“象”——海鱼(sea-fish);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隐喻之“象”——被束缚的倒影(banded one),两种“象”组合成一个复合之象。这个复合之象是作者强烈情感之“意”的沉淀后的呈现:第一个“象”如实写出诗人对池凝望的感官印象,也可以说,这种感官印象是凝望之“意”的张力所致;第二个“象”是作者巧思暗藏的情感之“意”的呈现,也是“意”的张力使然。第一个“象”是明喻,第二个“象”是暗喻,两者通过“意”的张力引领读者发现两者之关联,让两个“象”串联成一个“镜头”,瞬间闪现出“意”之美,这种美更多是“意”的张力所致,而“象”只是“意”的表现形式。这种瞬息的张力美正是诗人主观“意”志化的物象,从而达到一种共感的动力层次。H. D.坚信诗歌的意象基于客观自然,才可揭示诗人主观上“意”的情感张力世界,而张力之美也在客观之“象”与主观感情之“意”之间闪现。诗人在主观意志强烈迸发后,到过渡性阶段,创造物象,而基于物我认同的阶段后,双方可刹那产生相互效应,再到情之共感、象之共振,进而到“意”“象”共鸣的张力美迸发,而这种共鸣张力程度的基础是“意”。用格式塔心理学中“同形同构”理论加以解释,即为诗人主体的情感和物象的形态结构都同时有一种物理性张力,双方在物我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即可产生同态效应,由是而生共感(汪裕雄,2013:119)。
意象派运动活跃分子弗林特(F. S. Flint, 1885-1960)写过这样一首抒情灵动的诗“November”(十一月):
What is eternal of you
I saw
in both your eyes.
You were among the apple branches;
the sun shone, and it was November.
Sun and apples and laughter
and love
we gathered, you and I.
And the birds were singing. (Flint, 2002:91)
《十一月》寫得自然,灵动,抒情,表达了诗人对爱人深深的爱慕之情“意”。诗人在闲逸安详的情感下,使用连续性整体的结构,依次建筑十一月里暖暖的“意”之“象”: 苹果(apple)、太阳(sun)、笑声(laughter)、歌唱的鸟儿(singing birds)。这种建构手法依照诗人内心的情感印象与十一月里的客观物象相结合,并没有大幅度的时空跳跃。然而诗人内心欣喜,纵使是平常的客观物象,可是在诗人的情感表达里,却是空灵悠扬,而这种感觉的基础恰恰是富有张力的“意”。满满深情在十一月的阳光照射下,鸟叫声中,苹果树上,缓缓开出笑声。“意”与“象”的结合,又共同放映出空灵极致的张力之美,似乎是听得见的轻轻笑声和悠悠鸟鸣。读来抒情缓缓,张弛有度,回味无穷,这也正是“意”之张力美,是通过“象”而表达出的“意”之美。因为没有“意”,“象”莫过于自然之物,只有在人之“意”志下,才赋予了“象”之美和情。再次恰恰说明了H. D.所坚信的观点,即诗歌的意象基于客观自然(如,上面诗歌中的“苹果”“太阳”“歌唱的鸟儿”等),才可揭示诗人主观上“意”的情感世界。进一步解释就是,“意”是基于“客观自然”的象,才使“意”有了张力的媒介“象”,也才使得“意”的张力美通过“象”的媒介表现出来,从而使得“意”与“象”双赢,达到意象的通力俱美。
二、“象”之张力美
“象”的外延、接受和读者的阐释,使之在“意”的基础上具有了比“意”更大的张力。
此“象”指人、事物抑或是对外部世界产生感应而产生的一种直观印象,故其具有感官特性,是主观直接对客观的真实反映的获知。“象”可因不同的主体感受强弱程度或感受方式的差异而迥然有别。“意”生“象”,但“意”却不都为相同,故“象”为体验的感官之“象”。这种“象”就美学概念而言,应用语言艺术根据现实生活出现的各种现象精细准确加工而来,是兼具思想内容和审美意义的感观、鲜明的图画。而“象”作为一种审美对象,须是具备审美特征,饱含作者之“意”,能引起共感、共鸣的审美感受、审美想象和审美情感。
(一)视象张力
诗歌“象”的视象表现在于人们视觉触发的过程。当产生人们视觉神经被触发,随之也将刺激人们的视觉想象。一如别林斯基所阐述,诗人可捕捉一切的形式和色彩,而诗人赋有艺术家的能力,可把这种无形之物冠以形式和色彩。别林斯基所指是要诗人创造的“象”应该像画家一样,赋予色彩和形式,给人以具体的美感享受。“象”的张力很多时候不单单是平面的铺展,大部分是多维空间的建构,这种建构通过色彩变化、光线处理、透视作用、线条运动,可使平面的“象”变得立体。“象”通过刺激我们的审美想象能力,一步一步架构空间维度,进入到空间感。空间感的张力美此时更多地体现在具象的真实体验和获得审美快感。而此种视象的张力美并非仅仅靠色彩、线条等完成的,而是随着构成“象”的语言,刺激审美群体的审美感受和想象来实现的。因此,使得诗歌视象张力迸发,需得强化该“象”对审美主体的刺激力,进而要求诗人在建“象”之时,就得使用精确的语言。
艾米·洛威尔(1874-1925)的“Autumn”(秋)就极具视象张力:
All day I have watched the purple vine leaves
Fall into the water.
And now in the moonlight they still fall,
But each leaf is fringed with silver.
此诗精妙之处在于白天与夜晚的颜色变化、空间转换和线条运动。诗人白天注视着“象” ——紫藤落叶(purple vine leaves)飘入水中,背景充满想象,可以是光照下或是阴云里,偌大的背景下,紫色的藤叶就这样落着,画面空旷。月光渐渐地出来了,藤叶依然落着,染上了银色的光晕,飘入水面。诗人构思于色彩、光线、线条的渐进使用,画面实整而立体,空间之感交错显现。整个空间的视象张力在光线的对比和空间的放大缩小中产生:白天,紫藤落叶与光线强烈背景之间并未构建出强烈的对比,单一的线条运动着,整个画面在放大;天色渐暗,月亮渐出,银光映衬着落叶的线条运动,整个背景从白天的色彩明亮转换至黑暗,“象”随即缩小了范围。可以想象白天与黑夜光线动态变换,仅有单一的落叶在运动,整个光线运动从明亮再到黑暗,两者的空间之感交换闪现。因此,整个空间的视象张力张弛有度,一放一缩,读来在脑中闪现,充满无限想象。
(二)听象张力
“象”之听象张力,在于“象”刺激人之听觉想象,故而富有尖锐性。这使得审美主体成为听象张力或听象想象。而唤起审美主体听象的刺激力,需使用合适且极富感染力的语言建筑“象”。“意象派”代表倡导使用赋有感情(意)或与感情(意)相符的韵律去表达自然的事物,固守一成不变的抑扬格或抑抑扬格并不能充分地表现韵律。庞德在《自由诗》中说:“当所咏‘事物构成的韵律,比规定的韵律更美。”因此,庞德在《意象主义》提出第三条规则:“节奏是音乐性短句的反复演奏。”语言使用得当建筑的“象”,可使得审美主体和“象”之间形成互感双方,有着相同的生命运动节奏,在“象”“我”之间,人的情感活动和“象”形成的节奏应是同频共振的。判断听象张力的形成标准,则是节奏韵律是否达到谐和状态。宇宙间万物生命,都是节奏韵律的张力,诗人凭借敏感的心灵,感应、捕捉、精细语言加工,最终形成可听之“象”的审美感受。欣赏H. D.另一作品“Never more will the wind”(风再不会)如图:
全诗并无规律的音步和韵律,而是遵循“意象派”的主张,打破传统的韵律规则,使用赋有音乐性的节奏短语反复演奏。对于所咏客观事物“the wind”反复使用音乐性短句“never more”全诗反复吟唱,富含浓郁的情感。在第二节诗歌中,对“the snow” 连续抒发情感,自然地过渡到第三节诗里,以同样的语法和介词,换以不同的主语,构造不同的意象。这种无规律却又交错出现反复规律的韵律节奏短语,发音响亮,急促有力,两者交替使用,形成听象张力,仿佛听见风飞逝的声音,带来想象之音。单音节的长短元音结合,交叉读来,节奏轻快,不失激情。且该诗整体打破了英诗中传统一贯坚持的“五步抑扬格”(iambic pentameter)的局限,情感反而不受约束。飞逝而去的风仿佛就从身边掠过,没有留下丝毫痕迹,就如诗中节奏一样,高低起伏,仿佛那股风声也在我们耳边吹响,那听象张力再一次显现。全诗没有固定韵脚,更赋予了一种自由奔放、不受约束的张力,起起伏伏,一声一声地不断涌聚耳边,直击心灵,而后消逝于风。
三、结束语
英美意象派诗歌张力美探析终归是以语言为出发点,围绕这种“黏合剂”,对“意象派”诗歌“意”与“象”的张力之美进行探析,由而闪现诗美之张力,而这无外乎先发乎“情真”再到“切意”,进而“寄物载情”。而“意”“象”之间的摩擦与契合时刻在萌发诗的张力之美,正如雪莱所言:“诗揭开帷幕,露出世界所隐藏的美。”那么,“意” 之美、“象”之美也揭开了其中的“张力”。
【参考文献】
[1]朱徽.中英诗歌中的张力[J].黑龙江大学学报,1990(03):35-41.
[2]谢文利.诗歌美学[M].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43.
[3]黄晋凯.象征主义·意象派[M].北京: 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32.
[4]Peter Jones ed. Imagist Poetry[M].London: Penguin Books,2002:128,80,91.
[5]汪裕雄.审美意象学[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119.
[6]耿建华.诗歌的意象艺术与批评[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7]Hilda Doolittle. Never More Will the Wind. http://www.poemhunter.com/poem/never-more-will-the-wind/, 2015-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