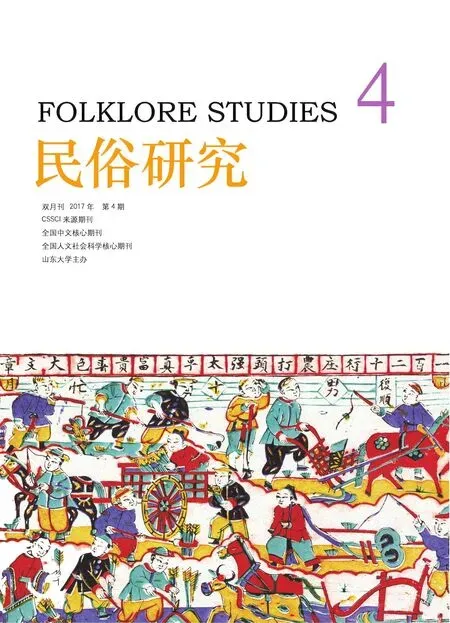“祭祀”与“纪念”之间
——对“东方之星”事件“头七”公祭的考察
2017-08-31王晓葵雷天来
王晓葵 雷天来
“祭祀”与“纪念”之间
——对“东方之星”事件“头七”公祭的考察
王晓葵 雷天来
灾害公祭作为一种公共社会活动和仪式象征体系的一部分,可以折射出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东方之星”游轮翻沉事件发生后,政府采用民间俗信“头七”的时间举行公祭,而公祭之仪式、内涵、主体却与传统俗信差异极大。在此背后,隐含着世俗性事件处理与信仰性阴阳沟通仪式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出世俗权力借公祭将死亡意义价值化、意义化的一贯逻辑,更进一步表明国家权力所形构的公共“纪念”仪式与民间俗信所支撑的个体祭祀之间的生死观存在差异。而透过对当代社会“祭祀”与“纪念”之间复杂关系的分析,可以透视唯物主义生死观和传统信仰正呈现一种既交汇又对峙的微妙关系。
灾害;民间俗信;公祭;仪式;“头七”
引 言
灾害造成的大规模死亡,是公共权力必须面对的事件。作为“善后工作”的重要一环,为死者举行公祭,既是公共权力对公民的政治责任,也是其道德义务的一部分。对应得体,会强化权力的正当性,而处理失当,则会引起受害群体的不满,甚至导致社会动荡。笔者曾经讨论过唐山大地震的公祭和记忆空间建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商业资本、地域社会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合作、利用、对抗、融合等复杂关系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仪式(如祭祀等)行为和仪式空间的建构往往成为多方力量角力的中心。*王晓葵:《国家权力、丧葬习俗与公共记忆空间——以唐山大地震殉难者的埋葬与祭祀为例》,《民俗研究》,2008年第2期。徐彬对中国汶川地震死难者的公祭进行过专门研究,他认为,汶川地震公祭得以成功举办源自多方因素,直接原因在于社会舆论的大力推动,而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内部(如社会特征、政府特征、情境动力、合法性之间)的相互影响及角力。*Bin Xu,“For whom the bell toll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Sichuan earthquake mourning in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vol.42,no.5,(2013),pp.509-542.
上述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分析权力主导的仪式性行为与“民间祭祀”的关系提供了基础。从上述的研究,我们看到,虽然丧葬习俗作为构成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的一部分,本来就兼有个体性和公共性的两面。但是,公祭和私祭在行为主体上有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公共权力主导下的仪式性展演,后者是个体基于特定的生死观举行的信仰行为。民国以来,革命政权推动的世俗化和科学主义的现世伦理,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生态,对丧葬习俗自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革命政权改造吸收了民间丧葬习俗中某些元素,创造出诸如悼念无名烈士的公共纪念和灾害死亡的公祭仪式。而一方面,国家权力和知识精英以“移风易俗”的方式努力改造民间祭祀方式,比如倡导用献花代替烧纸的“文明祭祀”等。民间对此虽有抵抗,很多民众依然按照地域特有的文化传统来举行祭祖祭神等活动。但是毋庸讳言,接受政府提倡的“文明祭祀”的人越来越多。比如我们在政府建设的唐山地震殉难者纪念墙前面看到的鲜花如海的场面,已经取代了香烟缭绕的原有祭奠方式。我们看到,过去权力VS民间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已经无法解释当代社会围绕公共死亡时间的祭祀或纪念活动的内在机制。我们在这里希望讨论的问题是,国家权力在形构公共仪式时吸收民间习俗元素这一主体性行为,对形成中国的公民文化的意义何在。因为丧葬习俗的背后是人们对生命价值的体认,其仪式是生死观的现实呈现,“视死如生”的文化传统也使得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个的重大课题。本文基于上述的问题意识,希望通过“东方之星”事件的祭奠活动,讨论围绕“祭祀”与“纪念”的文化力学。
一、“东方之星”事件与遇难者祭奠
“东方之星”游轮于1994年建造,船身长76.5米,总吨2200,隶属于重庆东方轮船公司。2015年5月27日,该游轮载406名游客(绝大多数为老年人)从南京驶往重庆。6月1日晚21时30分,游轮于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突遇龙卷风,游轮倾覆翻沉。6月2日凌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湖北省政府三千余名政府人员、武警消防、群众等参与打捞救援,救援至6月8日方结束。事故共造成442人死亡,仅12人生还。
2015年6月7日,官方组织的“东方之星”游轮死难者公祭仪式于湖北省监利县沉船附近江段举行。上午9时,时任中国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杨传堂宣布哀悼活动开始。参与救援的所有人员停下手上工作,脱帽伫立,面向遇难船舶默哀……同时,停泊在附近水域的所有船舶拉响鸣笛。*新华网,“东方之星”号客船翻沉事件救援现场举行哀悼遇难者活动,详见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6/07/c_1115536234.html,2015年6月7日,2015年9月15日。现场各部门、单位统一身着制服,列队整齐,仪式过程庄严肃穆。哀悼活动持续了三分钟,在队伍正后方,醒目的悬挂着数十米长的黑底白字横幅,上书“沉痛哀悼沉船遇难者”字样。
以上也是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中所传送的全部祭奠场景。新华网对公祭现场还作如此描述:“为了哀悼逝者,参与救援的人员在起吊船上搭起一个简易的祭台,上面摆满蜡烛、香、黄色的菊花。”
根据报道,在公祭的同一天,部分死难者家属在江边举行了民间的“头七”祭祀活动。
从7日上午10时开始,一些遇难者家属在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帮助下,陆续来到客船失事现场附近的江岸,为遇难亲人做“头七”祭。许多家属直奔江边,朝向“东方之星”客轮,有的在岸边点起香烛,有的向江中抛撒菊花,有的大声呼唤着亲人的名字。“爸爸,我们回家吧,家中亲戚朋友都在等着您回去!”来自南京的一位年约四旬的女士燃香焚纸,开瓶洒酒,跪在地上,撕心裂肺的呼唤让现场人士无不动容。*沉船现场举行“头七”祭数百人雨中默哀3分钟,新华社,2015年6月8日。
死者家属们来到江边,为遇难的家人们焚香、献花、献供、烧纸、下跪,这些仪式都是民间祭奠亡人的做法,和公祭的程序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两者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时间。换言之,双方都选择了“头七”作为祭奠的日子。
“做七”,亦称“理七”“烧七”“斋七”等,是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地区的一种古老丧葬俗信。*该俗信来源说法不一,最受认可的说法是源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佛教《瑜伽论》谓人死后,谓人生有六道流转,在转生之间,有一个“中阴身”阶段,如童子形,为寻求生缘,以七日为一期,如七日终,不得生缘,则更续七日,至第七个七日终,必生一处,以故有“七七”之期及逢七追荐之俗。(参见《北史·胡国珍传》记载“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另一说法认为做七习俗本于道教。民间做七既请僧众诵经,也请道士诵经。(参见清赵翼在《陔余丛考》卷三十二,赵翼对做七习俗起源进行过探讨:“按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做七”主要指人死后,死者家属每隔七天要在家中举行祭奠仪式,如设灵牌、焚香亮烛、供奉酒肴、做法事等,为亡者修福、超度。仪式累计要办七次,“头七”则是指头一个第七天。*关于“第七日”的时间,各地算法不一,根据现有资料看,主要分为从死亡当日起算、从死亡第二日起算以及根据死亡时辰起算三种算法,而第一种算法普及率最高。中国人认为,死者魂魄会于“头七”返家,家属应于魂魄回家之前,给魂魄预备一顿饭菜,之后举家出外回避。有些地区会在死者魂魄返家经过的饭桌周围撒上草木灰或炭灰,认为魂魄经过时会留下脚印。亦有地区认为死者魂魄会于“头七”当夜子时返家,家属应在家中烧制梯状物,有助于魂魄登天等。
“做七”习俗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始出现于上流社会丧葬习俗中,至隋唐时期,做七习俗逐步世俗化,渗入平民百姓的生活中并传承至今。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做七作为个体性较强、功能单一的祭祀活动,多见于家庭、宗族或地域等私人或小范围社会单位的丧葬仪式中,其举办并无权力、政治指向。*在中国古代,涉及政治意义的祭祀主要有“国家之祭”和“朝廷宗庙之祭”,两者主要祭祀自然神灵和先公先贤等。(参见王宵冰、林海聪:《公祭的语义衍变、古今形态与当代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此类祭祀日期多变、形式多样,与“做七”习俗不存在必然联系。而有关“做七”的记载则多见于风俗志、地方志、传奇、小说中。
辛亥革命后,伴随着国民政府“现代性”的标榜以及知识分子群体对风俗改革、社会进步的追求,民间信仰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中国社会落后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此期间,虽然“做七”俗信并未直接受到严重冲击,但在政治话语中,此类民间俗信已被视为陋俗和“迷信”。
新中国建国后,在关于传统文化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国民政府的思路,同时由于基层管理有效性增强,使“无神论”“科学主义”等世界观迅速至上而下得以贯彻,从而使得与丧葬有关的民间俗信亦开始频繁的与国家政策联系起来。民间俗信一时被统视作“迷信”“四旧”等而遭到全面否定,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影响到中国人的丧葬习俗。时人回忆道:“文革开始之后,丧事也被禁止并以追悼会取代……追悼会在饭后举行,所有人低着头站在灵堂里听大队干部念悼文。悼文大多是讲死者生前的苦难和功德,还要歌颂毛主席……之后不准举行烧纸钱、祭拜等祭祀仪式。”*吴鹤群:《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丧葬仪式变迁——以湘南灵官殿村为例》,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改革开放后,“做七”等丧葬习俗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政府组织的公祭,也开始引入“头七”的做法。2008年5月19日,该日是汶川地震死难者的“头七”,亦是中国历史上首个为普通公民而设立的全国哀悼日。自此,国家权力开始重新与民间俗信结合,“做七“由民间习俗进入国家的仪式层面。*该方案原为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于2008年5月16日提出,他之所以建议中央政府在“头七”设立国家哀悼日,是因为这与我国自秦汉始便流传的民间“做七”风俗相一致。蒲荔子:《专访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解析为何设立全国哀悼日》,南方日报,2008年5月20日。此后,作为一个丧葬祭祀符号,“头七”公祭一再出现于中国各类灾害事件中。而将民俗作为公祭时间设置的依据,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极为罕见的。*由于“头七”俗信的形成与佛教、道教有关。因此,该俗信主要分布于中外华人生活空间以及少数受佛教、道教文化影响的国家,如大中华地区(包括港澳台)、尼泊尔、泰国、日本、新加坡、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不丹、韩国、朝鲜、印度等。
二、“头七”习俗与现代公祭文化
现代公祭文化的诞生可追溯至近代,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普及以及社会形势的需要,在国民政府及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公祭成为民族国家文化建设促进民族认同、塑造民族共同体的一种现代仪式(如祭祀炎、黄二帝、孙中山和革命烈士等),国家权力的主导性和参与者的国民性得到彰显。但此类公祭建立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之上,与建立在公民意义上的公祭仍有较大区别。
中共建政后,民国时期的部分公祭理念为以群众路线立国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所继承,“公祭”中“公共性”的适用范围有所扩大,加上时局的逐渐稳定,使为灾害事件举行公祭成为可能。如1951年,承德市开中国为普通民众举行公祭的先河,为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杀害的承德市同胞举行公祭仪式。但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对日本进行军事扶植。因此,此次公祭政治意义高于信仰本身。而随后数十年,受政治因素影响,公祭在我国几近销声匿迹。直至改革开放后,1985年7月28日,唐山市政府组织召开的唐山大地震九周年公祭大会,这既是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公祭,也可被视作开中国灾害现代公祭之先河。但由于政府缺乏对民间俗信的正确认识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弱化等原因,此次公祭从组织、参与人员再到公祭精神的制定,都为“抗震精神”等一类政治话语所笼罩,较少顾及民间习俗和其背后的文化心理。*王晓葵:《国家权力、丧葬习俗与公共记忆空间——以唐山大地震殉难者的埋葬与祭祀为例》,《民俗研究》,2008年第2期。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2008年5月19日至5月21日设为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而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为普通公民而设立的全国哀悼日,刚刚出现便在全国范围受到热烈回应。
自汶川地震全国哀悼日起,“头七”公祭逐渐为国人所熟知。截至2016年,“头七”公祭已在八年期间内举办了近十次(见表1)。

表1 2008年-2015年“头七”公祭举办时间表(部分)
上表表明,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重大灾害的公祭日几乎都选择了“头七”。在可能的范围内,让自己政策与民间习俗尽可能吻合,是当今国家文化政策的理性选择。其中的益处自不待言,但是,要了解其效果如何,则必须考察在具体的仪式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三、“东方之星”的“头七”公祭
如上所述,2015年6月7日,官方组织的“东方之星”游轮死难者公祭仪式于湖北省监利县沉船附近江段举行。参与公祭仪式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官员、参与搜救的人民解放军、武警、消防部队官兵、公安干警等群体,以及湖北省委省、荆州市、监利县各级政府人员,长江航运系统海事、航道、公安等单位共700余人。此外,除部分记者外,几乎再无其他人出现在公祭现场。等于说,除了传统的“头七”仪式“缺席”外,作为与死者关系最为密切、约2000余人的死者家属群体也同样“缺席”。
镇江籍的死者家属“NN”表示:“当时的救援现场(公祭仪式举办地点)根本没给我们家属进去,头七祭祀是遇难者家属强烈要求下,由地方政府组织我们去江边祭祀的,(家属祭祀地点)离救援现场很远很远,伤痛,一辈子的伤痛。”*访谈人:雷天来,被访谈人:NN,访谈时间:2016年1月21日。
与以上访谈相对应的是其时的新闻:
按照国务院事件救援和处置工作组的统一部署和安排,7日上午9时,赵雯副市长带领上海前方工作组和上海部分遇难者家属在监利县政府会议室一起举行哀悼活动。工作组成员与家属代表一同收看中央电视台遇难者家属悼念活动直播,全体肃立为遇难者默哀。*沈竹士:《上海前方工作组和家属举行哀悼活动》,《文汇报》2015年6月8日。
针对访谈及新闻中可作如下总结:首先,家属不参与公祭并非自愿,而因身处由各地政府主导、安排的其它场合。其次,“公祭日”各级政府、部门均“按部署”,即执行国务院事件救援和处置工作组的决定,陪同、组织各自辖区的家属们在室内观看电视直播或到江边等地,以远离公祭现场、错开公祭时间的方式参与祭奠。第三,尽管公祭仪式的举办相当顺利,家属也可进行私祭,但对于不能去公祭现场这一安排,家属并不满意。
上海市虹口区的死者家属“X娇”对“缺席”公祭一事提出自己的理解:
“头七”的时候基本整个情况就是乱糟糟的,就是上头(政府)知道(救援)已经没希望了,家属还抱着希望。而且说白了,政府就是不想让家属参加公祭才突然说救不了人了,其实早就可以通知了,我也是在‘头七’知道消息的,因为也怕家属闹事。*访谈人:雷天来,被访谈人:X娇,访谈时间:2016年1月20日.
综上,部分家属们对于政府于“头七”安排的不满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因为家属祭祀亲人,却需要通过“争取”来实现;二是他们猜测自己不能参与公祭的原因是政府怕家属借机闹事。
湖北省监利县两办(县政府办和县委办)人员X某在“东方之星”翻沉后,被安排专门协调上海市的家属接洽及善后工作。围绕公祭家属们“不在场”的问题,他则主要提及政府的顾虑。首先,公祭区紧挨沉船现场,在救援结束和事故证据未收集前,为保证搜救、取证等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救援现场附近不宜大规模对外开放。其次,“头七”前后在监理的家属有近两千人,如此庞大的、心理负担严重的人群也不利于统一组织和公祭的顺利进行。特别是,不少家属情绪激动,政府也怕家属到事发现场(公祭场地附近)后会做出过激举动,比如轻生,这会产生更坏的社会影响。而围绕江边祭祀这个话题,X某提出,政府鉴于上述原因,要求他们工作人员向家属解释,希望家属不要在“头七”日去祭祀,但许多家属“意愿非常强烈”。因此,“为了顺应老百姓的习俗,指挥部做出人性化的统筹协调”,上级政府向监利县各单位作出指示,要求他们带领家属去江边祭祀。*访谈人:雷天来,被访谈人:X某,访谈时间:2016年3月10日.
如何看待政府与家属之间的对立,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沉船事件有责任事故的可能性,在没有查明责任之前,遇难者家属很容易对公权力产生疑问和愤怒。我们从对中国历次灾害公祭的梳理中看到,在主要由自然原因引发的灾害(如舟曲泥石流、玉树地震)中,“头七”公祭均向家属开放,尽管家属在公祭中只作为参与者。但在“技术环境”(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技术环境”是人类学关于灾害定义的一大类别,主要指涉引起灾难的认为原因,并区别于自然灾害。“技术环境”这一词语本身不含价值判断,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技术环境”灾害的讨论最终都难免回到对社会(尤其是政治)的反思,从而引发社会震荡。因此,世界各国对此都非常重视。在中国,“技术环境”灾害事件发生后均引发社会热议,并致使事件敏感度升高,而中国政府的管理问题(如疏忽、渎职等)常常成为中心议题。相关的灾害中,中国政府却从未与遇难者家属群体共同参与过公祭,且公祭几乎只向政府人员开放,即使家属们被获准进入公祭现场,也必然与官方哀悼错开。因此,尽管X某关于政府安排的说辞有理有据,但家属与政府的不“照面”,还是引起家属及社会展开负面的猜测。可见,由于“技术环境”灾害本身的敏感性,社会对政府某些行为的判断似乎已经达成某种“默契”。换句话说,“东方之星”公祭的分化更似一种必然的安排。
其次,在中国,非正常死亡后的丧葬活动本身就常常夹杂着争论及诉求,而近年灾害“头七”公祭的政治化,也常致使丧葬活动中的争论及诉求公共化和复杂化。尤其面对“技术环境”灾害时,家属们关于“政府怕闹事”的叙事实际上代表了一种社会普遍认识,即“闹事”是直接有效的维权方式,是家属对政策进行直接影响的一种民间逻辑。如2015年初,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头七”公祭中,就有不少遇难者家属不顾工作人员阻拦,执意向在场媒体诉说不满,以期向政府施压,扩大事件影响力。*叶宇婷《外滩踩踏事件记者手记:头七现场家属要求追责》,参见http://www.m4.cn/opinion/2015-01/1258595.shtml,2015年1月6日,2015年3月15日。因此,尽管“东方之星”事件受访家属说当时并未声称要通过公祭来与政府进行交涉,政府工作人员也不认为政府所为是在防止“闹事”。但当“东方之星”事件的家属不被允许出现于公祭现场时,家属自然就产生“政府有意为之”的联想。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看到将“头七”习俗纳入共祭仪式产生的问题,表面上看,政府举行的公祭,部分排除了死难者家属的参与,主要是因为担心家属“问责”可能导致的混乱。如果单纯从技术层面来考虑,我们很容易认为,如果政府部门的工作细致些,信息的沟通更透明些,上述问题就可以解决。
但是,唐山大地震的例子告诉我们,即便象地震这样的纯粹自然灾害引起的灾难,作为公共事件的处理方式,也不可能完全按照民间的丧葬习俗进行的。换言之,冲突的背后是一个丧葬习俗与公共事件处理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东方之星”的例子来看,我们可以找出一个世俗性事件处理与信仰性阴阳沟通仪式之间的矛盾。我们知道,在中国,丧、葬、祭是处理死亡的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仪式有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某个环节如果出现问题,仪式是不能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的。比如死因不明,或者围绕死因有争议,尸体是不能埋葬的,仪式就停留在“丧”的环节,不能进入“葬”,而后面的“祭”也就无法举行。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祭”的“头七”习俗会临时冻结。“东方之星”之类的事故,6-7天之内,让家属完全接受家人死亡的结果,进入“祭”的环节,本身具有技术层面的困难。因为“翻船”,很容易被怀疑有人为造成事故的可能,或者救援不力造成不该有的死亡等,当家人对死亡原因有怀疑的时候,他们的仪式感还停留在“丧”的阶段的时候,“头七”作为祭祀亡灵的功能是无法实现的。
四、“祭祀”还是“纪念”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同样在“头七”的日子里,灾害现场事实上举行了两个仪式,一个是官方的公祭、一个是民间自发的民祭。而官方的公祭选择了“头七”,可以理解为权力对民间习俗的尊重和顺应,甚至可以解释为国家权力“人性化”的进步。但是,上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冲突和矛盾依然存在,而且似乎并非是“工作做细致一点”就可以解决的。我们认为,正是“祭祀”和“纪念”这两个观念上的差异性,造成了上述的矛盾和对立。
我们知道,“祭祀”的本质是人与魂灵、鬼神沟通的仪式,其存在的前提是祭祀者相信和俗世相对,存在“灵界”。祭祀的仪式过程,比如诵读祭文、烧纸、献祭、上香等,都是和“祖灵”或“鬼神”沟通的方式。本文中的“做七”,就是迎接魂灵回家的意思。
在“东方之星”民祭的现场,死者家属们为遇难者焚香、献花、献供、烧纸、磕头,以及呼喊,都是和已经去往“异界”的亲人互通信息、传达情感的行为。即使在唯物主义、科学主义教育渗透到每个角落的中国社会,人们或许在理智上未必真正接受鬼神的存在,但是在主观上、情感上“希望”“要求”有这样的存在,唯有如此,才能满足自己对逝去亲人的眷恋和情感,这种“主观事实”的存在,是“祭祀”得以存在的心理和社会基础。基于上述的“神灵在场”的仪式活动,无论是公祭还是私祭,都可以成为“祭祀”。而事实上,采用“祭祀”的方式举行公祭并不少见。
如在2015年2月4日的台湾复兴航空空难分别举办了“头七”法会及“头七”公祭*台湾复兴航空空难“头七”法会于“头七”前一天(9日晚)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举行,后台北市政府与复兴航空于2月10日在该殡仪馆举行联合“头七”公祭,大陆及台湾方面各界代表参加公祭仪式。,头七法会由佛光山法师主持,法师带领罹难者家属引灵,家属手捧灵位,在法师引领下步入法会会场,4名法师礼诵《佛说阿弥陀经》,全程约3小时。为尊重家属意愿及隐私,场内不开放媒体进入。*台湾复兴空难罹难者“头七”法会举行3人仍失踪。详见http://news.xinhuanet.com/tw/2015-02/10/c_127477232.htm,2015-02-10/2016-03-03.
而在2012年10月1日香港南丫岛沉船事故“头七”公祭现场,香港道教联合会及港九小轮(涉事公司)分别为死难者进行超度法事。道教联合会的仪式在港灯公司鸭脷洲码头举行,逾百家属出席。家属先在码头致祭,以一炷清香、三鞠躬之礼拜祭至亲,由法师为死难者招魂及超度。海祭原定一小时,但强忍悲痛的家属不愿匆匆挥别至亲,法师应要求再诵经一遍。*《港撞船事故死者“头七”逾百家属送别》,《大公报》2012年10月8日。
以佛教和道教方式举行的“头七”公祭,遵循的是以“异界”存在为前提的信仰逻辑,佛教的礼诵经文、道教的超度法事,都是沟通人世与灵界的仪式性行为,在这里,公祭、民祭即使在规模、具体作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内在的文化逻辑是相通的。
而大陆政府在民国时代开始,就彻底推行了基于世俗主义、唯物主义生死观的丧葬仪式。这种仪式虽然也使用一些传统仪式的做法和说法,比如焚香、献祭、诵读祭文,在用词上也有诸如“安息吧”“英灵”“一路走好”,这类拟制灵魂存在的语言形式。但是,其背后的逻辑基础是否认灵魂的存在,仪式的对象目标不是死者,而是生者。形成当代中国丧葬文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文献,当推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这两部家喻户晓的作品的写作年代都是抗战时期,毛泽东参加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葬礼的时候,发表了如下讲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4页。
而对白求恩的死,有如下评价:
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6-10页。
毛讲话的核心是将死者的生命价值化、意义化,来教育生者。《为人民服务》虽然是在张思德的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但是,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的“祭文”,因为其言说的对象不是死者张思德的“灵魂”,而是参加张思德追悼仪式的人们。同样,《纪念白求恩》也同样是写给还活着的白求恩的同志们看的。换言之,如果说“祭祀”的本质是“灵魂在场”“纪念”的核心就是“生者指向”。前者是信仰的、后者是科学的。因此,以唯物主义、科学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政府,在丧葬习俗的问题上,采取了“变偶像崇拜为科学纪念”(胡乔木语)的方针。在这样的方针下,大陆即使公祭的时间外壳是采取了类似“头七”这样的“祭祀”的方式,其内容依然是“纪念”的方式。传统祭祀元素几乎被完全剔除。其目的也不是“慰灵”,“祭祖”,而是现实的政治或其他目的。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仪式上,明确说明了这一点。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4页。
寄托哀思,团结人民,显然已经和亡灵没有任何关涉,而是成为建立认同的一种方式。
比较港、台地区和大陆的公祭仪式,不难看出,前者无论是家属祭拜,还是僧道诵经超度,形式和内核都是“祭祀”。而大陆公祭在则是强调“纪念”的意义。比如唐山大地震后的首次公祭中,仪式也主要以默哀、敬献花篮等来表示哀悼,唯一可体现传统形式的只有公祭会场的一副挽联。*王晓葵:《国家权力、丧葬习俗与公共记忆空间——以唐山大地震殉难者的埋葬与祭祀为例》,《民俗研究》2008年第2期。而在近年中国历次“头七”公祭中,几乎都是“纪念”为内核的“头七”仪式,
但是,和战争、革命中的死者不同,灾难死虽然“不幸”,但是和战死不同,它很难直接“价值化”或“意义化”。所以,在早期的纪念文化主导的纪念仪式,需要把“灾难死”转写成“抗灾精神”,比如唐山市政府组织举办最早的公祭,以“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等标语来呈现纪念的意义。
涂尔干说,公祭致哀并不是社会对死亡的一个自发的反应,实际上,更是一个复杂的象征性的和具有政治意义的实践。*Durkheim.E.,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New York: Free Press, ([1912] 1995).这个判断正是“纪念”文化的核心意义。我们分析“头七”公祭在大陆的仪式行为过程中产生的内在矛盾的原因的时候,有必要将社会对死亡的自发反应的“祭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性行为的“纪念”区别开来考虑。唯有如此,才能理解尊奉唯物史观的国家权力主导的“公祭”无论如何也无法取代“私祭”的原因。两者的关系的背后,是科学的生死观和传统信仰的对峙。虽然“纪念”的生死观在逐渐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文化逻辑,日益主导公共文化中的仪式行为,但是,“科学纪念”也无法取代“偶像崇拜”所承担的情感和信仰上的功能。两者通过丧葬仪式上对立与合作,共同塑造了当代社会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 赵彦民]
王晓葵,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241);雷天来,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生(上海 20024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灾害记忆传承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4ASH01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