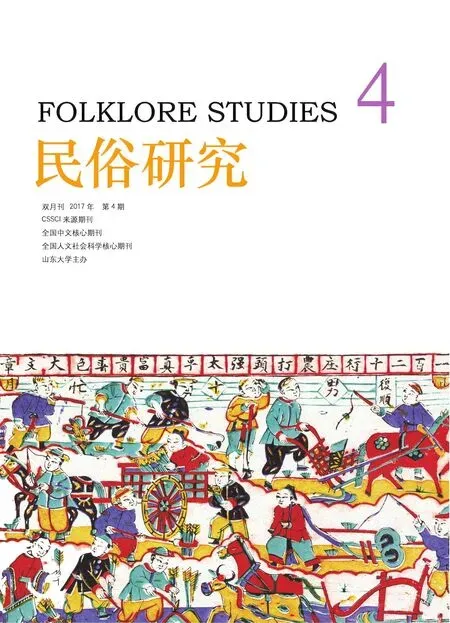先秦民间信仰与民神易位的反向衍进
——以兵学考察为中心
2017-08-31王震
王 震
先秦民间信仰与民神易位的反向衍进
——以兵学考察为中心
王 震
先秦自春秋以降,民间信仰中的“鬼神”,相对于日渐觉醒的人性精神,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但军事巫术却空前兴盛。民间信仰与民神易位在兵学领域呈现出反向衍进的态势。民神易位思潮肯定了人的价值,而基于民间信仰的军事巫术的兴盛,标志着兵民的心理诉求被纳入指挥决策的博弈,反映了对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灵归宿的观照与反思,二者是在不同向度上诠释了先秦人性意识的觉醒,为后世确立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信仰长期共存的二元对立结构,乃至构建多元语境交融下的文化生态,奠定了基础。
民间信仰;民神易位;反向衍进;兵学
一、上古神权垄断与民间信仰的调适与疏离
上古社会宗教的衍进,是一种官方神权垄断与民间信仰发展相互调适与疏离的复杂进程。众所周知,这个进程当始自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尚书·吕刑》,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48页。,以试图终结“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国语·楚语一》,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515页。的社会现象,将“通神”的宗教权力收归统治集团。但从后来的历史看,“民神杂糅”的情况似乎并未就此根绝,至少“绝地天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颛顼之后,统治者为垄断神权、巩固王权又多次采取措施。如《左传·宣公三年》载王孙满述及“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868页。,将各氏族崇拜的神祇集中绘制于所铸鼎上,实质上是夏后统一管理各族图腾的举措。再如《史记·殷本纪》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04页。武乙所为,极似魇胜一类巫术,结合殷商重巫传统分析,此当是天子与传统宗教势力发生了某种冲突所致,显然与神权争夺有关。又如西周之初,礼乐文化逐渐取代旧有的巫史文化传统,据《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57、758页。云云可知,此时以昊天和祖庙为祭祀对象的鬼神崇拜构成了社会信仰的内核,然而周王室严格限定了“通神”的等级,“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礼记·曲礼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268页。,特别是作为至上神的“昊天”,只许天子祭祀,而“免使人民有对神作偶像礼拜之习”*[日]五来欣造:《儒教政治哲学》,胡朴安、郑啸厓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5页。,即明确将交通上帝之权垄断于天子一人专属。
神权一经垄断,从理论上区别所谓“正祀”与“淫祀”则成为可能。《礼记·曲礼下》:“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268页。赵世瑜以“精英宗教”和“民间宗教”划分二者。*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第81页。这大致符合我国中古以后的历史情况,但在上古时期,恐怕还不能作此划分。先秦时期的民间宗教,几乎可以等同于社会宗教,因为先秦“社会结构的基本组织形式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面还是氏族及宗族,所以当时的民俗便具有着广泛的社会性质”*晁福林:《先秦民俗中的几个问题》,《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前,民间信仰实际上就是氏族信仰,“社会上还没有多少独立于氏族之外的‘民’”,与“秦汉以降的编户齐民时代”*晁福林:《谈先秦时期的“民”与“俗”》,《民俗研究》2002年第1期。大不相同。所以,按照后世的情况将上古社会宗教分裂为官方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二元对立结构,显然是不合适的。上古社会宗教主要形式就是民间信仰或氏族信仰,亦即西方民俗学所定义的popular religion或folk religion(大众宗教)。由此,我们必须厘清,“绝地天通”所垄断的是“通神”之权,而非信仰之权,这与后世朝廷禁绝民间秘密结社的情况是不同的。因此,统治者一方面力图垄断“通神”之权,以实现对民间信仰或氏族宗教的有效干预和控制,另一方面又必须适应和尊崇氏族宗教,借重民间信仰来树立权威。《周易·观·彖传》“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36页。,无疑“神道设教”必须建立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信仰根基之上,只有对固有民间信仰予以认可,才能使天下信服,否则,必然重蹈商纣王“弗事上帝神祇”*周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誓曰:“惟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此伐纣檄文,罪其亵渎上帝祖先,盖殷纣王之败亡,虽有多重原因,亦当与其曾试图挑战社会民间信仰,未能妥善处理而得罪于宗教传统势力不无关系。参见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20页。又《尚书·泰誓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80页。覆辙,付出惨痛代价。
二、从先秦兵书看民神易位思潮对民间信仰的冲击和影响
上已述及殷周之际传统的巫史文化开始向礼乐文化过渡,西周的民间信仰已将最重要的鬼神崇拜对象指向昊天与祖庙。不仅如此,周人对神(“昊天上帝”)所持态度已与殷商之民大不相同。《礼记·表记》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642页。在周人看来,“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81页。,故提出“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505页。“敬德保民”*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卷三《尚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7页。的思想。到西周晚期,周人甚至开始对昊天上帝表达控诉和不满,如《诗经·小雅·节南山》“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441页。。这些都是春秋民神易位之先声。到平王东迁之后,随着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原有的意识形态受到挑战,民间信仰中的“鬼神”,相对于日渐觉醒的人性精神,开始退居次要地位,人们普遍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085页。,因此“春秋时期在民与天、神孰重孰轻、孰主孰次的问题上,主导性的观念是民为主,而天神为次”*陆玉林:《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8页。。
受此影响,兵学著作中时时映射出些许唯物主义色彩。如《孙子·用间》篇“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第290-291页。,主张依靠人、而不是靠祭祀和术数以刺探军情,预先掌握信息。《吴子·料敌》篇“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有不占而避之者六”*高体乾等:《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43、44页。,列举了不用占卜而直接根据战场环境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情形。《司马法·定爵》篇提出“灭厉祥”,即禁止巫觋术数言论在军中蔓延,并将“灭厉之道”概括为“义”和“权”*高体乾等:《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74-75页。,也就是利用正能量的传播和因势利导,来确保军心的稳定。又《六韬·犬韬》(逸文)“用兵者,顺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则三军败亡”*杜佑:《通典》卷一六二,中华书局,1988年,第4176页。按宋颁《武经七书》原无此句,据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卷三辑入《六韬·犬韬》。,似乎天道相对于人事来说,反而无足轻重。问世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兵书,几乎都能从中找出轻鬼神、重人事的记载,这是当时的民间信仰受到民神易位思潮冲击的重要印记。
然而,若以上述片言只语认定这些兵学著作对于巫觋术数持全然批判立场,则未免轻率。固然,在当时“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轲等:《孟子·滕文公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4页。的残酷现实面前,迫使兵家逐步接受务实的世俗政治理性意识,但传统的民间信仰未必会瞬间终结。从以上所引文本看,《孙子》所谓“不可取于鬼神”云云,乃仅是就用间一事而论,非但不能过度解读,相反恰恰表明“取于鬼神”在当时是常规做法。《吴子》列举“有不卜而与之战者”“有不占而避之者”,亦说明占卜相当普遍。《司马法》“灭厉祥”之说,并非因为“厉祥”没有价值,而是为了稳定军心采取的保密措施。这一点可以同《墨子》相印证。其《迎敌祠》篇云:“望气舍近守官,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请守,守独智巫、卜望气之请而已。其出入为流言,惊骇恐吏民,谨微察之,断罪不赦。”又《号令》篇亦云:“望气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与望气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请报守上,守独知其请而已。无与望气妄为不善言惊恐民,断勿赦。”*吴毓江:《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第895、922页。此言守城之时,巫觋人员近太守而居,以便集中控制管理,他们要向太守报告实情,而对民众则只能报喜不报忧。《孙子·九地》篇“禁祥去疑”*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第249页。亦与此同。
到别人家做客,要走了,我说“不用送了”,然后拉开一个门是卧室,再拉开另一个是卫生间,最后,还是被送出去了……
尤其值得注意者,《孙子·计》篇将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总结为道、天、地、将、法,其中,“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杜牧注:“阴阳者,五行、刑德、向背之类是也”*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第4页。。《司马法·定爵》篇亦云“顺天、怿众、利地、右兵,是谓五虑,顺天奉时”*高体乾等:《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72页。。这显然是将术数方技之学纳入军事运筹的核心内容。
要之,从兵学领域看,民神易位思潮对于民间信仰虽有冲击,而影响极其有限。根据目前可见的文献资料,很难支持当时主流兵学理论对于军事巫术具有整体倾向性的批判态度。相反,民神易位思潮的传播越久,人的价值越被发现和认可,军事巫术反而越兴盛,且渐有学术化、理论化之势,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悖论。
三、民神易位思潮干预下军事巫术的发展与兴盛
民神易位的春秋战国时代,正是军事巫术空前发展和兴盛的时代,而且在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环境下,原有的民间信仰经士人吸收阐发,形成了阴阳五行学说,在兵学领域则催生了兵阴阳一派的兴起。
上古民间信仰中通行的一些传统巫术,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成熟,并在军事上广泛运用。自殷周以来,建立在民间鬼神信仰基础上的种种仪式贯穿军事活动始终,而犹以祭祷为头等大事。春秋时期,宗周礼制虽多崩坏,而军事祭祷反而日臻系统完善,主要表现为:“春秋在西周的基础上,一方面各国对上帝、祖先和诸神祇的祭祀和祷祝活动盛行并高度礼仪化;另一方面,因诸夏、夷夏间战争频繁,攻伐不断,规模和残酷程度逐渐扩大,‘祀’与‘戎’这两件‘国之大事’的相互结合也更加紧密。”*邵鸿:《春秋军事术数考述——以〈左传〉为中心》,《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1999年第1期。《墨子·迎敌祠》详尽记载了守城作战临战之前的祭祷仪式:
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长八尺者八,弩八,八发而止,将服必青,其牲以鸡。敌以南方来,迎之南坛,坛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长七尺者七,弩七,七发而止,将服必赤,其牲以狗。敌以西方来,迎之西坛,坛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长九尺者九,弩九,九发而止,将服必白,其牲以羊。敌以北方来,迎之北坛,坛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长六尺者六,弩六,六发而止,将服必黑,其牲以彘。从外宅诸名大祠,灵巫或祷焉,给祷牲。*吴毓江:《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第894-895页。
此篇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三条重要信息:(1)从“敌以东方来,迎之东坛,坛高八尺”的记述来看,祭祷程序规则极其严格,可证邵鸿先生所谓“高度礼仪化”之说不虚;(2)从守城之将主持祭祷,且与上引“望气舍近守官”“望气者舍必近太守”之语相印证,可知彼时一城之长(太守)即可“通天”,并在城中配备了专事巫术者,表明通神权限的下移与普及;(3)祭祀程序以东南西北的方位与青赤白黑之色彩以及八七九六之数相配,显然由五行相生相胜之说与易卦象数之变推演而来,必与兵阴阳家(详下)关系密切。
先秦的军事巫术,在宗庙除祭祷外,往往还要卜筮,即龟卜和筮占。同上文提到的祭祷和望气等术一样,龟卜原为殷周王室所垄断,也正是从春秋开始,随着王官失守、学术下移,进入了大普及的时代。据刘玉建统计,《左传》所载卜例与战争有关者多达20次。*刘玉建:《中国古代龟卜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74页。这20次军事龟卜中,有2次违卜值得注意。
其一在定公九年,“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卜过之,龟焦”*《左传·定公九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144页。,龟甲烤焦而不成兆,本不可以行事,卫侯执意为之,但最终并未遇到凶险,卫军安全通过了中牟。其二在哀公二年,“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铁”,战前卜之,龟焦,但是乐丁认为,“谋协以故兆,询可也”*《春秋·哀公二年》《左传·哀公二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155、2156页。,也就是说,先前曾为类似的事情作过龟卜,而得吉兆,今可参考上次,不必另卜,所以,这次龟焦是不算数的。赵鞅从之,果然大败郑师。
这两次违卜而取胜,说明春秋晚期,在民神易位的思潮冲击下,原来的社会民间信仰受到挑战,神的旨意有时仅供参考。然而,“仅供参考”,也是有参考价值的,特别是第二次违卜,还必须用“谋协以故兆”的借口以自圆其说,这就说明,“违卜”的事毕竟不能堂而皇之。而且,我们更应看到,《左传》载军事龟卜20次之多,除以上2次之外,其余18次皆依卜兆而行,且最终应验。这当然并不是因为龟卜本身具有某种科学性,而是由《左传》的作者在史料取舍方面的思想倾向所致,东晋范宁谓“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范宁:《穀梁传集解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361页。,殆即此意。然而范氏不知,《左传》之“巫”恰恰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像秦、齐、晋、楚一些大国,几乎每战必卜,对于龟卜的认可,大致代表了当时社会民间信仰的主流。
筮占原为龟卜的辅助。据邵鸿统计,《左传》计卜54次,筮18次,卜筮并用7次,6次为先卜后筮,只有1次反之*邵鸿:《春秋军事术数考述——以〈左传〉为中心》,《昌大学学报(人社版)》1999年第1期。,可见春秋以前,筮占居次要地位。而《周礼·春官·筮人》“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805页。,当是战国时期的情况。然而无论二者怎样此消彼长,总体来看,龟卜和筮占皆未衰退,反而更加兴盛。
春秋战国时期的巫术在军事领域应用广泛、形式多样,诸如星占、望气、择日、解梦、诅咒等等,大多早已有之。如乐律之占,早在殷周之际就已用于军事,“武王伐纣,吹律听声”*司马迁:《史记·律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240页。,春秋时,“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左传·襄公十八年》,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966页。,可见此时以乐律卜出兵吉凶更加趋向专门化,随军配有乐师,专司此术。
春秋军事巫术的兴盛,造成了巫觋人员的迅速扩张。过去王室垄断的“通神”之权,随着王官失守而下移,在诸侯乃至卿士、家臣当中间迅速普及,民间也产生了为宗族、村社服务的巫觋卜筮之人;到春秋晚期,巫觋人员进一步增加,战国时进而出现了诸多专事术数、方技(如上述星占、望气、择日、解梦、诅咒等等)的从业者。*邵鸿、耿雪敏:《战国民间的巫觋术士群体》,《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活跃起来。
据庞朴考证,阴阳思想源自南方楚地的枚占文化,至老子而抽象为一种哲学思辨,五行观念则是殷商龟卜文化遗存,阴阳五行学说乃是“不同系统的文化发生接触”,“经历容忍、冲突与融合”*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的产物。战国前期的齐人邹衍,借助稷下学的根基,进一步总结和深化了五行理论,并发展出五德终始学说,从而成为阴阳家的集大成者。同样在稷下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司马法》《六韬》《孙膑兵法》等一批齐国兵学的代表性著作相继问世,出奇设伏的变诈之兵从战争实践上升到学术层面,标志着先秦兵学的重大转型。稷下学术争鸣条件下,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滋养与战国战争形势的历史变革,催生了兵阴阳学说的产生。兵阴阳学说是军事巫术学术化理论化的产物,标志着在多种学术思潮碰撞与交融的影响下,军事巫术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汉书·艺文志》将兵阴阳的学术特点总结为“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0页。,这说明兵阴阳其实是多种术数方技理论在军事领域的深化与整合。上引《墨子·迎敌祠》所述临战祭祷仪式,显然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与兵阴阳家不无关系,同时该篇又提到了望气之术,“凡望气,有大将气,有小将气,有往气,有来气,有败气,能得明此者,可知成败吉凶”,又言及“举巫、医、卜有所长”*吴毓江:《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第895页。,说明巫医、术数、方技一般相互结合,而又划分不同门类,各有专攻。
兵阴阳家的范畴其实仅仅是一个门类,而非门派。据《唐李问对》卷上:“今世所传兵家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高体乾等:《中国兵书集成》(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240页。笔者认为,兵家四种当是编纂《司马法》的稷下学者,在为齐国梳理和总结兵学理论时,按照学术领域的差别所作的细分,至汉代,张良、任宏先后校书,并仍之,遂传至后世。所以,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之间,并不存在像“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那样的相互论争与批判。后来传世的《孙子》《吴子》《司马法》等著作,多讲权谋,探讨战略运筹,而于阴阳、技巧一类专精之学涉及较少,此术业有专而已,并无门派之见。至于兵家文献对于“鬼神”“厉祥”一类,似屡见摒弃禁绝之论,实有过度解读之嫌,这一点上文已作分析。总体来说,在当时军事巫术空前发展兴盛的历史条件下,兵阴阳学的实用价值其实颇受兵家推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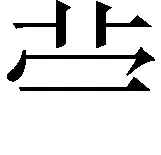

兵阴阳学融合多种术数方技理论以择吉用兵,影响甚广,今传世兵书多可见其遗迹。如《孙子·火攻》篇:“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第279页。又如《司马法·定爵》篇:“时日不迁,龟胜微行,是谓有天。”*高体乾等:《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73页。可见当时的主流兵学,对于兵阴阳学非但不排斥,而且十分认同。
经兵阴阳家发展最为完备的是星占之学,即班固所谓“随斗击”者。据江晓原统计,《史记·天官书》的星占学内容共17类321款,17类中以军事类为最多,计142款,占总数44.2%。*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4页。这反映了战国时期“争于攻取,兵革更起”,“臣主共忧患,其察禨祥候星气尤急”*司马迁:《史记·天官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344页。的情形。兵事越频繁,星占的需求就越急迫。诚然,对于星占一类数术之学,也有像韩非那样“龟筴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战”*韩非:《韩非子·饰邪》,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第122页。的质疑,然而这样的声音十分微弱。“‘天人感应’‘天垂象,见吉凶’的观念广泛深入人心”,“先秦典籍中,我们虽然可以找到上面所举的那类怀疑、贬斥星占学的少数史料,但更多的史料表明,那时各国统治者都是深信星占学、并且以星占学来指导他们的军国大事的。”*江晓原:《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3、155页。事实上,大量文献表明,包括星占学内的整个兵阴阳学说,乃至军事领域一切借重玛那力量的信仰及其表现形式,在当时受到广泛推崇,这是整个社会从平民到贵族普遍秉持的理念。
四、先秦民间信仰与民神易位的反向衍进态势解析
上文已经提及,战国中期以前,上古社会的民间信仰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氏族宗教,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氏族之外的“民”可以忽略不计。从战国中晚期来看,继商鞅率先实施“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鞅等:《商君书·境内》,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第114页。的法令之后,各国普遍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社会宗教系统也逐步呈现出后世民间与官方二元对立结构的雏形,“正祀”与“淫祀”之别渐趋明晰。但是,此时的军队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于郡县征兵制和军功授爵制的普遍实施,不仅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农民在士兵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韩非子·显学》,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第460页。渐成常态,出身低微的将领日益增多,打开了民间信仰渗入高端意识形态的传导通路。
正因如此,以兵学为中心考察上古社会宗教,就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民间信仰的发展与民神易位思潮的传播,呈现出反向衍进的态势。民间信仰的发展轨迹,经历了从原始的鬼神崇拜,到高度礼仪化的巫术,再到学术化、理论化的术数方技的演变历程;而民神易位的思潮,源自人性意识的觉醒和鬼神地位的下移,与民间信仰的演变形成了一种对抗性因素。然而在军事领域,这种对抗性因素并未引发兵家对鬼神崇高的消解,相反却表现为军事巫术在战争中的运用日益普及和广泛,且更加学术化、理论化,并最终衍生出兵阴阳学术体系。这一现象表面上看是一种二律背反,实则为同一命题的两个向度。无论是民间信仰在兵学领域的发展,还是民神易位思潮的兴起,本质上都根源于人的价值的自觉。
先秦社会从殷周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进入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王室衰微,强卿擅权,诸侯争霸,大国兼并,战争规模日益扩大,武器装备的进步、战略战术的更新,使得战场的拼杀愈来愈惨烈,一般来说胜负双方都要面临惨重的伤亡代价。与此同时,社会的进步促进了战争参与者的个体意识日益觉悟,战争个体(即士兵)的心理状态,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胜负不仅决定于交战国的经济、政治、人口数量和技术水平等条件,而且也决定于一国的民气了”*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16页。。在战场上,残酷与血腥的强烈刺激可能激发各级军吏士兵杀气腾腾的野性,而生命的脆弱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惊恐和沮丧,此时,鬼神信仰和巫术的意义就凸显出来。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通过对原始巫术仪式的考察,曾将初民宗教信仰的社会功能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注意到自保本能底另一套势力,使因生底欲求而来的积极冲动得到圣化的作用,变得有条有理,于是人心乃得安慰,乃得精神上的完整”;
第二,“又不单专使个人精神得到完整,同样也使整个社会得到完整”;
第三,“战胜恐惧、失望、灰心等离心力,而使受了威胁的群体生活得到最有力量的重新统协的机会、再接再厉的机会”。*[英]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9页。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巫术,正是在上述三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不需要去纠结或苛求当时各国将领和主流兵学理论对于军事巫术是否有一个科学的认识,重要的是,这些巫术确实能给军事行动的参与者带来一种积极的有利于夺取战争胜利的心理暗示(前提是“巫、祝、史与望气者必以善言告民”)。因而,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巫术的发展普及,以广泛的敬神事神为外在形式,而目的在服务于人——调动人的精神层面的积极要素以发挥最强战斗力,标志着兵民的心理诉求被纳入指挥决策的博弈系统,是人的价值得到尊重的另一种体现,也是民神易位社会图景的“B面”。如果说民神易位思潮的意义在于肯定人比神更加重要,而基于民间信仰的军事巫术的发展普及,则是对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灵归宿的观照与反思,二者是在不同向度上诠释了先秦人性意识的觉醒。
五、余 论
先秦民间信仰与民神易位的反向衍进实质是民间宗教的人性化与工具化的冲突。社会的进步刺激了人的精神需求,人的价值渴望得到尊重,一方面试图冲破宗教的桎梏而挑战神权,另一方面又追求“与神共舞”以满足信仰需求;作为统治阶级,则在不断垄断神权、利用宗教发挥稳定秩序和富国强兵作用的同时,又不得不对民间信仰作出妥协和适应。这就为后世大一统世俗政权下,确立正祀与淫祀、官方宗教与民间宗教的二元对立结构埋下了伏笔。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提出著名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即“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89页。。中国古代社会宗教系统的二元对立结构,作为一种“结果”,它缘自历代统治者难以跳出的“神权垄断的悖论”*邵鸿:《神权垄断的悖论:中国古代国家对术数活动的限制与两难——侧重于兵阴阳学方面》,《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一方面大搞神道设教,宣扬君权神授,并限制管控乃至严禁民间信仰和巫术活动,另一方面却又导致官府豢养下的数术方技之学日益僵化萎缩,而不得不征集活跃于民间的江湖术士,刺激了民间信仰的发展;而作为一种“中介”,中国古代社会的民间秘密结社传统正是长期依存于这种结构的,由此而在民间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一股反抗的暗流,当社会的失衡状态凭借自身的调适机制难以自愈时,就会异化为强大的爆破力(如黄巾军、白莲教、义和团等),这又迫使统治者反过来打压民间信仰,以规避可能造成的原有社会秩序的破坏。在“结构二重性”规律制约下,中国传统社会的多重宗教和社会思潮之间,反复上演着先秦那种“反向衍进”的张力,从而为社会多元信仰的共生提供了适宜土壤,也为中华精神的传承发展,构建了多元语境交融下的文化生态。
[责任编辑 龙 圣]
王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山东济南 250100)。
本文系第56批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项目编号:2014M561898)、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年团队项目“兵学视域下的经传体式研究”(项目编号:IFYT1702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