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岛屿写作:和四位导演谈镜头下的文学大师
2017-08-17
“目宿媒体”近几年推出《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系列电影》,他们主张以纪录片为媒介,透过年轻导演的诠释,把战后最重要的文学家介绍给新生代读者。他们的缘起提到:“藉此永久记录作家的重要事迹,也希望透过这些作品,重燃新一波的书写复兴。”
《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纪录片共出了两个系列,以大师为名,选取13位作家,并称为港台文学代表,一共拍了13部。13位作家是:杨牧、郑愁予、周梦蝶、余光中、林海音、王文兴、白先勇、洛夫、痖弦、林文月、西西、也斯、刘以鬯。
文学迷怕画面毁了大师的文字,镜头打扰大师的生活,四位导演用他们的电影专业告诉你,请放心。
【原编者按】
文学和电影的关系,历来是备受争议的。相比这时代的许多宠儿,文学的世界更为纵深、隐晦;许多作家更是隐身于文字背后的另一番世界,你在生活的表象中未必能够识见。镜头可以把他们的世界带到我们面前吗?2013年,美国导演Shane Salerno拍摄了《麦田守望者》作者塞林格的纪录片。文学和电影的相遇,越来越不局限于文学作品本身,还有创作者的人生。
2009年,和硕联合科技董事长童子贤,与行人文化实验室合作成立目宿媒体。创业之作《他们在岛屿写作:文学大师系列电影》,希望通过纪录片为媒介,让年轻导演的电影语言作为引路人,将台湾战后最重要的文学家介绍给新一代读者:“藉此永久记录作家的重要事迹,也希望透过这些作品,重燃新一波的书写复兴。”
时隔三年多,文学大师系列电影《他们在岛屿写作2》终于在香港上映。第二系列带来六位导演的作品,他们用电影,展现了七位文学大师的魅力。七位大师:白先勇、林文月、洛夫、痖弦、西西、也斯、刘以鬯。他们的魅力不仅在于文学作品,也在他们的人格、品性,以及他们的人生,同台湾、香港两个文化多元、身份复杂之地相映照。
是在拍大师的作品,还是拍这个人?“岛屿”系列的每位导演,都有这样相似的开始。他们知道作家的人生与作品是两回事,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这些大师的人生,也是生动的文学史。
电影和文学不能互相替代,导演们无意将大师的文字视觉化,也并非要解密他们文字背后的日常生活,满足好奇心。而是希望文学和电影,在他们的故事中,做一次有意思的对话。
2016年1月7日,香港首映典礼前,端传媒访问了四位台湾导演,谈他们与各自电影主人公的缘分、互动,拍摄时的趣事,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以及取舍处理的考量。以下是访谈摘要:
邓勇星:陪伴白先勇先生,走进他姹紫嫣红的人生花园
白先勇,22岁创办《现代文学》,小说《台北人》、《孽子》是一代人的文学记忆。从投身青春版《牡丹亭》复兴昆曲,到近年写作《父亲与民国》、《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追忆历史,邓勇星说:“他在看过这么多人物沧桑,最后沉淀出来的是一丝温暖。”
邓勇星,台湾导演,2002年推出改编自痞子蔡同名小说电影《7-11之恋》;2011年,电影《到阜阳六百里》,获得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最佳导演、第四十八届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和最佳女配角。)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 最早接触的白先勇先生作品是哪一部?
邓勇星(以下简称“邓”):《孽子》,学生时代就看过他的小说。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台湾很有名的作家,那时候也没有深入研究,就是看一个很好看的小说。
端:拍摄之后对他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邓:之前对他本人没有什么想象。慢慢介入开始交流,这也是第一次。他的人格魅力,是值得我们这些从事创作的晚辈学习的。比如温暖、诚实,他说从事文学,必须要百分之百诚实。任何创作都是一样的。
端: 在片中着重突出的部分有哪些?
邓:拍这部片就像写一本书,他本人就是一本很厚的书。每个篇章都有自己的价值,不太能忽略。他和朋友的感情直接影响他的创作态度;他对父亲的感情;他对民国史、对国家的看法;对昆曲文化的使命感……这些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白先勇的部分。篇幅上因为复杂程度,做一些调整而已。但不能用素材在片中的长短,判断我们觉得哪部分比较重要。
端:在拍摄过程中,和他的互动中,你的角色是什么?
邓:我更像是一个陪伴的人。不全然是观察者,也不像我在访问他。片名《姹紫嫣红开遍》是《牡丹亭》当中,杜丽娘唱那一段“皂罗袍”。我接触白老师的人生,就像走进花园的杜丽娘一样,“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他的一生太灿烂了。我陪伴他,让他带着我们在他生命的花园里走一遭。
其中有很多驚喜。比如我从来不知道昆曲这么美妙,我因为想要了解他去看昆曲。昆曲在美学上如此细致、极致,表达情感既奔放又节制,舞台设计既抽象又具体,形成它独特纯粹的美感。这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
再比如,我又重看了《台北人》,这一次又听他讲这一个个故事。发现这么多篇章,是有一个统一的影像意念的。这也很让我惊喜。他在看过这么多人物沧桑,最后沉淀出来的是一丝温暖,这也很像他这个人。
端:一直有人改编他的小说成为影视作品,之后会想拍他的作品吗?
邓:这个要看缘分,不能强求,我未来创作的过程中,如果和他的作品有交集,那才是恰当的时候。硬要规划,反而缺少了水到渠成的美感。
王婉柔:追溯洛夫先生的超现实主义创作脉络
洛夫,台湾诗人,从1959《石室之死亡》至今,一直在寻找、尝试不同的诗的语言。超现实主义代表诗作影响台湾文坛深远。2000年,创作三千行长诗《漂木》,打开了华人诗坛长诗的历史新页。将届70年的创作生涯,一再突破既有格局。
王婉柔,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英国Exeter University剧本写作硕士。2009年即参与岛屿写作第一系列制作,曾担任郑愁予纪录电影《如雾起时》制片,周梦蝶纪录电影《化城再来人》副导演、剪接、访谈人。
端:最初接触洛夫先生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王婉柔(以下简称“王”):高中就看他的诗,一直很喜欢。《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一系列就觉得要拍他。但是当时目宿媒体刚成立,洛夫老师在加拿大,我们还没有十足把握可以应付在国外的拍摄。
端:电影主要内容包括哪几部分?
王:其实这部片去年在台湾就上映了,庞大的粉丝群也有一些批评意见。主要是因为洛夫的诗作非常多,为什么我比较集中在他的战争题材诗这一块。
他一直坚持创作,有上千首诗作。我觉得作为一个纪录片,在有限的篇幅中,还是要找到一个主轴。最重要是我觉得,奠定洛夫老师的地位,就是他在金门写下的《石室之死亡》。这首超现实主义诗作,也影响了后来很多人。
他自己也在比较晚期的长诗《漂木》的序当中,写到他的创作,从《石室之死亡》到《漂木》可以画出一条轴线,这样一脉相承。从1959《石室之死亡》到现在,他一直在寻找、尝试不同的诗的语言。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主轴。
从金门炮战到越战,他都亲自到前线,在战地创作出非常好的作品。这也是他和其他诗人最不同的地方。
片名叫《无岸之河》,这是他诗集中的一本合集,收录了他早期所有的战争诗。从字面上看,“无岸之河”也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感觉。从他的作品谱系来看,也紧扣我这部片子的重点:诗与战争。
除了文学部分,我们也采访了他的太太、孩子。一个诗人的家庭会是怎样的。他太太给他非常大的支持,包揽家中琐事,把他照顾得很好,让他可以专心创作。
他的儿子在台湾是一位很有名的歌手,莫凡。莫凡和袁惟仁曾经有一个组合“凡人二重唱”。他谈到自己走音乐这条路和父亲的冲突,直到后来把父亲的诗谱成曲。
他每年会有一个秋季中国大陆行旅,会回衡阳老家。而且他在写书法,有很多活动,他都把这些集中在秋季。我们跟了一次他的行程。
还有一个意外收获,是有幸拍到洛夫和日本诗人辻井乔对谈。辻井乔本名堤清二,是前西武百货的大老板。辻井乔也写战争诗。这段的珍贵之处在于,辻井乔在诗作中,反省自己国家的行为,他和洛夫,两位同代诗人,关于战争、战争诗能有这样一个对话。
端:拍摄当中有哪些困难?
王:每次去拍之前准备访谈都要很久,很难让他觉察不到,纯然去观察、冷眼旁观。所以我到了现场,跟摄影讨论一下镜位,就要集中精力访谈,他也不会让我们全天可以跟着他拍。
2012年开始采访他的时候,他84岁,两年多拍摄。他这辈子大概被问过太多次,关于他战争经验,和他战争诗的关系。所以我们在采访过程中,有点像隔着一层东西,还触及不到他感受的最里面,就是他当时的状态。
这也是我觉得这部片有点遗憾的地方。甚至我们带他回去,当时在金门写下《石室之死亡》的那个坑道。但就算回到那个现场,我们还是抓不到他年轻时候创作的那个感受,因为时间太久远了。
关于战争,诗人自己讲出来是一个层面,他的诗作是一个层面,而我如何理解他的话语和诗作又是另一个层面。所以我处理的时候,特别小心,不要把诗作视觉化,那个做不好会很拙劣。画面上我尽量写实,而不是模拟他的诗作。
而在写实层面,怎么表达他的“超现实主义”?我选择尽量不要去解读他的“超现实主义”,而是去追溯他的“超现实主义”是在什么脉络下产生的。我找到了他当时接触的“超现实主义”材料,台湾一些诗刊翻译的法国的诗,还有他看过的里尔克诗集。在这些材料中,发现了一些他常用意象的来源。比如,台湾很少看到“豹”,但他的诗中有,在里尔克的诗中也看到了这个。
“超现实主义”还有另一条线索是从日本来的。台湾南部那时有个诗社,风车诗社,其中的很多诗人去日本留学。我们采访到一位成员林亨泰,他是直接接触日本的超现实主义。我去追溯这些脉络如何影响洛夫,而不是解读他的超现实主义诗作。
齐怡:林文月老师的心境,让她的生活可以如此美好
林文月,台湾史家连横之后,生于上海日租界,光复之后举家返台。家学渊源的她被誉为“台大第一景”,更是散文与翻译大家。
齐怡,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毕业,作品包括电视制作《再见美丽岛》、《看见台湾——美学台湾》纪录片,分别获得亚洲电视节最佳新闻节目及入围国际艾美奖。另有《诚:董阳孜移动中的雕塑》、《回头看决策——萧万长公职之路五十年》等十余部纪录片。
端:最早读过的林文月老师的作品是什么?
齐怡(以下简称“齐”):《饮膳札记》。她不是在写食谱,而是巨细靡遗地写人。她觉得做一道菜和写一篇文章,是异曲同工的。从充分准备材料,到完成的过程,她都很享受。
端:拍摄前后对她的印象有什么变化?
齐:看她的文字和拍她,最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情,一个是生活。她在生命的每一个转弯处,跟人温暖相遇的这些美丽的场景。
她的美丽也是台大当年一景,是很多人的美好回忆。她虽然性格温婉,但文字是刚毅、坚强的。《源氏物语》她翻译了五年半,66期没有一期间断。这需要很大的毅力、耐力跟恒心。《源氏物语》当中所有的插画都是她画的,素描功底非常好。
她优雅,但也有一点小叛逆,比如考大学时把志愿从“外文系”臨时改成“中文系”;不顾父母反对,选择嫁给当时还是穷画家的郭豫伦先生。
她喜欢在家宴客。那时餐厅打烊早,聚会的文人们还没有尽兴,她就常在家做菜,让大家比较自在。当时家宴的座上宾有台静农先生、郑骞先生、孔德成先生等等,三毛、林海音、齐邦媛也都是常客。所以在二十世纪70年代,林文月家的餐桌,是台北重要的一处文化风景。
她为了宴客准备不同的菜,都要写卡片。每次请客前,她都会写下客人名单、要准备哪几道菜、上菜的顺序、哪些菜可以先摆好的。上一次有谁来吃过了的菜,这次会换一道新的,她可以细致到这个程度。每个人爱吃什么她都记得。除了做菜的具体做法,她写饮膳更是回忆每一次客人的面孔。
端:拍摄当中遇到哪些困难?
齐:《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一系列就有邀请林老师,但她两次都婉拒了。2012年,她获得文化奖,我刚好在拍,就试试看能不能继续拍下去。但她还是没点头。
将近四个月过去了,后来我专门去了她童年在上海的家,按照她写上海童年的散文中的路径、视角,走了一遍她生活过的地方,回来发了6封email给她。但还是没能打动她。
我知道她每年过年会做萝卜糕,很想拍到这个场景,但她还没有同意拍摄。直到隔年的1月31号,她终于回复了我,只有一行字:“我们会在家里等你们,请放心。”
在拍摄的三年当中,我一共和她通了50多封email,因为她常住美国,我们很难见面。我希望她能了解我们的诚意,也希望通过她最熟悉的文字方式,和她交流,多了解她。
她是一个优雅、不疾不徐的人,到我们快要杀青,她才告诉我们,其实她心里在替我们着急,怎么还没有完成。她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是和我们同一团队的人了。
毕竟她不习惯面对镜头,所以比较难的地方,是我们要有技巧地带她入戏。请她不要武装、不要表演,自然地进入情境。
端:电影的关键内容有哪些?
齐:我们一直说她有五支笔:写散文的笔、写论文的笔、翻译的笔、教书的粉笔、画笔,还有一支锅铲。
她是台湾人,但出生在上海。她从小念日本小学,母语是日文和上海话。等到小学六年级回到台湾,日本宣布战败,她以为自己是战败国的人,就一直哭。
隔两天,被告诉说原来她是战胜国的人。身份认同的冲击和多元文化的影响,这种繁复的生命历程在她的身上,都成了创作的养分和能量。
她在香港出过一本自选集,叫《生活可以如此美好》。关键词是“可以”,她的经历中其实有很多磨难,但是她自己的心境,让生活“可以”如此美好。
殖民地的身份,让她从小好像知道一点什么,又不全然了解,只知道自己不纯粹是上海人,或台湾人,或日本人。身份认同的迷思一直伴随她成长。她记得八岁时,听到梧桐叶掉落在石板路上清脆的声响,那声音让她心头微微收紧的感觉。她是敏感、早熟的。
她经历的改朝换代、历史空间转换,也和台湾这个岛屿曲折的身份认同,是扣合在一起的。但她一直想要活出的人生是心地宽朗、美好的。
时空不凑巧的交叠,在她心中落下一个浅灰色的阴影。我问她,你的浅灰色阴影是什么?她说,浅灰色不也是一种颜色吗?她很庆幸生命中有浅灰色,这让她的生命更完整。她有宽阔的心胸,所以她的文字可以打动任何年纪、境遇的人。
陈怀恩:用电影和痖弦老师的诗,做一次有意思的共同创作
痖弦,台湾诗人,自1966年后不再公开发表诗作,但一首《如歌的行板》,教人永远记得他诗人的身份。写就这首人人琅琅上口的诗行,此后投身编辑工作,从上一世纪中至今,影响力仍在扩散。
陈怀恩,台湾导演,从事电影工作三十年,包括场记、剧照、副导演、摄影等等,与杨德昌、侯孝贤、张作骥等多位台湾知名导演合作。2007年自编自导第一部电影《练习曲》,温暖抒情地呈现台湾景观风貌。
端:拍摄痖弦老师遇到什么困难?
陈怀恩(以下简称“陈”):拍了快两年,开始比较苦恼的部分是,他一直在温哥华。他这么丰富的人生,我们却只有一点温哥华的素材。有三四个月被迫要想出新办法,怎么去呈现。隔年2月,他突然说要回台湾,我们就又调整。才发展出他比较特别的访友行程,也是片子比较特别的地方。
端:痖弦老师给你的感受?
陈:片中会看到他去拜访很多人。通常德高望重的传主,都是人家来拜访他。他很体贴,怕麻烦人家帮忙他的影片,所以他更乐于去拜访人家。他让晚辈都很自在。这部片子让看的人也感到轻松自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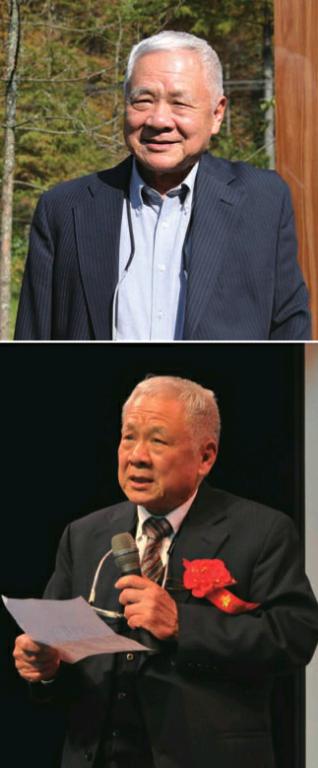
其实从头到尾根本搞不清我在干什么,他有担忧,但并没有拒绝。他很体贴的配合我们。《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一系列六位作家,大概有四部,他都有出镜作为访谈对象,讲这些老友的故事。我们当时开玩笑说,我们可以直接拍他,就可以知道所有人的故事。
而且他非常会讲,讲到每位作家最精彩的部分。他的确是非常棒的台湾文学发展的见证者,这当之无愧,很少人有这个接触面和角度。这和他长期在副刊工作的经历有关。他看着很多作家成长、成熟。这也是我们最早觉得他最有趣的部分。倒没有想去解构、分析他的诗作。
他看完片子说,文学和电影,在他的故事里,做了一次有意思的对话,在轻松和乐的气氛下完成。
端:这部片的拍摄构想有哪些调整?
陈:痖弦老师是个很特别的文学家,他最重要的作品集中在13年的创作时间,1953到1966。这段时间的作品完成了他的詩集《痖弦诗抄》。他传奇的地方是,并不高产,但三十年间都名列台湾前十大诗人。
他的作品不管什么年代去看,都有很独特和创新的地方。即使现在读,也不会觉得他的诗很老旧。虽然他的作品不多,但这88首诗的样貌非常丰富。所以他可以一直是桂冠诗人。我们拍文学家,不想像定论那样给他一个评论、肯定。
如果我对他作品有明确的解读,要按照一个规划去拍,我也会很小心。因为这不是剧情片,我们不知道作家会展现什么。所以我不想带一个鲜明的主观印象去拍。
痖弦老师和人相处很随和,容易沟通,但他的作品中也会有固执、甚至高傲的东西。他的作品很多是很年轻的时候写的。我开玩笑说,观众都被片子骗了。
因为看完你不会留意,他创作的时间很短,写的作品不算多。因为片子内容很丰富,大家可能也觉得他的作品很多。反而他有限的作品,蛮能把他的一生展现出来。
他的兩个诗人朋友吴晟、席慕蓉,背景非常不一样,他们的交集就是痖弦。痖弦能兼容他们的诗,他自己的作品中同时有两个方向的关照,比如《印度》和《红玉米》。《印度》在讲甘地,《红玉米》是他思乡的感受,看似全然无关的创作方向。
当吴晟和席慕蓉分别来谈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就是台湾独特的文化现象。台湾承载的多种文化的冲突,尝试去寻找和谐、互相包容,但可能一开口就会吵架。我们只是用电影去展现事情本身的风貌,没有注解,主观评断。
刚开始,还没有正式拍他的时候,没有把他和台湾不同文化对话这个角度联系在一起。当时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现代诗作者。他的诗有很多不一样的主题、形象、语汇。
诗作从字面看,和朗诵出来,会产生很不一样的效果。四下无人,在一个很安静的空间,把一首诗读出来,那个东西可能和你产生某种撞击,那是令人享受的被触动的感觉。
那不一定是理解、读懂了这首诗在讲什么。我们开始接触痖弦,也是被他的诗触动,觉得很有趣,但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没剪进片子里的素材,我们找了一些喜欢痖弦诗作的文学界的朋友做访谈,也请他们念诗。直到我们请痖弦老师自己念,赫然发现那是另外一个东西。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创作的过程很特别,这影响了诗的呈现。这部分是他口述,我整理之后的理解,没有放进片子。不想一个影片太高傲,有种看透一切、解读一切的感觉。我不想做所谓揭露痖弦创作秘辛。
简单来说,他的诗和他小时候听到的地方戏曲很有关系。他会反复朗诵,用很多声音来检验用字。他平时讲普通话,但念诗是用像唱戏一样的调子。所以后来有很多评论说他的诗很甜,充满音乐性,其实都和这个有关。
至于他的创作题材,很难说尽,他作为一个媒体人,什么事情都关心,比较博学。两小时的电影,怎么可能把一个作家一生的东西全部表现出来。
我们只能是从一个我们能理解的、表现的角度,去分享我们对这个作家的感受和想法。这不是一个文学研究评论或者生平传记,更像是电影和文学做的一个有趣的共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