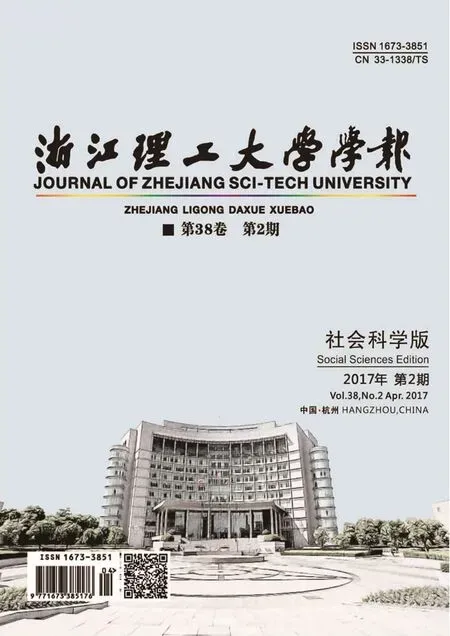商业电影影片名翻译标准的层级性
2017-08-16毛文俊付明端
毛文俊,付明端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18)
商业电影影片名翻译标准的层级性
毛文俊,付明端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18)
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名称译介研究倾向于以文本类型理论作为切入视角,将电影名译介中的翻译指导原则划分为平行而立的信息、文化、美学和商业四大标准。这种标准划分方式存在两大不足之处:一是研究对象过于笼统,未意识到不同类型影片在功能和目的指向上的差异;二是将所归纳的各译介原则置于同等地位,忽视了翻译标准间的上下层级。为对上述不足之处予以考察,以商业电影片名作为研究对象,对该类电影片名各翻译标准间的层级性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电影名译介;商业电影;翻译标准;层级性
自20世纪50年代伯明翰学派发出“重新界定文化定义”[1]的呼声以来,电视电影、报刊、儿童文学和广播等大众文化逐步摆脱学术研究中的边缘地位,进入翻译和文化研究的中心场域。其中,电影是大众文化的典型代表,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2]。通常来讲,一部电影作品涵盖的总文本包括了影片名、影片制作人员信息、剧本、台词、字幕等多个组成要素,其中影片名是最先进入观众视域的电影文本元素,是制片方和发行方宣传影片的广告和观众获取影片最初信息与初始印象的窗口。影片名往往能概括影片的内容或主题,揭示影片题材与类别,从而使观众在进行观影选择时获得必要的信息[3]。由于影片名具有重要的广告宣传和信息提供功能,对于一部外文影片而言,如何实现影片原名的最优化翻译,是左右电影推广成败的关键要素之一。
就如何实现电影名的最优化翻译,现有研究多从读者接受度和电影名的影视文本属性出发,以传统文学翻译的视角进行翻译策略和翻译准则探讨。例如,程敏[4]提出在翻译电影名时“译者应以忠实与否、接受美学和文本劝诱性程度作为基本翻译标准”;李立茹[5]认为电影名翻译的优劣在于“译名是否实现了语言信息、文化信息和观众效应三方面的对等”;范国文[6]将翻译电影片名时应注意的翻译准则概括为“信息传递、文化传播、审美愉悦和商业价值”四大功能准则;郑玉琪等[7]则将电影名翻译原则概述为“信息传递原则、美学欣赏原则和文化重构原则”。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提出的电影名翻译标准可概述为信息价值标准、文化价值标准、美学价值标准和商业价值标准四大标准。这种标准体系建立在Reiss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8]和Newmark提出的文本类型划分[9]的传统译论观之上,对电影名艺术性和文学性下的文本对等与否进行了归纳阐述,但对电影名应用性和商业性下的实用诉求关照不足。该种平行式翻译标准结构的最大不足之处在于将各标准间的层次关系模糊化处理,未意识到各翻译准则间的上下层级并加以区分。对此,本文对上述四大电影名翻译标准在商业电影影片名翻译中的先后层次进行梳理,以各标准对电影名翻译活动的影响效力为论述点,探讨了在商业电影影片名译介中存在于信息价值标准、文化价值标准、美学价值标准和商业价值标准四大标准间的层级关系(hierarchy)。
一、核心标准:商业价值标准
在商业电影影片名的翻译中存在主客体环境因素带来的渗透与影响。客体环境主导下的客观因素影响多源于源语文化和译入语文化间的差异性语言文化环境和文化积淀背景,这种差异性使得生产出的电影译名会与原影片名产生一定程度的信息错位或损失。为了补偿甚至消除该种信息错位与损失,译者不得不对文化差异性被动地顺化和适应,通过改写和另立译名等手段补偿存在的文化信息流失、变异和缺失,以实现电影译名的信息和文化认知价值。同时,译者具有一定的翻译自由和翻译改写空间,可基于个人翻译理念和对译作功能的不同定位,在文化环境大框架的制约下发挥译者主体性,对电影名译介中的修辞风格和诗学表达进行某种程度上的主动把控和疏导,以充分实现电影译名的美学价值和文化认同价值。
电影名的信息价值、文化认知价值、文化认同价值和美学价值构成了电影名译介中的信息价值标准、文化价值标准和美学价值标准。传统的电影译名研究将这三个标准置于平行而立的位置,未对其加以层级上的划分。但在实际的商业电影名译介中既不应将上述三个标准完全割裂开来分而立之,也不应将其置于同等重要的并列位置。而应意识到上述三个影片名翻译标准具有上下层级,存在一个最上层的共通结点,即电影名译介的商业价值标准。对于商业电影而言,将电影名译介到译入语文化时,无论是客体环境因素主导下对信息和文化认知价值的复写,还是译者主观引导下对美学和文化认同价值的再现,其最终目标都是实现电影名的商业价值,即尽可能多的吸引观众观影,以此创造尽可能高的商品收益。
电影名译介的商业价值标准根植于其文本载体电影本身所天然具有的商品属性。电影是一种以商业牟利为目的的文化商品,所有商业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场域语境,即商业化[6],因此,一部商业电影,从拍摄到制作发行都离不开市场因素对其的导向效应。诚然,电影的精神消费产品属性也赋予了电影作品文学创造性和艺术创造性,可将其看作是文化艺术元素的复合体,但从本质上来看,商业电影的文学和艺术创造性及该种艺术创造性所营造出的精神娱乐享受,最终仍是服务于商业收入的最大化。在现今市场经济体系和全球商业潮流下,观众从电影艺术性和美学价值中获取的精神享受和生活娱乐利益更加跳脱不开影片制作方和发行方对市场经济收益的诉求[2]。作为文化商品,商业电影是电影行业产业化时代洪流下,市场化经济流水线上制造出的经济效益导向型产品,其核心价值是经济交换价值,最终旨在实现影片制作方、发行方和其他利益相关人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作为电影文本有机要素和观众获取观影信息的最初文本窗口,电影名是影片主题、内容、类型或卖点的高度概括,是电影商品的最直观商标,起着影片初始广告宣传和吸引观众观影并进行相关消费的隐性导向作用。观众往往会从电影片名中直观地产生影片印象和影片联想,推测影片的主题和风格,并根据该种联想和推测是否符合个人的观影兴趣来决定是否观影和进行相关或后续消费。因此,商业电影影片名的翻译强调电影译名对观众这一消费群体的劝诱性,该类翻译实际上是一种“商业目的推动下的市场营销行为”[4]。在商业电影这种以利为先的商品本质驱动下,如何更好地实现电影译名所具有的、以商业推广和产品营销功能为特征的商业价值属性,以此攫取尽可能多的经济收入,是商业电影影片名译介的最核心指导标准。
二、基础标准:信息价值标准
电影的商品属性和电影名的宣传营销功能,使得商业价值标准成为商业电影影片名翻译中的核心标准,占据影片名翻译标准的最高层级。而影片名翻译流程中的信息、文化和美学价值标准,则是商业价值标准统率下的“一般性价值标准”[10]。在这三者之中,信息价值标准又优先于文化和美学价值标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与商业价值标准共生并存,二者呈现难以分割的缔合状态。
影片名翻译的信息价值标准强调影片译名需关注电影所描述的情节内容和故事主题,传递出影片旨在表达的情感立意和思想观念,使观众能获得相应的观影信息。和传统文本翻译一样,电影名翻译的信息价值标准也强调译文的“忠实”,但二者对这种“忠实”的界定仍有区别。二者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文本翻译所忠实的对象是原作这一直接文本来源,译作文本和该原作文本间往往可一一对应地回溯文字来源;而电影名翻译所忠实的最高对象并非是作为译作文本直接来源的原电影名,而是作为原电影名和电影译名共同文本宿主的电影影片本身。这种所忠实对象的非直接关联,使得译者在翻译电影片名时可摆脱原电影名的桎梏,获得更大的译介自由和改写空间,从而在译入语文化环境中灵活把控译文,以更好地实现电影名的商业价值和广宣作用。
例如,笔者以Excel 2007作为统计工具,对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旗下的1905电影网上列出的2014、2015和2016年度影评人数在50人以上且影评分数在5.0以上的美国影片进行译名翻译策略统计,总样本数为136,得出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统计结果,在总样本中采取完全忠实于影片原名的逐字翻译、译文语序调整、音译等直译翻译策略的影片名翻译样本只占38.97%,而采用改译和另译等创造性翻译策略的影片名翻译样本所占比重高达61.03%。由此可见,商业电影影片名翻译有别于传统的经典文学文本和应用型文本翻译,在翻译忠实度上具有更大的灵活度和自由度,并因此在翻译策略上更加多元化、富有创造性。

表1 电影样本影名翻译策略统计
但需指出的是,译名和原文本间忠实性非直接关联化所带来的扩大化译介自由,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为了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而无所束缚地任意改写和创译影片译名,即电影译名虽可跳脱于原电影名的束缚,但其改写和另译仍须在所译电影作品内容和主题的大框架下合理变化。例如曾有译者为吸引观众观影,制造噱头,而刻意将外语影片TrueLies翻译为“魔鬼大帝”。这一译名完全脱离了电影内容与主题题材,令许多观影者误以为该电影是一部科幻类影片,而产生先入为主的观影误区,在观影后大感上当。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电影BraveHeart的港版电影名翻译中。与内地将其直译为《勇敢的心》不同,香港译者将其译为《惊世未了情》。“惊世未了情”这一译法虽与原电影内容有所关联,传递出了部分影片信息,但从总体上来看仍是以偏概全,忽视了影片主旨。BraveHeart是一部史诗影片,描绘的是在William Wallace领导下,苏格兰人民为赢取自由而进行的不懈斗争。该部影片的故事主旨在于通过对宏大史实和英雄传奇的戏剧化描述,从而赞扬以主人公Wallace为首的苏格兰勇士们那种为了自由和独立而勇敢无畏地不懈抗争的勇者精神。该部影片中对Wallace和Isabella间爱情的描绘,是增添影片浪漫情怀、体现主人公铁汉柔情的烘托性元素,是商业电影借由宫闱恋情攫取观众关注而有意为之,但绝不是电影的核心立意。将其译为“惊世未了情”是以影片点缀元素取代了核心立意元素,易给观众造成认知误区,易使观众从影片译名信息中将该部影片误读为一部爱情电影。因此从总体上来看,“惊世未了情”这一译名远未符合电影名的信息价值标准,不如直译的影片名“勇敢的心”那般直抒主题,传达出影片核心信息。
从上述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电影译名信息价值标准指导下对原影片名的忠实再现,虽然在译者翻译自由度和操作空间上大于传统的文本翻译,但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为了实现商业价值标准这一最高指导准则而任意对电影译名进行再创造。在片名翻译中实现影片原名和影片译名信息价值的等值, 立足点就是要做到译名所指含义与原片内容的统一,忠实传递与原片内容和主题相关的信息[11]。借助过分夸大或以偏概全等手段过度改写或再创造电影译名,虽有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制造舆论噱头,吸引观众观影,但极易使观众在观影后产生被欺骗感和不满情绪,从而影响影片放映和发行后的口碑,进而对电影商业利益的长效获取带来负面效应。
在具体的电影名翻译实践中,对信息价值的践行标准可更具体地主要划分为影片主题立意信息、影片风格类型信息、影片原名字面信息和影片主线内容信息四大次级标准。上述四个次级信息标准的翻译策略特点和实例见表2。若把对电影译名商业价值标准的践行比作所要建造获得的高楼大厦,那么对影片名信息价值标准的实现就是该大楼的地基。使电影译名符合信息价值标准是为了最终实现商业价值标准,同时这也是电影商业价值成功兑现的必要条件,即想要使电影译名长效而充分地实现商业宣传功能,在观众群体中产生良好的观众吸引效果和后续发行口碑,就必须实现电影译名在揭示影片内容、主题和题材上的信息价值功能。

表2 电影名翻译信息价值标准的次级划分
三、重要标准:文化价值标准和美学价值标准
相对于商业价值标准的最高层级性和信息价值标准的基础必要性,文化和美学价值标准在电影名译介中处于从属地位。而两者之中,文化价值标准又优先于美学价值标准。商业电影名译介中的文化价值标准是指原电影名中的异质元素借由翻译的转化,在电影译名中得以有效再现,从而实现该元素文化内涵和联想意义在译入语文化群体中的正确传达和有效理解。
电影名译介的文化价值标准涉及到两个层面:文化概念认知和文化情感认同。文化概念认知标准立足于译名的可读性和可理解度,强调原电影名中的异质文化元素译介到目的语文化语境后,其所具有的现实指代和背后隐意不发生曲解和变质,能为译入语读者的认知图式和理解能力正确解读,不引起认知上的误区。文化情感认同标准立足于译名的可接受性和潜在情感影响,强调经译介转化后的源语异质文化元素不会与目的语读者的心理认知、情感诉求和道德观念产生冲突,不会与译入语文化长期积淀而来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观念产生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引起译入语受众的反感和抵触。对文化价值标准中文化情感认同标准的实现建立在文化概念认知标准的前提性践行之上。译者在翻译电影名中的异质元素时,只有先保证了该元素在所指和联想意义上的正确跨语言和跨语境转化,才能进一步优化其在译入语读者心中的文化情感认知效应。
具体到文化价值标准的践行上,译者最常面对的问题便是如何灵活地选择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应用于具体翻译案例。对于电影名译介而言,异化以异国情调为轴心,强调借由保留原电影名中的异质元素来留存文化陌生感和疏离感,以此激发观众的好奇心。而归化则以文化认同为轴心,将异质元素尽可能地等效替换为符合译入语文化传统的概念和表达,以此“取悦”译入语观众[5]。对上述二者的选择,应根据原影片名所代表的电影基本信息和文化信息与译入语文化环境的契合度灵活选择,并以译入语受众的文化心理期待为策略选用标尺。而就信息价值标准和文化价值标准间的先后级关系而言,若能在电影名译介中同时保证译名信息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实现,使其共同服务于商业价值标准,那么这自然是译者的译介首选。但是从现实来看,“语言一旦离开原有的文化环境,语言形式和它所赋予的精神力量就脱离了原有的和谐状态,很难在异域文化中产生完全同样的力量”[12],即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文化差异性带来的客体因素影响,译者很难同时兼顾文本信息的忠实传达和异质文化的充分留存,此时便存在取舍问题。之于商业电影译名而言,信息价值标准在层级性上高于文化价值标准,因为只有先确保了影片译名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是正确无误、真实可信的,才能实现电影名的长效广宣和诱导功能。若只追求异质文化的留存而忽略了信息的准确,即使可以短暂获取观众关注、带给观众一时的新鲜感,最终也会因影片名和影片内容的不一致而造成观众的不满情绪,影响影片的后续营销和发行。
在商业电影名译介的四大标准中,美学价值标准的层级性相对最低,往往对电影译名起画龙点睛、锦上添花的作用,而非不得不遵循的硬性指标。译者对美学价值标准的实现通常表现为对译入语传统诗学表达规范的有意顺化或逆化,借此使译入语读者在看到电影译名时能产生特定的阅读流畅感和美学享受。例如,笔者对中国广电总局旗下1905电影网上列出的2014、2015和2016年度影评人数在50人以上且影评分数在5.0以上的美国影片在华语市场中的译名词符长度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统计结果发现:在总数为136的统计样本容量中,翻译为贴合汉语表达习惯的四字格语言表达形式的电影名翻译实例,所占比重高达51.47%,远高于其他词符长度的短语或句子译名。

表3 电影样本译名语言表达词符长度统计
由于美学价值标准的践行通常只涉及到译名的用语、修辞和风格,而不牵涉到信息和文化内涵的传达,因此该标准并非电影名译介中的强制标准。译者若能在电影名译介中实现影片名的美学价值,自然是上上之选,但若为了精简或表意明确而放弃美学价值标准,也无伤大雅,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电影译名对电影内容和主题的正确传达。例如美国影片OrdinaryPeople, 将其译为《凡夫俗子》这样的四字格形式,自然更贴近汉语表达习惯,但若把它译为《普通人》,也同样可传达出影片故事以小人物生活为主线的影名信息,不会造成读者的误读和理解困惑。
四、结 语
在电影名译介中存在商业价值标准、信息价值标准、文化价值标准和美学价值标准四大标准。这四个标准并非处于同等重要的并立位置,而是处于纵向上的不同层级,对译者的商业电影名译介过程具有先后级指导顺序。其中,商业价值标准处于最高层级,统括信息、文化和美学价值标准,是电影名译介的核心指导原则,也是其所要实现的根本目标;信息价值标准是商业电影名译介的基础原则,也是实现商业价值标准的必要前提;文化价值标准是建立在信息价值标准成功践行基础之上的电影译名优化原则,包括显性的异质文化概念转化与传达,以及隐性的文化内涵认同和接纳,其层级性低于商业和信息价值标准,高于美学价值标准,具有重要的增益性作用;美学价值标准处于纵向层级性结构的最底层,涉及对译入语传统诗学和接受美学的有意顺化或逆化,包括了译者在炼字、修辞和用语风格上的选择,并非电影名译介中的硬性原则,其一般起到的是使译名更为出彩的画龙点睛作用。
在商业电影影片名的译介中,译者对信息、文化和美学价值标准的追寻,最终都是为了实现电影商品属性赋予影片译名的商业价值,即尽可能多的吸引观众观影,进行相关消费,以此最大限度化的获取经济收益。译者在翻译商业电影名称时,需理顺上述四大标准间的层级关系,以商业价值标准的最大化践行作为译介的最终目标,以信息、文化和美学标准的实现作为翻译策略选用的判定标尺,灵活、因文本制宜地选择电影名译介策略。若在实际的商业电影名翻译实践中,出现了上述四大标准难以兼顾的局面,译者应以层级性更高的商业价值标准和信息价值标准为指导,合理地借由改译或创译等多元化翻译策略来实现上述两大高层级影名翻译标准,同时可部分牺牲对文化价值标准和美学价值标准的践行。
[1] WILLIAMS R.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M].Harmondsworth:Penguin,1957:79.
[2] 田路.论英语电影片名翻译中的信息传达、审美艺术及商业价值[J].电影文学,2009(15):162-163.
[3] 阮红梅,李娜.电影片名翻译的文化适应[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6,25(4):138-142.
[4] 程敏.翻译,创译,还是重命名:换一种角度看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9):161-163.
[5] 李立茹.归化异化相得益彰:浅析电影片名的翻译[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S):286-288.
[6] 范国文.商业化语境下英语电影片名翻译原则再探讨[J].疯狂英语,2011(6):180-183.
[7] 郑玉琪,王晓东.小议电影片名的英汉翻译原则[J].中国翻译,2006(2):66-68.
[8] REISS K. Type, 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 Decision Making in Translation [M]. London: Routledge,1981.
[9]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10] 王惠玲,张碧航.目的论在电影名翻译中的运用[J].西北大学学报,2006,36(5):158-161.
[11] 贺莺.电影片名的翻译理论和方法[J].外语教学,2001,22(1):56-60.
[12] 周红民.翻译的功能视角:从翻译功能到功能翻译[M].南京:科学出版社,2013:117.
(责任编辑: 任中峰)
A Study on Translating Criterion Hierarchy of Commercial Films’ Titles
MAOWenjun,FUMingd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 on film titles tend to regard text typology theory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o classify translating criteria of commercial films’ titles into four equally important norms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informative value, cultural value, aesthetic value and commercial value of films. Such criterion classification mode mainly has deficiencies in two aspects. Firstly, the objects of study are too general, and the differe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films in functions and goals fail to be realized. Secondly, translating criteria are in the equal status, and hierarchy of translating criteria is ignored. To solve the mentioned deficiencies, this paper sets titles of commercial films as the objects of study, and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hierarchy of translating criteria.
translation of film title; commercial films; translating criteria; hierarchy
10.3969/j.issn.1673-3851.2017.02.005
2016-10-30 网络出版日期:2017-01-19
毛文俊(1993-),男,浙江衢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学翻译方面的研究。
付明端,E-mail: fumingduan@aliyun.com
H059
A
1673- 3851 (2017) 01- 0033-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