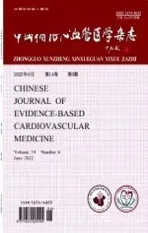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心率管理策略
2017-08-15吴金春常荣
吴金春,常荣
指南解读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心率管理策略
吴金春1,常荣1
自2012年ESC心力衰竭(心衰)指南、2013年ACCF/AHA心衰诊断与管理指南、2014年中国心力衰竭诊断与治疗指南以及2016年ESC急性与慢性心力衰竭诊治指南的发布,心衰的诊治理念也逐步更新,最新ESC指南根据患者左室射血分数(LVEF)值,将心衰分成3种类型:射血分数降低型心衰(HFrEF)、射血分数中间范围型心衰(HFmrEF)以及射血分数保留型心衰(HFpEF),并根据症状、BNP或NT-proBNP等数值更加细化了诊断标准[1]。在治疗原则上,基本围绕“黄金三角”药物治疗,即以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S)抑制剂改善心室重塑、β受体阻滞剂降低心脏耗氧、利尿剂减轻液体潴留的推荐治疗方案。除此之外,恰当使用辅助器械的综合治疗也是重要治疗手段。在心衰病生理中,交感神经系统(SNS)和RASS激活是症状加重进展、病情反复的主因。具体表现为体内神经内分泌过度激活,作用于心脏和肾脏的β受体,可引起心肌收缩力增加、耗氧量增加、心率加快、水钠潴留等变化,引起患者胸闷、气憋、劳力受限或者平卧受限,各种罹患因素相互叠加甚至互为因果,引起射血分数明显下降及严重的临床症状和后果[2,3]。在这一病生理变化中,心率变化既是判断心衰是否控制的指标,其控制不佳也是心衰加重的重要诱因。新公布的2016 ESC心衰指南中对心衰患者的心率管理策略作出了进一步的推荐。本文结合该指南建议,从心衰患者心率控制的意义,心率管理的目标,以及心率管理手段方法等方面进一步阐释解读。
1 心率控制的意义
近观心血管疾病研究历史,经典的Framingham研究中对5209例男性随访36年的资料表明,随着心率增快,无论是冠心病死亡率、心血管病死亡率还是全因死亡率的发生都逐渐升高[4]。INVEST研究明确了冠状动脉(冠脉)疾病中静息心率与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关系,结果显示,心率每提高5 次/min,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6%,心率大于75 次/min与心血管事件增加相关;此外,SHIFT研究及BEAUTIFUL研究通过倍他乐克、伊伐布雷定等药物试验证实,认为单纯降低心率对心衰患者是有益的[5,6]。从心衰发生发展的病生理过程中可看出,早期由于交感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激活及各种血管活性物质的激活而使心率加快,通过加快心率这一代偿机制来提高心排血量,以维持脏器及代谢需求,早期代偿通常是有益的;但长期神经内分泌系统过度激活会对心脏产生直接毒性作用,增加心肌耗氧、缩短心肌灌注时间,加重心肌缺血,恶化心室收缩运动,使心肌细胞增厚、凋亡、坏死,促进心脏重塑,引起心律失常,从而加重心衰进程[7,8]。因此,病理性心率增快是心血管病死亡率增加的独立危险因素,心率是反应交感激活的窗口,已经成为慢性心衰治疗的新靶点,近年来的医学研究及指南推荐也明确提出了心衰患者心率控制的临床意义及具体建议。可见,心衰患者心率控制,即可作为临床治疗的一项监测指标,同时也可作为预测改善预后的指标,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控制较快的心率,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降低住院率及死亡率,改善长期预后。
2 心衰患者心率管理的目标
依据近年来的循证医学研究证据,对于心衰患者,维持较慢的心率和较低的心率变异是可行的,且较低的心率可视为心衰是否控制的一项重要指标。对于窦性心律患者的心率控制,2012 ESC心衰指南、2013 ACCF/AHA心衰诊断与管理指南、2014年中国心衰诊断与治疗指南及2016年ESC指南均指出,总体目标静息心率维持在55~60次/min为宜,未强调心率的进一步降低[9-11]。对于心房颤动患者,新指南对其进行了详细解读,应用药物或射频消融等介入手术治疗恢复并维持窦性心律是最佳方案,然而,对于高龄、心房结构已发生严重改变(如左心房前后径>55 mm)、合并其他严重合并症等无法行复律治疗或很难维持窦性心律的,建议静息心率控制在<80 次/min,6 min步行心率<110次/min可能更好,并把预防血栓和脑卒中发生放在首位。同时指出,对于房颤患者,由于其心功能已发生明显下降,严格的心室率控制势必进一步降低心排出量,进而影响心功能。研究指出[12-14],心室率低于70 次/min与预后不良相关,对心率过快或过慢的患者,可能需要房室结消融或起搏,同时,对于收缩性心衰患者,可考虑用CRT代替双心室起搏(Ⅱa类推荐)。
3 心衰患者心率管理的药物策略
3.1 β受体阻滞剂 β受体阻滞剂是能选择性地与β肾上腺素受体结合,拮抗神经递质和儿茶酚胺对β受体的激动作用的一种药物类型,降低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起到减少心脏做功、降低心脏耗氧、延缓和改善心室结构重塑的作用。早期国内《β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滞剂在心血管疾病应用专家共识》对β受体阻滞剂在慢性收缩性心衰中的应用做出了相应推荐[15],但需注意治疗宜个体化。然而β受体阻滞剂目前在临床使用中仍存在障碍,主要是一些患者达不到β受体阻滞剂的目标剂量,尤其在急性心力衰竭和伴有血液动力学不稳定的早期。新指南指出,所有有症状(NYHAⅡ~Ⅳ级)的慢性收缩性心衰,除非有禁忌或不能耐受外,均需长期应用β受体阻滞剂(推荐Ⅰ类,A级证据)。目前对于心衰患者的心率控制,治疗达标的静息心率仍以55~60 次/min为宜,轻度活动后心率增加幅度不超过20 次/min。在治疗幅度方面,平均心率降低8~10 次/min时效果较好,降低>14 次/min时,患者死亡率显著下降[16,17]。在心衰患者治疗过程中,应尽早达到能耐受的最大剂量,降低静息心率,使其最大获益,同时需注意发生心动过缓、房室阻滞,心衰加重等问题,尤其在用药早期以及增加剂量时需特别注意。
3.2 洋地黄类药物 洋地黄类药物主要包括地高辛、西地兰、毒毛旋花子甙K等,由于其正性肌力和负性频率,被用于治疗心衰和房颤,能较快缓解症状,减少住院次数,曾在心衰治疗中上处于较高地位。新指南指出,应用地高辛的主要益处在于减轻患者心衰的临床症状,降低患者再次住院率,但不影响生存率。同时指出,窦性心律患者心率偏快,在应用β受体阻滞剂后仍不能控制到目标心率的患者,可选用伊伐布雷定。但指南中将β受体阻滞剂与地高辛是否合用来控制心率,暂未找出明确的临床证据。因此,对于接受了地高辛治疗的患者,其临床研究终点(死亡和增加住院风险)在部分研究中是有争议的。另外,地高辛治疗有症状的心衰并发房颤患者,对减慢快速心室率是有用的,指南中仅被推荐应用地高辛治疗射血分数下降心衰(HFrEF)并伴快速心室率的房颤患者,推荐静息心室率在70~90 次/min之间,活动后心室率不超过110 次/min,这与2014中国心衰指南推荐一致。可见,洋地黄治疗心衰或在总体评价上处于中立地位,被认为是不太受肯定治疗作用的。需要指出,应用地高辛时需注意禁忌证和慎用情况,如严重的窦房传导阻滞、Ⅱ度或高度房室阻滞、急性心肌梗死(AMI)后、合用胺碘酮、β受体阻滞剂等,不适当应用洋地黄类药物,或者与负性传导作用药物合用,可能会带来较严重的临床风险,需加以注意。
3.3 伊伐布雷定 伊伐布雷定是一种选择性窦房结细胞起搏离子流(If)通道阻滞剂,通过抑制起搏电流降低窦房结的自律性,从而起到减慢窦性心率的作用,因此,它只应用于窦性心律的患者[18]。2012年2月9日欧洲药品监管局(EMEA)正式批准单纯降低心率的新药伊伐布雷定用于合并收缩功能异常的慢性心衰治疗,2015年4月15日,美国FDA宣布批准伊伐布雷定用于慢性心衰的治疗,以减少心衰恶化而住院的风险。2016心衰指南继续对其进行应用推荐。其适应证主要为使用最大耐受剂量β受体阻滞剂的情况下心率仍≥70 次/min的稳定型心衰患者。该适应证的获批主要基于SHIFT研究结果。SHIFT研究发现,伊伐布雷定使心率下降10.9 次/min,使主要终点事件下降18%。但是,需要指出这些临床获益是在合理的β受体阻滞剂、ACEI/ARB、醛固酮受体拮抗剂治疗下获得的[19]。新指南推荐,已经应用了目标剂量或最大剂量的β受体阻滞剂、ACEI或ARB和醛固酮拮抗剂充分治疗后仍有症状的LVEF≤35%,且窦性心率仍≥70 次/min,应考虑应用伊伐布雷定降低心衰住院和心血管死亡风险(Ⅱa,B);对于不能耐受β受体阻滞剂或存在禁忌症的有症状且LVEF≤35%、窦性心率≥70 次/min应考虑接受伊伐布雷定治疗(Ⅱb,B)。然而,在实际临床中,心衰患者中很大一部分到中后期都出现各种心律失常及难以控制的心衰,如房颤、室性心律等,真正能保持症状稳定,且维持窦性心律的心衰患者较少,因此,其临床广泛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仍需要进一步拓展探讨[20]。
4 心衰患者心率管理的器械治疗策略
心衰患者器械治疗主要包括双腔起搏器植入治疗(DDD)、心脏再同步化治疗(CRT)、 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 或CRT-D的植入治疗,起到纠正缓慢心率,改善心衰症状,纠正快速心律失常,辅助维持心脏正常心电活动及机械活动,减少心脏恶性事件发生,增加存活率,延长寿命的作用。
4.1 常规起搏器植入治疗 ESC起搏指南推荐,当心脏停搏超过6 s时,甚至与症状无关时,要进行干预。然而,这些推荐主要是对没有明显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提出的,对于HFrEF患者,更短的停搏就可能需要干预。在ECG监测中,如果检出停搏大于3 s,首先应检查所用的药物,并减量或停用相关药物,如倍他乐克、胺碘酮、地高辛和伊伐布雷定等。对于有窦性停搏的患者,可以考虑停用β受体阻滞剂和双心室起搏,优选间隔部位起搏,以起到改善症状、防止心衰加重[21]。目前研究较多的希氏束旁起搏也取得了较多的证据,但由于其操作复杂,手术时间长,需要特定的电极,以及无法保证希氏束以下阻断的患者正常应用,因此具有一定局限性。对于心动过缓或停搏的病因是窦房结病变而房室传导正常时,应当首选维持正常的房室收缩顺序的起搏模式,并鼓励自身起搏;对伴有高度房室传导阻滞的HFrEF患者,CRT优于右室起搏;已经植入了传统起搏器或ICD,之后尽管优化药物治疗,或因为高比例的右室起搏发生了心衰恶化的HFrEF患者,应当考虑升级到CRT。需要植入ICD进行一级或二级预防的心衰患者,则可直接选择CRT-D治疗,以改善症状,改善预后,降低猝死。新指南更加突出心衰的分级分类管理,细化适应症。因此,心衰患者器械治疗的获益,在于根据最新指南推荐,选择合适的患者,应用最佳临床证据的治疗器械,使其最大获益。
4.2 CRT植入治疗 CRT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双心室起搏纠正房室不同步、室间不同步或心室内不同步,增加心室充盈与排空,提高射血分数,优化房室传导时间,增加心室充盈时间,减少二尖瓣返流,改善心衰症状的作用[22,23]。CRT-D为带有心脏转复功能的CRT。在选择器械治疗之前,须慎重衡量获益与风险,根据指南推荐,严格掌握适应症与推荐级别,让患者获益最大。与2012年指南相比,新指南对CRT适应证进行了修改,新指南指出,在使用ACEI、倍他乐克、利尿剂等优化药物治疗至少3个月前提下,在中到重度心衰患者中,用CRT治疗效果较好的患者中,2/3归因于生活质量的改善,1/3归因于延长的寿命。新指南指出,HFrEF患者,无论NYHA分级,若存在心室起搏适应证以及高度房室传导阻滞,推荐使用CRT而不是右心室起搏,以降低发病率(Ⅰ类);对于房颤患者, LVEF≤35%,NYHAⅢ-Ⅳ(药物优化后),QRS≥130 ms,使用适当方法确保双室起搏比例或者能够转复为窦性心律的患者应考虑使用CRT改善症状,以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Ⅱa类)。然而,当QRS波<130 ms时植入CRT可能有害,因此对于QRS波时限<130 ms的患者,新指南不推荐CRT植入。指南通过几项临床研究的结论指出,心电图呈LBBB图形的患者,对CRT更可能发生有利反应,而非LBBB图形的患者,反应则不太确定。关于究竟是QRS波时限还是QRS波形态,是对CRT有利反应的主要预测指标,还存在争议[24]。
4.3 ICD植入治疗ICD在心率管理方面,主要是进行恶性心律失常的监测,予以电复律、电除颤治疗,从而降低猝死风险和全因死亡率[25,26]。新指南更加强调ICD一级及二级预防治疗。一级预防适应症患者主要包括缺血性心脏病(40天内有心梗发生则不被推荐)和扩张性心脏病。二级预防适应症主要是从室性心律失常所致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中恢复良好功能状态下,预期生存时间>1年的患者[27]。不推荐的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40 d内有心肌梗死史患者不推荐,因为其并不能改善预后,并有可能发生心脏破裂等风险,二是NYHA Ⅳ级并伴药物治疗效果欠佳的患者不推荐,除非其是CRT、心室辅助装置或者心脏移植适应证[28]。总之,对于症状性心衰(NYHAⅡ-Ⅲ),优化药物治疗3个月后仍然LVEF≤35%,预期良好生存>1年的患者,推荐使用ICD降低猝死风险和全因死亡率。
5 结语
最新的2015年《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指出,心血管病死亡占城乡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位,农村为44.6%,城市为42.51%。随着社会老龄化速度加快,心衰的预防治疗更加刻不容缓,诊治任务更加艰巨[29,30]。2016年欧洲心衰指南较2012年版增加了新内容,提出了新理念,包含内容更加全面、清晰,旨在帮助医务人员把最新的循证医学证据应用到心衰诊治决策中。根据最新指南推荐进行心衰的规范化诊治,让患者最佳获益,并在临床应用中发现问题,综合分析,通过临床实践寻找循证医学证据,并反馈于临床研究及应用。
[1] Ponikowski P,Voors AA,Anker SD,et al. 2016 ESC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ute and Chronic Heart Failure[J]. Rev Esp Cardiol (England),2016,69(12):1167.
[2] Tanai E,Frantz S. Pathophysiology of Heart Failure[J]. Compr Physiol,2015,6(1):187-214.
[3] 高山钟,张向阳. 慢性心力衰竭病理生理和药物治疗研究进展[J].心血管康复医学杂志,2009,(03):301-4.
[4] Ho JE,Larson MG,Ghorbani A,et al. Long-term cardiovascular risks associated with an elevated heart rate: the Framingham Heart Study[J]. J Am Heart Assoc,2014,3(3):e000668.
[5] Fox K,Ford I,S t eg PG,et al. Heart rate as a prognostic risk f actor in patient s with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left ventricular systolic dysfunction (BEAUTIFUL):a subgroup analysis of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Lancet,2008,372(9641):817-21.
[6] Braunwald E. The war against heart failure: the Lancet lecture[J].Lancet,2015,385(9970):812-24.
[7] 李洪仕,万征. 舒张性心力衰竭病理生理和治疗进展[J].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2012,(04):244-8.
[8] McMurray JJ,Adamopoulos S,Anker SD,et al. ESC Committee for PracticeGuidelines.ESC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ute and chronic heart failure 2012: The Task For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ute and Chronic Heart Failure 2012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Developed incollaboration with the Heart Failure Association (HFA) of the ESC[J]. Eur J HeartFail,2012,14(8):803-69.
[9]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中国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2014[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14,42(2):98-122.
[10] Ponikowski P,Voors AA,Anker SD,et al. 2016 ESC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ute and chronic heart failure:The Task For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cute and chronic heart failur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 Developed with the special contribution of the Heart Failure Association (HFA) of the ESC[J]. Eur J Heart Fail,2016,18(8):891-975.
[11] Li SJ,Sartipy U,Lund LH,et al.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Resting Heart Rate and Use of β-Blockers in Atrial Fibrillation and Sinus Rhythm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and Reduced Ejection Fraction:Findings From the Swedish Heart Failure Registry[J]. Circ Heart Fail,2015,8(5):871-9.
[12] Tadros R,Khairy P,Rouleau JL,et al. Atrial fibrillation in heart failure: drug therapies for rate and rhythm control[J]. Heart Fail Rev,2014,19(3):315-24.
[13] Ganesan AN,Nandal S,Lüker J,et al. Catheter ablation of atrial fibrillation in patients with concomitant left ventricular impair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fficacy and effect on ejection fraction[J]. Heart Lung Circ,2015,24(3):270-80.
[14] 黄峻. 《β受体阻滞剂在心血管疾病中应用的专家共识》精要[J]. 中华高血压杂志,2011(2):109-11.
[15] Kadish A,Nademanee K,Volosin K,et al. A randomized controlledtrial evaluating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cardiac contractility modulation inadvanced heart failure[J]. Am Heart J,2011,161(2):329-37.
[16] 甄锦焕,黄纪文,张惠敏,等. 强化心率控制指导药物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临床研究[J]. 岭南心血管病杂志,2015(4):513-5.
[17] 都丽萍,李喜西,杜小莉,等. 心力衰竭患者地高辛中毒的药物治疗管理[J]. 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2016(21):2000-2.
[18] 何海潇,郭晓曦,张慧敏. 伊伐布雷定与心血管系统疾病[J]. 心血管病学进展,2012(6):792-6.
[19] 何亚菲,林文华. 伊伐布雷定对慢性非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心率变异性的影响[J]. 中国循环杂志,2016(11):1111-4.
[20] 钟丽球,黎艺毅. 伊伐布雷定在慢性心力衰竭治疗中的应用[J]. 河北医药,2016(5):756-8.
[21] Gasparini M,Proclemer A,Klersy C,et al. Effect of long-detection interval vs standard-detection interval for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s on antitachycardia pacing and shock delivery: the ADVANCE III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2013,309(18):1903-11.
[22] Steffel J,Robertson M,Singh JP,et al. The effect of QRS duration on 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a narrow QRS complex: a subgroup analysis of the Echo CRT trial[J]. Eur Heart J,2015,36(30):1983-9.
[23] 郭玮琼. 左室射血分数降低伴宽QRS波群的心力衰竭患者的预后评估[D]. 河北医科大学,2015.
[24] Moss AJ,Schuger C,Beck CA,et al. Reduction in inappropriate therapy and mortality through ICD programming[J]. N Engl J Med,2012,367(24): 2275-83.
[25] Aziz S,Leon AR,El-Chami MF. The subcutaneous defibrillator: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J Am Coll Cardiol,2014,63(15):1473-9.
[26] Yap SC,Schaer BA,Bhagwandien RE,et al. Evaluation of the need of elective implant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 generator replacement in primary prevention patients without prior appropriate ICD therapy[J]. Heart,2014,100(15):1188-92.
[27] Opreanu M,Wan C,Singh V,et al. Wear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 as a bridge to cardiac transplantation: Anational database analysis[J].J Heart Lung Transplant,2015,34(10):1305-9.
[28] Chung MK,Szymkiewicz SJ,Shao M,Zishiri E,et al. Aggregate national experience with the wearable cardioverter-defibrillator:event rates,compliance, and survival[J]. J Am Coll Cardiol,2010,56(3):194-203.
[29] 陈伟伟,高润霖,刘力生,等.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5》概要[J].中国循环杂志,2016(6):521-8.
[30] 任贤亮,杨楠. 住院心力衰竭患者心率管理现况的调查分析[J]. 中国医药指南,2016(28):95-6.
R541.61
A
1674-4055(2017)10-1153-03
1810007 西宁,青海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常荣,E-mail:qhschangrong@126.com
10.3969/j.issn.1674-4055.2017.10.01
本文编辑:杨新颖,姚雪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