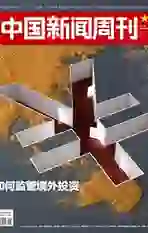盖伊·特立斯的纽约折叠
2017-08-12苏琦
苏琦
似乎人人都是孤岛,但又没有任何人是一座孤岛。
纽约不乏被仰望的人,纽约更不乏被遗忘的人,但在盖伊·特立斯的笔下,众生平等。
这并不是说,他们得到了相同篇幅的报道或描摹——那是不可能的,面目模糊的大众只能享受到群像的待遇,虽然盖伊·特立斯尽量在蒙昧的群像中用难得的细节给他们增添一点个人色彩。这里所说的众生平等,是指他们在盖伊·特立斯的《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中得到了同样的悲悯。被仰望的,被平视和挑剔;被遗忘的、湮没无闻的,被打捞出记忆的水平面。
特立斯笔下的纽约人分为三种。一种是真正的芸芸众生,比如成千上万的出租车和公交车司机、酒店和办公楼清洁工;一种是特色人群,比如专门修建大桥的以印第安人为主的建筑工人;再一种则是辛纳屈、迪马乔和海明威等所谓的明星。在特立斯筆下,他们共同构成了纽约的传奇、纽约的特色和纽约的风致,没有高下之分。
传奇终会如白云苍狗般风流云散,庸常的生活会日复一日地继续,一代又一代的人被时光吞噬,只有纽约永远存在。表面上看起来,有些人负责纽约特有的浮华,芸芸众生则构成喧嚣的背景,但到最后,尘归尘,土归土。纵然是千面人生,到了特立斯笔下也终难免一抹悲凉的意味。
大城市有很多,但似乎只有纽约因其规模和特有的丰富性而成为生活之海。各种欲望、各种人生在其中翻腾,似乎人人都是孤岛,但又没有任何人是一座孤岛。人们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穿越折叠,彼此相会。比如下班后来写字楼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们,通过每年捡到的数量巨大的硬币、假牙,以及每年撞破的N起丑闻,与白领们表面光鲜的职业生涯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特立斯笔下总充满大量的数据,大量的细节。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和无意义的数据,织就了一个无远弗届的致密之网,将人们的人生相互勾连,共同构成了纽约特有的底蕴和生命的底色。这就是纽约,这才是纽约。特立斯的纽约和此前此后的纽约一样,是势利的,但直到此时,纽约的势利中还是不乏温情。
现在人们说起特立斯,总是喜欢强调他如何敬业,如何反复采访,甚至如何在没有当面采访的情形下通过外围采访和大量的功课获得独家报道的效果。这自然是想重温媒体的黄金时代,顺便含沙射影地批评新媒体时代的浮光掠影和碎片化写作,以浇传统媒体人的心中块垒。但这种说法太技术派了。仅靠技术和勤奋,画不出清明上河图盛大的人间烟火,更描摹不出红楼梦的繁复与苍凉。而特立斯笔下被仰望与被遗忘的纽约各色人生,恰恰兼具这两者的特色。
“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6万加仑啤酒,吃掉350万磅肉,消耗21英里长的牙线。在这座城里,每天有250人死去,460人出生,15万人带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这里还有500名巫师、600尊雕塑和纪念碑、30万只鸽子……”这无疑升腾着清明上河图的勃勃生机和万千气象,而对《时尚》杂志编辑部的细腻描摹,因其扑面而来的香艳、才情和势利,无疑让人想起大观园。
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敏感到病态的悲悯之心,和对一个城市发自肺腑的热爱,与此同时,还能硬起心肠,不让廉价的同情心泛滥至遮蔽客观冷峻的观察视角。当然,话说回来,只有一颗敏感悲悯的心,一腔的热爱,而没有一支生花妙笔,也无法细致地呈现纽约的血肉和风骨,更遑论纽约的气息。
其实盖伊·特立斯很难说是一个典型的媒体人,他更像是一个厕身媒体的文人。好像他自己也是这么定义和定位自己的。他不仅仅是纽约的传记作者,也是美国社会生活的刻画师。如果要为他在中国找一个知音,恐怕要来一番穿越,因为最合适的人选恐怕是明末清初记录下东南繁华梦灭的张岱。而我们自己时代的张岱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