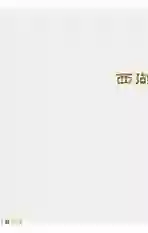自传与公传:一九八三(一)
2017-08-09董学仁
董学仁
友谊信箱
1983年第一天过得很快,晚自习时,刘凯、袁宏先和我留在寝室,把两瓶大连白酒喝到一滴不剩,度过了大学里的最后一个新年。
如果还要补充一些细节,那可太多了。首先,下酒的菜都吃光了,是一棵很大的白菜,洗净了切成细丝,拌上盐、糖、醋和蒜末。二是每个人都醉了,那天的我很兴奋,胃肠反应快,一会儿就吐了,吐在刘凯拿来的塑料桶里。接着是宏先,那天他有些压抑,一直喊冷,吐了以后也就好了。最后是刘凯,那两人清醒了他才醉,像麻醉一样,把塑料桶伸到他下巴底下,也要吐到自己的脚上。三是三个人在醉了之前,都到宿舍楼前的空地上发飙。我说能把一大块石头举起来,结果摔痛了屁股。刘凯的手表丢在那里,过了几天才找回来。
三个人同岁,现在都是二十八岁,比年龄最小的同学大了八九岁。这三个人也成了奇迹,在社会上混了七年,经历太多,领悟的能力也大了不知多少,那点儿大学课程学起来像玩儿一样,好在那课程刻板僵化,谬误挺多,偶尔和老师同学们争论一下,辨别对错,也是一种乐趣。
大概是那次喝酒时的许多感慨产生了共鸣,在大学毕业前做一件热闹的事情,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利。于是,春节过后重新开学,三个人去了大连广播电台软磨硬泡,发了个免费广告。
那个免费广告说:
我们是辽宁师范学院中文系高年级学生,感谢社会提供给我们的学习机会,愿意以知识和能力回报社会。现在我们建立一个“友谊信箱”,为各界青年解答人生中的疑问,解决学习中的难题。欢迎您来信和来访面谈,您的来信请寄大连辽师十五号信箱。
广告是在周一早晨播出的。
上午三个人照常上课,下课时被找到中文系办公室。一位老师先问了为什么要建友谊信箱,都想为社会做哪些事情,然后才说,上午你们上课的时候,来了一个老太太,请你们帮她去法院打官司。老师还说,老太太是“二战”遗孤,她的事情太复杂,不是你们管得了的,所以就劝她回家去了,是哭着走的。
老师替三个人接待时,留下了她的姓名,叫李秀峰。还留下她的地址,秀月街。家里没有电话,没留电话号码。
坐了一个小时公交,找了两个小时左右,终于敲开了她的家门。
李秀峰并不老,五十二岁,身材中等,脸型近圆,肤色稍白。
坐下来之后,我们静静听她讲述自己的身世。
她爸爸是日本军人,随部队侵入中国东北部,战败匆匆撤退,把她托付给了翻译官。那年“二战”结束,她十五岁,成了遗孤。没多久翻译官被枪毙了,她先后换过几个养父,也曾被卖到妓院,后来有两次嫁人,都被虐待,驱赶出来。第三次嫁人,与丈夫生了三个女儿,但夫妻两人的生活已走到尽头,快要离婚了。
她这多半辈子,受苦挺多,变得刚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正像我们想到的,不是这次与老伴的离婚官司。
她在一家医院做了多年的护理工,三年前退休。那时她的一个女儿长大了找不到工作,她只能用提前退休的方式,让女儿进那家医院上班。(在中国劳动岗位奇缺的年代,这种方式叫“以老换少”,提前回家一个年老的,换上一个年少的。)
几个月前,医院领导找到她,老李,你劝一劝你的女儿吧,还没结婚,别到男朋友家里去住,那样做影响不好。(那时的领导什么都要管,但这次是好心。)
李老太就去女儿的男友家找女儿。她记得那一天是星期日,因为她出来时是被那家人打出来的,打晕了倒在马路上。第二天是星期一,上午八点钟就有法院的人传她去了(很明显,那家人与法院有密切的关系),有人拍桌子大声训斥她,说她干涉婚姻自由,再不改正就严肃处理。
(不知道这个日本血统的李老太,认定自己没错就决不服输的劲头,究竟来自哪里,是不是来自她的民族性?)她后来听说,女儿男友的爸爸是那家法院的院长,把她找去吓唬一顿也是分内的权力,但她决不服输,一次次找法院讲理,硬要争个是非。当然,她的屈辱越来越多,屈辱感越来越强。这时的她,碰巧就听到了广播电台里的广告。
这事不算复杂,但我们管不了。实际上,这事已转化成她与法院院长私人间的矛盾,还夹着准亲属关系。我们与那个院长见了一面,问了问李老太说的那些,差不多都是事实,但如果让法院的人向李老太道歉,却是根本不可能的。
李老太把她的事情跟我们说了一遍,情绪就慢慢平静下来。我们替李老太分析了她的处境:住房是丈夫的单位分配的,这次离婚以后,很可能她没有住的地方;她的退休金少,如果再没有孩子的赡养费,很难维持一般的生活。所以,离婚和索要赡养费这两个官司都要打,都要争取好一点的结果。
我们三个学中文的人都没有律师身份,但这算不上一个问题,多读些法律条文,多往法院跑几次,也就行了,后来的诉讼结果也还算让人满意。那时民事诉讼的场合还看不到律师的影子呢,只有刑事诉讼有时能看到。直到我们考上大学的1979年,才有了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原则性规定。
在1983年那几个月里,我们与李老太越来越熟悉,有时也在她家里吃饭,比学校食堂的菜好吃,营养也增加了。比如,她炒蒜薹之前,把一根根蒜薹纵向剖开再切段,调料味道就进去了。她说这是在医院里当护理工时的做法。有一次她挺遗憾地说,商店里买不到咖喱,不能给我们做一顿咖喱牛肉。
墙上挂着一只外国拨弦乐器,四对八根钢弦,叫曼陀林。我们向李老太借了带回学校,在寝室里慢慢弹拨,声音不大,温和宽厚,并不扰民。那时已经有了日本电影《典子》,结尾是无臂少女典子游向大海的一场戏,气势很大,画面很美,伴奏的音乐就来自曼陀林。
李老太说了一个好消息,日本政府找到了她的父亲,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在东京和大阪都有企业。再下一步是查到她的出生文件,估计不到一年,她就可以迁往日本了。对她来说,这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但她告诉我们三个人的时候,脸上很平静,没有流泪。
比她更早迁往日本的,是她的大女儿。大女儿的婆家也是日本的“二战”遗孤,回国安置的手续办得早些。五月里的一天,李老太去大連火车站送别那一家人,我们也陪着去了。送别的人很多,大连还剩下的四十九户遗孤,都早早聚集在月台上。
火车开动了,那些遗孤们站立的地方,脚下都被泪水打湿。在那个场合,只有我们,办“友谊信箱”的三个大学生没有流泪和抽泣,这让我们显得无情,多少有一点尴尬。
这世界哪是真哪是幻
那个夏天到来时,有个小伙子找到友谊信箱,述说他的苦恼。
他说两年之前没考上大学,他的生活方向还很好,跟着一位老师学画油画。可是就在那年,他的爸爸得了重病,眼看就不行了,把他找到跟前,告诉他一个秘密。原来他不是爸爸妈妈的亲生子,是收养来的。那一天爸爸躺在医院里,呼吸很弱,力气不够,没有再说下去。他就等着爸爸身体好些,再把他亲生父母的事情告诉他。等啊等啊,爸爸的病完全治好了,再也不像有病的样子。
他于是有了苦恼:爸爸恢复健康之后,不肯告诉他的亲生父母住在哪里,或者曾经住在哪里,还否认在病中说过他是收养的孩子。而他呢,总要追问自己的神秘身世,想知道亲生父母是谁。这样一来,他与家里的关系就搞糟了,爸爸妈妈苦恼,他也苦恼。
刘凯、袁宏先和我去了他家里,跟他父亲单独谈话。时隔多年,已经记不住当时的细节了,只记得那个家庭环境较好,父母有一个房间,他有一个房间。父亲像是读过书的人,从事技术工作。父亲对我们说,这孩子从小挺善良挺聪明挺爱幻想,是个好孩子。考大学没考上,我们也没给他多少压力,可是他想象出一个被收养的故事,并且当真了,非要有结果。我们劝他,他不相信,还得请你们多开导他,让他分清这世界哪是真哪是幻,学会在真实的社会中生活。
父亲与儿子的两种说法,不可能都是真的,那在逻辑上说不通。我们也分不清谁是真的,怎么劝这小伙子呢?
有些事情需要时间来证实,不是马上就能找到答案的,眼下必须做的是,在不能确定之前把它放在一边,不让它干扰眼下的生活。我们的这个想法,小伙子还能接受,后来与家里的关系没那么糟了。
小伙子常来辽师校园,聊一聊他读的书,他做的事。我们也觉得他有一点玄乎,有些话是真是幻不好分辨。比如他说不出多少画油画的专业知识,却说他画了一幅女子裸体油画想送给我们,一米多宽,一米来高。我们笑了笑,然后拒绝,没有让他把那幅可能会有的人体写生拿来。有一次他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们也笑了笑。
小伙子还是常来,直到我们毕业离校。现在想起来,他第一次来时,未必期望我们能帮到他什么。他需要的,可能是与“档次较高”的人交谈,以及在大学校园出出进进的感觉,于是自己也变得重要,在虚拟和幻化的好心情中得到满足。
真的世界是真的,幻的世界就不能是真的吗?
有位乡下女子来信,说起一件她童年遇到的灵异事件,以及在那之后她遇到的苦难。
那时她五岁还是六岁,拿瓶子去供销社打酱油。打了酱油出来,有个没见过的老奶奶,叹了一口气对她说,孩子,你的命太苦了,你跟我走吧。老奶奶盯着她看,她也盯着老奶奶看,忽然发现老奶奶没有双腿双脚,是悬在空中的。她大叫一声,跑回了家。到了十几岁,放映露天电影的人来了,村子里的男女老少都去看。有个淘气的男孩子捡起一个挺重的土块,隔着墙扔向看电影的人群,偏偏砸到了她的头上,外伤好了,内伤没好,留下了犯傻发呆的毛病(这从她特别笨拙的来信笔迹看得出来)。她的信里还写了一件事,也够苦的。她十五岁那年,放学走在玉米地里,前面有人拦住了路,她转身往后面跑,后面还有一个人,再也跑不掉,被那两人强奸了。
促使她给友谊信箱写信的,是她现在的生活让她感到很苦,还看不到苦的终点在哪里。现在她快到三十岁了,嫁了个男人也好几年了,那男人一见她看书就狠狠打她,而她没事儿的时候就喜欢看书。在这封信中,她没有具体描述丈夫的样子,但我们能想象,以她自身的条件来看,那个娶她的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怎么才能制止男人的家暴?她问我们。
这一回轮到我们犯傻发呆了。
如果按照那位“悬在空中”的老奶奶说的,她的命太苦了,我们几个人又怎能帮助她呢?那位老奶奶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物,可能是另一个层面的灵异、神通或先知,偶然路过她的童年时光。按照我们世界的逻辑推理,老奶奶一方面能够帮助她,可以改变她后来的生活;一方面又不能帮助她,不能改变她后来的生活。这是因为,如果能够改变的话,她就不会受那些苦,老奶奶又怎么会看见她长大以后的受苦状态?
对于她童年遇到的灵异事件,我们找不到合理的解释。所以,我们给她、给有关部门寄去的几封信,可能不会有明显的效果。
我们没有任何神通。我们不能包打一切。我们在她的生活距离之外。
我们只能是她陌生的、安全的倾诉对象,使她的心里宽舒一些。
友谊信箱收到的信越来越多,从大连扩大到辽宁,再扩大到外省。这是因为省里的报纸发了一篇报道,还是在一个重要的时间,放在头版的醒目位置,接下来国内几份大报也有报道,让我们的友谊信箱成了大学生回报社会、帮助各界青年人的一个典型。
我们每天忙着读信与回信,出去走访的时间明显少了。这样还是忙不过来,好在有了学校的支持,由中文、数学、政治、历史等各系团委负责,回复来信中与各自学科相关的疑难问题。更贴心的是,所有回信的邮费不用我们几个人负担,学校全都管了。
这样一来,我们几个就省下了很多时间,用来回复一些重要的来信,比如那些说及青春和人生困惑的来信。
在回信时,我们用了笔名,第一个字都用了友谊信箱几个字的谐音。刘凯用的是“友直”,来自孔子的“益者三友”,即“友直友谅友多闻”。袁宏先用了“相竹”,这有一点像女性使用的笔名,以至于来信的人称他为知心的姐姐。我用的是“宜久”,一个善良的愿望,希望友谊信箱的寿命很长。
那只是一厢情愿,长不了的。因为那是我们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毕业之后,我们三人奔向不同的城市,从事不同的職业,怎么有机会联手做事?唯一的可能性,是我们毕业之前,低年级的学弟学妹接过友谊信箱,继续办下去。
后来我才知道,还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可惜失去了。当时这件事在省外影响挺好,就有人打了报告,建议在大学里推广友谊信箱这种形式,让这种方式固定下来,组织在校大学生为社会服务。这个报告送到省里,负责此事的官员觉得这种大学生团体很难实现政治上的领导,于是这件事被永远搁置,不会再有人提起。
一个小妹的非意外死亡
她在来信中说,她想自杀。
她说她十八岁了,在职业学校读二年级,明年才能毕业,但是,她说她活着的日子太长了,遇到的烦恼太多,不想承受一天又一天的痛苦。
这封寄给友谊信箱的信,还需要再看一遍。袁宏先看了以后递给我,我看了再递给刘凯。刘凯只仔细看了信封,说上面有她学校的名字,我们走吧,去她学校,越早越好。
人命关天,越早越好。
学校还在上课。见到她的班主任老师以后,我们才知道,事情比她在信中写的还严重。她想自杀,不只是一个想法,已经有过一次自杀行为,被家里及时发现救活了。班主任说,学校老师和她家里一样,也担心她现在不想活下去,还会自杀。还有,她说她十八岁,那是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是虚岁。如果按照周岁计算,她只有十七岁。
你们问她为什么要自杀?学校也问过她,但她不肯回答。我们现在也想知道。班主任说。
什么?有什么办法让她不自杀?学校也没有好办法。你们大学生想出什么办法,需要学校配合的,我们一定配合。一会儿她就下课了,你们先跟她谈谈吧。班主任又说。
班主任介绍的情况,没有超出我们的预料。跟我们在路上想的一样,可能得不到有用的帮助。班主任还希望等她下课以后,我们几个人和她在办公室里谈话,那时他也在场,可以多了解一些情况。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还是让班主任回避的好,因为她想自杀的事,可能与家庭与班级都有关系。
她下课了,是那一天的最后一节课。我们和她一起走出学校,找个人少的地方,坐下慢慢谈。
洪英,坐下聊吧。我们直接叫她的名字,把姓直接省略,语气就亲切一些。
洪英算是高个子女孩,快到一米七了,身形不胖。她的肤色比较白,她的眼睛看你时自然大方,让你觉得她表情开朗,不像是性格内向和比较压抑的人。如果仅仅读过她的信,没有听班主任说她有过一次自杀,你还真不容易相信她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
她遇到了什么事情?
小時候,七八岁吧,她就长得高,但身体比较弱,找了会武术的师父跟着练习,越练身体越好,越练越喜欢武术。这武术不仅强身健体,更讲究中国传统观念中的“义气”二字。这样一来,她从小到大的玩伴都是同门的师兄师弟,往来密切。到了她读中学,没等放学,那几个男孩子就在学校门口等她;前天是那个,昨天是这个,今天又换了一个,然后搭着肩膀,嘻嘻哈哈,快乐地走了。
一些谣传就是这时候兴起来的,说她和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鬼混,说她和几个社会流氓在一起鬼混,说她自己就是一个社会流氓,等等,越传内容越多。
她说到这里,不用往深里说,我们也明白了。这时候,我们的脸上一定出现了挺深的同情。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民族有个臭毛病,就是爱传话,特别是谣言,关系到男人与女人关系的谣言。其中要是有关于女孩子名声的谣言,就传得更多更厉害,足以让人陷入深重的痛苦之中。
我们民族的人,对自己的道德标准很低,却不影响对别人的标准很高。举个例子说,两个人骂仗,不必要具体说出对方的道德缺陷,只要把自己做过的不够道德的事情,一股脑都拿出来指责对方,必定会让对方招架不住的。
剩下的事情我们都能想到了,在一个道德低下的社会,洪英身边的人,她的老师和同学,以及她的家人,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从这些谣传出发,都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以对她帮助的名义,对她评判和批判,蔑视和歧视,冷漠和冷落。这些都出于一个社会的疾病:自己没有尊严地生活,也不容许别人有尊严地生活;自己没有个人生活选择的自由,也不容许别人的自由选择。
洪英想自杀,不是她特别绝望,是她很厌恶这个环境,不愿意生活在这些人生活的世界上。这个社会从打进入专制时代,几千年了,就是这样。
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她说起那些让她烦恼的事情,语调很平和,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这种冷冰冰的态度让我们惊讶,又隐约觉得,要劝她好好活下去,真是件困难的事情。
在她家里,我们跟她父母和姐姐在一起商量,遇上这样的事情,家里的人也都有压力,但这压力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更不能转到洪英身上,逼着她立即切断和师兄弟们的正常联系。家里可以给她温暖,但不能代替社会的温暖;现在,习武不仅是她的兴趣爱好,也是她从社会获得关心和支持的主要来源,如果突然切断了,她活下去的愿望就少了一部分。
我们又去找了洪英的班主任老师,跟他商量在学校这个环境里,怎么减少社会谣传对她的不利影响。中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谣言杀人的例子,也有许许多多的人无辜受害。现在这件事的关键是,社会的谣传离她很远,学校里的谣传离她很近。老师、同学不能相信那些谣言,不能把习武师兄弟的正常来往看成不正当的异性关系。只要大家能够相信她,给她时间证明自己,也给她机会融入学校里的活动,那些谣言会一点点消失的。
说了那些话之后,我们也不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出现明显的效果,洪英与他们的紧张关系有一些改善就行了,我们就有时间改变洪英的想法。
那个春天和夏天显得很长。
从我们校园出来,坐一段无轨电车,就到了洪英的学校。有时我们去那所职业中学门口接她,边走边聊送她回家;有时带她到我们的校园,让她感受一下大学生们的生活;有时我们和更多的同学去周末的公园,也带上她一起去。袁宏先那时有一架海鸥牌照相机,拍下了大家在公园里的合影。她站在我们之间,身高与我们相似,脸上轻松愉快的神情也与我们相似。
后来想到的,是我们当时没有足够的经验去说服一个女孩子。我们也给她讲过许多事情,包括古希腊传说中的西绪福斯,因为太聪明了受到处罚,要他推着一块石头上山,那块石头总是快到山顶时滚落下来。看来这是无休无止的处罚,但西绪福斯每天都用尽力气推石上山。他是人不是神,他要用超脱的态度对抗众神的蔑视,得到自己的尊严。他并不着急,只有心急地渴望幸福,痛苦才会在心灵深处升起:这才是那块石头的胜利。
我们的一个失误,是试图用更多的接触去影响她,向她表明这世界上好的一面。那是虚假的影响,因为我们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高尚的、超出社会存在的道德——几个大学生去帮助一个轻生女孩,出于良知,当成义务,费尽心机,但这是不能长久的,只是一种没有必然的偶然。一旦我们离开,就没有谁像我们一样出现在她身边,那个社会的污浊又将她淹没了。
我们注定要离开,那年七月毕业,离开那座城市。
过了一年多,刘凯收到一封信,从大连寄来,寄信人是洪英的姐姐。
她在信中说洪英也毕业了,有了工作,但是工作不久就自杀了,抢救没成功。信中还说,洪英走了,我爸我妈很悲伤地想起来,你们几个大学生陪她度过的那几个月,是她这一生里最快乐的时光。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