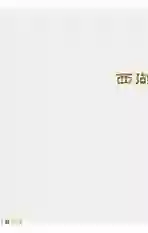《北回归线》的第一片树叶
2017-08-09刘翔
刘翔
1、灰
《北回归线》的第一片树叶是灰色的,我说的是这本著名民间诗刊的创刊号的封面,也可能这就是“北回归线”诗派的基调。不是红色,不是白色,更不是黑色,而恰好是灰色,这是偶然吗?也许真的仅仅是一种偶然,因为,封面的设计者是方跃,他偶然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封面。
让我回到对封面的描述,这个封面的设计让我想起荷兰科学思维版画M.C.埃舍尔的作品。这是一件体现所谓“空间逻辑学”的作品,黑与白在汇合,灰色的基调上是白点。图案的两头略暗,越向中间越明亮,仿佛在那里有一个真正的破晓。在图案中间的浅色中,出现了四个黑字:北回归线,但这时,那些白点也悄然变成了黑点。
这是偶然的吗?也许不是。《北回归线》诗刊的创始人梁晓明非常喜欢这个封面,他选定它作封面。那一年,他25岁。当时,他已经是一位著名的先锋诗人,作品发表在许多一流的民间诗刊上(如《非非》)。他喜欢演讲和朗诵,在许多大学有自己的拥趸,你有时必须挤开一堆崇拜者才能看清楚他:细长秀气的手指抓着一本诗集或他最新创作的一些散乱的诗稿(像抓住一些正要飞走的翅膀),英俊的脸是一件混合着真诚和自负的杰作,他习惯披一件围巾——如果这是在冬天的话——但并不真正用来围住脖子,而是让它垂下来。
2、米缸
我和梁晓明结识的时间,大约是1986年初,但比较深入的交往却是在一年以后。在1987年秋天,晓明给我看了他的新作《告别地球》,这部“寓言式的组诗”完全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突围之作。1984年,晓明完成了名诗《各人》的创作。表面上看,这是一首口语诗,一首情景诗,与“他们”诗群或其他南方生活流诗群的作品有一定的相似度。(当然,《各人》的重要性已经从时间和境遇中孤立出来,它拥有了独立的生命,具有了更普遍的超时代的意义,连晓明本人也在当时低估了它。)实际上,到了1987年(诗歌的实验性创作更早就开始了),他就希望掀开新的篇章,以组诗的形式凝聚更开阔的世界。在《告别地球》这组诗中,他一一拷问了这个地球上的各种光辉与价值。他呈现了诗人最后的绝望:他要告别那个“灰地球”。灰色,是的,想起自己的青春,就是灰色的。那时火红年代的红色已经熄灭,变成了一种隐痛。而日常生活是灰色的,梁晓明当时的工作场景是街道,他巡视街道,负责管理那里的市容市貌。他穿过老城的盲肠寻找新的堵塞点:“我一直在大街的手里,被栏杆牵扯/被无用的日子拉着衣袖/散步在风中,激情,和夕阳下。”(《离》)
一次,我去看梁晓明,他并没有带我去他办公室(他厌恶某位颐指气使的科长,讨厌办公室无聊的气氛),而是带我到一个蓬头垢面的小米店,我们坐在两个盖了盖的米缸上面热烈地聊起来。当时,他已经完成了《告别地球》,我们一起读他的新作,聊起诗歌,聊超现实主义诗人和画家的作品,聊他新看的书,在聊到恰佩克的《鲵鱼之乱》时,他说:上帝要人神圣,必先让他平凡。米店老板善意而茫然地看着我们——当我们激动地一边从米缸起身,一边快意地拍着变白了的裤子。
3、超现实主义
随着二十世纪60年代以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作品陆续被译介过来,诗人们发现,如佩斯、萨克斯、聂鲁达、阿莱克桑德雷、埃利蒂斯、米沃什、塞弗尔特、索因卡等人的作品都有鲜明的超现实的成分,但这些人的创作与法国典型的“超现实主义”(主要是指布勒东式的创作,而艾吕雅有所不同)又有一些不同。(用一句评价佩斯的话来说:他们“远远看上去是超现实主义者”,我有时也称他们是“边缘超现实主义者”。)
与原教旨主义式的法国超现实主义不同,这些诗人的作品更多地扎根于现实的腐殖土中,而且时时回望(不是决绝而去)那些象征主义的大師们: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叶芝、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
一些中国南方的诗人正是在这些作品的激励下,写出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中国式超现实主义作品(主要在南方,我也称他们为“南方超现实主义诗人群”),这些作品至今仍然没有过时。诗人梁晓明正是其中的翘楚。
4、极端主义
说到《北回归线》的创刊缘起,必须要扎根于其氛围中。二十世纪80年代,杭州有不少诗歌群体,如何鑫业等人组织的“十二路诗社”,朱晓东等人创建的“地平线”。
梁晓明也参与和发起了一些诗歌团体。如“极端主义”,酝酿于1985年,印出流派刊物《十种感觉》。成员有梁晓明、余刚、王正云、李浙峰、勒夫等,诗刊也收了西川、贝岭等外省诗人的作品。
“极端主义”的宣言是:“它讨厌规则,反对逻辑,厌恶理性,对从古而来的一切成为习惯的东西,它都抱一种怀疑态度。它崇尚大自然的生长方式,崇尚想象的权利,崇尚原始冲动。它一感到自己的今天和昨天没有什么变化,它便要感到烦闷。对于历史来说,个性越独具,孤独感便越甚。极端主义的头可以在天空中注视日球的升落,而它的脚却始终在地球的大地上。极端主义也可以理解为专横主义,它只重视自己,外界始终是它的房子。你可以找到它的存在信息,却永远不是它本身。我们宣布:诗歌是一门宣泄的艺术。诗歌必须从虚无中走回来,回到最基本的层次。”
我不太清楚这个宣言是出自谁的手笔,它有比较典型的法式超现实主义甚至“达达主义”的味道,有余刚和梁晓明的混合风格,也许他们的思维混合在一起了。
所有的极端主义总是很快会流散,四分五裂,这个小团体也一样,刊物印了一期就停了。
5、诗友圈
在梁晓明自己撰写并公开出版的几个大事年表中,参与极端主义与参编《十种感觉》这个经历都没有被列入。被梁晓明列入“1985年大事表”的是另一个刊物,就是他自己出资印刷的《从九月开始》。而实际上,这本刊物是1984年12月印出来的。这是一本真正展现南方诗歌的集子。集子收入了梁晓明、孙昌建、徐丹夫等浙江诗人的作品,也收入了王寅、陆忆敏、陈东东、贝岭、于荣健、成茂朝等“海上诗派”的诗人。
1996年、1997年,诗歌交流的气氛不错,以梁晓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诗歌小圈子,其中有余刚、郑继文、徐丹夫、郭良和我等。有时上海的陈东东、孟浪等诗人也会过来一聚。隆冬时节的漆黑夜晚,我们会骑车一个多小时,来到某位朋友家中,大家围坐在一个炉子边大声朗诵埃利蒂斯、圣-琼·佩斯以及其他诗人的作品。我也听过陈东东朗诵他的诗句,“把灯点到石头里去”(《点灯》),声音比较轻,慢慢的、软软的、迟滞的声音,可是,逐渐地,你感到了这种语言点燃的光照进了灰色的生活,劈开了内心的囚牢。当时物质虽然匮乏,但半夜的几根烤年糕散发的清香就足以让人终生难忘。在精神上,大家都有歌唱的强烈冲动,都渴望唱出自己的声音。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写过:“被扼住的歌喉最想歌唱。”这种渴望对梁晓明或对其他人,都是如此。当然,在这个小圈子里面,真正在个人创作上自成局面的,能够坚持先锋性的还比较少,确切地说,只有梁晓明、余刚等极少数几个人。
这个时期,梁晓明已经在酝酿编辑一份真正的民间诗刊,它是先锋性的,是国际视野的,是立足全国的,但刊物的名称还没有。在晓明的心中,这份诗刊是一本同仁诗刊,不应只有浙江作者,且作者不以亲疏而定,他从来不觉得论资排辈与诗歌有何关系。当时,我作为后来者,一个陌生人,能够被接纳,我感到非常高兴。确实,晓明要编辑的就是现代的、先锋的、新颖的诗歌。他一直认为诗歌是天才的事业,他看重诗人的才学,但更看重他们的才气。
当《北回归线》正式出刊的时候,杭州的这个小小诗歌朋友圈瓦解了,因为许多人难以置信,自己的作品竟然并没有被纳入其中。
6、扉页和刊首词
打开《北回归线》的扉页,我们就看到了目录。主编是王建新。差不多在《北回归线》创刊十年后,我才认识建新大哥,一位慷慨、豪情、思维缜密的人,若非必要,他可以像石头一般沉默,但他总是有非常强的执行力。第一期上并没有刊登他的作品。他自己的回忆是这样的:“他(晓明)还叫我拿几首作品也刊发一下,但我当时自认为我的作品还不够先锋,后来就没拿出来发上去。”但是,他拿出了一千元支持这本民刊的印刷,这种无私的古道热肠在今天看来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的一千元可是一笔巨款啊,我特别查了一下资料,1988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1119元。我刚工作不久,一千元相当于我近两年的收入,当时,晓明的收入也不高(即使他有一点稿费),我完全可以猜想到他拿到这笔钱的兴奋心情。建新大哥并不富裕,但他就是一个热心肠,一个可以和朋友肝胆相照的人。其实,我以前一直有一个错觉,以为建新是一位“实业家”,直是到了2015年11月,建新写出了回忆文章,刊发在第十期《北回归线》上,我才了解了真相。他是这样回忆的:“当时虽然爽快答应晓明这一千元钱,但我还是有点发愁。当时,我还是在厂里上班,我拿的是三级机修工的工资,只有四十二元五毛一个月,这一千元相当于我两年的工资。而我为什么会答应晓明,而且让他后天就来拿呢?其实钱就在我身上,只不过是我和爱人存了几年,想叫朋友去深圳买一台录像机的钱。我留一天余地,是想回去如何在爱人面前圆个谎话而已。当然,我还有本事圆谎,也圆了《北回归线》的梦。”哦,原来是这样,太感人了!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北回归线》的顺利降生。
责编是两位:孟浪和梁晓明。孟浪,本名孟俊良,生于上海,祖籍是浙江绍兴,二十世纪80年代是“海上诗派”代表人物。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他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人,他是一个外表有点蛮荒、内心比较柔软的人。他喜欢喝酒,喝了酒就非常健谈,可内容就像烟圈一样绕着绕着。
《北回归线》最后定形应该是在1988年的上半年,其时梁晓明和孟浪确定下来想搞一个刊物,名字想了很久,最后,接纳了孟浪提出的名字。北回归线,是太阳的光线在北半球能够直射到的离赤道最远的位置,是一条纬线。也就是地球绕太阳公转所绕成平面与地球赤道面所成的最大角度,也是黄赤交角的角度。北回归线作为地理位置贯穿中国和世界许多地方,这个名称比较开阔,不那么极端,于是一下子打动了梁晓明的心,他一拍大腿说:成,就是这个了。名称的开阔性带来了诗人选择上的开阔性,第一期《北回归线》选择的诗人中,来自浙江的4人,来自上海的3人,来自四川的2人,来自深圳的2人,来自美国的1人(严力)。
由于孟浪在深圳待過一段时间,所以这第一期他就约来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稿子,比如王小妮、徐敬亚的稿子,比如陈维刚译、刘小枫校的海德格尔论荷尔德林的文章《追忆诗人》,其时,刘小枫还在深圳教书。
现在回到目录,第一期上,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有比较强烈的超现实主义的味道,比如梁晓明、余刚、陈东东、何小竹、金耕、苏伞(他是一个年轻、有才华的诗人,在半个空页上印有他的两首诗,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在目录中出现)和我本人的诗,王寅的诗也有一点超现实的味道(从艾吕雅或阿波里奈尔的影子来看)。余刚是创刊阶段的一个重要的诗人,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却内心丰富的人,他曾和梁晓明等一起提倡“极端主义”诗歌团体,在其时的诗歌大展中独立一格。他的《大海抓住的语言》让人耳目一新,那介于达利和博尔赫斯之间的风格让我迷恋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何小竹《梦见苹果和鱼的安》是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可是,我当时有点遗憾刊登在这儿的诗歌没有那么吸引我。王小妮的诗《注视伤口到极大》显示她一直在向自己的内心开掘。严力刊登的诗包括他的代表作《还给我》,当时,他的后现代主义风格还不是特别明显,从我的视野看,也是超现实主义的。
当然,是否属于超现实主义已经不重要了。当时,超现实主义被我们中的一些人视为最先锋的一种诗歌,可现在看来是有偏颇的。从世界范围看,从时间的进程看,诗歌的探索和先锋性可以更多元、更繁复的。
然后,翻过扉页,就是刊首词。由梁晓明撰写:
首先,《北回归线》是一本先锋的诗刊。它的内涵更多是同人性的,它是怀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而站立出来的(注意,我说的是现代诗,而不是人们一般意义上的诗)。《北回归线》从来相信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大国,如果现在不是,那将来它也必定是。而且《北回归线》从来也相信,中国的现代诗大国的发展必定是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的,离开我们这一代人,中国现代诗的未来就将无从谈起。
《北回归线》的诗歌重视的是人的根本精神,它的努力的明天是在世界文化的同构中(我说的是同构一种世界文化、而不是跟从)找到并建立起中国现代诗歌的尊严与位置。
艾略特忧心忡忡地望着大地上的人类的圣徒心情,埃利蒂斯自由明亮的歌声中的希腊精神,圣-琼·佩斯挥洒自如、上下飞翔的法兰西民族的豪爽与潇洒的人生态度,无一不发放着迷人的光彩和对人类文化的一种贡献。
在中国,再上升一点,在中国的《北回归线》,就是在这样的旗帜招展中,用它自己的一双啪哒啪哒踩踏春天的脚,发现了最属于自己的天空,可以使自己微笑的天空、葡萄、大麦和信心。
口号是属于烟雾的,思想是自由生长的,作为诗人来说,唯有诗歌才是他的方舟,才是他足以有信心渡过艰难又漫长的生涯的希望;也唯有诗歌,才是他带给混沌人类的一束光芒。从这样的意义上,《北回归线》注意的诗歌是人的本质的反映与精神。
这样,作为一个梦想的阶梯,作为太阳生长的新鲜苗圃,北回归线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了。
奇怪的是,这个写于三十年前的,多少有点浪漫主义的寄语并没有过时。(布勒东承认,可以把超现实主义看作是浪漫主义的尾巴,“然而却是一根很有攫握力的尾巴”。)我们可以不矫情地说:这个发刊词昭示的精神仍然在我们的前方闪烁。
7、米罗
把《北回归线》再往下翻,就来到它的第一首诗,那是一首组诗:《歌唱米罗》,作者梁晓明。
梁晓明特别喜欢米罗,他所理解的那个米罗与他是完全相契的,那就是自由。对米罗的爱看来会伴随他的一生。
在一篇文章中,晓明写道:“当看到霍安·米罗的‘一滴露珠惊醒了蛛网下睡眠的罗萨莉及‘小丑狂欢节时,我全身都被震动了,当我看到肢体也有它自己的语言,而小虫子、凳子、椅子、灯管、手风琴、鏟刀、所有的动植物,甚至各种器具都竭力地扭动起自己的身体、在竭尽欢乐的舞蹈时,我当时就想,这就是我的诗!”
是啊,“大地把人摁在大地上”,而米罗式的“超现实主义”则帮助他发现神奇。这种神奇仿佛奇迹,可以把人从僵化的家庭、工作和社会环境中超拔出来。这是奔向太阳、月亮、外国和梦幻的力量,竭力挣脱枷锁,向上、向上飞去。
8、回到灰色
最后,我把翻开了的《北回归线》第一期又合上,灰色的封面又出现在我面前。在灰色的中间,是白色,像那根线、那根神秘的纬线。线的中间有黑点。现在是白天,但黑夜从无数个鱼嘴中被吐出来。
有一次,梁晓明和另一位著名的诗人一起被邀请作演讲,那位诗人自称是一位红色的诗人。然后,台下的中学生提出了这样的一问:“请问梁老师,你认为自己是什么颜色的?”晓明沉吟了半晌,说:“我应该不是红色的,但也不是黑色的。我可能是灰色的吧。”
《北回归线》三十年来,一共出刊十期,十个封面就像十片叶子。它的第一片叶子是灰色的,第二片是白色的,第三片是鲜红色的,第四片和第五片又回到了灰色,第六片是深红色的,第七片是淡蓝色的,第八片是极浅的灰色,第九片是淡黄色的,第十片是蓝色的。
灰色是一种谦逊的颜色,暧昧的颜色,它可以容纳所有的极端,包容所有的探索。它可以容纳所有颜色,它预示了所有彩虹。可是,灰色也是一种拒绝,拒绝媚俗,拒绝合唱。没有这种拒绝,它的纯粹性和先锋性就无法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