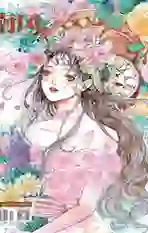七支簪
2017-08-02尾羽
尾羽
拾柒
别别扭扭地住了几日,若漪从她大娘的房间睡到她姆妈的房间,幸亏没有人再给我们难堪,硬要我们睡同一间房。
走的时候倒是坦然,她只是说,想去月老庙看看。我依她,那天之后我就告诉我自己,依她罢,依她罢,她想怎么样,我都同意了。
我们走进偌大的月老庙,可谓济济一堂。都说安乡哪,要数蘅安的河灯最美丽,池安的酒楼最热闹,秦安的月老最灵验,霭安的香糕最好吃。
我看着成千成万的红条迎风飘扬,好像一朵朵红莲在风中烂漫地飘荡,无所寄托,问她:“这是什么?”
“许愿的红条儿。若是想嫁给好人家,就在树上系上一条,求月老许个好姻缘。”
我看着左手边大大的木架子上全都系满了竹木块,竹木块的两面都写满了大大的名字,就又指着问她:“这又是什么?”
她漫不经心地答我:“想要白头到老的情侣,等到找到了彼此的良人,就摘下一条红绸条,两个人一起写块儿竹签,系在这,等着一生一世,永不分离。”
我上前饶有兴趣地翻着竹签,有个小和尚跑过来劝阻我道:“施主,莫碰!这都是其他施主向月老祈求的诚愿,您碰了就不灵验了。要是您喜欢,旁边有竹签,您也可以请一块儿。”
我心想灵验个什么,要灵验,秦若漪怎么还会在我身边?一偏头,发现秦若漪已经跑到很旁边的一棵缠满红绸条的树下,向一个仙风道骨的老人讨教着什么。我看着拿着扫帚的小和尚,拿出一张银票说:“看你们这木架都这么旧了,给你们点钱去修葺下。”
果然还是财能通神,他看着银票唯唯诺诺地摆出手接着,我却一把拿回来,指着秦若漪说:“你要是想要,就过去听听那位小姐问那个老头儿问了些什么,然后告诉我这老头儿是怎么答话的。记住,不要被发现了,快些回来,这些钱就是你的了。”我话还没说完,这小和尚就像几个月没吃羊的狼,朝着秦若漪那边奔过去了。
没一会儿,小和尚向我亟亟地奔来了,喘着气说道:“这位少爷,我都瞧瞧听清楚了。那位小姐问我师傅,他有没有帮一位叫秦家的小姐和莫家的少爷配过姻缘。”
“那你师傅怎么说?”
“嗨,说什么我压根没听。少爷,看在您对我们月老庙这么好的份儿上,我老实跟您说了罢,我们师傅根本就没帮过秦小姐和莫少爷配过姻缘。几个月前,秦家的秦夫人早就用一对玉佛像买通了我们师傅,让他和莫老夫人说,莫少爷的良配就是秦家的小姐。还有后来配的八字,自然是做做样子。”
在淡漠的震惊里,我敷衍地把银票给了他。秦若漪,比我想象得更可怜。什么千里姻缘一线牵,只不过是一场秦家一手安排的戏。秦若漪的大娘,看着像亲娘一样温柔待她的女子,却把她卖了。或者,所有人都晓得?我恍然大悟,明白了秦若潮为何说,他把她推向了我。秦家的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救她,都迫不及待地把她往我这个败家子这里推。
她说她不信金玉良缘,今天她既然问了,就说明,这颗七窍玲珑心什么都晓得了。若她证实了,所有的人都背弃了她,她会不会比我想象的更难过呢?
正想着,她却忽而不见踪迹。
我着急了,在人群中一顿乱找,却被那师傅叫住了:“莫少爷。”
我回头,他将一个包袱交给我:“秦姑娘替您请了只签,托我将这包袱,转交给您。”
我抬起头,看着那些堪称灵验的红绸条,还有被风吹乱的维系着姻缘的竹签,陽光直射我的眼睛,眼前的一切有些眩晕,红绸条也变成了一团又一团的红雾。我眯着眼仔细看,终于看清楚了,新挂上的竹签上一面写着“莫懿”,一面写着“孟菀笙”。
我打开包袱一看,一叠我这辈子也花不完的银票放置在一个匣子里面。
“她可还有什么话,留给我?”我负气将那包袱丢在地上,问一旁仍旧淡然的师傅。
“她让我转告你,她从不爱做棒打鸳鸯的事。你要的所有,她已经给了你。而她祝你们,永结秦晋,一世白头。”
拾捌
蘅安的河灯节真是热闹,摩肩接踵的人们端着老妪们做的各色河灯在街上热热闹闹地走着,每盏河灯都长着魅惑的赤色火舌,在微有凉意的秋日里让人找到掌心的温暖。姑娘们的脂粉香气熏染着辉煌一片的长街,熙熙攘攘的声音沉落在红枫铺成的大道上,让人迷乱。
她不知,我已偷偷跟了她一路。
我看见她向在河边兜售河灯的老婆婆随意买了几盏,红艳艳的花瓣在光的笼罩下柔和了许多,便在她不远处,放下我事先准备好的河灯,用手推着水波,让那盏河灯一下漂到她面前。
她先是看见了河灯里的一支芙蕖翡翠簪,那是她出嫁前,奶奶在秦安时定下的秦簪。我因当时与她怄气,藏起来没给过她。
她看到了簪子上她的名字,低下去的头一下子抬起来,我看见她眼中的光把我照亮了。
她拾起河灯,问我:“你为何还要回来?”
我看着她,想要攒出一个笑,却不觉泪已润湿眼角:“我虽窝囊,也必守信。”
她忽然落了泪:“莫懿,你蠢不蠢哪?你蠢不蠢哪!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没想到,他们什么都安排好了。我是为了他们才去莫家的啊!可是他们呢,在他们心里我算什么?你还有孟菀笙,莫懿,可是我谁都没有了,我在乎的人,他们都不要我了!我这辈子,再也回不去秦安。可你呢?我放你回你的秦安,可你为何偏偏还要回来!”
我就那样一下子抱住了她,轻轻拍打着她的背,第一次学会把给孟菀笙的温柔分给她一点点:“你放走了我,可我又能去哪里?你是我的妻,只有你在的地方,才能作我的家。他们不陪你一世白头,我莫懿陪着你,看红莲成灾,韶华落尽。只要是你愿的,我都依你。我没了菀笙,你也失了秦安,我们又扯平了啊,阿漪。”
在赤色烛光里,我将那芙蕖簪插入了她的发间。
而我没有告诉她。那日,我拿起有着她名字和我名字的签,踮着脚挂在了最上面的一排架子,换下了她写的签。我在风中听着那些竹签敲打在一起,就像我和她纠缠不清的姻缘,命中注定无法分离。
坐在归程的船上,我看着她将头搁在我肩上,一动不动地木然看着眼前那条深不见底的河。黑白的眼珠分明,湿漉漉地像池安清晨沾了露珠地青石板大街,一览无余的空白。
“只有秦安,才有芙蕖啊。”
“为什么偏偏不喜欢牡丹,不喜欢水仙,不喜欢腊梅,只爱红莲呢?出淤泥而不染?”
“兴许,是因为荷叶能泡茶入药,莲藕能做吃食,莲子能炖汤熬粥,而红莲也能碾碎了做香糕吃。”
“这么肤浅的理由?阿漪,你从来没有亲手做过东西给我吃。人人都说你的手艺好,可是你偏偏不给我做。”
她笑笑,伸出自己的手,手中是一个青玉瓶:“拿去罢。”
我迟疑着没有接过。她补充道:“那么这是我亲手调的药,祛疤用的。手上留了疤,不好看的。”
我想起上次我同阿诺挑衅自讨苦吃留下的疤。她竟还记得。
我却只说:“我又不是姑娘,要好看做什么?”一边说着,一边还是口是心非地拿了过去。
“醒酒时也是有用的。你若醉了醒来头疼,就嗅一嗅。”
那时的我,却并不知,以后的年月里,我倒是更愿意醉着。
拾玖
我未曾想到,我会在蘅安遇见孟菀笙。
她对我说:“莫懿,我找了你很久很久。我从法国一直找到这里,幸亏你在这里。”
她又说:“我背弃了我的家人,我什么都没有了,莫懿,幸亏你还在这里。”
她最后说:“现在我再也不是法国的孟菀笙,会画画的孟菀笙。香榭里大街只是一个遥远的梦了。我不是用手画油画的孟菀笙,我是用手弹琵琶的花楼的头牌歌姬,但莫懿,你在这里,幸亏,你在这里。”
她嫣红的血溅在我青白色的广袖上,让我晓得这不是个梦。我眼看着她从二层的阁楼里开窗跳下,眼看着她的手骨应声折断,眼看着她声声唤着我的名字昏睡在我怀里。
簇拥的人群密不透风,老鸨用团扇劈开了一条路,啧啧啧地执着团扇点着我的脸说:“这位公子,闲事莫管,来人,将这个贱婢抓回去。”
“慢着,”我从怀中掏出一张银票扔给她,“这位嬷嬷,从此你莫要再找她的麻烦。”
老鸨接了银票就换了一张脸,谄媚地笑着说:“怪不得这贱婢不肯跟陆老爷,饿了她三天逼着她跳了楼,居然还遇见你这位财神爷。”沙哑的笑声扎得我耳朵疼,但我顾不得和她计较,直接抱起菀笙去医馆。
事情这样清晰。菀笙晓得我回来成婚不告而别,竟宁愿和家里人反目,也执意来安乡寻我。走到这里,想必没有路费再支撑她走下去,才到花楼里当歌姬,却被什么老爷看上了。老鸨这贪财的人,必和老爷串通好了将她关起来,硬逼着她嫁到那个老爷家里。她一时无奈,跳了楼,居然那么的巧,正被我看见。
菀笙也是生在水乡,大户人家的女儿,从来娇生惯养,和我一样在法国大手大脚惯了,却为我这样受苦。以前她明明最爱的是画画,纵然天生一副好嗓音,也不屑唱歌。但现在,她居然这么作践自己。
我给了医馆许多钱,他们告诉我,无性命之虞,但右手恰好先着地,估计是要废了。我嘱咐他们一定照顾好她,等她醒了告诉她我迟早会回来看她。
她曾是我想与之共老的女子,最妍丽而又骄傲的女子,现在却这样为我枯竭。我没有留在她身边,纵使她身负重伤,纵使她需要我,但是我居然想到的,还是秦若漪。我想著,她一个人,河灯节后人又多,若有闪失,又怎么得了?菀笙在这里不会有事,故我飞奔回客栈找她。
不曾想,掌柜对我说:“莫少爷,莫夫人已经走了。她留了口信给我,说先行一步了。”
竟这样心急。竟这样等不得我。
在回池安的路上,我在船里反复想着这两个女人,我想,我迟早要在她们之间做个决定的。
但回到池安之后,我终日都在怕。怕这个傻丫头被来要账的人刁难,于是我再也不去酒楼花楼寻欢作乐,而是整日在街上乱逛;怕这个傻丫头不晓得自己照顾自己,于是悄悄给在树下小憩的她添上一件披风;怕这个傻丫头被族长责难,所以听了阿杏的话第一时间冲进去找她。凡此种种,难以细数。
第一次,听见德叔对我说,她让我的债主上门去问她要账,我心想她真是不晓得那些老鸨和满脸横肉的老板的厉害。所以我懒得再去花楼和酒楼买醉,反正现在醉了,她也不会心疼我,反而我倒是越醉越清醒,越觉想念。
第二次,我看见阿诺想要叫醒她,却不忍心熟睡的她被打断,于是我走向前给她盖一袭披风。那日的阳光太妖娆,照得她格外的乖巧,脸上温柔的嫣红让人着迷。我吻了吻她的眉心,动作已经快于了我的思绪。
我当时想,若她醒了朝我笑,即便菀笙再怎样的可怜,我也会放弃与她浪迹天涯。其实我对菀笙的爱情,已悉数变成了愧疚和责任,还有同情。炙热的情虽然动人明艳,但也易枯槁,我现在却只想有细水长流的一份温情。我晓得若漪给得起,却不愿给。
第三次,我在族老前握着她的手,她却一下子就挣脱了跑出去。我到花园里找她,她醉了,我终于听到了她的醉后的心底话:前前后后,我只是莫家的莫懿,而不是她的阿懿。我同阿诺说,她说的不是真心话,可其实,我只希望听到,她说她有这么一点点在乎我。
第四次,我握着她的手说,愿她说一声想我了,并唤我一声阿懿。可是我还是没有等到那一声阿懿。她不懂,为何我还会握着她的手不肯放。我一直在给她和我机会,但她从来不要。
第五次,我兴致勃勃地煮了莲藕羹去看她,还未推门,便听见她和阿诺在房里谈话。
她说,惟愿来世不要再遇到我。
没错,这就是她的心底话。从她进门我给她难堪开始,她就已经漠视了我对她种种的弥补和好,一切我做的都是徒劳。
我仓皇而又绝望地笑,拿着手中的碗一直在长廊上漫无目的地游逛,手上的冰冷一直蔓延到心里。看着白雪飘洒在这大宅里,我只想冰雪也将我埋葬。那一天起,我最后的一根稻草都被她无情地剥夺。
我越来越少去看她,我早已说了,她愿的我都依。既然她不想看见我,那么,我自然不会去再看她。只是在冬日里,我还是用手炉烘着手,默然地画着她的画像。画始终都是骗人的念想,没了念想,人又要怎样苟活世间?
为了躲着她,借口去秦安办事,但我先去了蘅安找孟菀笙。
我曾深深喜欢的人,现在却成了我的一壶酒,来让我忘记另一个叫秦若漪的人。我不发一言地抱紧了菀笙,对她说:“菀笙,再等我几个月。”
所有莫宅的人都道我无情,抛下秦若漪三个多月。其实我只离开了她十天,去秦安和蘅安的十天。其余的两个多月,我从秦安买来了红莲的种子,一天一天,沿着河渠,看着手下们一点点将那种子种在池安河的河泥里。我想明年的今日,我不在了,这些红莲还在池安守着她,她看见了池安的莲花,就不会再去想起秦安,想那些抛弃她的亲人。
孩子燃起了新的希望。她生下我的孩子后,我是多么欣喜地去看她。我甚至想,若她说她挂念我,我必当负了我对菀笙的承诺,告诉她其实我想同她和孩子一起,等着池安的红莲开放。
但她只是打量着我,轻启樱唇:“你必然是高兴的罢。我生下的是儿子,莫家有后了。奶奶再没有理由难为你我了。”
原來我给予她的,从来都是被束缚的伤痛。我以为我的爱让她展露笑颜,但其实,却成了她嗤之以鼻的枷锁。
她从来就未爱我。她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挣脱莫家的牢笼。
而我却倾尽全力,只为博她一笑。
那一刻,我真的开始恨秦若漪。我疯狂地用手扫去并排而立,好似佳偶的一对白瓷茶杯。它们碎裂在地上,而我的心碎裂在她淡漠的眼神里。
是时候要离开,我再没理由留下。
我走的那日,正下着瓢泼的雨。我这样在她面前落荒而逃,我问她我演的戏好不好。我演了这么久的戏,骗所有人包括我自己我不爱她,对她却从来没有演过戏。我赠她她所要的,抑或她不要的,我的所有,究竟这一生,谁薄情,谁长情?
阿漪,我背弃了我的诺言,不因我寡情薄意,因你从来吝啬说一句爱我。
廿
故事的最终,我又一个人去蘅安看河灯。在汹涌的人潮里,我望见了你,你虔诚地放下了我的簪子,将它放在了河灯里。
已经二十年了。这二十年里的想念与伤痛顷刻消逝殆尽,一瞬只让我看见这支你留着的玉簪,在火花里闪烁。我忘了你种种的绝情,因我晓得,你也记得我,你至少还记着我,用了二十年去记我。
这二十年很冗长很冗长,每日在漂泊中我不是没想过我们的重逢,却没料到是在这河灯的光影里看见了你。
你不晓得,我每年都会画一幅你的画像,岁岁年年,长记心间,斯人难觅,唯画寄情。我问你我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其实,也不过给站在我眼前的你画一幅像。
你不晓得,那一河的红莲,是我赠你最后的礼物,并着我的离去。如果你在后来的岁月里,爱上了比我更好的人,你再也无需担心什么——这是我欠你的,我该还你。
你不晓得,在月老庙的那一个黄昏,对那个放我自由的你,望着伤痕累累的你,我早已情根深种。总想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才会如此眷恋地握着你的手。
你不晓得,我不敢在你面前说这些我对你做的事,说一句我的心意,只因我以为你会懂。早知你这样的木讷,阿漪,我用十几年想清楚,我早应该告诉你,阿漪,我最爱的人不是菀笙,是你。我不该再用奶奶,再用你二哥,再用菀笙作借口。我觉得你吝啬,其实我也不愿低头,直接同你说我爱你。
现在,我终究明了,其实你也用了这样的二十年,记住了我。你也用这二十年,反反复复思量着那些我再也不会晓得的事情,反反复复思量着那些埋在你心底却从未说出口的爱恋,直到如今我们重逢。
爱不过是那一瞬的悸动,却折磨了我们彼此二十年。我们背道而驰,越走越远,始终有缘无分,阿漪。
我想挽回,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回首已是百年身。我重新拿起了那支玉簪,放在手心,望着你,却任由汹涌的人潮把我们冲散,没有再去喊你的名字。
回首已是百年身。阿漪,若百年之后你看到了我写的日记,看到了这封长信,看到了这支玉簪,看到了这么多的画像,我的悔恨,你应明了。我当时说不出的许许多多情话,原宥我,我再也无法亲口告诉你——在池安镇里住着一个倔强的丫头,她是我心心念念的人,她是我的阿漪。
那时,我一定不在了,但池安的莲花,你要看着,孤灯清夜芙蕖寐,想必一定漂亮。
惟愿来世,共度朝夕。
廿壹
莫之耹递给我的包袱里,竟是莫懿写给阿婆的信、画下的画,还有那支我要寻的玉簪。我取出那支玉簪,深望良久,也只有凄然的痛楚。一段本应相依相守的佳话,却变成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痴念。
若他们没有遇到彼此,莫懿依旧做着那个千金买醉的混世魔王,阿婆只做着那个温婉可人的大家闺秀,如此相安无事,笑看盛世浮华,也应是好的。
偏偏相逢,偏偏又错过。
我正叹惋着,冷不防莫之耹已站在我面前,笑吟吟地看着我,问:“可看完了?”
我点点头,将除了玉簪的所有东西都归还于他,问:“你是从何处得来的呢?”
他又拿起茶杯兀自倒了一杯茶,啖了一口才说:“你不晓得之前在这的阿婶是何人么?”
我说:“不过就是个卖茶的人么?”
“错,”他定定地看着我,“她就是孟菀笙。”
我一时惊讶不已。
他说:“想必莫懿折磨的不仅只有他和你阿婆,还有孟菀笙,从她的容颜你自然看不出她曾几何时的妙容了,所幸莫懿带着她,还是找人把她的手医得半好了。还有,”他好像有几分惋惜地说,“莫懿已不在这世间了,一周之前他就去了。自然,他只能据实以告孟菀笙,托她来找你阿婆。却不曾想,你阿婆走得更早。”
“他们到死都不晓得彼此的心意了。”
“这又何妨,”他又展开了折扇摇了摇,“依我看,可怜人只有一个孟菀笙。莫家觉得亏欠了你阿婆,莫氏不仅将她的牌位放在莫氏宗祠,还将她葬在莫氏的祖坟里,葬的可是鸳鸯墓啊!”
“鸳鸯墓?那莫懿……”
“莫懿的骨灰被孟菀笙带回了,早已被葬在墓穴中。他们奈何桥上自然还会相见,若有执念,来世再做一对有情人便是了。可惜孟菀笙一人,还要如此凄凉地过活,只因还承着你阿婆相让莫懿的一份情。”他收起了扇子,皱眉叹气道。
“这些事,你如何都晓得呢?”我哈着气往玉簪上吹,不由觉得疑惑。
“我如何晓得?我便是莫家派来找孟菀笙的人。其他的,你就不需再问了,即便问了,我也不会再答了。”他收起扇子,猛地夺过了我的玉簪,说道:“这一桩往事,已经结了,我说的话,勿要再告诉任何人。”
“干吗无缘无故抢我的簪子?”我着急了就想去拿,却又被他的纸扇所挡。
“可还记得你答应了我什么?我有个条件,就是这玉簪你不能拿回去。”
“为何?这簪子本是出自我阿爹之手,理应归我。若你毁了也可以,但你绝对不能留着它,留着这簪子是要遭罪的!”
“哦?遭罪?秦莫语,你老实告诉我,为何非得找到簪子,却又要毁了它?说实话了,我就还给你。”他将簪子悬空放在我头的正上方。
“我死活也不會告诉你的。”我看拗他不过,反而转了个身,不再理他,所幸想拿起包袱走,之前不忘恶狠狠地对他说,“你要是遭了报应,可别怪我。”
“秦莫语,别走啊,”他突然挡在了我面前,嘴角上扬地说道:“我毁了簪子,可你要再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觉得遇上这个混账真是逃不过的大劫,想着太阳穴就突突地疼,我只好说:“世上真有两种人拗不过,一种是你这种无赖,一种是你这种流氓。成了,我依你就是了。”
他闻言很满意地点了点头,将玉簪掷到脚下,狠狠踩了几下。玉簪瞬时只剩白色的齑粉,多少往事都随风而去了。
随后他拿起了包袱,对我说道:“午时在船埠等我。”我拦了他一下,奇怪地问他:“为何要在船埠等你?”
“你要寻的不过就是你小册上的簪子。你说好巧不巧,我也是为了它们所来。而你不会不晓得你要找的簪子,有两支在蘅安祁家的手里罢?”
我一下子懵了,这种消息他都晓得,他果真意有所图。“你是要,跟我一起寻簪子?”
他轻笑了一声,转头望着我说:“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秦姑娘,你压根就没有钱负担船资,不如我们各取所需。我有的最多的就是钱,我也只是想寻来簪子图个新鲜,据说安乡一线,人们都晓得你阿爹手艺最好,而这套花簪最是出名。我只不过是个闲人想寻来看两眼,你不会不肯罢?况且,我有的是钱买这种消息,你不会亏的。这事,我看就这样定了。”
他语罢漫不经心地从包袱中抽出几张银票,不管不顾我的意愿,强行塞在我手中:“拿着。”
我不接:“就算我同意,也不该拿你的钱。”
他弯下腰将银票卷起塞在我腰带里:“小姑娘,看来你还是不懂钱能通神的道理。装有骨气是没有什么用场的。”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又像一阵风一样消失在我的眼前。这个怪人,先前称是游山玩水而已,分明只是不让人起疑。他也一样要找到那一副花簪,但仅仅是为了赏玩一下就满足了么?
下期预告:
秦莫语与莫之耹为了寻找芍药簪与牡丹簪来到蘅安。莫语却发现莫之耹在半夜偷偷摸摸私会以前的旧情人,跟踪后不幸被他发觉。慌不择路逃跑之后,她误入牡丹园,中了迷药后被一位戴着面纱的女子绑走。醒来时,她才发现,那女子就是她要找的苏伊洛,而苏伊洛的姐姐苏将离也被一起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