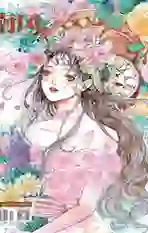也遇滩涂惊起白鹭
2017-08-02蒋祖贺
蒋祖贺
1.
林少平敲门进屋的时候,徐江江正一个人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他跟过去站在她的身后,窗外细雨纷纷,雨中的上海到处霓虹倒影,街上的行人奔走于不同的际遇,她也不看他,轻轻说道:“下雨了。”
林少平提醒:“采访要开始了,记者已经到了。”
那是场和往次无异的采访,江江性子平和,耐心听完问题然后娓娓回答。
“徐小姐,作为一个旅行作家,这五年里你走过这么多地方,你最钟意的是哪里?”
“安固里小镇,我的故乡。”
“传言您是在那里遇到了傅豫行?”每篇报道总要比之前有些新意,吸引眼球,记者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开始变得刁钻起来。
“你去各地旅行是为了找傅豫行,你写书也只是希望有朝一日他可以看到你,甚至你在每本书的结尾都会贴一张寻人启事,将自己真实的联系方式公诸于众,可是你找了五年还是没有他的消息,你都未曾想过放弃吗?”
徐江江想了想,眼神落向远处。
“我曾经读过这样一个故事,古代有张羽煮海的故事,他为了能够和被龙王囚禁在海底的龙女妻子在一起,不惜在海边架锅想要将海水煮干,结果神仙被他的行为感动,便施以仙法,使得海水沸腾,最后龙王只好将龙女推出,最终张生携妻而归。我相信,有时痴执一些也是好的。”
记者不依不饶:“你有没有想过,他已经忘了你,不愿意见你或者身边已经有了其他人?”
江江浅浅一笑,“那是其他的事了”,她顿了顿继续说:“我要做的只是找到他。”
她说完低下头,手指摩挲着印在书末页的那张照片,像是手中拿着的是这世间最珍贵的珍宝。
她还记得这是最初见傅豫行时偷偷拍下的,当时他站在院子里一棵巨大的榆树下,薄光透过树冠斑斑驳驳地落在他的耳郭和颈窝,他的头发修的短而利落,眉眼清俊。
照片下面,有一行小小的字。
傅豫行,身高178,或許还会长高,喜静不喜讲话,会拉小提琴会写很好看的瘦金体。
如果你有他的消息,请联系我。
最初有太多人发各色邮件来,有人好奇她和傅豫行的故事,有人祝愿她最终一定会找到,有人说她是炒作,也有人说了一些他的踪迹,她每封都细细看,也循着信里的信息去找,只是她踏过了万水千山依然徒劳无功,有好心人询问她是否有其他信息。
江江摇了摇头,没有。
这么多年了,她所拥有的不过是这样一张模糊的照片而已。
安固里的那栋老房子,灰色调,长长的巷街,不很宽敞,但是敞亮干净,有碧草幽兰点缀,家户门侧斜支出一块木板,写得是江氏客栈,算不得草书,笔画勾连间拖出潇洒。有人推门移步,清瘦的少年左下眼睑睫毛间有一个小小的痣。
长长的一生里,他们明明早早相逢。
2.
江江家在安固里小镇开了一家民宿,十六岁的江江就能够在店里独当一面了,什么穿戴的客人是大客人,什么时候应该加价她比谁都清楚,那时她还梳着两个牛角辫,夸起安固里草原来摇头晃脑很能唬人,她年纪小旁人瞧见她的模样自觉的娇俏天真,再加上她嘴巴甜,叔叔阿姨唤起人来,真把人逗得心甘情愿掏荷包。
林少平这时候就会瘪着嘴讥讽她,“你看没看过新龙门客栈,你就是店里的黑心老板娘金镶玉。”
江江才懒得理他,只当是夸她如同张曼玉一样风华绝代。
只是林少平还没有想到,江江之后会遇到傅豫行就好比张曼玉遇到梁家辉。
那日,江江正躲在柜台里面看少女漫画,突然听到有人问:“小姑娘,我们想要长租,叫你家大人出来。”
江江听到是个大生意,本能地堆起笑脸抬头,面前是一位年逾四十的中年男子,但是仍旧外形潇洒举止优雅,她眼珠一转,现在是淡季极少有客人来,而此人方才说要常住,一定是有一些必要的事情要办,她想要装作难为情地借口淡季长租耗费太多人力,探探口风再做加价的打算。
那男人显然并不在意价钱,未等江江说完便打断直接询问房价。
江江喜不自胜,可是就在江江开口的前一瞬间,她突然看到了站在男人身后一个清瘦的少年,走廊里透过的光照在他的眉目间,明明是十七八岁的光景神情却又冷峻老成。
江江只觉得心中像是被人投进了一颗小小的石子,而涟漪一圈圈散开,让她堪堪红了脸,于是她鬼使神差地给了对方一个低价。
男人的字好看,江江歪着头辨认了一会才念出,傅晖。
突然间她仿佛又想到什么要紧事,冲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叫:“每个人都要签字的。”
少年回过头来疑惑地看着她,她咬了一下嘴唇,朝他下颔一抬,“这是我们这里的规矩。”
然后江江看着他一步步走近,拿起柜台上的笔,在那本入住登记册上端端正正写上自己的名字,傅豫行。
江江的笑意漫到了唇角,他稍稍抬头与她平视。
“你这么精明的女孩子也会相信漫画里的故事吗?”
江江看清他眼底的不屑,怪的是一向伶牙俐齿的她那一刻只是愣在当地看着傅豫行的身影消失在走廊的那一头。
她后知后觉地发起脾气来,转身取来一把小刀将他的名字从登记簿裁下去,揉成小团扔进垃圾桶,又觉得不解气忿忿地对着垃圾桶骂了几句大混蛋。
江江给人低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江妈耳朵里,她气得跳脚,左眼睛的眉毛挑到额头上去,告状者林少平站在一旁气得腮帮子鼓鼓地瞪江江,还不忘帮腔数落她。
江江觉得林少平的样子像极了鼓着大气泡的青蛙,忍不住低头抿嘴偷笑。
这下被江江妈看到了,更是火上浇油。
“徐江江,罚站一小时。”
江江耸耸肩,漫不经心地踢着脚边的石子,只怪自己一时色令智昏做了傻事,白没了一大笔生意不说还被傅豫行摆了一道,实在可气。
3.
那晚有些微冷,她抱着胳膊在原地靠抖动来保持热量,过了一会林少平冷着脸扔了一件外套在她身上。
江江狠狠剜了林少平一眼,将外套罩在身上便转过脸去。
她打从心里讨厌林少平,只是奈何双方父母是半辈子的好朋友,她自小自愿不自愿地要和他一起玩,只是江江比他小上两岁,他就时常欺负她,似乎最大的乐趣就是逗她哭。
林少平踱着步走到江江对面语气轻佻地问。
“怎么,你喜欢上那个从南方来的小白脸啦?”
江江的脸霎时间从腮边红起来,漫上耳朵去,最后她恼羞成怒朝林少平的位置啐了一口,“呸,你才喜欢那个小白脸,我和他不共戴天。”
谁料林少平却没有立刻离开,他站在暗处,脸隐在朦胧里。
“雁过无痕,它是不会记得途经的水潭的,你可别犯傻。”
傅晖当真在安固里常住,三个月后,大家就传开了他的怪异行为。就连江江也想不通气质出众的傅晖为什么放弃之前的生活,而是在景区找一份类似负责维持排队秩序的工作,这份工作十分辛苦,薪资也单薄,何况安固里湖旅游淡旺季很明显,可是无论每日有没有客人,他都会按时六点起床,然后穿戴整齐站在进入景区的必经之地,眼睛望向远方,像是一尊雕像。
至于傅豫行,他很少出门,大多时间是坐在窗边安静地读书或者拉小提琴,也不和人讲话。
林少平靠在柜台边总结,“两个人都不正常,你看上的小白脸不会是哑巴吧?”
江江生了气,狠狠地踢了林少平一脚,林少平疼地哇哇叫:“怎么了,你心疼了。”
这句话刚好被从房间走出来的傅豫行听到,他喜怒不明地看了江江一眼,转过脸去对林少平说:“房间里漏水。”
林少平皱在一起的五官还未舒展开,呲牙咧嘴地瞅着身旁冷着脸的江江,并不答话。
最后是江江耐不住性子,推开林少平,弯腰取出工具箱,腮边牙关一紧,冷冷地对傅豫书说:“走吧。”
屋里水管坏了正不倦地往外喷水,傅豫書一副少爷样站在门口抱臂居高临下地瞅着江江忙活,江江动作慢,他也不急。
“哎呀。”拧扳手一歪,原本已经关上的水管又咧开,水迸溅出来,江江立刻遭了央。
傅豫书悠然踱步而来,蹲身,从江江手中拿过扳手将缠在水管上的铁丝用劲扭上。
水停了,江江的头发湿漉漉的垂在眼前滴水,她瞪着傅豫行。
“你就是故意看我出丑。”
他掀眼,“我们租房,房间出现问题原本就应该你们来解决,何况,我本来打算叫那个男生。”
傅豫行的话有理有据,江江憋了一阵只甩下一句“你就是故意”。
江江因为傅豫行生了好一会闷气,院子里猫在树荫下蜷成一团,用慵懒的午睡打发漫长的时光,小草投在地面上细碎重叠的阴影。
她在本上写了好几个傅豫行的名字,然后再用笔狠狠划掉来撒气。
4.
江江和林少平打的赌是直到暑期安固里旅游旺季的时候,她才输的。
景区工作量大,傅晖中午只能留在景区休息,他多付了饭钱,于是江江家每日中午的饭桌上多了傅豫行的一副碗筷。
傅豫行是南方人,吃东西的口味和北方不大一样,口味清淡到极点,江妈做的菜对他来说太咸,他每次都要备一个空碗放上清水,无论什么菜都被他吃成水里捞。
所以当在一旁埋头翻白眼的江江听到江妈吩咐她,以后每天中午她单独为傅豫行做一份不放盐的菜,她理所当然唰地站起来冲傅豫行喊。
“你怎么那么招人讨厌呢。”
江江立下的在傅豫行离开之前再也不和他说一句话的誓言,被她一着不慎违背,林少平喜滋滋地看着江江愿赌服输地将一百元上交。
“我从现在重新立一个,这次赌资是二百。”
大概是江江命里注定和钱无缘,在她咬牙切齿地重新立誓的第三天午后,她先前偷吃冰激凌太多,到了黄昏胃病发作起来,她疼得在床上缩成一团。
正是客栈最忙的时候,江妈抽不出时间照顾她,就连平时如同一只苍蝇赶都赶不走的林少平都偏偏不在。
疼痛如跳针一样一下一下传来,傅豫行拦腰将她抱起的时候,她也顾不上说话,任由那人抱着她去了最近的诊所。
诊所的大夫算不上和善,看了病情开了药留下一句以后少吃凉的东西就躲回里屋,剩下傅豫行在帮她烧热水,她撑着力发脾气。
“傅豫行,不许你管我。”
她一直疼到夜里,额头往外渗豆大的汗珠,傅豫行不理会她之前的警告,扶她半靠他怀里,他的手修长比她的体温稍高,轻轻覆在她的小腹上,稍有些肉感,掌纹微微粗糙,像是灌进去的一大杯热水。
很小的时候,她总喜欢躺在母亲怀里睡,午后许多阿姨会来家里聊些家长里短,她半睡半醒可以感到母亲胸腔因为说话的起伏,让她有种莫名的心安。
“傅豫行,你陪我说会话吧。”
若是搁在平常,傅豫行一定会无视她的要求,可是月光透过窗缝隙间投到地上,冷冷的一片,很白很淡的月光,他的声音低沉有些微微的沙哑。
“我妈其实做菜不好吃,每道菜都有一股子糊锅味,原来年轻的时候似乎一直是我爸做菜。只有一样我喜欢,她包的馄饨下到锅里就像一朵云。”
江江听到里屋电视机传来的声音,还有吊钟一刻不停地滴答声,傅豫行过了很久才接着说。
“你妈妈是爱你的,她跑来找我送你去诊所的时候鞋带开了都没注意。”
江江听了心里像是被什么钝器割了一下,隐隐作痛。
父亲早逝,江妈一个人撑起整个客栈,岁月将她打磨成一个市井庸碌的女人,别的孩子拥有的专属于母亲的关怀,江江得到的都很少,比如今晚,其实她是偷偷怨过的,只是她没想到傅豫行会看出来。
5
大概归功于傅豫行,江江的胃第二天好多了,傅豫行煮了小米粥,刚出锅盛在碗里会烫手,他站在锅后,朦胧的白气腾起将他坚毅的五官柔化,粥被他捧在手里轻轻地吹。
江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傅豫行,动作有些笨拙,她躺在床上噗嗤笑出声。
她在之后好几个夜里反复确认了那一夜傅豫行掌心的温度,她有些脸红,叹了声气在床上来来回回滚了好几周,将脑袋埋在被子里,小腿抬起来在空气中了扑棱了几下,最后无力放下。
因为这件事,江江开始觉得傅豫行似乎没有从前那么面目可憎,于是寻着借口有事没事就喜欢跑到傅豫行的房间,理由从调查住客满意度到视察住房是否有任何老旧危险层出不穷。
久而久之,傅豫行习惯了房间里会出现她的身影,也习惯了她无所事事唤他阿行。
熟络之后,江江知道了许多有关傅豫行的事,比如他已经具有两位数琴龄,江江时常缠着傅豫行拉琴给她听,渐渐地她也知道了大顿特的练习曲、巴赫随想曲、莫扎特和柴可夫斯基,他的曲调明朗清澈,眼神专注和清绝。
江江也会小心翼翼地问:“你们会在这里住多久?”
傅豫行摇摇头,他靠在墙壁上,闭着眼睛。
“不知道。”
那是江江第一次知道关于傅晖来安固里的原因。
从前,傅豫行的父母是十分要好的。”
节日里,他们会出现在西餐厅的落地长窗旁,餐厅的情调高雅浪漫,酒红色丝绒窗帘,繁复的褶皱,水晶灯下,烛台纤长,餐具熠熠发光,他们像是这世上任何一对相爱的夫妻。只是后来感情在平日的油盐酱醋中磨损耗尽,大约是从两年前,他们开始不停地争吵,砸东西,冷战。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年,最后一个人选择了离开,而这时另一个人才突然惊醒,明白自己有多爱这个女人。
江江张大了嘴巴,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她有些艰难地开口。
“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因为,她曾经说过安固里或许就是天堂和尘世的交接点,这里适合散漫地行走,天地茫茫,天人合一。”
“所以你爸爸才会选择一份这样的工作,他相信终有一天你妈妈会出现在这里,他是在等待一个挽回的机会。”
江江感觉自己的胸腔仿佛被被什么东西填满了,一切都有了合适的解释。
傅晖不肯在这里买一间房子,而愿意支付昂贵的长租费,他甚至帮傅豫行聘请了私人教师却不想办理手续让他在当地的学校借读,是因为他固执地相信,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等到自己的妻子,一切重新来过。
江江弯下腰,她突然想去摸一摸他下巴上因为小提琴的腮托已经磨出的一块厚厚的茧。
她想起林少平总是搞混“一步之遥”和“触不可及”,此刻她竟然觉得这两个词太像了,尤其是听他在微光之中讲述时,那一刻这两个词根本是同义词。
6.
林少平对于江江和傅豫行的亲近嗤之以鼻,他找来许多古书描述旅经某地的书生和当地小姐产生的爱情悲剧。
“江江,你明不明白,傅豫行迟早是要离开的,到时候就只剩你守着旧景独自伤情,你指望他会记得你吗?”
“有意思了,我偏偏喜欢。”
正午的阳光在窗台慢慢地跳跃,幻变成一点点白光,她那迎着窗外天光的小脸上几乎要映出辉来。
她想起之前听过的一首杨千嬅的歌,她是这样唱得。
愿意与他一起,未怕天行雷。
林少平或许是真的生了气,青筋尽往他脖子上绕,摔了门出去。
傅晖来到这里一年之后,他要等的人始终没有出现,他做出了妥协,将傅豫行送去县城一家私立寄宿中学,只有周末才能回来。
江江至今还记得自己在路口等得脚麻站起来想要活动一下的时候,刚好看到傅豫行坐在车上单腿支撑,那双眼睛里隐有星芒闪动。
他叹了口气,“上来吧。”
恰逢夜灯开闸,小路上稀稀疏疏没几个人,她会拉着傅豫行的袖子喊他加快速度,他们嗖嗖骑过去,刚好一盏灯一盏灯地接连亮了起来。
她在那一刻,将脸靠在傅豫行宽厚的背上,风从耳边呼呼而过。
车轮滚过地面,有微不可闻的啷啷声,细听竟像是首歌。
她听见自己小小声说了句。
阿行,阿行。我原本不想喜欢人的。都是你,都怪你。
黄昏的阳光最有人情味,薄薄的一层橙黄,晦明影翳间被拉得长长的渐变,对面斑驳的房顶、某扇窗子里迎光的君子兰旁趴着一只被晒得金灿灿的喵,另一扇印着喜字儿的窗边垂着奶白色窗帘。
他们不急着回去,傅豫行就将单车停在道路一旁,两个人一起躺在草地里,江江翘起高高的二郎腿。
傅豫行给她读汪曾祺改写的《瑞云》。
书中最后瑞云恢复容貌,她高烧红烛,剔亮银灯,贺生却不像瑞云一样欢喜,他觉得若有所失,他心中重新涌起当年只能仰视不能靠近的无力,情到深处会百般觉得自己配不上心上之人。
他念这段话的时候,目光专注凝视着书,声音那样温柔地流淌过江江的耳际,因日落后昏暗的景色而模糊,因周围其他的声音而模糊,模糊而美丽的犹如雾夜星河。
江江情不自禁,凑上去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然后她歪着头,笑盈盈地看着一脸愕然的傅豫行,一仰头学着影视剧里那些挑逗了名门正派的小妖女,眯了眯眼。
“怎么,你不知道吗,我们安固里的女孩子都是这么豪迈的。”
傅豫行没有回应,他垂了垂眼,长而浓密的睫毛遮挡着,江江看不见他的目光。
只是她当时并不知道,也是要过去好久好久,她才知道傅豫行实则是将自己比作贺生,爱是自卑的根源。
7.
江江忐忑辗转了好几日,最终确认傅豫行打算对她的告白无动于衷,这个发现令江江十分挫败。
她闷在屋子里自怜自艾了好几天,只有林少平来看她。
“就说你是自讨苦吃。”
他见江江将脸转向别处并没理他的打算,倒也不介意。
“后天鎮长嫁女儿听说要放烟花,在家后面景区的城门上,借部队的大炮,我带你去解闷吧。”
江江来了兴致噌地坐起来,头发乱糟糟一团顶在头发,圾上拖鞋跑出去敲傅豫行的门。
她复读机一样告诉傅豫行放烟花的消息,然后满怀希望地等着回应。
“我对烟花不感兴趣。”
江江将手撑在门框上,装作蛮不讲理的样子。
“我不管,后天八点我在那里等你。”
江江对于傅豫行是否会应邀不确定,她吃过晚饭便去抢先等待,挤在人山人海里,抬头便是大片大片的璀璨,烟焰蔽天。
她心里打好了千千万万遍腹稿,带着胆怯和紧张的成分,不停说着“借过,借过。只是直到放射烟花快要到尾声的时候,也始终没有等到她要等的那个人。
周遭所有人都喜眉喜眼,唯独她,只有她。
林少平不知什么时候站在她身边,他说:“你看这烟花多可爱。”
江江说,是可爱。
“他对你不好,其实是对你好。”
谁也不会想到傅晖会在安固里等待三年,江江能夠明显看到他的变化,他的眼睛变得浑浊,衣着不再整齐,或许就连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他对现在的等待生厌。
他每天都要喝许多酒,但是照旧六点起床守在景区,但是同之前不同的是,他醉醺醺地斜倚在门口,两只手软垂着,有时他甚至会忽然拉住一位游客问,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妻子?
许多游客开始向景区的管理部门投诉,几次协商无果,很快傅晖就被辞退了。
但是傅晖仍旧每日早起去景区,不知道是谁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叫一个人告诉傅晖有人曾经见到过他妻子,只不过好像是去了香港。
这个消息漏洞百出,不过是吃准了傅晖的软肋,他那份卑微又凄怆的期望使他沦为了别人的笑柄。
江江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刻跑去告诉了傅豫行,而等他们一起赶回去的时候已经看到傅晖弯着腰收拾行李,他看到傅豫行,满眼惊喜。
“快,阿行,我们一起去香港找你妈妈。”
江江站在一侧,她看着这个曾经潇洒的男人如今满脸沧桑,鬓间生了白发,他的模样像是得到允诺的小孩子,她偏过脸去,心里忽而柔柔牵扯一下。
傅豫行蹲下去,面对着自己的父亲。
“爸,妈妈不会回来了。”
这话像是一颗炸雷,听到的傅晖忽然站起,他的手扬了起来。
“你再说一遍。”
他的声音冷得让人打寒噤,江江生怕傅豫行再说出什么话,上前拉紧他的衣袖。
一时间,房间里十分静寂,两个人就这样沉默地对峙着,最后傅晖缓缓地放下了手,他的手指插在发间,慢慢地坐了下去。
江江在那晚听到傅豫行久违的练琴的声音,几个关键的衔接被处理的上气不接下气,就连音准也出了问题。
江江的心跳有一种奇怪的频率,迎面是深深而又凄寂的黑夜,仿佛一切前景转身化成一堵墙。
8.
傅豫行要离开的消息是林少平第二天告诉江江的。
“傅晖现在需要有人陪,他是一定要走的。”
江江以为自己会大胆泼辣地哭一场,窗外天色阴晦,细雨绵延不绝地落在院子里,从榆树的树叶上溅起碎语的声音。
她一边往自己的房间走一边低低地碎帛似的哭泣。
听到有人敲门已经是深夜了,江江坐在床边,她知道是傅豫行却并没有开门的打算,门外的人也并不坚持,敲门声渐无,就当江江以为他离开的时候。
她听见他开口,将他这一生所有的秘密告诉她。
傅豫行母亲决定离开的那一天似乎和往常没有什么区别,母亲照旧早起准备了早饭,然后将他叫起,在饭桌上嘱咐他一定要好好练琴,每个音都要认真扣。
电视里在放财经新闻,桌上只有餐具偶尔磕碰的响声,窗外有猫在叫。
他开门的最后一刻,母亲叫住他,阿行,下午你放学妈妈带你去照相好不好。
其实在那一刻他就知道妈妈从此于他而言可能永远只是一个音信杳然的称谓,他轻轻带上了门,答了声好。
也是从那之后,他讨厌拍照,即使留下一堆影子,从前的日子也不会回来,索性不要。
也是在那一刻他明白,人与人的关系有时候像是一叶舟,它随风,随浪,不随你。
江江哭的波长和夜晚其他混声的波长合在了一起,因而傅豫行没有听见她的哭声。
她抱着希望,得到允诺的希望,还会相逢的希望问了一遍又一遍。
“你还会不会回来?”
他的声音微微沙哑:“你看完我房间的书的时候我会回来看你。”
就因着这句话,安固里每天从等待中醒来的人由傅晖变成了江江。
她将汪曾祺木心苏童矫健李碧华严歌苓老舍董桥读遍,却都是枉然。
她被岁月驱赶着长大,周遭人山人海,抬头便是夺目光景,她却心猿意马,东张西望妄图在人海中寻找一个相似身影,却无一次凑巧过。
月不得明,露不得下。
而她未能得见他。
但是江江不是傅晖,她不会只等在原地,她开始写书去各地追寻傅豫行的脚步。
眼下越无希望,她却有信心,像是在赌那匹最瘦的马。
尾声
那场签售会结尾,江江注意到人群里一个泪流满面的女孩子,她穿过拥挤的人群走到她面前。
“你怎么了?”
她哭着说:“江江姐,我知道他的消息。”
江江并不像自己曾经设想过无数次的那样激动,相反她的手僵硬地停在身旁,机械地问出一句。
“他在哪里?”
女孩儿的手绞着衣服下摆,结结巴巴将事情的原委说了出来。
原来傅豫行没有失约,五年前女孩想要自杀,傅豫行发现这个坐在他对面的女孩子不正常,在她下车的时候跟着她,然后不出所料的她跳进了离火车站最近的湖,于是他立马跳下去救她,只是他救上了女孩子之后,自己的脚却被湖底的海藻缠住,等到警方赶到的时候人已经没有了呼吸。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江江伸出手抓在女孩的肩膀上,青筋暴起。
林少平听到了动静赶过来,将她的手拉下来。
“江江,冷静一点。”
女孩大概是被江江的样子吓到了,缩着身子哭作一团 。
“我不知道,我是不经意看到你书里的照片才发现那就是大哥哥的,我不是有意的。”
原来那日,傅豫行跳下湖救人的时候,将身上的物品就扔在一旁的草地上,而有人趁乱将他的东西偷走。
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警方贴了好几日的消息也找不到亲人,最后只能立了一块没有名字的墓碑,风穿过泥土的缝隙,飘落的灰尘堆积了一地细小的沉默。
江江随着女孩一起到了傅豫行的墓前,墓碑上没有他的照片和名字。
她的手抚上去,微笑地唤他。
阿行,阿行。
我再也不能等你了。
江江不记得她呆了多久,她能够感觉到夜幕在她右手边渐渐沉下来,像坐在小舟里,忽悠一下,浓墨喷薄。
她突然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从那天的漫天烟花里她早就失去了他。
只是江江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坐在那辆开往安固里的火车上,对面的阿姨问起小伙子要去哪里。
窗外光景变幻,他眉目温柔。
去看我心爱的女孩子,江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