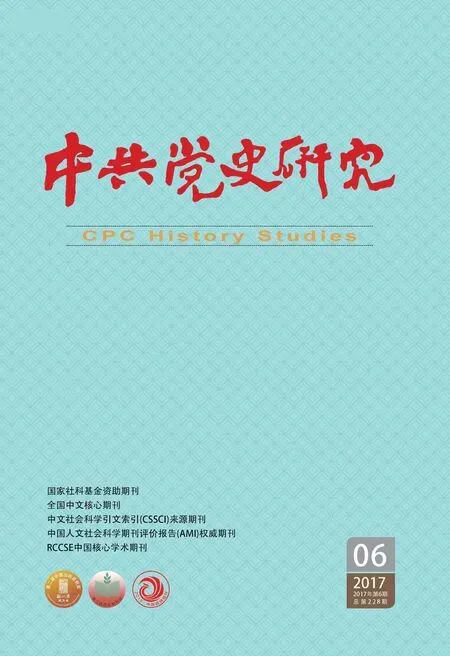天津解放初期工厂接管的历史实践与伦理意涵
2017-08-02符鹏
符鹏
天津解放初期工厂接管的历史实践与伦理意涵
符鹏
天津解放初期,中共面对工厂这一新的社会空间,创造了新的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接管之前,中共对天津工厂的历史理解并不深入;接管之初,干部的工作能力和组织准备也不充分,不断遭遇各种层次的问题和矛盾。面对这些不理想的状况,中共通过调整干部的工作状态,完善组织结构,理顺矛盾关系,逐步找到把握现实的实践契机。进而在每一阶段的工作中,渐次重组工作经验、组织形式与现实问题之间的互动与配合关系,从而解开不同层次历史实践中的结构性矛盾,将资本家、职员、工人及其组织形式推向中共期待的工厂民主建制方向。
天津;工厂;历史;伦理
引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立了工人阶级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对于工人阶级的这种地位,传统的革命史和党史研究围绕“翻身”叙事,形成了一套简明的规范化论述。当这套论述对应的社会现实发生转变之后,原有的叙事形式逐渐被抽空内涵,无法为人们提供把握过去时代社会实践和伦理生活的通道。近年来,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以不同方式对1949年后工人研究的推进,正是力图在学术层面对此加以重审。然而,细察起来,这些讨论往往在无形中受制于后冷战思维,先在预设工人阶级地位的意识形态虚幻性,并通过西方流行的极权批判和治理分析,在国家/个人的二元对立结构中,论证工人阶级被国家控制和利用的种种状况。事实上,这种讨论之所以获得优势地位,主要依赖于个案分析的选择。但研究者惯于从精心选择的个案中很快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判断,而对于个案本身所对应的特定历史环节及其在不同社会实践中的位置缺乏必要认知,最终过于简单地在个案分析和社会总体性之间建立表征关系,却无法真正触及1949年后工人问题的历史脉络和思想内涵。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对自身主人地位的认识,并不是以阶级论简单对应的结果,而是依赖于“建国”这一历史实践对于工厂空间的重新组织和打造。因而,如果不理解这一实践的展开所要求的那些历史条件以及所克服的结构性难题,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阶级论,都无法获得进入1949年后工人问题的历史感。在这种意义上,如何把握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接管工厂的历史实践,便成为思考工人阶级主人意识生成过程的前提所在。本文拟以天津解放前后工厂接管为中心,讨论中共以怎样的历史理解面对这一新的政治议题,调动了怎样的组织经验来处理工人——工厂——工会的三位一体关系,又如何克服新的历史情境中的结构性矛盾,从而将工厂打造为新的伦理空间。①工厂接管是解放前后中共城市接管工作的核心部分,“管理和建设城市中最中心的问题是管好工厂、发展生产的问题”(《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3页)。尽管在以往的城市接管研究中,工厂接管是研究者关注的论题之一,但大多数研究侧重从整体上概述中共城市接管的政策依据和历史过程,而缺乏对于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究。近年来,少数研究者的关注点逐渐转向城市接管个案的考察,但对于工厂接管的描述往往只是书中篇幅不多的孤立部分,至于其中的关键性问题则鲜有追问,诸如中共的工厂接管建立在怎样的历史前提之上?这项工作与其他接管工作构成了怎样的结构性关系?接管过程所遭遇的不同层次的矛盾关系对中共的革命经验带来了怎样的实践挑战?中共又是如何不断调整实践方式,逐步推展工厂的民主化改革,重构工人在生产空间中的伦理经验?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将构成本文重新整理和思考这一历史实践的基本线索。
一、旧制度下的工厂与工人:接管工作的历史前提
1948年11月,平津战役开始后,中共着手计划接管平津两地。12月份,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的工作人员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城工部部长刘仁带队到长辛店集中,准备接管北平工作;另一部分由城工部委员杨英带队到津西胜芳镇,筹划接管天津工作②王左:《进城前的回忆》,《天津接管史录》 (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第25页。。在随后的建制规划中,出于对北平可能作为未来首都的考虑,人员配置有所倾斜。但与之相对,天津的工业基础和工厂数量都超过北平,工业水平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③参见〔美〕贺萧著,任吉东译:《近代天津城市的塑形》,《城市史研究》第28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226页;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室:《解放前的天津工业概况》,《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华北局对于接管这样一座大规模的工业城市同样非常重视,尤其将工厂和工人问题视为工作中心。时任天津军管会副主任的黄敬特别强调:“进城后最根本的工作是工人运动,发展工业,恢复秩序,甚至对私人资本实行国家的领导,如果没有工人参加,则也很难领导。故政策的能否实行,秩序是否搞得好,工商业是否能发展,其根本环节,就在于天津的工人运动。”④《黄敬同志关于军管时期天津职工运动的讲话》(1948年12月30日),《天津接管史录》(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60页。
他在此强调的工作原则,对于理解天津接管非常重要。在此前对沈阳、石家庄和济南等城市的接管中,中共对于工厂和工人的根本性地位并没有形成这样的明确意识。而这一原则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前的实践经验。石家庄是中共接管的第一个中等城市。在接管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当时土改中“左”倾思潮的影响,再加上解放初期各种沉渣泛起,石家庄一度出现混乱局面。尤其是对于接手的工厂,因循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实行“工人有其厂”,分割财产,很快导致停工停产。同时,接管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并不重视工人运动。中共中央专门对此提出批评,“石家庄已解放了一年多,我们的干部还有这样倾向,即知识分子干部愿意找资本家职员学生谈话,农民干部愿意接近农民贫民,而工人却少人理会”,并由此强调:“工人阶级被遗忘,共产党忘了本队,在目前走向全国胜利连续地解放大城市当中是一个最严重的现象。”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615页。针对接管石家庄的这种教训,中共曾作出认真总结,希望此后的接管工作能够引以为戒。
在解放天津前一个多月对济南的接管中,由于吸取了此前的教训,接管过程较为顺利,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混乱局面。但在很多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仍然处于谨慎摸索的状态,并没有明确工厂和工人问题的根本地位。在平津战役的准备阶段,党中央指示华北城工部选派干部去济南学习经验,经过十余天的短暂学习,返回城工部汇报宣讲。①赵琪:《进城前后在市委机关工作回忆》、陶正熠:《天津接管过程中我的经历》, 《天津接管史录》(下),第12—13、395—396页。接管济南的经验对于中共接管平津非常重要。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5—6页。上述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确立的。那么,对于缺乏工厂管理经验的城工部干部来说,这一原则能否应对即将到来的接管工作?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追问这一原则包含着中共怎样的历史理解?而这种历史理解对应的天津工业和工人状况的历史前提又是什么?
近代天津工业受制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官办工业发育不良,止步不前,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更是处处被动,多有破产。然而,在这种工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抗争意识。从1918年至1926年,中国工人运动迎来第一个高潮时期。上海工人发动628次罢工运动,但与这种激烈的抗争态度相比,天津工人的反应颇为冷淡,只有14次罢工的记录②GailHershatter,TheWorkersofTianjin,1900-194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6,p.210.。天津工人抗争意识的匮乏,并非因为北方工人的保守,而是与这座城市重视商业、轻视政治的市民风气相关③参见王凛然: 《革命与认同:1949年中共对天津的接管》,《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2期。。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人的这种利益诉求被组织和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亦即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因素主要是籍贯、亲缘、庇护和阶级,阶级关系并没有成为他们组织自我的核心条件,而是由这些因素共同形塑的生存策略。在这种生存策略中形成的依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工人的行动可能,不同组织因素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还带来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因此,只有大型工厂中的产业工人才有反抗的可能,大多数的小工厂工人则毫无反抗的意识条件。
1928年北伐战争后,国民党赶走奉系联军,开始掌控天津。由于各军系之间矛盾重重,中央和地方之间貌合神离,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薄弱。事实上,从北伐开始到抗战爆发的十年,是国民党工运工作的黄金时代。北伐时期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再加上蒋介石的监查和解散,感召力和影响力都大大受损。而国民党则积极改组工会机构,从1928年开始相继发布《工会法》《工厂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法律条文,企图充分掌控工会和工人活动。国民党工会的基本方针是倡导劳资合作,鼓励民族抗争,反对阶级斗争。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国民党通过协调劳资冲突,的确为工人争取到不少劳动权益。④参见李永逢: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劳动保护研究(1927—1937)”,博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4年;赵洪顺: “国民党政府劳工政策研究 (1927—1949)”,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但是基于反对阶级斗争的原则,他们借助资本家和帮会势力控制工会和工人的企图时时扭曲这种诉求,终究未能消除与工人群体的隔膜,赢得他们的信任。
1937年7月,日军占领天津,整个城市的工业都受到日本的军事管制,国共两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都几乎销声匿迹。1945年抗战的胜利,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来得很突然。当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接管天津的敌伪军队、机关和产业时,因为毫无准备而乱成一团。各种国民党派系势力都希望从中谋取利益,中饱私囊。对于如何处理敌伪产业,国民党并无前章可循,具体的接管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将日本的企业查封管控,要求其交出名册,听候处理;另一种是对一般的工厂和商店按照原有清册接受,并另派人员开工营业。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不乏营私舞弊、损公利私的情况。⑤参见杨大辛、方兆麟编:《天津历史的转折——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1988年,第9—11、104、113—114页。结果导致工业生产全面瘫痪,直到1947年才得以大体恢复。
国民党在混乱的接管过程中,已经隐隐担忧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打入工人内部,甚至有草木皆兵之感。因而,他们很快通过重组工会,建立“防共小组”,推行保甲制,建立以“职工福利”为名的反共组织,与中共展开工运领导权的争夺。然而,事实上,此时中共在工人中间的组织影响力较为微弱,并不足以与国民党的“黄色工会”抗衡。而当国民党不同派系在工厂问题上发生利益冲突时,往往会栽赃共产党的指使,以便掩饰自己的利益诉求。①参见杨大辛、方兆麟编:《天津历史的转折——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回忆》,第82—91页。国民党内部组织的这种溃败,使得工人对其寄予的期待很快破灭。再加上连年粮食匮乏、通货膨胀,工人的不满情绪不断冲破“黄色工会”的掌控,发展成罢工抗议事件。从天津市社会局和总工会的档案资料来看,从1946年开始,劳资纠纷不断增加,工人的抗议活动也越来越频繁。鉴于这种状况,1947年5月1日,国民党社会部部长谷正纲视察天津,提出对工人的四点希望:扶助劳工组织;改善劳工生活;提高工作效率;爱护工厂,加强劳资协调②《谷部长对天津市工人的四点希望》(1947年7月1日),天津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25-2-3496-30。。但这些一贯的劳工政策已无法应对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重新挽回工人的信任。到1948年前后,随着中共地下组织在工人中间影响力的提升,自发的抗议活动逐渐在局部转变为有组织的罢工游行,不少工厂倒闭,勉强存活的工厂也只能维持间歇生产。
正是在上述历史前提下,中共开始筹划接管天津的准备工作。而从1948年黄敬《关于军管时期天津职工运动的讲话》来看,华北局在明确以工厂和工人工作为中心的政策时,强调中共在战争时期脱离工人阶级,“这次我们进入大城市是归队”。对此的后果分析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无产阶级失去先锋队的公开领导,国民党摧残镇压工人中的先进分子,故工人觉悟较低组织涣散。二、共产党长期地失掉了离开了本阶级,这就影响了党员的成份 (农民、小资产阶级较多),使非无产阶级思想常常侵入,同时,无产阶级参加解放区建设的也就很少。”③《黄敬同志关于军管时期天津职工运动的讲话》(1948年12月30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60页。显然,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共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阶级认知,以及此前城市接管中尚未定型的工作经验。在紧张的战争状态和短暂的筹备工作中,他们还不能充分地对上述历史前提进行深入的整理和总结。
在胜芳整训中,天津市军管会制定了《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纲要》《关于接管天津的任务与方针》《关于接管工作中几个原则问题的决定》 《接交注意事项》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政策的核心原则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④《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9页。。这个原则是陈云在接管沈阳时提出的,此后的接管工作大体照此而行。但经过接管石家庄和济南的经验教训之后,华北局在接管天津的问题上更明确地指出,对于国民党的行政和党团机构采取彻底取而代之的办法,而对工厂企业的接管则突出强调“原职、原薪、原制度”的“三原”准则。这项准则对于原有的国民党工厂体制和工人状况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中共干部来不及建立整全的历史理解的情况下,这项准则在具体工作中将会遇到怎样的现实问题?以往的研究并不深究这些关键议题。而在接管实践的展开中,接管干部则必须对此作出整理、分析和介入。
二、组织形式、革命经验与实践能力:关于工厂接管干部问题
从1949年1月14日开始,经过29个小时的战斗,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如何有领导有秩序地安排好接管工作,对于中共而言,便成为更具挑战的政治任务。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接管干部的工作能力。
在华北局对平津两地的接管安排中,干部配备的质量对北平有所倾斜,但数量差别并不大,参加胜芳整训的干部有7400多人,“所有干部都是来自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工作岗位,思想情况极为复杂,不同人反映出了不同的想法”⑤《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对外贸易接管处接管工作总结》(1949年3月10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246页。。如此庞大数量、思想复杂的干部,经过短短一个月时间的整训,便开始参与接管工作。可以想见,干部的工作状态势必难以达到中共期待的效果。事实上,从军管会及各工厂接管部门的总结来看,当时参加接管的干部数量虽多,但“质量又远不及数量”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接管城市工作初步总结》(1949年3月), 《天津接管史录》 (上),第109页。,且“在胜芳学习时准备坏的方面多,好的方面准备很不足”①《天津市工商局接收社会局初步总结》(1949年1月31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198页。,这意味着接管干部的工作能力并不理想。因此,如何安排和调动这些干部,对于接管的组织形式提出很高要求。
正如卢卡奇所言:“组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正象在每一种辩证的关系中一样,这一辩证关系的两项只有在这一中介中和通过这一中介才能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②〔匈〕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89页。换言之,理论的抽象观念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只有在组织形式中才能获得具体性和现实性,转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行动。不过,理论与实践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之中。组织不是理论的投射形式,理论的对错与否都要经过组织形式的检验,才能获得介入现实的实践契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特别强调组织作为一种意识过程的主观能动性。不难明白,组织形式的这种认识特质,对领导者的主体状态提出相应的能动性要求。
中共在城市接管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天津同样采用了军管会统一领导的方式,其组织构架大体如下:

从表面上看,这种党政合一的组织形式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但事实并非如此。接管工作不同于中共一般的组织工作。军管会的任务包含“接” “管”两个方面。就工厂接收而言,这是一项临时工作,它所要求的组织形式是临时性的,而工厂管理则是长期工作,它要求相应的组织形式的稳定性。军管会作为例外状态下的组织形式,需要同时涵括这两种不同的工作要求,并完成二者之间的接合和转换。经过此前城市接管的历练,这种组织功能已经稳定下来,但并不能保证它与具体工作任务和现实状况之间的自动配合。
军管会作为临时性的组织,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其与原有组织系统之间的冲突。参加接管工作的7400多位干部,有来自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石门市委、渤海区党委、冀鲁豫区党委等部门的干部,有长期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有各区党委党校及大学的学生,还有少数工人积极分子。其中不少干部是临时借调来参加接管工作,有人因此产生了严重的“临时思想”,认为“反正是要走的,因此不愿多负责任,不解决问题,恐怕将来结账拖了自己”③《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摩托接管处接管工作总结》(1949年3月14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303页。。这种心态导致被分派的工作停留在表面,游离于军管会的组织管理。而问题的根源还在于组织形式的矛盾, “由各系统调来之干部,尚有个别部门以直属上级决定之名义抵制军管会各部门负责人之命令的,军管会各部负责人也因来自不同地区,与干部联系有所顾虑,使某些问题不能完全贯彻”④《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1949年1月15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102页。。这一矛盾不仅大大降低了接管工作的效率,而且加剧了借调干部不安心工作的状况。面对此种情况,中共及时调整接管干部的隶属关系,所有各地各系统派来的干部,在组织领导、政策、行政管理、工作计划、日常生活等各方面都必须暂时切断与原有系统的领导关系,确保军管会作为集中领导的组织形式的地位。除此之外,军管会与天津市地下党组织以及工作组之间领导地位的矛盾,也都经过多方磨合,才最终得以消除。
即便军管会化解了不同工作任务之间的冲突,其组织状况依然并不理想。当时接管干部从上到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参与接管城市。在短短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中,尽管军管会也安排人员对天津的工厂状况进行清查和统计,但对于实际的组织要求并没有相应的经验基础,只能依据政策大体分配。而一旦进入实际的接管工作,中共很快就发现情况与预期的差距。由于接管前干部配备不周密、分工不明确,对各工厂情况的掌握不充分,因此,人员分配往往宁多勿少。如此安排导致接管工作缺乏秩序,干部力量不均,不能配合实际需要,出现“上忙下不忙,少数忙多数闲”的现象。①《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对外贸易接管处接管工作总结》(1949年3月10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258页。
如前所论,类似的混乱状况在1945年国民党接管敌伪产业时也曾出现过,最终对接管工作造成巨大损失。而要避免这种后果,顺利开展工作,就必须应对组织和个人都不理想的状况,使二者的关系与现实需要充分配合。
一方面,个人实践状态的调整依赖于组织能动性的发挥。一个良好运转的组织能够通过不断校正工作方式,重新定位个人在组织中的位置以及个人与现实的关系。每一个干部都不是赤手空拳进入军管会组织的,而是带着过去革命实践中累积的工作经验。因此,组织在重新调整其与个人的关系时,必然会碰到不同来源和形式的革命经验。当时参加接管的干部大部分来自农村,而农村工作是中共创造革命经验的主要来源。划分阶级成分,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完成土改,由此再造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但这些革命经验并不能直接转为城市接管工作的方式,尤其是面对农村干部不熟悉的工厂。农村干部的生活习惯、工作作风和业务经验,都不容易很快调整到工厂环境所要求的状态。因此,当时军管会领导认为:“完全在农村工作的区乡农民干部,一般不适宜于接收城市工作。接收企业的干部,一方面要懂得政策,另方面要有业务知识,否则起不了作用,反闹出笑话,造成对党的不好影响 (这次天津接收中,有许多干部看不懂人家的会计账目,看不懂英文簿记,使旧人员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没有人才)。”②《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1949年1月15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102页。
基于这种判断,军管会倾向于“多调政治上可靠,经验丰富,又在根据地工作过的老工人、职员,少调纯农村生长的干部”③《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接管城市工作初步总结》(1949年3月), 《天津接管史录》 (上),第109页。,“地下党员一般的都很好,他们对城市的工作能力比农村的干部强”④《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1949年1月15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101页。。当然,军管会并非就此对农村干部的状态置之不顾。事实上,接管干部普遍遇到的问题是找不到该做的工作,当时不少工作总结都反映干部工作积极认真,但能力普遍不足, “看不出问题不会主动地做工作”⑤《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摩托接管处接管工作总结》(1949年3月14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302页。。这种状况不仅是因为接管干部对具体情况不够熟悉,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找到介入现实的方式,所以,当时接管干部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工作难以深入下去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电讯接管处电信局接管组接管工作总结报告》(1949年6月3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350页。。这一问题在农村干部身上尤为严重。对此,军管会并没有采取简单的政策教育办法,而是强调“对新从农村来到城市之干部应具体帮助,只单纯原则指示不能解决问题,不但具体的帮助,同时须对具体事情从思想上解决,使其能从一件事情扩大到其他事情的处理上去,使其有勇气敢负责工作”⑦《天津市工商局接收社会局初步总结》(1949年1月31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198页。。换句话说,对于政策的掌握和领会,需要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进行深化。但对农村干部来说,如果不首先从思想上打通以往革命实践形塑的狭隘经验主义造成的认识障碍,便难以通过解决具体问题而获得同新的现实打交道的能力。也正是通过这个过程,组织逐渐把握了不同干部的性格倾向、经验结构和工作特长,从而有效地将之安顿在适当位置,充分发挥个人的实践能力。
另一方面,一个组织的运转是否具有活力,不仅依赖于个人在组织中能否各安其位,而且取决于组织内部个人之间的关系状态。思想认识不完整,而现实是完整的。以局部的眼光来处理整体性的现实问题,自然难以看清每一个具体问题在整体中的结构性位置,无法把握不同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脉络。当时的军代表制度分为四个部分:军代表、旧行政、职工组、职代会。由于各自工作重心不同,具体头绪纷乱,往往自主安排,互不沟通,导致步调不一,彼此不满。①《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电讯接管处电信局接管组接管工作总结报告》(1949年6月3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349页。
显然,只有组织能动地自我校正,实现内部团结,才能以整体性的方式与现实状况相配合。在接管初期,由于干部认识水平的差异,组织内部出现不少不团结的情况,如工厂接管干部与地下党的联系问题,“由解放区进城干部对他们缺乏热情,不了解他们的处境和情绪,冷淡对待,有些还批评他们,又未能迅速按照他们能力分配工作,致使地下人员大失所望,热情降低,后经教育解释,分配工作,始行纠正”②《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 (1949年1月15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101页。。组织团结并不只在于组织成员建立起对于政策文件的共同认识,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否意识到自我与他人在组织内部的位置关系,并在日常工作中达成相互配合的伦理状态。
组织形式对于接管干部这种总体性意识的要求,不仅体现在工厂接管工作的内部,而且指向城市接管的整体,“入津后贸易、金融、管理、财政、工业、交通,许多挠头的问题,不好解决,工作上配合不起来”③《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贸易接管处接管工作总结》(1949年 3月 10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244页。。工厂接管不是孤立的工作,尤其在由接到管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与财政、金融、贸易、交通等方面的工作密切相关。一旦无法形成恰当的配合关系,工厂的物资储备、财务管理、日常生产都会陷入停滞状态。如前所论,由于未能处理好这种整体关系,不管是国民党接管敌伪产业还是中共此前的工厂接管,都出现过只接不管、重接轻管的教训。在接管天津工厂初期的总结中,中共意识到:“这次的组织形式我们认为基本上是对的,但有的混合组织在工作上仍有问题,主要毛病是接与管不能很好连接。”④《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摩托接管处接管工作总结》(1949年3月14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302页。因此,在接管后期,军管会特别强调:“在初期接收阶段已过,要求如何处理走向建设的时候,接收和管理就应分开建立领导的组织,接管部应该集中于如何完成接收,逐步交给管理机关;而管理机关则应该如何按系统地分配到有关系统进行经营,并解决经营中的资本、原料、薪资等问题。”⑤《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接管城市工作初步总结》(1949年3月), 《天津接管史录》 (上),第110—111页。
正是以这种相互配合的总体性要求为指导,在接收环节完成后,不少工厂很快投入生产。对于因为种种困难而无法复工生产的部分工厂,刚刚接管的金融机构积极贷款助其渡过资金难关;军管会全力组织全市国营工厂互通有无,调拨原料;贸易部门派出人员赴各地采购急需原材料;工厂内部也发动职工挖潜、献物,设法克服生产困难。通过多方面的互助和配合,到1949年2月底,绝大多数工厂已经恢复生产。截至3月底,全市工厂全面复工复业。在组织形式随着现实需要而磨合和推展的过程中,接管干部的状态也因此不断得到提升和锻炼。原有的具体工作越发与更大的整体性建立起意义的连带感,并由此以充实饱满的态度克服过去革命经验的凝滞,不断调整与现实打交道的方式,创获新的工厂接管经验和实践能力。
从1月15日天津解放开始,不过是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共在组织形式和接管干部的状态都不理想的情况下,通过不断介入和回应不同层次的接管问题,及时调动和调整组织形式的能动性,理解和把握不同干部身上累积的革命经验,逐步构造组织和个人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既使接管组织的形式和功能得到完善,又打开并扩充了干部理解自身工作意义的整体性意识,使得不同方面的工作能够相互配合和共同推进。可以说,在天津工厂接收完成、管理工作开始的时候,中共的组织和干部状态已大为改观,渐趋良好。
如前所论,天津城市接管的目标是彻底替换原有的党政团体,而以“三原”原则保存工厂。然而,一旦接收工作完毕,中共开始组织生产活动,国民党工厂体制的矛盾便日益凸显。对于缺乏工厂管理经验的接管干部而言,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些矛盾的构成方式和内在因由,便成为改造工厂生产空间的首要任务。
三、国家·资本家·职工:劳资矛盾的新状况
国家、资本和工人是劳工研究尤其是劳资关系问题研究的基本分析要素。以往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劳资问题的考察,往往是从这三种要素出发,以经济和阶级分析来直接对应中共组织工业生产的过程。这种处理方式既抽空了特定历史过程中人的精神处境和情感状态,也忽视了这一关系在解放前后语境中展开的历史前提和问题脉络。因而,要理解接管天津后工厂劳资关系的矛盾形式和思想内涵,就必须首先进入中共触碰和把握这一问题的前提和脉络。
事实上,天津接管工厂的复工并非一帆风顺。中共试图延续的“三原”原则首先在资本家那里遇到了阻力。在最初的一个月里,失去国民党体制保护的资本家陷入巨大惶恐。他们对共产党的到来满怀疑虑,大多数厂主都害怕情绪激昂的工人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肆意报复。再加上在原本的萧条状态下,原料采购和产品销路困难重重,又有反动宣传散布中共要实行“三三制”(即政府、工人和资本家利益均分),越发加重了他们的不安情绪。不少资本家不愿继续经营,或转移资金逃向港台,或以各种理由拖延开工,迟迟不发欠薪和年终分红,并设法解雇工人,减少开支。因而,这一时期的劳资矛盾主要是欠薪、分红、解雇和要求复工。据天津市十个区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段的劳资争议有441件,其中上述问题就占了315件。①《黄敬同志在各界代表会议上的书面报告》(1949年9月5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492页。
面对这种状况,接管干部反复对资本家宣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并申明中共团结资本家开展生产活动的愿望。但这些宣传并不能完全说服资本家,而往往被理解为表面的拉拢和迎合。为此,接管干部有针对性地了解资本家的生产困难,及时安排银行贷款放债,贸易部门则疏通销售渠道,为复工复业提供经济条件。这些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资本家的惶恐情绪,促使他们很快恢复生产。
然而,接管干部不久便发现,恢复生产的工厂经营状况并不理想,不少工厂的产量和销量都在下滑,甚至赶不上解放前的水平。对于如何经营和管理工厂,干部普遍缺乏经验。而要应对这种状况,就必须直接介入工厂内部的生产空间。当他们开始进入工厂内部,首先面对的不是生产要素和管理体制,而是每一个具体的人。一旦与具体的人接触,他们很快察觉到政权更替在国民党旧职员身上所引发的前所未有的情绪动荡,“在下级职员中,害怕因我入城干部代替工作,造成失业;在技术人员中,则均对我入城干部不懂技术业务而轻视;在高级职员中,部分初则畏惧,现在则企图麻痹诱惑,腐蚀我入城干部,假意殷勤,或组织职工刁难我入城干部”②《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接管城市工作初步总结》(1949年3月), 《天津接管史录》 (上),第109页。。
不难明白,不同层次职员面对接管干部的反应,与其在原有工厂官僚体制中的不同位置相关。比较而言,下层职员对中共多有期待倾向,技术人员采取观望态度,而高级职员则充满对立情绪。这些不同层次的差异,要求接管干部采取不同方式开展工作。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一旦介入具体事务,干部就发现这些不同层次差异所对应的旧体制生产关系的遗留,“如能深入下层就会发现不少工头领班生活较优,随着高级职员走。因此讲话时要格外留神。杂役人员多与高中职员有联系,表面上对我们很好,实际上并无好心,高级职员一般的爱摆臭架子,你不摆架子他会轻视你,为了工作必要时对他们摆一下也是必要的”,“对上层职员要机智敏感地发现与分析其思想活动及顾虑,及时予以解决。对下级职员与工人,则须深入团结教育,在复工之短期过程中,除必要的个别谈话外,一般的暂少进行个别谈话,以免在高级职员中,因不了解我们而起怀疑顾虑,甚至发生离职潜逃,影响恢复工作之进行”①《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交通接管处接管工作总结》(1949年4月)、《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电讯处接管方案》(1948年12月30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295—296、75页。。
显然,旧体制的生产关系滋长了复杂微妙的人情关系网络,这些旧的人情关系往往成为政治工作的首要障碍。接管干部体察和把握这些人情的能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得益于中共以往在农村养成的群众工作经验。这些经验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被重新调动并激活,成为开展新工作的基本着手点。接管干部通过这种方式,既有效化解这些关系网络的负面效应,也顺势将之引向政治工作的有利方面。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打开工作局面,介入下层职员和工人日常生活的困境,“战争炮火中,有的个别职工受了伤,或是家里受了损失,我们及时进行了救济,对职工启发教育工作也很大,局内救济了一位工友,另一位工友父亲生病,经济困难,一位下级职员,死了老婆,无钱埋葬,分别借给了一些钱,在全体职工中,发生了很大影响,和国民党压迫职工,官僚主义成了鲜明的对比”②《天津市公用局企业接管工作中的几点体验》(1949年5月),《天津接管史录》(上),第208页。。如此细致周到的扶助工作,有效消除了他们对接管干部的畏惧和隔阂。
然而,这又引起了工人的不满情绪,核心问题是工人对职员“原职原薪”的不满,这对中共实施的“三原”原则提出挑战。其一,职员在“原职原薪”的接管政策下,获得了稳定的生计来源,但在观念层面一时还不能破除脑力劳动者的优越感。其二,某些职员在国民党时期压迫工人的行径,在“原制度”的原则下得到延续,从而引发工人的不满。其三,国民党时期的工资状况极为混乱,工厂职员中既有亲信关系又有同乡关系,工资收入往往与能力不匹配。同时,不同系统的工厂各立标准,差距悬殊。工人们都对此深恶痛绝。
对于前两个方面的问题,接管干部通过说服教育,打掉脚行把头制、工厂工头制、棒子队等压迫组织,很快使秩序渐稳。比较棘手的是工资问题,“工人的意见大部分集中在经济利益”③《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部电讯接管处电信局接管组接管工作总结报告》(1949年6月3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347页。。可以说,工资问题构成职工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种意义上,职工矛盾的实质乃是劳资矛盾,尽管其表现形式并非工人对资本家的直接斗争。要缓和这种形式的劳资矛盾,就需要对工资结构作出调整。而调整工资结构,必然会触及职员利益,进而波及资本家的收益以及与之相关的体制关系。当时七届二中全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尚未召开,中共还没有出台相关文件,接管干部对于这种性质的劳资矛盾缺乏应对的依据,只有原则性的“劳资两利”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市政府的解决方式极为谨慎,采取了“保证工人实际工资”和“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方针,充分考虑了各方诉求,力求在不同利益关系中寻求平衡。但在实际落实的过程中,采取了以地区为单位而不是以行业为单位的办法,结果导致有些厂方抵制工人的正当要求,矛盾再次激化,有的则无条件退让,致使生产再次陷入困顿。④《黄敬同志在各界代表会议上的书面报告》(1949年9月5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493页。不仅于此,与政府干部相比,工会干部和区委干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往往在情绪和态度上更偏向工人的要求,从而在干部之间形成僵持局面,同样影响矛盾的最终解决。这些不同层次的矛盾关系,使得劳资双方依旧缺乏信任,生产状况徘徊不前。
时任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很快注意到这种情况,并反馈给毛泽东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第36页。。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马上安排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工作。1949年4月10日,刘少奇一行到达天津。在一周时间里,他亲自深入工厂,接触工人和私营业主,邀请重要的工商资本家座谈。4月21日,刘少奇专门到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视察工作。东亚公司在天津纺织界颇有地位,当时该厂的劳资关系十分紧张。许多工人都认为,既然已经解放了,就应该分资本家的财产,实行“共产”,分掉库存的毛线,由此出现“吃鸡”还是“吃蛋”的争论。针对这种状况,刘少奇到厂后便召开劳资双方代表的座谈会,重点解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与此前接管干部的解释不同,他直面劳资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剥削问题。反对剥削正是革命后工人激进行动的理论依据,也正因此,一些干部在劳资纠纷中踌躇不决,不愿纠正工人的自发愿望。刘少奇在解释时,特别强调工人在政治上的解放并不等于马上不再受剥削,剥削关系不是资本家和工人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也有其进步性,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只能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对于迫切需要恢复生产的工厂而言,不应该抛弃任何一个有用的人,“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既然‘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怎么倒怕资本家办厂开店呢?”②《刘少奇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换言之,对于剥削的理解不能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应该充分意识到它在特定历史状况中的结构性位置。解决剥削问题并不是天津恢复工厂生产所面对的首要问题。作为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工厂能否恢复生产,对于当时的财政、金融、贸易、交通以及农村的生产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工厂的良好运行依赖于生产空间中不同位置的人能否对彼此处境达成谅解,并形成相互支撑的配合关系。一旦脱离这种具体处境来反对剥削,便会导致生产停滞和工人失业,进而影响整个城市的经济与社会稳定。
除与资本家座谈外,刘少奇还对天津工厂的职员和工人分别发表两次重要讲话,即《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的讲话》 (1949年4月25日)、《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49年4月28日)。前一篇讲话的中心是调整职员与工人的关系,后一篇的主题是教育和纠正工人的激进态度。相较而言,后者更为直接地切入劳资矛盾的具体状况。在这篇讲话中,他对这种自发的盲目激进倾向提出批评,强调工人的极左态度只会逼走资本家,导致工厂倒闭。当时曾有人认为:“资本家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但刘少奇则指出:“开了合作工厂没有呢?开了很多,但没有一个搞好的。这是过去的事实,这种错误过去犯的很多。”③《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52页。
刘少奇的这种批评与他在过去工运实践中的沉痛教训密切相关。在1937年写给张闻天的信中,他特意谈到大革命中组织工运的教训。当时各地的工人运动都出现严重的极左倾向,如“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搜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对此,中共未能采取有效办法,最终导致运动失败。在刘少奇看来,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他从组织安源煤矿工人开始便深有感触:“工人要前进,但除组织苏维埃外,无法再前进。结果还不能不阻止工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对于这个难题,他遍问国内外工运领袖和专家,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答复。当1927年的极端现象再次出现时,他在极度困恼中领悟,“这是中国工人运动中特有的问题”。④《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213、216、217页。但如何引导“左”倾工人实现“高度的觉悟和高度的纪律”的结合,却始终没有合适对策。因此,当刘少奇见到天津工人这种极左态势时,变得颇为忧虑。即便在这次讲话中,他也未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其对职工关系和职工与资本家关系的调整,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
天津市政府很快组织学习刘少奇讲话,并发布《中共天津市委关于传达刘少奇同志指示的决定》。根据他的讲话精神,制定了以集体协商为中心的劳资纠纷处理办法,即《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 (草案)》《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草案的几点说明》。通过成立劳资协商会议,签订集体合同的形式,有效缓解了原来不同层次矛盾的单方面对峙状况,形成“劳资两利”的集体协商机制,天津工厂的劳资纠纷大大减少,生产逐渐恢复,为城市的整体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在刘少奇天津讲话精神的指导下,军管会提出并实施的劳资协商机制,后来成为许多城市处理劳资矛盾的示范经验①不久,《人民日报》连续刊文介绍天津工厂组织劳资协商的经验,如《改进私营企业生产和劳资关系的有效组织——天津私营工厂的劳资协商会议》(1950年4月28日)、《天津私营北洋纱厂正确运用劳资协商会议解决劳资争议改进生产》 (1950年5月22日)、《天津市劳资协商会议的成绩和目前存在的问题》(1950年5月24日)。。对此,不少研究都倾向于将这种经验简化为刘少奇讲话的直接产物,却忽视了劳资矛盾在工厂接管初期展开的历史前提和问题脉络,以及接管干部针对这种矛盾在不同阶段之呈现方式所采取的推进问题解决的具体步骤。而一旦脱开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整理,便很容易抽空劳资问题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构性内涵。从这种理解出发,便不难明白,仅仅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论,或是当下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都不能帮助后人深入理解这一矛盾背后所对应的历史状况,尤其是当事人的精神处境和情感体验。真正重要的是,问题解决的过程是中共在充分掌握政策的前提下,通过理解和把握他们的自我感知和内心诉求,不断破除僵化的理论教条和经验惯性,从而逐步打开工作局面,推进每一环节问题的解决。
不过,以劳资协商来化解国家、资本家和职工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是接管干部介入生产空间的第一步。尽管经济手段及其重塑的劳动关系在革命胜利后的危急时刻平衡了不同层次的矛盾,使得工厂生产得以有效运转,但这并不足以将其打造为充满活力的劳动空间。如果工厂生产中不同位置的人不能因此形成良好的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原有的矛盾结构将会以不同形式重新浮现。在这种意义上,只有进一步改变工厂的生产关系,才能实现这种改造诉求。而要改造生产关系,就需要创造一种新的工厂管理方式。
四、再造劳动的伦理空间:民主建制与工会的再定位
以往对于工厂接管的理解,往往止于接收阶段,并不深究之后的管理问题。然而,如不将之视为长时段的历史过程,就容易丧失把握接管问题的整体性视野。事实上,如何管理接管后的工厂,对于缺乏经验的接管干部构成巨大挑战。而要理解中共思考和应对工厂管理的方式,首先要理解这一尝试在现代以来工厂管理实践中的位置。资本主义工业在近代中国发轫之时,为适应分散的劳动力资源,工厂管理主要实行的是包机制或包工制。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流行的“泰罗制”(又译“泰勒制”)传入中国,很快在工商界流行开来。“泰罗制”的核心是所谓“科学管理法”,即资方在有效降低损耗、增进效率的同时,对生产过程和工人实施严格控制。尽管“泰罗制”强调劳资协调是推行科学管理的根本,但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由于对工人的严格掌控,不断遭遇他们的罢工抗议。②对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冯筱才:《科学管理、劳资冲突与企业制度选择——以1930年代美亚织绸厂为个案》,《史林》2013年第6期。中共在接管之初对于“三原”原则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基于对这种生产组织效能的基本理解。在管理工作的调整开始之后,接管干部便意识到对这种体制的批判性学习。也就是在批判其剥削本质的同时,承认其适应现代技术的合理之处,强调“必须向资本家和旧职员学习。不独是旧有的生产组织制度,就拿旧有的人事管理制度来说……也是决不可简单加以否定的”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1949—1952),中国物资出版社,1996年,第243页。。这种批判性设想尽管在后来制度实践的不同历史条件下多有变化和调整,但并没有被彻底否定。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共在革命根据地的公营企业管理实践。从30年代开始,根据地的公营企业学习苏联企业管理经验,实行“三人团”制度。在此之前,中央苏区的工厂生产陷入困境,厂长无权,管理混乱,浪费严重。到1933年,亏损严重的工厂已经生产不出合格产品。刘少奇了解这种情况后,亲自到工厂调查,并撰写《论国家工厂的管理》一文,提出通过“三人团”及工厂管理委员会来应对困境②《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176—184页。。1934年4月10日,中央苏区签发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的《苏维埃国有工厂管理条例》,明确建立“三人团”及工厂管理委员会的体制:“在厂长之下,设工厂管理委员会,由厂长、党支部代表、工会代表、团支部代表、工厂其他负责人、工厂代表等五人至七人组织之,开会时以厂长为当然主席,以解决厂内的重大问题,管理委员会内组织‘三人团’,由厂长、党支部代表及工会支部代表组成之,以协同处理厂内的日常问题。”③《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历史文献》,经济管理出版社,1986年,第40页。但这种民主体制在实施的过程中依然问题重重,三人对彼此工作不了解,往往意见不一,无法配合。整风运动之后,“三人团”逐渐被厂长负责的一元化管理取代。可以说,根据地建设中工厂管理方面的教训多于经验④周恩来后来在回顾这项制度时说道:“过去是三人委员会,在延安是这样,但支书常常不了解生产过程,不懂得这些问题,他只以为他是只做党务工作的,在三人委员会中发表不了什么意见,把党务工作抽象化,工会主任只以为自己是代表工人的,脱离了生产,只知道减少时间,增加工资搞福利事业、文化娱乐;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工作,把厂方看成资方,也有的厂长只作行政管理,不做群众工作,不依靠群众的积极性,三人团往往开会是对立的,不是好好讨论生产计划,而是解决三方面的关系问题,过去成绩也有,但是很小,作用不大。”周恩来:《对赴哈参加六次劳大代表的指示》 (1948年4月28日),李桂才主编: 《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 (1948—1988)》,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页。。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共在城市接管后探索新的工厂管理体制。
尽管中共在根据地公营工厂实行的民主化管理改革并未真正成功,但这种探索方向没有改变。在工厂实现民主建制,这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工厂经营要求的经济核算、科层管理和机器作业,都无法为工人民主意识的养成准备必要的环境条件。即便是当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苏联,在工业管理体制中仍然实行“一长制”。在这种意义上,中共重新开启的工厂民主建制议程是前所未有的。
在城市接管工作开始后,中共的基本设想是在工厂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1948年8月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最早将这两种民主建制视为工厂民主化管理的基本内容。而对于这项制度的具体讨论,先从东北老解放区开始。1949年3月4日,《东北日报》刊发社论《企业管理民主化是改进生产的重要保证》指出: “办好一个人民企业主要依靠两条,一条是企业化的经营,一条是民主化的管理,两者必须很好的结合。”这里的“企业化的经营”,主要指向中共对于国民党原有资本主义经验的批判性继承。而关于“民主化的管理”,该社论具体解释了这两项制度的基本设计。大体而言,工厂管理委员会是企业统一领导的最高权力机关,成员除厂长、工程师和主要生产负责人外,必须吸收相当数量的职工代表参加。而职工代表会议则是在工厂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直接联系职工并传达和落实领导决定的组织形式。经过东北工厂的管理试验之后,1949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公布《关于在国营、公营工厂企业中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与工厂职工代表会议的实施条例草案》,明确了这两项制度的性质、职能和实施办法。次年2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由李立三起草的社论《学会管理企业》,在强调这两项制度重要性的同时,也特别指出工会对于实施效果的关键作用。后来,刘少奇更明确地说:“职工代表会议,也就是工会的组织,哪个厂的职工代表会,就是那个厂的工会的代表会。”①《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369页。从这些表述来看,工会建设是这两项制度实施效果的组织基础,它更直接地关系到工人的身心状态和伦理关系,成为工厂民主建制的主体根基所在。至于尚未能够落实这两项制度的私营工厂,更完全依赖工会来拓展有限范围的民主工作。
天津接管工厂的民主化运动,正是在上述制度和观念脉络中展开。如前所论,解放前的天津工运并不兴盛,中共的阶级基础薄弱。黄敬在胜芳整训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中共接管城市是“归队”,是找回“本阶级”。在他最初的设想中,接管之后不应马上建立工会,而是成立临时工厂管理委员会,“军事代表、厂长、工程师、职员及工人代表优秀积极分子参加,但最后决定权属于军事代表。有什么决定,工人代表就带到工人中去,征求工人意见,用这个组织来反映工人意见与工人共同讨论问题,教育工人通过这个组织也来进行其他工人组织,如合作社,纠察队等”,“这样通过复工、工厂管理委员会等,就可以发现工人领袖,一切酝酿成熟的就可以成立工会”②《黄敬同志关于军管时期天津职工运动的讲话》(1948年12月30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61页。。
之所以没有马上成立工会,是因为在接管初期,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势力尚未除尽,再加上投机分子、流氓甚至特务分子等随时会混入工会组织,利用工人的不满情绪,煽动他们破坏工厂。在此前的城市接管中不乏这类惨痛教训。因此,黄敬强调,等一切酝酿成熟之后再成立工会。而在此之前,他对工厂管理委员会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根据地管理经验的延伸。但是,这种管理制度对于不同层次人员和代表之间的配合关系提出很高要求,这在接管初期是难以企及的。与黄敬的设想不同,在解放后最初成立的实际上是职工临时代表会。这个组织很快参与到领导职工复工复业、协助清点接收以及职工学习和福利工作。不过,即便是这种易于操作的组织形式,也由于职工层次差异和组织过程仓促,导致一些不纯分子混入其中,大大延缓了组织完善的过程,直到1949年3月才改选成立职工代表会。③《天津市公用局企业接管工作中的几点体验》(1949年5月),《天津接管史录》(上),第218页。
在职工临时代表会发展到代表会的过程中,工人的个人意识也逐渐发生变化。缺乏领导和运动历练的天津工人,最初基本上不了解中共,在情感上颇为疏离。对于接管干部来说,职工运动的首要工作便是拉近距离,消除隔膜。他们采取个别聊天、拉家常、开座谈会等方式,听取工人的呼声,解答工人提出的问题,“如为什么叫共产党?为什么叫解放军,又叫红军、八路军?”正是通过这样有针对性的常识普及工作,“逐渐解除了工人群众的疑虑,对我党我军有了些了解,主动找我们反映情况的人多了”。④张振华:《关于接管天津中纺一厂的回顾》,《天津接管史录》(下),第183—184页。
经过这一层工作,军管会开始调整工厂管理的“三原”原则,实施民主改革运动。1949年3月,黄敬指出,进行民主改革,便是加强已有的职工代表会,建立和完善工厂管理委员会⑤《黄敬同志关于民主改革运动的讲话》(1949年3月10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430—431页。。依照这种方针,在3月底4月初,大部分单位的工厂管理委员会逐步建立起来。然而,与此同时,工人在旧时代被压抑的个人诉求进一步释放出来,并显现为资本家、职员和工人之间多层次的复杂矛盾。显然,组织建构并没有及时回应工人的诉求,并潜在地助长了这种诉求的自发倾向。黄敬后来在总结这一问题时说:“我们在一进城不久,就提出民主改革。当时这个问题虽然是存在着,但党的力量不强,群众觉悟不够高,职员情绪不够稳定,所以是提得过早了。”①《关于三年来工作总结与今后工作任务——黄敬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8月18日), 《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天津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3页。这种矛盾状况在4月份刘少奇视察天津之后,经过劳资协商会议和集体劳动合作的调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但问题在于,经济关系调整还不能与民主建制形成良好的配合关系,工人的自我意识并没有因此得到充实和提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会的组织工作被提上日程。
1949年4月底,天津市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天津市总工会筹委会。刘少奇出席会议,并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天津市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发展会员,建立工会,按照产业把工人组织起来,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5月1日,李立三参加天津解放后的第一个劳动节,号召大家学习刘少奇讲话的精神。随后,在二人的具体指导下,天津市总工会筹委会开始按照系统组织工会。但如何具体开展组织工作,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②李立三曾转述刘少奇的说法:“现在工人运动到底如何搞法,虽在六次劳大有个方向,但具体的作法都没有,而且许多同志都是新归队的,在农村搞了二十几年,就是以前有些经验也忘了。有些同志是新参加工人运动的,没有经验,有些同志虽然有些经验,也是在国民党政权下工作的一套经验,至于在我们的政权下的工作经验也是完全没有的。”《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80页。。因而,实际的组织过程并不顺利,当时工会干部普遍存在的“关门主义”态度,导致工会在成立的最初5个多月内,天津市只有一半工人加入工会。经过调整,直到1950年1月天津市总工会成立时,情况才有所好转。而另一种“官僚主义”作风则使得不少工人在加入工会后不久,便对缴纳会费和频繁开会产生抵制情绪,甚至有部分工人选择退会。③参见梁丽辉:“新旧更迭中的巨变:建国初期天津工人研究 (1949—1956)”,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2年,第54—56页。事实上,这两种不良倾向的出现,为工会工作提出了两个层面的问题:如何理解和把握工人加入工会的自发愿望?如何在工会中开展民主生活实践?对此,刘少奇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他的理解。对于工人加入工会的动机,他曾有这样的判断:“普通的特别是政治上落后的工人,他们来加入工会,并积极参加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既不是要来建立共产党与工人群众之间的桥梁,也不是来参加共产主义的学校和建立人民政权的社会支柱,他们通常的出发点和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使工会成为保护他们日常切身利益的组织……如果工会脱离了保护工人利益这个基本任务,那末,他们就会脱离工会,甚至还会另找办法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工会就会脱离工人群众。”④《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7—98页。以此来看,工人是否对工会有认同感,工会能否留住工人,关键在于工会如何对待工人的个人利益诉求。
与此同时,对于工会如何在工厂开展民主实践,刘少奇在不同场合都特别强调学习中共在军队进行民主运动的经验。1948年1月,在毛泽东起草的指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中,将中共军队内部的民主概括为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等三个方面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5—1276页。。刘少奇所强调的经验主要是指政治民主方面,即批评与自我批评:“本来军队是没有民主可言的,但我们几百万军队里都这样搞了,而且搞得很好,在军队里叫官兵关系,在国家工厂就叫职工关系”,“我们队伍里,进行自我批评时,有连长光说或者多说好处,下级便不满意。而相反的,有的连长、排长自己光说错误,不说好处,结果士兵就说,我们排长、连长,还有一些什么什么好处,很公正地指出来,提高了他的威信”⑥《刘少奇论工人运动》,第339、340—341页。另外,他在《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中也同样提到军队民主经验的重要性。。刘少奇倡导的这种民主实践方向,真正触及工厂内部伦理关系调整的核心环节。天津市工厂很快将这种经验付诸工会工作。1949年11月,市长黄敬在写给毛泽东和华北局的报告中,首先提到工厂内部关系因此发生的变化:“以往的情形是自上到下层层强制、监督,自下到上层层欺骗、应付、磨洋工、偷懒、敷衍是极普遍的现象。解放以来这些现象大体上都没有了,到处是一种新的气象。劳动态度完全改变了,一般工人都自动地积极生产。过去靠上面监督强制着才能办的事情,现在以群众的自动或互相批评、互相督促就办到了。在工人地位的提高及民主的问题上,曾经一度引起职员们不安的情绪,但在号召职工团结与发动职员主动的自我批评后,关系也就正常了。”①《黄敬给毛主席及华北局的综合报告》 (1949年11月22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583页。
随着工厂伦理空间的改变,天津工业生产也在逐步恢复和提高。1949年五六月以后,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国民党时期,并且继续增加。然而,好景不长,从10月开始,工人的状态发生变化,增加速度开始延缓。当时除了积极分子之外,其他工人的劳动积极性普遍下降。有工人提出:“生产长一寸,生活加一分行不行?”很多人不再回应积极分子的号召,并产生了抵触心理。有的工人党员、团员领导甚至采取类似监工的方式,更加招致工人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工厂的生产氛围每况愈下。在黄敬的理解中,这种情况表明,仅靠政治教育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套新的领导生产的方法②《黄敬给毛主席及华北局的综合报告》 (1949年11月22日),《天津接管史录》(上),第584页。。但在笔者看来,这种判断并不准确。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既有的民主建制突然失效,无法领导生产,而在于上述民主实践与工人的个人利益诉求之间的不吻合。换句话说,工人不能从生产民主的实践过程中获得期待中的个人利益。因此,问题的根本在于如何理解工人的个人利益诉求在工会民主实践中的位置,怎样弥合中共期待的工人主体高度与其自我理解之间的差距。这些问题关系到工会民主实践的方向,以及这种方向对工厂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配合关系提出的要求。
事实上,黄敬发现的问题并非孤立的现象。不久,中共高层对工会的认识出现分歧,并引发激烈论辩。追溯起来,论辩由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而起。1949年6月,他与陈伯达对于公营企业的理解出现分歧。陈伯达认为,公营企业中公私之间的利益完全一致,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而李立三表示,尽管两者的利益完全一致,但仍然存在一定矛盾,即“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日常利益之间的矛盾”。他强调,对于这种矛盾,应以毛泽东所提出的“公私兼顾”原则加以解决。③李立三:《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公私兼顾政策问题的几点意见》(1949年6月12日),《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131—134页。对于这种观点,李立三此后在多篇文章中加以进一步解释,概括起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毛泽东所说的“公私兼顾”应该有两层含义,既要兼顾国营和私营工厂之间的利益,也要兼顾国营工厂内部的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他并不赞同那些否定后一方面的意见,而特别强调其作为管理原则的重要性。④李立三: 《公营企业工会工作中的公私兼顾问题》(1951年4月11日)、《关于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会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1951年9月28日)、《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1951年10月2日),《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第261—275、288—295、296—299页。第二,工会应以“公私兼顾”的原则处理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即行政与工会的矛盾。在这种矛盾出现时,工会应该站在工人的立场,保护他们的个人利益。在这种意义上,工会应该在党政关系中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管委会是行政组织,工会是群众组织,共产党是党的组织,这三个组织都是独立的,谁也不能向谁下命令。工会不能命令党,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同样党也不能命令工会……党对工会的领导,是通过党在工会中的党组和党员来领导工会,使党的意见变成群众的意见”。⑤李立三: 《关于工厂管理民主化与劳资纠纷问题》(1949年7月10日),《李立三赖若愚论工会》,第27—28页。
在这场论争发生的同时,邓子恢和高岗之间也出现了同样性质的意见分歧。李立三赞同邓子恢的观点,而高岗的态度和陈伯达则非常相近。刘少奇对李立三和邓子恢的态度表示支持,并专门写出《读邓子恢和高岗同志两篇文章的笔记》,进一步延伸讨论其中各种矛盾的性质①刘少奇的这份笔记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并没有公开,直到后来编辑《刘少奇选集》时才得以发表,但删去了其中引述邓子恢和高岗的相关段落,更名为《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92—99页。。这场论争最后以1951年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上李富春、陈伯达批判李立三的所谓“工团主义”“经济主义”“分配中心论”等错误而告终,各级工会必须完全服从党的领导的指示也从此被明确下来②参见李富春:《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分歧——1951年12月20日在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上的结论》、《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1951年12月22日全国总工会党组扩大会通过),《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册,中国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96—116、84—95页;《陈伯达在全总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1951年12月21日),《工运理论、工运史研究文献资料选编》 (2),1987年,第111—118页。。
毫无疑问,这种批判方式是粗暴的,对此后的工会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1957年,不少人开始为李立三辩护,认为当时大规模开展批判运动的方式是不恰当的,“经济主义”问题并没有中共估计的那样严重,尤其在基层工会和工人中,只是局部的现象③王文兴: 《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问题》 (1957年3月),《中国工会四十年资料选编 (1948—1988)》,第542页。。后来的研究者对于这场论争的讨论,也无一例外地赞成李立三的观点,同情他受到不公正批判的遭遇。但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讨论都未能对这一论争所包含的历史问题展开深入分析。这场批判背后隐含的问题是,如果以“公私兼顾”的原则来理解工会对于工人的个人利益保护的正当性,那么,工人很容易因此将个人劳动的价值理解为通过为国家利益做贡献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满足,而这正是天津工人希望实现“生产长一寸,生活加一分”愿望的思想逻辑所在。在这种意义上, “公私兼顾”的原则在无形中被转化为“公私协商”的诉求。那么,一旦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私”的正当性,工会民主实践最终在工厂生产中打开的伦理空间,便只能是西方意义上的“契约共同体”,而非社会主义的价值共同体。卢卡奇曾说过:“只有当一个共同体内部的行动成为每一个参加者最关心的个人事情时,才有可能消除权利和义务的分裂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社会化分离以及他被控制他的社会力量肢解的组织表现形式。”④〔匈〕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12页。在西方现代政治传统中,契约共同体的思想建立在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二分的基础之上,无法克服个人与社会分裂带来的原子化境遇和价值虚无主义。就此而言,李立三对于工会独立性及其对应的工人个人利益的强调,便可能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释放出价值的离心力,最终难以通过民主化管理将工人打造成真正自觉的主人翁。
尽管这场论争发生在中共高层,基层工会并未参与其中。但是,在1949年天津的工会民主实践中,同样遇到如何处理党、政、工、团之间关系的问题。当时讨论的核心同样是党的领导地位问题。经过多次座谈讨论之后,最终明确了“工、团组织除接受上级组织的领导外,还要接受同级党组织的领导”。1950年底,天津市企业党委总结了《天津市国营工厂企业中党如何统一领导的意见》,由此在工厂管理的组织形式上明确了党委的统一领导地位。⑤崔荣汉:《解放后天津市国营企业中的党组织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天津接管史录》(下),第389—390页。经过这次调整之后,工厂管理的组织形式大体实现了内在的配合和协调,工会民主实践的方向由此与工厂生产的要求达成统一。当然,工人的个体意识并没有因此达到中共所期待的高度,但经过此前层层推进的工作方式,新的劳动主体将在工厂伦理空间的有效运转中焕然而生。然而,工人由此表现的劳动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对李立三批判中并未被充分消化和整理的上述思想问题,这些问题成为此后工会工作不断遭遇的实践挑战。
五、余 论
天津的城市接管更接近中共城市接管的一般状态,虽然这一实践避免了沈阳、石家庄等城市接管的不理想状态,但也未能在整体工作上达到接管北平的成效。因此,中共在接管这座城市工厂时所创造的新的工作经验和组织形式,对于此后的接管工作具有某种示范性意义。通过理解这一历史过程,对于我们思考中共建国的实践议程如何在既有的历史基体之上打造出新的社会空间,显然十分重要。如前所述,在天津工厂接管工作的整个过程中,中共的历史理解、干部能力和组织准备都不理想,甚至最终开展的工会民主实践也并没有马上达到预期状态,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自觉程度不高,计划性不强,只是零敲碎打,带有很大自发性,步调也不一致,参差不齐,时间拖得长, ‘三反’中来了一个民主补课才大体解决了这个问题”①《关于三年来工作总结与今后工作任务——黄敬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8月18日), 《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天津卷),第383页。。即便如此困难重重,甚至还有以往革命经验的混杂与纠缠,但中共通过调整干部的工作状态,完善组织形式的不同部分,化解矛盾关系的各种层次,逐步形成富有成效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并非一劳永逸,而是不断遭遇不同实践情形中的现实困难,经由调整政策、经验、组织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最终顺利接收、转化和改造旧时代的工厂体制,初步实现了新的工厂民主建制。
本文通过重新返回天津工厂接管的历史现场,深进中共历史实践曲折复杂的路径和样貌,探讨了工人作为新的国家主人诞生的历史前提。以往对于工人的主人意识之生成的理解,往往略过接管这一阶段,而直接进入对50年代开始的民主化改革、合理化建议、劳动竞赛、抗美援朝动员、“三反”“五反”运动等一系列后续历史过程的讨论。然而,一旦我们不去讨论这种主人意识产生的历史前提,那么就不能理解它的历史构成和观念逻辑。事实上,通过对此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工人的主人意识的起源,包含着多种复杂历史因素的纠缠和混杂。中共理解和改造这些因素的过程,不是简单的观念提纯工作,而是充分打开了个体理解自身与整体之间的相互构造关系。在此意义上,这种主人意识的观念逻辑,既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主体论,也不同于西方以契约论为基础的现代个人观。建基于对这种差异的理解,在处理1949年以后工人意识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变化形态和矛盾构成时,我们便不会轻易以阶级论或个人主义的视角作出或正或反的判断。
此外,以往对于工人阶级主人意识的理解,总是不由自主地陷入黑格尔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辩证运动”,仿佛这种意识的生成仅仅通过不断的政治教育便可以实现。本文的讨论同样试图凸显组织形式与这种自我意识的配合和互动。天津市市长黄敬在1952年的工作总结中这样说过:“光说工人是主人翁还不行,必须实行上面这一系列重大的措施,工人经过人事、工资、制度、人与人关系等上的改革才能发动起来。通过这些改革,工人发动得越来越充分,觉悟越来越高,新的工作制度陆续在建立,就在这当中完成了民主改革。”②《关于三年来工作总结与今后工作任务——黄敬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52年8月18日), 《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天津卷),第383页。事实上,天津接管干部所做的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不断调整组织形式与个人意识之间的关系,以便每个人在各自位置上充分调动主体的创造性,更加充实饱满地投入到共同体的事业之中。
时至今日,工人阶级经过60年的历史演进和蜕变,早已不复昔日主人的模样。重新进行这项历史研究工作,不是为了无谓的怀旧,而是希望通过理解这段历史过程的动机机制、运转方式和内在诉求,在层层掩饰的时代风尘背后,寻绎历史脉动通向现实和未来的曲径幽路。
(本文作者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北京 100089)
(责任编辑 吴志军)
Historical Practices and the Ethical Meaning of Factory Takeovers during Early Period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Tianjin
Fu Peng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 liberation of Tianjin,the CPC faced new social space for factories,providing an opportunity to create new work experience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Before the liberation of the city,the CPC’s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factories in Tianjin was inadequate. Furthermore,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ccupation,cadre work abilities and organizational preparations were insufficient,and the CPC encountered various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at all levels. Confronting these unsatisfactory conditions,the CPC adjusted cadre working conditions,improved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rationalized contradictory relations,and finally created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to grasp the reality. Thereafter,during the work at each stage,the CPC gradually reorganized interac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work experiences,organizational forms,and practical problems,thus unlocking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at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historical practice,and,based on the desires of the CPC,brought factory democracy to the capitalists,staff,workers,and their organizations.
D232;K271
A
1003-3815(2017)-06-005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