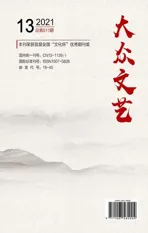《母与子》:一首冷峻的诗
2017-07-31峨眉电影集团610000
吴 莎 (峨眉电影集团 610000)
《母与子》:一首冷峻的诗
吴 莎 (峨眉电影集团 610000)
亚历山大•索科洛夫(1951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早期拍摄的电影几乎全部遭到苏维埃政府的禁映,一度转向纪录片创作。1986年,获得同时引荐他到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工作的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的大力支持,他的电影才得以解禁,并在80年代末进入国际视野。1995年,索科洛夫被欧洲电影科学院列入世界优秀电影导演之列,影片多次在国际及国内电影节上获奖。2011年,他凭借《浮士德》获得威尼斯“金狮”大奖,事业达到巅峰。他由于偏爱长镜头、崇尚演员的自然表演、孜孜不倦地探索人类存在的本质问题,而在年轻时被称为塔尔科夫斯基第二,很快,“他便成了索科洛夫第一,而且他是唯一没有人模仿的导演,因为至今还没有人像他那样解释电影的概念。”1。他用“死亡三部曲”——《第二圈》(1990年)、《石头》(1992年)、《沉寂的往事》(1993年)开始了较《悲伤与麻木》(1987年)、《日蚀》(1989年)更为哲理性的思考,同时拓展了电影语言的多种可能性,但影片晦涩难懂,一篇评论写到:这些影片只有观众找它时,它才有可能见到观众。
1997年的电影《母与子》,是索科洛夫继“死亡三部曲”后的又一次大胆尝试。影片极简,共68分钟,类似于某些实验电影,没有情节,没有完整的叙事,时代、背景模糊,整部影片只有两个不知姓名的人,他们各自只有一个身份:母亲和儿子。影片描写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荒村木屋里,儿子悉心照料母亲临终前的最后几天。二人看似温情,实则疏离、难以沟通,在自说自话中讨论生死、上帝、生存的真谛。母亲和儿子寥寥几句对话、少到极致的动作把他们充满戏剧性的关系轻易暴露出来,体现了索科洛夫对人性体察的细致入微:他们可以是这世界上任意一对母子,具有象征意味,代表着疏离、充满伤害、谎言的任意一对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影片与拉斯冯•特里尔《狗镇》中的极简场景——被白粉笔勾勒出的平面房间、场景相类似——延展开来,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生这样的故事。影片“空白点”较多,父亲的缺席、母亲的前半生、儿子为何如此孤僻无情影片都有意不去交代,留个观太多遐想的空间。
一、诗话电影语言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法国先锋派的理论家和创作家认为:电影应当像抒情诗那样达到“联想的最大自由”2。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与先锋派持同样的见解,在《打倒情节和故事》(1924)中提到“没有情节的电影,就是诗的电影”,并对如何在电影中运用诗的隐喻、象征、节奏等技巧进行探索。苏联的诗意电影渊源深厚,主要经历了以蒙太奇学派为核心的隐喻诗电影和受巴赞的长镜头理论、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的诗电影两个阶段,其中塔尔科夫斯基的《乡愁》、《镜子》打破传统的叙事结构,运用大量隐喻、象征,触角深及心灵王国,意境深邃,是苏联诗电影的代表作。索科洛夫在这方面与塔氏极为相似,他的《母与子》高度抽象,像一首娓娓道来、冷峻又绝望的诗,延续了索科洛夫的影像风格,体现出索科洛夫对艺术的终极追求。
A.情绪结构。《母与子》几乎没有顾虑场景之间是否有线性的情节联系,而是极力舒展场面内的情绪,通过一幅幅充满诗意的画面,将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绪蔓延开来。影片时常穿插看似突兀的空镜头、固定镜头:风吹过的草地、远方呼啸而来的列车、乌云笼罩的月色、木然伫立的废弃村落……将人物内心情感外化为一幅幅苍凉的画面。
B.节奏韵律。《母与子》外部节奏舒缓、深沉,无论镜头的推拉摇移,还是镜头内人物动作都非常缓慢。儿子抱着母亲从木屋内走出,蹲下,继续行走,追求一种接近生活的自然流畅的节奏。然而在平缓的外部节奏下,蕴蓄着母亲和儿子感情的波澜和漩涡,内在节奏紧张激烈。

图2:《母与子》构图之美
C.画面构图。在电影发展过程中,前苏联诗电影学派为蒙太奇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与前苏联电影重视构图的一贯特点相同,索科洛夫在《母与子》几乎每一帧都是一副19世纪俄国古典主义的油画,给人凝重庄严之感。同时,索科洛夫通过滤镜使影片虚幻缥缈,笼罩在一种悲伤的、诗意的氛围。
D.长镜头。《俄罗斯方舟》(2002年)是索科洛夫对长镜头最极端的一次试验,被概括为“2000个演员,300年俄罗斯史,33间古老的隐修院套间,3个交响乐团和一个连贯的场景”,全片未经剪辑,只有一个镜头,也是索科洛夫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影片。《母与子》大量的长镜头把母亲临终前的死亡恐惧、儿子即将失去母亲的孤独恐惧无限放大。时间被索科洛夫用镜头定格、延长、凝固下来,气氛凝重压抑。

图3:《母与子》变形镜头
E.隐喻。影片广角等变形镜头较多,主要用在儿子和母亲依偎时,暗示、隐喻出母亲和儿子之间扭曲的关系。索科洛夫在画面造型上经常对实际环境的破坏或者使其变形。如:《沉寂的往事》中,墙和房子以及怪兽的变形扩大使得人在其中受到极大的挤压。而《悲伤与麻木》(1987年)中作为背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场面以不成比例再现在银幕上的画面使得人物变形,更突出剧中人的生活环境的危险和不实际感。同样的变形镜头在索科洛夫2003年拍摄的《父与子》中也出现过——父亲和儿子之间存在乱伦关系,儿子走过一段狭窄的街道时,墙面倾斜,给人压迫感。如同上世纪30年代表现主义电影《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通过变形和夸张的处理,将现实物质世界转换为内心的自我折射,带给观众诡异的噩梦般的感觉。
此外,母亲和儿子不加修饰的表演、寂寥萧瑟的环境音等,都创造出诗的氛围,每一个画面都流溢出诗的色彩和诗的情愫,体现出索科洛夫对人生哲理的深刻思考,在形与神、境与思的艺术境界上达到高度融合。索科洛夫对感伤、脆弱、纤细的生命状态进行的冷漠刻画,对存在本质的终极追问,使电影这一仅百余岁的艺术形态可以与任一本哲学著作相媲美。
二、多义、复杂的人物形象
在影片中间的时候,儿子翻出9B班学生寄给母亲的明信片,观众才知道母亲年轻时是一名老师。也是通过两人简短的对话,母亲的形象一步步丰满起来:她总是不回家,常年住在学校,脾气变幻莫测,对儿子没有尽到母亲应有的关心,就像儿子说的“总是对我不好”。她也许在中年时有一段外遇,儿子发现她珍藏的一封言语暧昧的明信片,在儿子质问这个人是谁时,心理的病痛投射在身体上,突然病情加重,呼吸困难,其实只是在逃避躲藏,封锁内心。儿子要求她“不要总是对我不好”的时候,她却只怕自己春天没有穿得出去的衣服,而对儿子的情感需要、物质需求漠不关心。同时她不得不在病入膏肓的时候回到故乡,依靠儿子,面对曾经被自己伤害过的人。在自己将要离世的时候,开始对儿子未来的生活感到担忧,害怕儿子也经历她所经历的那些痛苦。
儿子细腻,敏感,情感诉求总是得不到回应,用反哺的方式获得被母亲需要的满足感,而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他用面对情人才有的语气向母亲说话,对母亲充满爱怜,这是他“俄狄浦斯”情结的最直观表现。母亲提到儿子出生的时候天气寒冷,空气清新,孩子长大后一定聪明,但是无情。儿子认为自己如果不有些头脑,心就会碎。母亲是儿子的唯一的情感寄托,她是这个荒村里儿子唯一的依靠。在想到母亲即将离开,儿子在树林里痛哭失声。
他们之间的感情在索科洛夫诗话、冷峻的的电影语言下暗中涌动,有冷漠,有不舍,有伤害,更有面对这个世界时的无奈。
三、索科洛夫电影的哲学式思考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讲到:“这个日益加剧的个体化进程又意味着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日益增加, 也意味着个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 对生命的怀疑增大, 个人的无能为力感和微不足道感也日益加深。”3索科洛夫在《母与子》里无疑也展现了这种孤独感:一个人孤独,两个人更孤独。儿子和母亲尝试沟通,总是以母亲的自我言语而告终——人与人是难以沟通的,疏离的,人与人的交往往往具有某种功利性而无法真正深入对方内心。索科洛夫表现孤独感的电影还有《悲伤与麻木》(1987年),郊区的一所大房子里,应主人的邀请,一些人前来做客。慢慢地,他们之间构成了种种错综复杂而又难以捉摸的关系。他们无法进行交流,每个人都显得孤僻而孤独。他们追求自我表现,疯狂地跳舞,从不考虑其他任何人和任何事。所有人都以自我为中心,结果他们的行为举止构成一个个荒谬而毫无出路的“绝境”。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
在对生死问题的思考上,《母与子》延续了“死亡三部曲”的主题。《第二圈》(1990年)中,索科洛夫用近于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将一个人离开人世的具体过程展示在银幕上,给人一种枯燥乏味、丑陋恶心之感。死亡在此没有得到升华,而是显得丑陋可怕。人的死是如此渺小,进而比喻生也同样渺小。1992年,索库洛夫推出“死亡三部曲”的第二部《石头》。如果说《第二圈》描写人的死亡,《石头》则展示了作者一种新的思考空间——对人死后灵魂的再现。《沉寂的往事》结束了索库洛夫对死亡主题思考的三部曲,表达了作者在黑暗中的徘徊,在“失去了界限的生与死、光明与黑暗、犯罪与惩罚之间的绝望与寻找”。《母与子》同样在这个层面上将生与死的界限模糊,儿子生的恐惧远远大于母亲的死亡恐惧。与即将离世的母亲相比,也许继续活着的儿子所要承受的痛苦更大。母亲毫不掩饰地说自己害怕死亡,这种死亡恐惧在于“我们来自虚无,拥有名字,拥有自我意识和内心深处的情感,胸中极度渴求生命和自我表现——即便如此,还是要死”4。死亡恐惧因本我中“生的本能”——“潜伏于人的生命之中的创建性、进取性的活力”、“引发生存、爱欲和发展的内驱动力”5而产生。“生的本能”让人们追求不朽,成为永恒,恐惧死亡。
本片荣获1997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安德烈•塔科夫斯基奖、俄罗斯电影评论奖和评审团特别大奖。
注释:
1.俄《消息报》2001年6月18日。
2.来源于百度百科。
3.弗洛姆:《逃避自由》,国际文化出版中心2002年版,第58页。
4.林和生:《拒斥死亡》,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5.孙小光:《弗洛伊德的本能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生本能与死本能》,《长春工程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1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