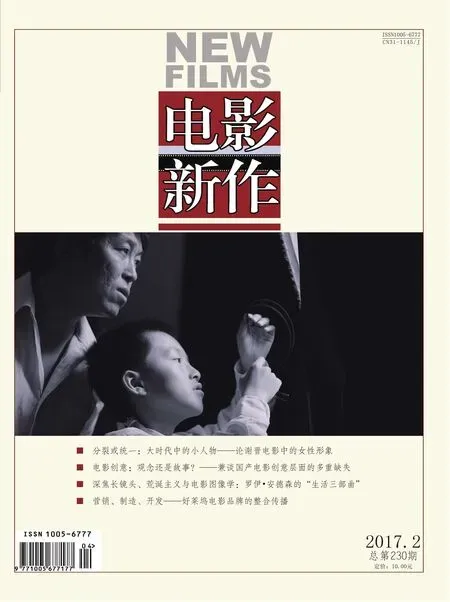《罗曼蒂克消亡史》:在虚构的消亡中进行美学建构
2017-07-25程波
程 波
《罗曼蒂克消亡史》:在虚构的消亡中进行美学建构
程 波
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用一种并非历史还原,而是虚构叙事的方式讲述了一段老上海的罗曼蒂克如何在家国情仇的残酷现实中消亡的故事。形式自觉的意识使得影片叙事和影像呈现出一种作者意识控制下的黑帮片和黑色电影的类型感,且具有明显的个人化美学建构,这样的美学建构通过“原型”等载体与价值观建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虚构 叙事 原型 形式探索 美学建构
《罗曼蒂克消亡史》是导演程耳在《第三个人》和《边境风云》之后的第三部长片。程耳在学生时代拍摄过多部实验性短片,其中毕业短片《犯罪分子》是一部用35mm摄影机拍摄的影片,节奏明快、情节性强,显现出个人风格支撑下很强的类型片色彩。2007年,《第三个人》公映,影片虽然带有明显的惊悚片类型特征,却也具有诸如大段对白,过多室内镜头等看上去与这一类型的普遍商业需求不完全一致的个人性。2012年的《边境风云》是他导演的第二部长片,获得较大成功:四段章节式的铺排、叙事视点的转换、贩毒和警匪元素营造的边缘空间和心理感受,打破了传统叙事方式,让人对故事和讲故事的方法都觉得眼前一亮。作品获得3000多万元的票房,对一个中小成本电影来说,商业上可算成功,更重要的是,程耳通过这部影片,在观众尤其是影迷群体中获得了很好的口碑,拍摄“个人风格痕迹极重的商业电影”成了“程耳烙印”。不过,程耳几年前在有关《边境风云》的访谈中说:“我个人对《边境风云》的票房期待是,能小赚一笔,但不会赚得太多,实际上3000多万元的数字正符合我的设想。小赚一笔,能保证我下部电影还有人投资;但票房过亿或者更多,并不是我最重要的追求——因为要达到那样的票房成绩,极有可能会损失很多东西,而损失的那些东西,又极有可能就是我最想表达的美学追求和价值观。对于某些导演来说,表达审美追求和价值观,是比获得高票房更加核心的追求。”①
作为一个学院派,阅读经验对于程耳的影响比较明显,一个表浅的例子,他的几部影片的片名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影史上的经典作品,他的电影中也隐约有卡罗尔・里德、弗朗西斯・科波拉、大卫・林奇、昆汀・塔伦蒂诺、科恩兄弟、伊纳里多等人的影子。虽然作品不多,但是我们又能很明显地感觉到程耳作品对于类型元素综合之后,在不拒绝观众的前提下,在价值观表达的同时,向着个人化影像叙事方向的美学建构。
《罗曼蒂克消亡史》同样体现了这样的美学建构。故事放在老上海背景下,似乎天然具有某种概念化的怀旧和浪漫,不过填充这种概念的是黑帮、暴力、杀戮、复仇还有“家仇国恨”的纠葛,表面的浪漫在一层层的拆解之下呈现出的是人的困境和命运的荒诞感,电影的美学特征似乎就是在“浪漫”的消亡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从故事层面上说,《罗曼蒂克消亡史》的主线可以按照故事时间的顺序概括为:葛优饰演的陆先生在日本入侵的战前,为他大哥出面处理章子怡饰演的小六(大哥的姨太太)与男明星偷情的事情。他安排自己信任的妹夫浅野忠信饰演的日本人渡部(实际为潜伏多年的日本间谍)送小六出城,途中渡部杀死司机和男明星,强暴小六并把她带回秘密囚禁在自己开的日料店的地下室里,使小六成为他的性奴。五年过去,战时,日本人因陆先生拒绝合作,密谋要杀死他,他们先杀了陆先生信任和依赖的女管家王妈,陆先生与日本人摊牌,却被自己的兄弟张先生出卖,一场枪战后,陆先生在保镖的极力保护下侥幸逃脱,但回到家却发现妹妹已经被日本人杀害,妹妹和渡部的两个儿子却没有死,陆先生离开上海去往香港,陆派杀手潜回上海杀死张先生。此时渡部已经回到日本军队,他临行前准备杀死小六但在最后一刻放弃了;日本战败后,陆先生从收容所里救出战时沦为军妓的小六,并带着她去往菲律宾的日军战俘营,杀了已是美军战俘的渡部。

图1.《边境风云》
这样的故事如果仅仅平铺直叙,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线索,那么很多张力和悬念可能就没有地方附着,也会缺乏新鲜的美学形式。这就要说到《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叙事层面了。
首先,多线索叙事对故事进行了有效切割和奇观化的重新组合。葛优、章子怡、浅野忠信三个主要人物不仅各自拥有一个独立的叙事视角,而且三者之间互为犄角,承载了故事最主要的矛盾冲突。葛优与浅野之间包含着信任与欺骗、家庭与国族的矛盾;葛优与章子怡之间存在着爱情与伦理、依赖与拯救的问题;章子怡和浅野之间承载着个体的诱惑和意淫、性权力与暴力、乃至隐喻性的日本与中国之间复杂微妙的民族矛盾问题。矛盾的出发点和表面都是“浪漫”的,而深层和落脚点都是“消解浪漫”的。
三者的独立视角让故事具有了局部的“非全知性”:陆先生处事不惊,深邃难测,觉得自己控制着一切,有城府有手段让人心生畏惧却又不得不敬佩,但他不过也是命运戏弄的对象;小六充满了欲望,既风情万种又张狂不羁,容易被诱惑却也极易让人意淫,但即便是这样的女人,在面对暴力的凌辱时却也是一个无力反抗的弱女子,甚至因为恐惧而麻木地屈从,不过在外力的帮助下,她最终获得了枪杀渡部、挣脱自己弱点、人性回归的机会。渡部自称是上海人,愿意保护上海和日本人对抗,他沉稳和善,会专门为猫去做一份日料,但这样的外表下他却是一个隐藏极深,甚至能够骗过所有人的日本间谍,他的内心因为长期的隐藏而具有了一种扭曲的暴虐。三个人物相互的纠葛和矛盾,最终让这些局部的“非全知性”逐渐缝补齐全,让观众获得了对故事完整性的心理需求,从而具有了整体上的“全知性”。加之在这三个主角之外,吴小姐、童子鸡这两条辅线与主线之间形成了呼应和补充的关系,也拓展了主线在人物社会阶层、结合电影圈从而自况等方面的空间。就是这种多线索交织、按照带有陌生感的线索和逻辑逐步显现故事完整性的方式,使电影增添了很大的魅力。
其次,悬念的设置,以及为悬念服务的伏笔、分晓乃至反转的设计,体现了电影在叙事与故事结合上的一致性。叙事的悬念一般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真相是什么,二是叙事的片段与真相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一种逻辑迷惑,后者则是一种“反格式塔”的逆完型心理。《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悬念由一个最大的反转支撑,那就是渡部的真实身份以及他在故事中的作为。很显然,如果按照时间顺序,那么这张底牌很早就会暴露,为此,电影将陆先生与日本人矛盾及火拼的故事提前,并让渡部在这个故事里成为陆先生的帮手且在枪战中“死去”。他对陆先生的欺骗和对小六的性暴力充分刻画了这个人物的双重性,不仅让故事整体上呈现为两个层次,而且合理地联系了这两个层次,出人意料和合情合理达到了平衡。为此,渡部对日料的痴迷,对孩子和妻子的不同态度,对小六“婊子”的蔑称和饭桌上为她捡手帕时隐藏的欲望,这些都构成了这个反转的伏笔和铺垫。除此之外,几条线索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构成了悬念。吴小姐与丈夫和“戴先生”的故事,童子鸡与前辈和妓女之间的故事除了“小部分”和主线在逻辑上有联系,“大部分”与主线又没有直接联系,这会让人迷惑。客观上,这是《罗曼蒂克消亡史》“野心”有点大的表现之一,支线故事想要捎带的东西过多,想要“全景式”地呈现社会风情画的结构,这分散了人们对主线的注意力,如果这个悬念没有完全解开,对观众来说就成了真正的迷惑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的“野心”又是值得鼓励的。因为,这里面透露出导演对于“作者性”前提下借用类型元素进行美学建构的探索和自觉。这就引出第三个层次的问题。

图2.《罗曼蒂克消亡史》
《罗曼蒂克消亡史》的结构和形式放大了内容核心冲突的张力,使之有着黑帮片的外观,但更进一步说,又有着“黑色电影”的美学追求,再进一步说,又带有很强的作者性。盗亦有道的黑帮传奇、奇观化的暴力之美是黑帮片的表里,但最终呈现的却是“消亡”,是一种荒诞感和无力感,这又是黑色电影的精髓,主线之外的“枝蔓”,使得黑帮争斗,复仇主题之外泛化出来一种独特的美学气质:怀旧的民国氛围、有腔调的上海味道这些是被虚构了的“罗曼蒂克”是如此易碎。开始时,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确定感十足,优雅自在,即便像童子鸡这样的底层小人物也是如此。然而,上海腔调终还是敌不过你死我活的家国矛盾,人们不得不放下架子,面对现实,变得迷茫空洞起来,如同影片英文名“浪费的时间”隐喻的那样: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是最有魅力却又最为残酷的时期,战前的上海时尚气息十足,纸醉金迷,光鲜亮丽,日本人一来,孤岛乃至沦陷之后,之前的“罗曼蒂克”又显得那么荒诞,那么没有价值,时间似乎都被浪费在浪漫之中了。进而,使用一种偶然的、松散的逻辑联系主线辅线,不仅可以扩大呈现这种荒诞感的空间,还原历史具有更大的广度和质感,也能更好地与故事里呈现出的主题和价值观匹配。当然,电影中的还原不是历史的,而是叙事的,是选择性的,是创作者进行一次美学建构和符号化的过程。所谓的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指涉,比如陆先生身上杜月笙的影子、吴小姐身上电影皇后胡蝶的影子、“拍给下个世纪看的电影”对于某个导演乃至对于某种电影美学的影射等等,都是如此。所谓的“在地性”,比如上海话和上海腔调、完全没有在上海取景的电影场景都是符号化的体现,都是一场对消亡的虚构,或者说是“为了消亡的虚构”。在欺骗、背叛、死亡、杀戮和复仇之中,这些虚幻的浪漫感消失了,在叙事对时间的重新编码后,个体、家庭、帮派、国族的欲望在被戕害之后得到了宣泄。从叙事到影像上的黑帮和黑色电影类型因素的运用,对老上海空间的文化想象,对暴力(包括性暴力)的影像化。正是在这样的虚构中,导演的个人美学风格有了明确的显现。
这样的美学构建,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那就是如何处理个人美学趣味和大众认同的问题,如何处理美学建构与传统审美积淀之间的创新和继承的问题,如何处理美学建构和价值观建构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笔者在此只对《罗曼蒂克消亡史》中两个具体的问题进行回应。
第一,为了杀渡部而先杀死他大儿子的问题。这是一个“美狄亚”原型的运用,合适不合适另外说,但是悲剧性的东西不能完全被残酷单向的东西取消替代。陆先生杀死他这个亲外甥,因为孩子是唯一能对渡部这个欺骗者、戕害者乃至侵略者惩罚的手段,他只在乎孩子,打死孩子不是逼他承认是侵略者,而是让他心痛,别的东西甚至杀了渡部自己都惩罚不了他,只有杀他儿子才是惩罚。这不仅是杀害孩子道德不道德的问题,而是深刻的悲剧性的东西。而且,为了更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观,那个小儿子并没有杀,这已经是对侵略者的仁慈了。西方悲剧美学中的“美狄亚”经过了中国化的“仁”和“恕”的改造,呈现出一种大是大非上毫不含糊,但又不简单粗暴地丧失悲剧美的平衡感。
第二,关于小六被虐待的问题。章子怡的表演,为放下偶像包袱做了突破和探索。但是问题是影片里通过文本上传达出来的东西,也许还有一些寓意,小六形象来源于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意淫,渡部捡拾小六的手绢也好,摸耳朵也好,像日本对中国战前的关系。渡部侵犯绑架乃至让小六沦为性奴的生活就是日本人侵华罪行某一种折射到个体上的隐喻。小六是一个受损害的女性,这其中甚至也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东西存在,这一层章子怡演出来,程耳没有刻意渲染,没有让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表现出来的东西更明确,因为这不符合主流的审查。这样的受损害当中也有对国民性柔弱的反思,进而有对于中日两国关系的一种深刻的象征。小六复仇最后拿枪打死渡部,小六第二次拿枪对着渡部,跟前面被绑架时的第一次呼应,前面有柔弱、有恐惧,所以没有开枪,而这个时候有突破有反省开枪了,这个跟国民性批判之后,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之后的褒扬结合在一起,获得人性自由以后对性侵者的复仇,突破了某种限制之后的复仇,这个复仇有价值,不仅是正面积极的,而且是合乎历史和人性的。对比前几年的《色戒》,这样的处理是“政治正确的”,又是极具个人美学风格的。通过具有审美积淀的“原型”运用、把“类型元素”乃至“中国元素”与个人风格结合起来,最终实现美学建构与历史建构和价值观建构的内在一致性。
现在的中国电影环境,商业类型片不说了,即便是所谓的艺术电影在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上和自觉的形式感上都不太够。所谓的多样性除了价值观、除了故事的题材和叙事内容之外,美学形式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市场乃至评论界对形式探索缺乏更多的认同或者宽容,“形式大于内容”常常成为扼杀形式探索的口实。程耳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刻意的地方是有的,但是形式和叙事之间有机的结合,以及用某种讲故事的方式能让故事更有意味、更精彩,为什么要对这种形式探索嗤之以鼻呢?艺术电影和观众之间本来就不完全有隔阂,艺术电影进入到市场,或者用某种方式接近观众、接近市场的探索,这样的刻意是有价值的。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罗曼蒂克消亡史》虽然票房并不理想,但在与《长城》同场竞技中有着口碑上的不俗表现,影片的风格化和作者气质构成了电影市场分层最直接的例证。相较于《长城》的高概念,《罗曼蒂克消亡史》则是“文艺范”十足。《罗曼蒂克消亡史》作为华谊2014年的重点项目,影片原定于2015年国庆上映,后因导演程耳对剪辑效果的苛求,在历经一年的修改后,才最终与观众见面。事实证明,自觉的美学建构意识和精益求精的制作态度从来都是成就一部电影的不二法宝,而由影片引发的热议和争论,也能促使人们对增速放缓时期的中国电影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进行更好的思考。
【注释】
①《虽然商业,但绝不流俗——导演程耳的艺术追求》,李博,《中国艺术报》2012年10月19日
程波,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市电影学高峰学科(2016年度项目)及2016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项目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