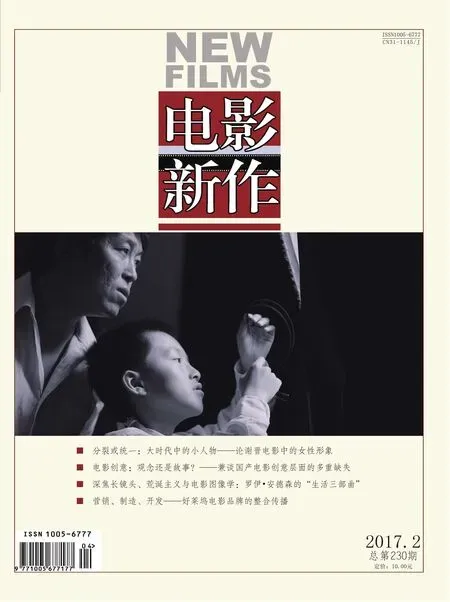国产家庭伦理片的“虚焦”生活流与“神经”喜剧倾向
——《重返20岁》与《奇怪的她》的比较研究
2017-11-16李佳营
李佳营
国产家庭伦理片的“虚焦”生活流与“神经”喜剧倾向
——《重返20岁》与《奇怪的她》的比较研究
李佳营
《重返20岁》改编自韩国影片《奇怪的她》,曾创下中韩合拍片票房之最。两部电影题材内容的高度同步留下了极大的比较思考空间,结合角色设置、场面调度与叙事背景对影片的类型、文本风格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来考察中韩两国跨文化改编的叙事结构与影像语言的叙事学倾向、生活流叙事的侧重、家庭伦理题材与“神经喜剧”的定义,以及后现代解构与家庭伦理价值重构等方面的同与不同,为中国家庭伦理题材电影未来的发展寻求有益的借鉴。
家庭伦理 “神经喜剧” 生活流 儒家观念
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动荡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心理危机和大规模的情感危机,普罗大众的生活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波及。生活压力的与日俱增,使大多数观众的需求转向了纵情娱乐和情感发泄式的文化产品,于是,小成本喜剧电影成为这一轮“口红效应”的受益者。①同时身处21世纪,日新月异的世界背后价值观的混乱和社会文化固有认知的破裂开始使人们安全感匮乏,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信仰与传统伦理价值的回归来填补为物质膨胀所挤压的精神空间,与现代化和现代人生活合拍的、家庭伦理题材为主的轻喜剧再度流行也实非偶然。
韩国CJ娱乐公司在2014年初出品了由黄东赫导演的电影《奇怪的她》,创当年本土年度票房亚军,观影人次达865万。《重返20岁》改编自这部电影,于2015年年初在国内上映,短短三十多天斩获3.5亿元的票房,一举打破中韩合拍片在国内上映的最高票房纪录,也为近年来国内日趋减少的家庭伦理题材电影拓开了一番新的天地。
这两部以家庭伦理题材为主的轻喜剧与以往的传统家庭伦理片不同,其中最为吸睛的一点是主角穿越时光的奇幻之旅,引起了年轻人——同时也是影院主力军的关注。而电影中“重返20岁”的年轻身体与老龄化思维、行止的矛盾所带来的戏剧化效果,有笑有泪的背后,也藏着的是对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老年人赡养和老中青价值观代沟等问题的追问和关注,是一份难能可贵的人文关怀。《奇怪的她》的成功为《重返20岁》的高票房埋下了伏笔,而从电影的跨国改编角度来讲,必须更加主动地从剧情、角色、社会背景与生活场面,乃至于类型、风格等方面,与跨国市场的在地性文化经验建立起一种更为密切的对应关系。②所以,当叙事时空由韩国移植到中国,其影像呈现的变化是耐人寻味的。
一、中韩家庭伦理叙事结构的同与不同
从整体上看,两部电影都是典型好莱坞式商业片的叙事逻辑。主要人物作为因果叙事的中心,以其性格为基点来设置主角人生的转折点。女主角重返年轻,她有了新的人生目标:实现年轻时的歌唱理想,而阻碍她自我实现的是儿子寻找失踪的母亲这一副线。在家庭责任与女性自我实现的拔河中,最终,她为亲情舍弃了自己刚刚萌芽的事业与爱情,选择了更为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血缘家庭的圆满和解。虽然二者走的都是家庭伦理轻喜剧的套路,情节组织方式与影像叙事表达却有着明显的区别。
通常情况下,影片开场的戏剧目的在于引起观众兴趣和营造叙事氛围,以这一点为例,中韩的切入点有着明显的不同。《重返20岁》选择的开场是一个抒情长镜头,通过对父母亲情、家庭结构的展示到儿子成长、妻子作为另一个女性介入、母子关系渐渐疏离直到儿子走进悬挂片名的教室。这一段落点明了母子、家庭之间的关系,定下了温情怀旧的影片基调。而《奇怪的她》则选取“球”作为一个叙事聚焦点或者说“麦格芬”,通过不同球类运动的动态影像来譬喻女性从青春到衰老这一普适的女性话题,不但拓宽了影像视域,也奠定了影片的喜剧基调。随着躲避球重重落地,转场入儿子探讨老人歧视问题的课堂。这一叙事序列背后的视觉符号运用非常丰富且娴熟。“球”本身植入了剧情悬念,也让观众有兴趣去探索它背后的隐喻对象和主角的生活遭逢。情节元素编织考验的不仅是导演的情节组织功力,还有对观众的影像理解素养的信心。对比《奇怪的她》富有活力的镜头语言,《重返20岁》的抒情步调阐释性强,但相对保守。
两部电影都以女主角的“奇遇”为叙事主线,顺时序展开全片。围绕这一主线的是儿子寻找母亲、电视台选秀(爱情线)、孙子的音乐梦三条副线。在叙事线索网状交叉的过程中,同辈人的平行比较如女主角和红衣老太,两代人间的垂直参照如女主角与子一辈、孙子辈间矛盾共同建构了一种对比共构的叙事关系。当核心主角与不同的支线人物形成多重对照关系时,主副线人物的成长也就与彼此间关系的变化、事件的发展休戚与共。
《奇怪的她》的第一幕,儿子在课堂上提出老年歧视问题,学生的回答侧面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的严重,通过语言的衔接切入了咖啡厅里女主角对自身前史的第一人称描述、老朴对她的暗恋、红衣老太言语挑衅后大打出手、因老朴受伤探望时她与老朴女儿关系的紧张、男主角选拔歌手、婆媳矛盾、孙子乐队的矛盾等,不同人物及其背后的故事线索渐次浮出水面,服药的儿媳、孙子乐队糟糕的主唱、女主角将被送到疗养院、昔日亏欠的故人登门寻衅等细节也为后来的人物行为动机与叙事转折铺垫齐备,年老的女主角面对绝望而无助的生活现状,需要“触底反弹”——变回一切皆有可能的20岁,像她喜爱的明星奥黛丽・赫本主演电影《罗马假日》一样开启一场脱离世俗人生、重返青春的奇幻之旅。可以说,韩版第一幕27分钟的铺展异常工整,叙事节奏紧凑几无冗余。
而再审视《重返20岁》第一幕的叙事,该片对每一场戏内的喜剧化表现、情节的对比巧合非常重视,此处可见中国传统文学叙事中“对偶美学”的痕迹。所谓“对偶美学”讲求的是传统阴阳互补的二元思维模式,用米歇尔・扎伐台尔的话说是对等形式的重复再现,类似行文时的对偶句,这点在戏曲/戏剧中较常出现,多根据一连串人物或情境的主要性质如雅俗、动静形成对立或对等的对偶结构。③电影中儿子在课堂讨论老年歧视问题的间隙,插入了女主角坐公共汽车的情节,红衣老太的新皮鞋与女主角破鞋子的对比,女主角打麻将说“一塌糊涂”、训狗时说“闭嘴”和着挤兑人的拍子等等对偶镜头与细节设置都颇具趣味,与韩版明显不同。但这种结构放置到电影中有明显的缺陷,因为一一对应式的情节编织往往会局限影像本身的表现力,也会使影片整体意涵的传达流于浅薄化和简单化。《重返20岁》对琐碎的生活言语与戏剧化细节的重视,相对的是在整体的情节转承、人物动机、叙事纵深力度上的不足。然而,这些过分追求生活流的冲突桥段,从根本上而言是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叙事结构的。
《奇怪的她》中,主线和围绕女主角的几条副线均有各自稳妥的收尾:孙子“潘智河”从“暗黑视觉系”的浮夸做派到用心歌唱,实现了音乐梦想;无业的孙女接替她做了歌手;婆媳间的相处走向和谐;儿子对家庭问题的关注和处理方式有了变化;与男主角的照面不相识让人怅惘,徒留一枚发夹信物;“彩蛋”中老朴找到了青春照相馆重回年轻,与暗恋多年的“小姐”关系也有了新进展。“吴末顺”的人生已经不同了。而《重返20岁》则像一次彻底的奇幻旅行,鹿晗饰演的“项前进”前后变化并不明晰,歌曲无非是流行到复古的反复轮换,服装造型更是千篇一律的偶像路线;儿子在家庭中似乎从来处于一个不成功的调解者身份,直到最后也没有发生什么实质的改变;媳妇的变化没有过渡,“李老头”这条线更是在收尾时被彻底忽略。一切不过绕回原点。
二、影像叙事语言的比较与叙事学分析
每个观众内心深处都渴望实现一种理想化的生存状态,所以在观影的过程中会对银幕彼端的人物产生镜像式的认同,这种认同感是通过精心设置的影像空间调度组合相应的镜头语法来实现的。特写镜头作为构成主观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在镜头语法的构成中是非常重要的。以唱歌的两场戏为例,主角第一次展露歌喉是咖啡馆/老年活动中心的一场戏:《奇怪的她》以“朱老太”俗辣的表演来反衬,特写镜头中舞台球灯旋转在“吴末顺”的脸上形成影影绰绰的光效,雨打枝叶、顺屋檐而落都营造出感伤的氛围,引导观众走近女主角的创伤记忆;而《重返二十岁》的情节耽溺于“沈梦君”和“陈老太”的争吵,拖沓的琐碎事故与韩版简洁而“走心”的表演相比过于浮夸,这一重要情节的叙事功能未能有效地发挥。最后一场圆梦戏中,两部电影也选择了不同的场所:《奇怪的她》选择了内景演唱会,由舞台顶端女主角的原生内视觉聚焦浸入,主观的摇晃摄影将观众带入第一人称的感知之中,台下众人的喧哗之声在升格镜头里由远即近,“一个声音只有当某些畸变(声音的过滤、音频的部分缺失等)造成一种特殊的听觉,才能将一种不可见的机制表现出来。”④通过原生内听觉聚焦的方式,声音带动了叙事节拍的变化,抽离出一个“回光返照”的奇幻时刻,“这么多的人,在等着我们的歌”,女主角终于变成了自己梦想中的样子,也燃尽最后一丝青春,光晕黯淡,Magic time⑤消失,“灵魂黑夜”悄悄地潜行到了脚下;《重返20岁》则选择了室外音乐会的大舞台,场面调度能力的不足暴露无遗,现场收声效果不佳,台下的喧哗声和热烈的氛围使观众很难捕捉到情节表现的重心和这场戏在电影叙事中所具备的“功能”,叙事节拍完全混乱。罗兰・巴特曾将普洛普“功能”的概念引入了叙事元素的分析,并提出了对情节单元的新见解。巴特认为叙述作品的最小单位可以分成介入情节、对行动与结果形成驱动的“功能体”与提供人物、环境相关情况的“指示体”两种,他曾说“功能体的本质是叙述中的将能开花结果的种子”。⑥显然,《重返20岁》“功能体”的薄弱,使得“行动”失效,对叙事“结果”的驱动也显得牵强。
随着“灵魂黑夜”的到来,孙子出车祸需要大量输血,第三幕随之展开,留给女主角的青春时间就此进入了倒计时。在故事高潮到来之前,这是一场需要重点铺设构思的戏码,对第三场主角人格的升华有重要的助推作用。生病与亡故的情节作为提升人格境界、促使剧情逆转的功能单位是应用于中韩两国家庭伦理电影/电视剧领域的、由来已久的以情动人的叙事习惯,而这种苦情戏思路的反复使用本质上遮掩的也是一种商业逻辑——“大影像师”通过对场面调度的掌控和视点转换的内在节奏来调动观众的心理共鸣。
可以说,在影像的维度中,观众的同情乃至认同的情绪,都是通过多种视觉聚焦有技巧地组合带入的。以第三幕医院内的母子对话戏为例,儿子向女主角提问,女主角站在镜头前部,前虚后实,母亲无法面对被揭露的秘密;正反打镜头接过肩镜头,母亲的情绪明显受到强烈冲击,她打断儿子准备离开时被拉回正面镜头,叙事节拍开始转入了悲伤基调。二人镜头由中景转向近景,画面构图也由松收紧。最后二人拥抱,镜头分别切入二人特写,该场景从容收尾。通过原生内头拍摄呈现出影片人物无法克制的内心情感,观众一步步将自我投射到影片人物的身上。反观《重返20岁》镜头重心的偏移和固定的拍摄手法很难提炼出母子二人互动时的情感波动,仅仅是言语和音乐的手段,很难达到像前者在影像空间表达中所呈现出的动人效果。电影叙事本身能够在镜头里同时表现叙事行动及其背景,并且在空间呈现上优于其他媒介,《重返20岁》在影像叙事能力上的薄弱是很难通过言语叙事(台词、音乐等)来弥补的。观众看到的不过是瞬时感官的外壳,内心的情感投入会因声画表达的失衡而不断流失,“情感不足音乐凑”的老套思维需要从影像的现代化表达中清除。
三、“虚焦”的生活流与“神经喜剧”的再在地化
美国学者博格根据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区别曾经做过一个具体的分析,通过媒介来呈现的叙事是虚构的,事件发生比较集中且有完整的起承转合,叙事冲突也较为激烈而持续。他认为人们需要的就是饶有趣味的叙事,日常生活的分散、重复、缺少事件、目标模糊等性质是与叙事的要求相悖的。⑦虽然日常生活的元素是家庭伦理叙事影片的有力支撑,但二者并不能简单的等同,在电影中日常化的情节也承担着必要且具象的叙事功能——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奇怪的她》中女主角在打工的咖啡店出场,因勤俭节约而穿了一双破鞋,被“红衣老太”出言奚落后,二人大打出手。虽主角性格好强、嘴巴毒不讨喜,使媳妇神经衰弱到住院,还有着不堪的过去,但她对恩人的背叛有为养育儿子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媳妇的抑郁也和其自身不善于表达的性格、丈夫对家庭内部矛盾的轻忽有关。那些在战争时代备受生活煎熬而来的、坚韧积极的秉性使她不仅带领孙子找到了新的音乐信仰,最后也仍旧选择为家庭牺牲自己来之不易的第二次青春。影片为人物增色也不乏技术性的添加,将内心独白与对话相混合的叙述方式,将女主角的心理活动外化,为其直率讨喜的性格添了一笔。“吴末顺”这一角色以励志人生的上升弧消弭了观影的代沟,向社会传递了一份乐观的正能量。
与韩版不同的是,《重返20岁》对人物有着更为生活化、接地气的塑造。女主角“沈梦君”出场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儿子的课堂插入她与年轻人的互动充满了谐趣;活动场所由韩国的咖啡厅转入老年活动中心,打工贴补家用换为麻将桌上的老太群戏;“李老头”教训大龄单身女儿使用的是婚恋节目《非诚勿扰》的“梗”;女主角变身后的澡堂戏变为中国大妈标志性的广场舞;韩剧变为国民剧《还珠格格》等等。主角们成为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普通人,固然使本土观众更有亲切感和同理心,但影片忽略了对人物特征本身的戏剧化加工——即通过场面调度来烘托不同角色的个性和放大人性的闪光点。家庭伦理片常以角色为中心,如果作品徒有情节而忽略人物的塑造,或者情节压倒了角色,剧情发展都会显得扁平而不够立体,理想效果是情节与人物两相结合。⑧两部电影平行比较下,“吴末顺”汲汲营营、事事要强的励志生活态度变成了“沈梦君”刀子嘴了一辈子、老了愈加没人懂的状态;“吴末顺”为抚养儿子“小揪儿”有过劣迹,这一情节在《重返20岁》中被删去后,导致人物改变前期的铺垫不足和电视台初登台唱歌的回忆片段情感单薄;“沈梦君”由于闪光点铺垫的不足显得无理取闹,其擅长言语讥讽的市井俗常小人物气息与“吴末顺”率真洒脱的、精神巨人的形象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些伏线在高潮戏——喧宾夺主的外场演唱会舞台和调度精巧的内场演唱会舞台中搏出了高下,前者仅仅停留在怀旧的层面,后者发掘出的却是另一种人生有阴晴圆缺的复杂况味。
从类型电影的角度来说,两部电影都有着“神经喜剧”的特点。焦雄屏将路易斯・杰克布斯的《美国电影的崛起》中提到的“screwball comedy”翻译为神经喜剧,用“神经”表示古怪胡闹、不可理喻的行动,与此种类型电影的特点互为参照。“神经喜剧”一方面有高乘喜剧的成分,如注意对白和人物之间的互动,对人生社会有所参照,批判大多委婉含蓄;另一方面,个别场面也吸收了低乘喜剧的元素,如穿插惹笑的肢体语言、吵架、打闹等。“神经喜剧”往往选择介于两种取向的中间。⑨《奇怪的她》中重返年轻的吴末顺20岁的身体里装着70岁的记忆,一副“童颜”和行事老派、家乡方言、举止粗鲁等特点的结合让人忍俊不禁;《重返20岁》的“沈梦君”虽然肢体语言不如前者丰富,但一派普通中国老太的操心絮叨、牙尖嘴利也让人觉得亲近得仿若邻里。两部电影的不同在于对社会批判处的着眼。
《奇怪的她》中穿插了许多颇具讽刺意味的细节。韩剧的拖拖拉拉,生活糜烂而肤浅的青年一代(公车上的小混混),娱乐圈歌手光怪陆离、一味追求外表出位和高超技巧、用心唱歌的人越来越少(孙子之前的乐队、“豆包”)等等。高乘喜剧针对人性弱点与可笑一面,来批判社会制度的矛盾与不公,其讽刺未必尖锐深刻,但利用高超的表现手段制造笑声之余,可以对观众的思想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如明明靠家庭养活、没有工作、不知人间疾苦的孙子却以所谓的重金属、“视觉系”摇滚讽刺资本主义贫富差距与88万世代⑩的爱情,无病呻吟,在被女主角的阳光乐观感染之后才逐渐找到新的音乐道路。儿子是研究老年人问题的专家却仅将其视为社会公益问题和病理问题来看待,对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并非真正从心的理解,母亲出走、婆媳问题以及忽视、嘲弄老人的不良社会风气等等矛盾和代沟,在老头和公车小混混并肩站在LED前抹着眼泪听她唱歌的这一刻消解了,大众媒体日渐丧失的公信度也有所回升,娱乐圈造星工程有了新气象,这些都有熟悉的主旋律“气味”,但通过潜移默化的展示,观众并不排斥这种认同于主流价值的方式。
反观国内,很多富于社会批判性的影像化修辞尚且举步维艰。大众对于家庭伦理片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解通常停留在肥皂剧式的或者纯说教式的乏味。于是为了吸引更多年轻观众,《重返20岁》招揽了新生偶像来表演,但显然,实际的表演效果并不理想。国产电影重视的是“神经喜剧”在世俗化层面的应用,然而无论是社会热点现象的“裸白”笑料(《非诚勿扰》《最炫民族风》《还珠格格》等等),还是人物的言语讥讽都未能到位和准确地行使其叙事目的,而且,在这些着重于角色的戏谑恶搞、贴近民众的情节中,过分追求真实的市井人物也会阻碍我们的认同。所以,尽管《重返20岁》足够生活化、接地气,但终归只是低乘喜剧的里子,秉持了不说教、亲民性的言语原则,其价值判断却在过度的生活流中“虚焦”了,使得这部家庭伦理片终究缺乏本应具备的、实质的人文关怀和正面向导。
四、后现代文化的解构与家庭伦理价值重构
将“生活的原生形态”视为艺术反映的高格实际上是模糊艺术和生活界限的后现代艺术论的价值观念。后现代化的表现本身有其危险性,那就是对于价值意义的消解,而且归根结底,家庭伦理片是以人伦温情和主流价值回归为主要目标的。
中韩两国遵从的都是儒家传统,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这一点从两国的商业类型片的创作中就能窥测。而中国家庭伦理片对单一场景、戏剧化表演的追求与韩国家庭片在日常生活层面所呈现出的平淡之美不同,后者仍然可以看出受到儒家传统较大的制约作用,人们对于家庭关系和礼教(影片有意强化的部分)非常重视。韩国电影自上世纪末的“光头运动”后分级制取代了审查制,韩国电影飞速发展,观众的影像理解能力有了很大提升的同时,表现家庭伦理的作品比我国有了更多的优势和展示空间。虽然韩国家庭伦理片尝试以传奇色彩的题材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但基本上属于静水流深式的温馨,重视的仍然是电影的整体性承接,唤醒观众内心在漫长而琐碎的生活中丢失的、最单纯美好的况味。
“儒学在稳定社会秩序和家庭关系、焕发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加强团体亲和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人们所公认的。”儒学是韩国现代家庭伦理与社会文化的重要基石,虽然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念已经占据了很大的位置,但就世俗生活的层面而言,儒家传统仍然作为主旋律发挥作用。在家庭组织中,传统的孝悌观念是儒家文化非常强调的一点,三世同堂的家庭在韩剧中也有很多的表现,“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依然很多。一家之长(通常是父亲)和年长者受到其他家庭成员敬重与遵从,晚辈子女要态度谦和。无论家庭内外,都要尊老敬长、使用敬语,代际的划分非常严苛。而在《奇怪的她》中,女主角虽年老却自力更生,出外工作;重返年轻之后不再小气,为自己大变身;回到20岁后一改老年人的古板,开始追求新生活和新的爱情。由此可以窥见,当下的韩国电影在加入了现代西方自由、民主与平等的观念后,也不忘弘扬韩国社会一以贯之的儒式家庭传统,共同组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家庭伦理片的文化蕴藉。反观国内,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儒家的家族传统在中国血脉日益微单。计划生育实施以来,独生子女家庭日渐增多,且一如西方家庭的婚后独立越来越多,几世同堂的旧日光景已经渐渐消失,一家三口、两代同堂成了主要的家庭结构。现代国人对于儒家思想缺乏理性、系统的认识,简单地将其与封建守旧划上等号,所以中国的家庭伦理片对于儒家传统中敦亲睦友、人伦亲情的表现力是很贫乏的。在国产的影像视野中,无论是为人的谦和礼数、对老人的尊重和亲人的体贴、到家庭的责任,这些最平凡的却深深扎根在民族精神里的信仰,已经被家庭伦理题材里一众通俗闹剧、低俗喜剧或者刻意的煽情狗血桥段吞没了。这既是韩剧风靡内地的深层缘故,也是《重返20岁》虽“技艺”并不精湛,却在内地获得成功的原因,原作改编时内里包裹的人文关怀底色唤醒了我们久未被亲情“这件小事”动容的心。
结语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经说过,人类家庭是一个伦理的实体。这也即是说,家庭作为人类道德产生的始基,蕴含着人类道德不断发展演进的胚胎和萌芽。当国内电影市场被好莱坞大片和中小成本低俗喜剧装点得“繁荣”无限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急于融入西方价值观、速食文化目光投向短期利益回报时,这些观念无一例外都在慢慢消解着传统道德的本土立场。而且,家庭伦理题材电影一味追逐与年轻观众的观影喜好结合时,也面临着传统道德价值的一再折损。
儒家观念与西方现代观念的冲突是中韩两地都存在的矛盾,退居世俗生活层面的儒家传统受到西方现代观念很大冲击。儒家思想强调以理节情,重集体(家国忠孝)甚于个人,重等级(尊卑有序,长幼有序)而轻平等,也有男女有别夫妻上下,重道德而轻牺牲,重义而轻利,与西方现代文化流入的个体价值实现、重平等观念是有区别的。但二者并非全然不同,儒家文化对于以理节情的强调,同时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强调;对礼的强调,包含着对他人的尊重;而对孝的强调,体现着对老人的关怀;对信与仁的强调,更是同样为现代文化观念所追求。所以传统道德修养的强调并不是与现代文化观念完全相悖的,而是互为表里,互为补缀的。
韩国电影倾向于挖掘出人性内心深处的闪光点来寻求观众的共鸣,带领观众通过谐趣的镜头语言来关注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以家庭温情之力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化解了平凡生活的无常与无望。所以《奇怪的她》和《重返20岁》的观影体验中,我们都无法否认的是,“吴末顺”这一人物更为可爱。国产家庭伦理题材电影重视人物生活化的表现,但过分戏剧化的真实人物反而显得不讨喜、格局小,这一国产家庭电视剧中承袭来的、塑造人物的惯用手法在大银幕上并不合衬。观众在电影院中希望看到的并不是身边随处可见的俗套,而是寻求一方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伸张的幻想投射之地,庸俗笑料所堆砌出的笑料过于浅薄,带来的情感冲击力也是瞬时的,并没有给观众留下太多结合平凡中的高贵人性来进行深入思考的余地。
《奇怪的她》以娴熟的影像叙事语言和丰满的故事情节让我们清晰地感知到两种层面的情感慰藉:一层是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一层是家庭责任,二者都有着深层次的人文关怀的意味。女主角为了“大我”牺牲“小我”代表了一种集体主义的、儒家式传统价值观念的反刍,结尾彩蛋里的想象性弥补也贯彻了喜剧的基调,冲淡了恋情无果的忧伤。在结局以肉体的衰老隐喻一个母亲心灵的崇高时,女性在家庭中的价值也得以正名,最终回归了稳固血缘家庭结构的中心。而《重返20岁》拘泥于局部情节的喜剧化表现,忽略了整体影像呈现的合理组织,有首无尾,最终只能抵达煽情怀旧的层面。其实无论是对人物内心情感的表达,还是影像叙事的手法,我们还有太多需要向韩国电影学习的地方,虽然其情节构造对巧合的注重可能违背了我国家庭伦理片反映现实生活的追求,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观众对韩影的热切关注、喜爱和追捧。近年来,韩国电影远销海外,其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成功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
2015年下半年大热的电影《夏洛特烦恼》《港囧》等片也都类属于家庭伦理题材和“神经喜剧”的范畴,其中对温情伦理与主流价值观的伸张不乏有益的尝试,但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娱乐并不能长期的等同于恶俗,观众的审美判断会随着观影经验的增长而提升,从狂欢化的、言语维度的速食娱乐走向更具现代化意味的、影像符号化的人文关怀是喜剧精神必要的提升。毕竟,电影作为文艺作品有责任向社会树立生活美的追求、传递正能量,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陈晓云,中国当代电影思潮与现象研究(1979—2009)[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3:349.
②石川,《重返20岁》:跨国改编与东亚经验[J].电影批评,2015(2):67.
③蒲安迪,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49-51.
④[加拿大]安德烈・戈德罗、[法国]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M],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87.
⑤Magic time:摄影术语。指代日落前的十几分钟,光线最柔和、最适合拍摄的时刻.
⑥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事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98-199.
⑦[美]博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9-182.
⑧郑树森,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98.
⑨郑树森,电影类型与类型电影[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141.
⑩88世代:指韩国初入社会每月工资仅有88万韩元(人民币5346元)的高学历低工资的年轻白领们.
李佳营,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互联网+’语境下华语电影产业融合研究”(项目编号2015EWY003)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上海大学电影学高峰学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