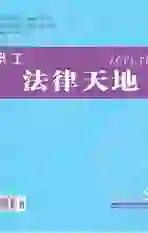浅析目前非法经营罪的立法弊端
2017-07-24秦帅
秦帅
摘 要:我国社会正在朝二元社会结构方向发展,刑法的发展会更加朝向尊重市民权益领域,定位会更加准确。然而在现行刑法中,仍然保存着一些类“口袋罪”的罪名,这不利于我国刑法的发展。其中非法经营罪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罪名。本文通过梳理非法经营罪的历史流变,分析该罪名价值取向发展等,从司法实务出发,厘定该罪名目前的立法弊端,希望完善该罪名和其他类“口袋罪”的立法。
关键词:非法经营罪;口袋罪;空白罪状
一、罪名由来
非法经营罪是由我国1979年的投机倒把罪演化而来,一个罪名的设立的背后必然有巨大的立法原由、价值判断、社会和市场需要。法律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他服务于经济基础。1979年刑法是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产生的,如果不分析当时的经济社会体制,也就无法梳理投机倒把罪的设立价值需求。
很多学者对于该罪名的立法价值需求重点从我国传统刑法观和苏联体制立法模式影响等方面进行的分析。笔者认为以上都是较小的影响因素。对于投机倒把罪的立法更深层的分析应立足于立法时的社会经济条件。
投机倒把罪的废除予否的争议本身没有意义,但是从不同的声音里可以看出诸多价值分歧,有利于我们把握立法的实然走向。学界出现过保留说、废除说、分解说。笔者认为,法律的修订离不开对大环境的分析,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管理更加朝向开放,自由的方面,鼓励商品经济的流通,活跃市场。立法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投机倒把罪必然退出历史舞台。
在市场经济兴起的大背景之下,伴随着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投机倒把罪分解为数个罪名,其中主要是非法经营罪。而承担规范社会经济秩序责任的“新罪”在实践中出现大量司法解释、地方法规,变成了新的“口袋罪”。
二、非法经营罪的特点及立法缺陷
1.空白罪状中的“国家规定”
“国家规定”的判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非法经营罪所规定的条款中,“国家规定”引起了较大的理解上的歧义,而“国家规定”的涉及的法律规定的范围决定该罪名的成立与否。其次,“国家规定”决定该罪的适用范围,“国家规定进行了限定,该罪名则减小了适用范围,反之亦然。
2.明确性与无限扩张的悖论
(1)兜底条款在本质上属于概然性规定,亦被我国学者称为堵漏条款。刑法对犯罪行為的规定天然地具有不周延性、不完整性。对此,中国古代曾采用“比附援引”的类推方式加以弥补。此外,还设立兜底罪名以备不时之需。兜底条款还增加了法律的弹性,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在裁判时具有了较高的灵活性,相应地也提高了刑法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不易解决的悖论,非法经营罪的设置使用了概括性的方式,这是其饱受争议,而兜底性条款的设置使其不周延,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出现了立法机关所预想不到的行为方式,顺着兜底条款预留的窗口,大量的司法解释和地方法规弥补了该罪名的高度概括性使其更加明确具体可操作但是同时带来了该罪名的无限扩张,想具体明确就增加解释,越解释越扩张无度,“口袋”越大。
三、非法经营罪的立法价值取向反思
(1)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投机倒把罪完成其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其立法价值的取向延续到了非法经营罪身上,即注重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忽视个人关怀。非法经营罪过度“扩张”使得私权收到潜在威胁,在明确自身同时使得刑法稳定性得不到保障,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2)有违刑法谦抑性精神。刑法的谦抑性是多种价值的集合体现,他旨在控制刑罚的使用秩序,保障社会规范的合法运行,规制刑法对社会关系的干预位阶。基本原则在于刑法的后续使用、成为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的最后砝码。
而肆意的扩张非法经营罪的范围势必造成刑法资源的浪费,过度刑法化,侵害市民的私权范围,干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长期下去,这是与现代刑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表现。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更预言“刑法发展的极为遥远的目标……是没有刑罚的刑法典”。
四、立法完善建议
对于非法经营罪完善的原则必须是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上,具体措施是限制其扩张,首先是空白罪状的明确限制,其次是兜底条款的取消使其确定,合理分化为其他罪名去“口袋化”。
我国刑法第96条己经明确规定了“国家规定”的范围,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仍不断出现将部门规章或者其他效力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作为“国家规定”进行参照进而认定某种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很多学者对“国家规定”的范围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有的认为只包括法律,有的认为应包含司法解释,然而,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96条的规定是比较合理的。既然我国刑法对“国家规定”的范围已作明确规定,笔者认为我们应当严格遵守该规定,既不缩小其范围,也不肆意扩张其范围。
非法经营罪由于设置了兜底条款,使该罪具有了高度的概括性和开放性,随之而来的这种不确定性既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也有违可预测性要求,并且还为非法经营罪在立法上和司法上的扩张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不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如果取消了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对于司法解释、司法实践无限扩张非法经营罪的趋势,就可以进行有力的阻却,使非法经营罪的范围具有相对确定性,符合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刑法对市场经营活动的规制是有限的,从而更好地体现了刑法谦抑性原则。经营者对法律的可预测性也随之提高,不仅可以更好地发挥法律的规制作用,也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如果伴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型的非法经营行为,我们可以通过制定单行刑法或刑法修正案的方式来解决,保证了罪刑是由法律制定的,排除了司法解释对非法经营罪的扩张。
参考文献:
[1]姚建龙.刑法思潮与理论进展[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版
[2]张天虹.经济犯罪新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4]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陈兴良著.《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德]拉德布鲁赫.《刑法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