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情”交辉的器宇恒心
2017-07-24陈镭
陈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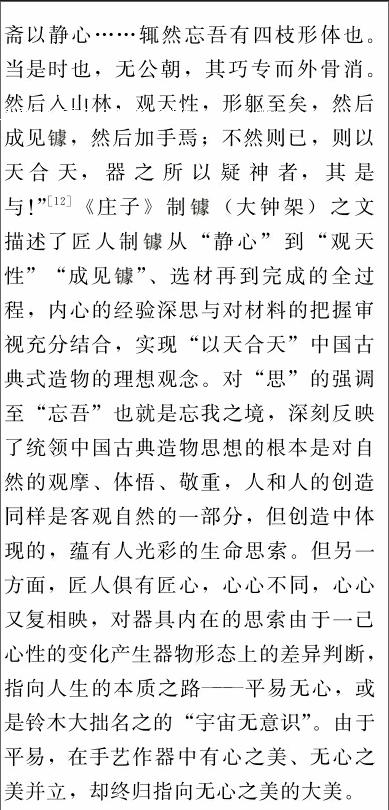
对于“手艺”与逝去的“手艺”时代,如同盐野米松之言“有人说它们太老旧了,也有人说它们太落后了,但是还是有人觉得那些手艺很好,也还是有人用它们”[1]。在依赖廉价工厂劳动力激发全球消费经济的背景下,工艺研究或归属于各类专门艺术研究机构,或纳入日用品市场的产品工业设计范畴,更高端的工艺美术则进入高层次的艺术消费领域,“手艺”成为二者视野之外的孤独存在。当“传统”成为近乎“高大上”且富含政治寓意的象征,当奇观成为令人厌烦的审美疲劳,那些存活于人间、饱藏温情的“手艺”,也许唤醒的不过是手手相递、茶饭团圆的朴质往日,联结的不过是异貌同质、千针万线的山水原乡,抒发的不过是莫名而厚、深藏于心的所谓“祖国”以及对于这片土与人的爱意。
《手艺与禅心:寻找中国匠人之旅》成为近年来手工艺题材图书少见的贴心之作。如作者浅草所言,在“不小心读到”[2]日人著作之后,“不仅发现了中国也有最好的匠人和手作,也是我体验过的最好的游走中国的方式”[3]。这种游走,也许是近于原生态的朴素记述,却让人得以窥见人心凝聚、万象纷呈的“物”世,触碰到器物藏华、“心”“手”相连的“人”情。
一、百姓日用即是道
教化与造物。从根本上注重人的生活实践,提高和完善人的生活,是自《易》“利用安身”[4]以来中国古代美学实用主义的根本所在,与“未知生,焉知死”[5]、“道”是“日用当然之理”[6]的现世人生观紧密联系,逐步发展为王学重镇王艮“百姓日用即是道”的哲学美学观。在相对沉寂的古代物质文化研究成为当下研究界热点之际,再度从“日常生活”深入到“日用器物”中,其实质是从“日常”向着“日用”历史目光的发展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正史之外民间生活世界的真实存在。
所谓“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7],意在从百姓日常生活中去发现“道”“日用”之中,“日”为时间观念,是为常态化的生活;“用”为价值判断,是为实用性的选择。衣、食、住、行既是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也是艺术化生活的基础源泉。“百姓日用”本身便交织着人情世故,与人性欲望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日常人生中显现的良知良能以“道”的观念高度肯定。当下知识界习为贬义的“教化”一旦进入造物环节乃至宗教式语境中,“人”成为“日常”的制造者与体验者,原型道德观念借助人个体存在的意识成为凝聚在人手造物中的修养实体。“一件器物就是无文字的圣书,所说的是皈依和奉献之道,也就是救助之教吧。在这复杂的现实世界,工艺是了解美的最佳场所,就是最底层的凡人也会被救助之手所引渡。”[8]“教化”也就成为“日用物”中“日常”时代精神的艺术形塑,成为人生意义的光彩灌注,这也是“被救助之手所引渡”的手艺禅心所在。
物世与人世。如果说《手艺与禅心》是要写“清安空宁”的手艺与手艺人们“我看到的他们身上的禅心”[9],其核心依然难脱寓世情于物的“人心”。且向深思,则人心为意,意化为象,生发“意象”交诞的万千物形,依物性勾画物形,做成实物,复归日常生活审美需要,形成“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交相辉映。“物的世界”因人心的“活泼”而同样“活泼泼”,而生机勃发。“人的世界”因物态的亲近而成为体贴的人世。
器物来源于人的生产生活实践,器物之美同源于此。物是自然所生,但人造的器物同样是宇宙间的一部分。人造之物世本属无,然而有人世则有此物世。物世本是人世,人世映现物世,造物人则有事,事、物在人的主体参与中形成息息相关的客观世界,共同构成、体验、展现着“道”这一运动着的规律漩流。人既身心沉沐于中而不自觉,又能够自觉地感受、体悟、把握,在沉沐中施展实践积累的经验技能,在实践中总结造物的新经验,进一步提升造物及其物成中的“道”蕴之美。
日用与平常。在描写滇滕古纸时,浅草写出“湿漉漉的”纸张触感带动手艺的生命触感。在文明古国的文明典型中,古老造纸术本是文明生命的一部分,与手温契合的,自有无所不在的日用之心。无日用之“平常”,就没有天然的人生合度。“平常”成为日用器物之美的关键要素,附着于生命本体的“滋润”“亲和”成为内在的美感渴求。
进而思之,在工艺领域,“大传统”“小传统”实质直如贵族文化与平民文化,唯手艺之物,贵族平民,各有用度。平民有“日用”,贵族亦有“日用”,“平常”日用即是跨越阶层,即是一代代人生逐步形成,由之而生的手艺之作亦存固定的形态,越是基础性的“平常”的变迁,越是思维模型的动基改变,越是具有全盘性的重大历史文化生活改变。能够导致“文化传统的变迁”的器物细节之变对应思维方式之变,是日用之道,常应天心,展示出美感把握中實用理性对于规律性的深入感悟之美。大道万千,会晤多途,工艺之道展示出的,正是“凡夫俗子”所能体味的生活日用之美,“蔑视凡庸、尊重异常器物的看法已是次要的了。无事、平常,即谓之淳朴的自然的境地”。貌似微小同质的生命集结起来,汇化人世之大美。这种美,生于生活之沃壤洪流,归于广土之众民心魂。
二、手上功夫本“无心”
技与艺。《手艺与禅心》广罗建水陶、越窑青瓷、斫琴、翡翠雕刻、核雕、海派旗袍、缂丝、瓷胎竹编、折扇制作、龚扇(竹丝团扇)、银匠、乌铜走银、个旧锡器、滇滕古纸、团扇、紫砂壶、桃花坞年画、精细竹编、苏绣、玉雕计二十种我国传统手艺并持艺者生涯。“手工技艺至少包括技能、技巧和技术三部分。技能是身体的协调性和加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熟练度,技巧是解决问题或形成个人风格的诀窍,技术包括工艺流程、工艺法则、实体性工具等。显然,这三部分内容中技能是因人而异的,易变的,具有较强的体验性特点。技能高的人能出神入化,达到艺术境界,但技能不可传,全靠个人修为,它也就无法成为‘共享性技术。技巧虽然多少带着体验性,但它与技术类似,本质是相对客观的,比较容易量化,或加以口头、文字和数据描述。”[10]手艺内涵之“技”的三个层次如写作与创作之分,唯有习技臻于圆熟,方能呈现意象。技巧之美于反复形成的量化之美中升华,为从量变到质变提供了从技到艺的契机概率。
以细节展现价值判断,展现手艺胜处,是《手艺与禅心》的特出。工艺的创新进步,成为匠人内在的生命突破。“技”与“艺”,凝结在手上功夫,以手而成艺,呈现大千世界纷繁意象,隐藏着人世整体的心态。技熟于心,而忘技,遂成为艺,成为呈现自然人文之美的创造性的产物,就已隐含了规律性的“道”。含道之器物,将富于秩序的人世自然规律纳入造物过程中,材料分解,造型出新,物得以开启先天的材质而成为可“用”之器。从“技术”的进展,到“技巧”的揣摩研析,到熟能生巧,塑造器物的过程仿佛人的自我塑造,融合了匠人生活、创造的身心。技成于艺,则技不自觉中拥有了生命,一代代传承中,技自行成长,与“造物”的人构成互为体用的辩证双方。连绵于有涯之生,也构建了万物采用、百技化艺的人类手工艺世界。
思与作。手艺出自人生,却必须面向有情无情的自然万物,所谓“有情”,在人心自处。所谓“无情”,在物我未连接时,客观世界自成天理循环的系统。老子谓“朴散为器”,通俗言之,“诗文是由单字、单词组成;布帛只有通过裁剪才能做出美丽的服装;一根完整的木头,只有分割成碎板,才能做成家具”。[11]将自然赋予的物质材料分析、解剖、打散、重组,将原有材料的自然“完整”化为人生命赋予的新的“完整”,赋予其另一种自然性,这是人化、微观的“改造自然”“人化自然”与“微观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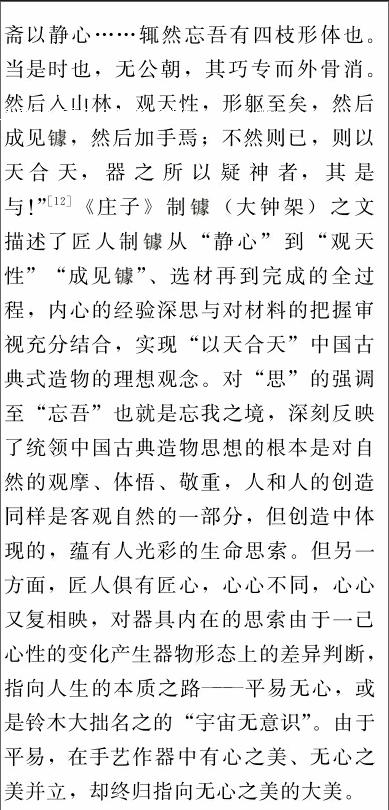
心与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3]器、道相对相应,形成了中国古典哲学的重大命题。道器之辩并非本文的中心关切,但对待器的精神态度,实质上是对待物的超越性思考。“器观念从情感载具逐渐泛化为实用物品,既赋予精神意味而得到重视,又因其特定功用而受到贬抑。”[14]器物与利益、制度、阶层、日用的结合,造成了器物文化与人类文明的诸多结合点,为手艺从世俗物质层面向传达人类内心抽象观念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物与人、物欲与人性、自然品性与文化人性等重大命题蕴含其中。人作为具体的感性存在物,从观念系统的“心”之角度出发,需要借助形象化的媒介展现人生之存在。金玉—君子,日用—平实,器物比德,德注器宇,在实用性功能基础上器物实现了由形式美到精神意蕴、由生理快感到心理快感的升华。道德源于人心,心,既是手艺成为审美客体的源泉,又是审美主体的根本。机械工业制品也反映设计者的灵感、理念,但机械复制制造万千产品,常现一二人之心。手艺特别是注入审美意识的手艺,则具有强烈的创造性与自发性,体现出自然造化的人器合一,成为自然生发万物的一分子。手工造物是一整体行为,与人生内在的存在意识息息相关,成为一种包含生活智慧、做人态度和生活习俗等人文品质的内化。心物之间,在时代文化的大势下以心能驱动审别物质、度量形制、构具品质,是人这一创造性生命在综合自然他生命的特出造就新事物的创造过程,透露出人生旨趣的利生利身之美。
“手是最直接、最人性的力量,是人将自己同外界联结统一的‘枢纽。手创造物品的能力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15]手与物的交感体验,手以技能驾驭造物,体现出劳动的创造之美与人智之灵。手艺造物中,“手”之“琢磨”斫削的作器过程,反映着人生生存之道。手为人身最活跃器官,是人以手艺造物的主要媒介。文化演变至今,成为人类灵性的象征。造物过程中,“对成功的劳动、对被掌握和使用的对象的愉悦必然会引起快感,其中无疑包含了出于萌芽状态的、我们所说审美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的提高”。[16]無论古之比德抑或今之比德,无论君子之貌抑或日用之心,手艺作器从器质走向制度,再走向观念文化,呈现出审美经验向人自身之美或言主体之美的转化。在心手共鸣的乐章中,打通生命通道既赖于人与天理人世呼应,也在身心合一甚至脱落身心。
三、器物美学的生命温情
今昔交映之美。对手艺人生命故事的书写与内在坚守的刻画,是《手艺与禅心》的突出亮点。书写器物的三重生命层次———器物自身的命运与使用价值,造物的手艺人习艺、成艺、守艺、化艺等生命的故事,使用器物的人在器物中凝聚的往事记忆,就是书写器物凝聚的时光交错之美。器用之具,从汉唐浑厚富丽至宋代淳朴纤秀,再到明代典雅质朴[17],凝聚着时代历史的审美风貌,为器具的时空审美提供了丰厚的样式基础。在不同领域劳作的匠人面向世界、祖国与古老历史文化遗存,脑海中的图案、现实中的选择、个人心性的喜好,使得手艺成为隐形的文明寄存,刻载着今昔生命的超越。
人生有尽,乐声无涯,在生命的重建、存在的重建中,生命实现了超越。超越成为人性本质的生成,又不断开启重建着人存在的尊严。《手艺与禅心》陈述着在忘我中人存在的自我意义。“在各种粗糙的用具上,也蕴藏着多少岁月、多少艰辛的劳动以及单调而反复的成熟。”[18]反复的劳作实践,既是匠人个体肉身存在的物质来源,也在反复中借助技能的提升寻求着自我存在价值的实现。器物一旦成型,激发着使用者、欣赏者与创作者心灵上的碰撞,器物在此又成为人这一认知主体间沟通的桥梁,散发出纵穿时空通道的超越今世之美。道、技、器,三者交复涵结,纵化为矫健飞腾的生命纽带,以心志的激活,理性的切入,借助器物审美信息解码的重构,展现岁月静好的时空秩序超越之美、普遍之美,是理解手艺及器物之美的历史性关键。
日用人情之美。柳宗悦将器物之美总结为实用之美、秩序之美、道德之美,单纯之美,健康之美,信仰之美。浅草则走上了与盐野米松相似的寻访之路,以更为具体的手艺人生展现道、技、器、人四者间的潜移默汇。二十种人生汇聚二十种手艺,人世沧桑中直指手艺之心的,是日用人情之美。《手艺与禅心》中写家庭之爱,行走之艰,故乡之恋,将人间情注入手间器,处处都是乡路风光。日用,成为家人相聚时情感符码的代寄。器具,成为匠人生命意志真挚的贯注。日用器具所在,在千家万户,烟火人生。器具外形固重,但结实耐用、材质过硬、手艺精巧,是日用中实用之美的关键。而在日用人情中,唤起的是共生存在的禅心厚意。
人生形态各异,美之价值判断各异,如鲁迅先生言,贾府里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19]。只有那种真正进入自家生命之中的经历才能配成为体验以及相同意义上的体会、体察、体证、体味等一类堪称是深入骨髓的内在经验[20]。千万日用中集结抽离出来的朴实精神,是天行健的人间活力所在。唯此朴实,是大道所在。质、形、色、纹绽放着日用自然之华,透射出无念为念的人情朴实之美,散发出与自然境界呼吸与共的禅意。情唯真而珍,艺以真而贵。在因地制宜、情意合度的前提下,人、物在天地生化中交换着情感信息,外向的知识之道与内向的纯真之眼,不能不借助日用人情而凝结出更易为人把握的仁心超越。
故土本质之美。故乡或曰本土,在东亚式的儒家语境下具有独特的审美含义。漫长的农耕文明奠定着安土重迁的思维方式,也生长出高度秩序化的伦理系统、礼仪传统、宗族意识与乡土人情。人的生物性需要是复杂的,在物质需求外还包含了多样化的情感需要。现代人对手艺的生命温情,其文化基因或言情感基因成长在对土地、历史的自我世界与消逝的往日时光里。手艺器物综合了日常生活的历史、人情与日用要素,所谓“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与地方的出产特质结合起来,形成了特殊、广阔、多样的表现空间。自然差异赋予了参差错落的地方手艺形态,它既具“本土知识体系”[21]的现实意义,又饱含本土天然赋予的、代代传承的材料、造型、风韵以及集于一体的人生情感之美。
故乡是出生地和养育地。故乡于手艺之所以如此珍贵,不仅仅因为器物价值凝聚的实用体验,不仅仅因为个人、家庭之爱在器物情感的寄托。手艺造物、器物流传的过程,涵盖着乡土社会中人情往还的传统空间。这是一个更为接近或言更为体现人生“本质”的情感空间。太湖镇湖镇上的绣娘们“称刺绣为‘做生活,是女性贴补家用的基本方式,刺绣做得怎么样,跟相亲嫁人都有很大关系,手工最好的那一批可以刺绣为职业,免去农活之苦,受人尊敬。多少年来,镇湖镇上的女孩子都会或早或晚地拿起针线来,在穿针引线中成长,变成母亲、祖母,又以各种方式教女儿、孙女拿起针线……”[22]在造物与易物的时刻,亲族、朋友、师徒、主顾,业缘得以交流,主顾信任合作,人际交往、信息集散交流,人与人在共同完成器物自产生而使用的全过程,手艺是“生活本能”,承载着沟通、关系、润和的社会功能,成为乡情物化情感体验的重要维系。
四、结语
在以道贬器的时代,手艺成为百姓日用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在机械工业时代,传统手艺反成为现代人文知识者关注、欣赏的审美主题。人生人世是如此矛盾的年代,接受、欣赏主体的变化验证着时代变迁。毋庸讳言,对手作及器物的人文关怀,洋溢着研究者、爱好者面向传统、发掘手艺之美的热情,也容纳着现代社会种种压力下转向一己内心求索的“沉浸”甚或逃避。但无论如何,那些关注本土、保护传统的努力,其愿望是“要体现的是脚下的文化———日常的文化,作为生活和城市记忆、哪怕是昨天的记忆的历史文化;本设计所要表现的是野草之美,平常之美,那些被遗忘、被鄙视、被践踏的人、事和自然之物的美”。[23]关注的起点已经决定了,用耐心和汗水编织的“澄怀格物”也许在后工业时代的语境下将无可避免地走向工艺的高端化,但其“平常心”的起点已满含禅意。“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心知肚明,做到了怀抱追求与守护清净有多了不起。”[24]手动,心静,动静在手艺器物间,进而获得一点禅心的清宁,或是华美的愿望,或是平常的共祈。
注释
[1][日]盐野米松:《留住手艺》,英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2]浅草:《手艺与禅心:寻找中国匠人之旅》,文汇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页。
[3]同[2],第1页。
[4]周振甫譯注:《周易译注·系辞传下》,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61页。
[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先进第十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3页。
[6](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二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70页。
[7]王艮:《王心斋全集·语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8][日]柳宗悦:《工艺之道》,徐艺乙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9]同[2],第3页。
[10]廖明君、邱春林:《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变迁———邱春林博士访谈录》,《民族艺术》2010年第2期,第21页。
[11]姜今:《散朴篇》,见: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研究会编:《工艺文化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12]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达生篇》(最新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68页。
[13]周振甫译注:《周易译注·系辞传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50页。
[14]周瑾:《道器交济:形而上下之中》,《中国文化》第四十一期,第60页。
[15]鲍懿喜:《手工艺:一种具有文化意义的生产力量》,《美术观察》2014年第11期,第13页。
[16][匈]乔治·卢卡契:《审美特性》(第一卷),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
[17]王家年:《士人·家具·境界》,《中华建设》2013年第1期,第62页。
[18][日]柳宗悦:《民艺四十年》,石建中、张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页。
[19]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见《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20]杜维明:《魏晋玄学中的体验思想》,《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7—213页。
[21]杭间:《手艺的思想》,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22]同[2],第242页。
[23]俞孔坚:《足下的文化与野草之美》,见孔祥伟、李有为编:《以土地的名义:俞孔坚与“土人景观”》,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72页。
[24]同[2],第2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