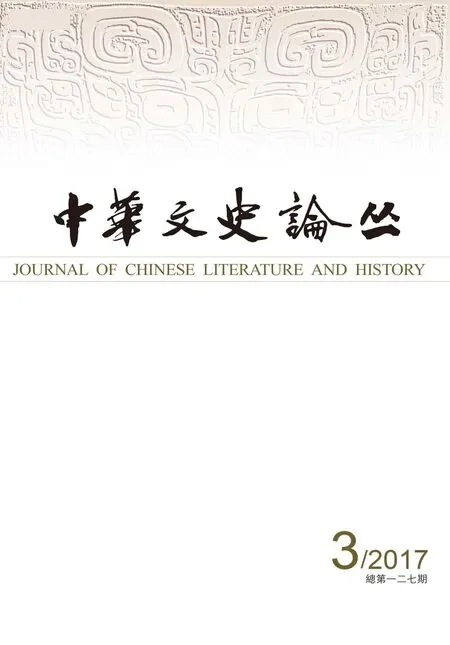從王通《續六經》到貞觀、開元的改撰《禮記》❋
——隋唐之際經典意識的變化
2017-07-24吴麗娱
吴麗娱
提要: 隋唐之際是思想變革的時代。本文通過《中説》一書討論隋王通《續六經》的思想理念,論證其書對於貞觀、開元“改撰”經典的啓發。認爲王通的《續六經》是試圖創建中古正統和打造帝王之道的時代新篇章,不僅影響了貞觀之治,也帶動了隋唐之初的疑經改經之風,引發了諸多經學爭議和禮制改革,促進了新經典的出籠和經典意識的變化;並認爲從貞觀、開元的“改撰《禮記》”,甚至直至中晚唐之際的“新《春秋》學”,都可以從王通的論述中發現其思想淵源,如此三者相續,構成隋唐思想變革的主線,此爲研究中古思想史不可忽略,且有待深入的一個論題。
關鍵詞:《中説》 《續六經》 《類禮》 《類禮義疏》 改撰 經典意識
文中子王通是隋代著名大儒,相傳曾講學於河汾,著有《續六經》等。王通自宋代起就是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在古今中外的評論和研究中,質疑其人其事者有之,論説其思想、學術者亦有之。*研究論著如尹協理、魏明《王通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駱建人《文中子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鄧小軍《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李小成《文中子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按關於王通的歷代評議及論著,參見李小成《文中子考論》。然而語及文中子,有一個現象卻不得不注意,這就是其著作公然自稱爲“經”,而本人也竟敢上擬周、孔,以“聖人”自居。對如此僭經擬聖的做法,歷代不乏譏評。如宋人張洎的《賈氏談録》即載如下一則:
(唐)劉蕡精於儒術,讀《文中子》,忿而言曰:“才非殆庶,擬上聖述作,不亦過乎?”客或問曰:“文中子於六籍如何?”蕡曰:“若人望人,文中子於六籍猶奴婢之於郎主爾。”後遂以文中子爲六籍奴婢。*張洎《賈氏談録》,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36册,頁130下。按此則也見於錢易《南部新書》戊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63。
此中劉蕡其人對王通“擬上聖述作”的憤慨躍然紙上,而“六籍奴婢”之稱亦足見對王通之作的貶斥和不以爲然。宋人司馬光、晁公武乃至清人章學誠亦無不指責王通好大欺愚、模擬竄竊,對之大加撻伐;*司馬光《文中子補傳》,邵博《邵氏聞見後録》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0;晁公武撰,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一《儒家類·阮逸注〈中説〉十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443—444;章學誠著,葉瑛《文史通義校注》卷一《内篇一·經解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10,112。按批評者論議甚多,不具引,參見駱建人《文中子研究》第一章《傳論》,頁19—24。當然也有很多人並不認同,如明崔銑、高拱、近人章太炎駁僭經説均甚力。*參見崔銑《中説考·序》,《續修四庫全書》,9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487下。高拱《本語》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49册,頁828下—829上。章太炎撰,龐俊、郭誠永《國故論衡疏證》卷中,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76—290;參駱建人《文中子研究》,頁22—24。不過無論贊成與否,令人深思的卻是王通這類做法的出現和影響。繼王通之後,唐貞觀、開元中,又出現了企圖“改撰《禮記》”的呼聲和《類禮》(也稱“《次禮記》”)之類新編經典的創作。“改撰”無疑也是要重新打造經典,這使人不能不注意到王通的思想及其開創之功。
與王通研究有關,任繼愈《中國哲學發展史》曾於隋唐卷的《儒學編》給其學説以“新經學”的定位,並闢專章予以論述,*見《中國哲學發展史·隋唐卷·儒教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7—54。李小成關於文中子也言其創造“新儒學”是要“直承周孔之道,走出一條不同於詮釋經學的道路”。*李小成《文中子考論》第五章第三節《南北之學與文中子的新儒學》,頁143。祝總斌先生不久前撰文,提出王通著作所體現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對中唐韓愈大力提倡的道統以及宋儒相關創建的應有啓發和影響。*祝總斌《關於王通的〈續六經〉與〈中説〉》,《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2期,頁283—285。李偉更是將王通在宋代儒學道統中地位提升與韓愈、李翱的並稱及北宋古文發展的趨勢聯繫起來。*李偉《從“韓”、“李”並稱看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古文發展的趨勢——兼論王通在儒學道統中地位提升的原因》,《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第2期,頁287—312。其他中外學者關於王通其人及思想傳承也有很多研究,考察事迹之外,内中不少也談到王通與韓愈及宋學的關係。*錢穆《讀王通〈中説〉》,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頁1—17。市川本太郎《隋の大儒文中子の思想》,《國士館大學人文學會紀要》第3號,1971年,頁199—237。吉川忠夫《文中子考——とくに東皐子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史林》第53卷2期,京都,1970年,頁87—120。Howard J. Wechsler “The Confucian Teacher Wang T’ung (584?-617): One Thousand Years of Controversy”, T’oungPao 63.4-5,1977,Leiden, pp.225-272。Ding Xiang Warner “Wang Tong an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Zhongshuo: A New Evaluation of the Source Materials and Points of Controvers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1.3, 2001, New Haven, pp.370-390. Jue Chen (陳珏), “History and Fiction in the Gujing Ji(Record of an Ancient Mirror)”,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55,2007, St. Augustin, Germany, pp.61-97.參見傅揚《王通、儒學和隋唐思想史》,《臺大歷史學報》第43期,2009年6月,頁269—276。談及與韓愈及宋學關係或評價,如岸田知子《文中子中説——成立についての思想史的考察》(木村英一博士頌壽記念事業會編《中國哲學史の展望と摸索》,東京,創文社,1976年,頁461—475;池田恭哉《王通と〈中説〉の受容と評價——その時代的な變遷をたどって——》,《東方學》第128期,2014年。
但是,就王通思想影響儒學發展而言,畢竟需有長期的過程。而隋及唐初,也包括唐前期在内的聯繫顯然是其中不可缺失的一個環節。那麽貞觀、開元的“改撰”之舉是否與王通的思想、理念有關?事涉隋唐之際經學思想變革的一樁公案,故本文擬從“改撰”出發,嘗試將其中的脈絡和内涵梳理清楚。
一 引子——“改撰《禮記》”的説法與來源
“改撰”一詞,始見於《開元禮》制作之初,這就是通事舍人王喦建議用“改撰《禮記》”之法:“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但宰相張説則反對,提出“折衷”已有的《貞觀》、《顯慶》二禮,從而爲《開元禮》的制作定下了基調。*《舊唐書》卷二一《禮儀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818。筆者有文論及於此,認爲理解“折衷”一詞,是認識《開元禮》制作的關鍵,並因此討論了《開元禮》一書對於五方帝的處理,以及相關禮制與經學的關係問題。*吴麗娱《從經學的折衷到禮制的折衷——由〈開元禮〉五方帝問題所想到的》,待刊。但現在看來,還有一點也應當明確,即所謂折衷與“改撰”並非風馬牛不相及。以往的研究已證明,折衷而成的《開元禮》中,並不是没有“改撰”舊禮制的成分,而最初所見的“改撰”,亦並不完全是針對《開元禮》,而是直奔《禮記》經典本身。
《舊唐書·元行沖傳》曰:
初,有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遽令行沖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沖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開元)十四年(726)八月奏上之。尚書左丞相張説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録,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絶,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於是賜行沖等絹二百匹,留其書貯於内府,竟不得立於學官。行沖恚諸儒排己,退而著論以自釋,名曰《釋疑》。*《舊唐書》卷一二,頁3178。
又《唐會要·修撰》有曰:
(貞觀)十四年(640)五月二十一日,詔以特進魏徵所撰《類禮》賜皇太子及諸王,並藏本於秘府。初,徵以《禮經》遭秦滅學,戴聖編之,條流不次,乃删其所説,以類相從,爲五十篇,合二十卷。上善之,賜物一千段。*《唐會要》卷三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759。
兩處史料説明,先是曹魏孫炎已經改變了《禮記》舊本,按類抄書。貞觀中魏徵又根據孫炎本加以整理,並增添注文,謂之《類禮》,其書删掉了戴聖《禮記》的一些内容,予以簡化且“以類相從”。元行沖再解魏徵之注,是又於注上加疏。至於王喦要求《開元禮》削去《禮記》舊文,顯然是在元行沖疏的基礎之上更進一步。據《唐會要·論經義》,“太子賓客元行沖等,撰《禮記義疏》五十卷成”的時間是開元十四年(726)八月六日,*《唐會要》卷七七《貢舉下·論經義》,頁1667,下引文見頁1668。按《禮記義疏》即“《類禮義疏》”。應在討論《開元禮》撰作的同時或稍前。《會要》所載撰疏經過及疏成,遭到張説反對,“上然其奏,遂留其書,貯於内府,竟不得立學”,亦與《舊唐書》説法一致。今見《新唐書·藝文志一》有“魏徵《次禮記》二十卷(亦曰《類禮》)”,和元行沖“《類禮義疏》五十卷”前後相從,*《新唐書》卷五七,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434。特别示出了二者關係。由是推知王喦要求削去《禮記》舊文而以新事編之,是在元行沖上書同時或稍後,且因元行沖書而言之,兩事一而二、二而一,故都以張説反對的話爲告終。
經典的注疏,唐以前有多家,經學在私家傳授的基礎上形成了不同的家學門派。南北朝義疏學十分發達。隋及唐初以後,舊義疏學日漸衰落,特别在孔穎達領撰《五經正義》之後,對經典的解釋南北一統,定於一尊,加之科舉的配合,舊義疏學已無存留的餘地。但經學並非像人們以往所認爲的就此停滯不前,毫無發展。魏徵《類禮》、元行沖《類禮義疏》顯然不再遵循和隸屬舊義疏學的傳統範疇,也已不再受其思想束縛。因爲他們不打算再遵循家學規範,也不再跟從前人的章句訓詁亦步亦趨,照元行沖的話説就是所謂“修古義則非章句内學”的“變易章句”者。他們的新著顯然是要摒棄前人專重章句訓詁的舊義疏學,從而追求經典本意,直達古人的原始精神和境界。臺灣學者林慶彰先生指出,唐中期至北宋是“回歸原典”的一個活躍時期,*林慶彰《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中國文化》2009年第2期(總第30期),頁1—9。但從這裏看其源頭還要更早。既要修古義、變異章句就包括對經典内容意義的重新認識和發揮,甚至改寫,由此或賦予新的、時代的理解,或另行建構新篇章,這也是爲何王喦能提出削去《禮記》舊文,而以新事編之的原因。關於這一點,還可見下文的具體論述。
魏徵作《類禮》自然是元行沖和王喦“改撰”《禮記》思想的來源。但是對經典加以改造或者重編是不是自魏徵開始,魏徵又受到何種啓發要這樣做呢?上文説到魏徵是在曹魏孫炎基礎上修改加注,但孫炎師學鄭門,今史料中存留關於他的記載都是對經文字義的解釋。而他所改的《禮記》注本不過是“以類相比,有同抄書”,並没有什麽實質性的變異,所以如果説改撰自他始,未免有些牽强。且二人相隔數百年,魏徵除了用他的底本外,很難扯上太多關係。據元行沖説:“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伷增革,向逾百篇;葉遵删修,僅全十二。魏公病羣言之錯雜,紬衆説之精深。”*《舊唐書》卷一二《元行沖傳》,頁3179。可見孫炎之後,還有人試圖對《禮記》加以整編,而魏徵則是在此基礎上,對衆多錯雜的説法加以批判,而尋求經典中精深禮義的正解。所以如果就真正“改撰”的意義來説,魏徵本人也不能算是發明之祖,事實上對他有重大影響的應當還另有其人,而談及這一點,則撰作《續六經》而被稱作文中子的王通便不能不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王通事迹見於《新唐書·王績傳》:“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仿古作《六經》,又爲《中説》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説》獨傳。”*《新唐書》卷一九六《隱逸傳·王績》,頁5594。據説唐初的一些重臣都是他的學生。宋人阮逸於《文中子中説序》評論説:“若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魏(徵)、二温(大雅、彦博)、王(珪)、陳(叔達)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阮逸《文中子中説序》,張沛《中説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這裏没有提到的還有竇威、薛收、杜淹等人。諸人包括魏徵與王通的交往、對話都見於《中説》。晚唐皮日休在所撰《文中子傳》中,稱王通“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皮日休《文中子碑》,《唐文粹》卷五一,四部叢刊縮印本,409册,頁368下。似乎也意識到王通思想對貞觀之治及治國者的影響。但是唐朝重臣是否多師從王通,能證明的材料很少,對王通《續六經》和《中説》一書,前人已提出不少質疑。而如司馬光,雖在《資治通鑑》中簡要記録了王通向隋文帝獻策及教學諸事,*《資治通鑑》卷一七九隋文帝仁壽三年(603),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5599。但仍於所作《文中子補傳》中,提出《中説》是在唐室既興之後,由通弟王凝與通子福畤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邵氏聞見後録》卷四,頁31。這一説法也被後來的學者所接受。*王冀民、王素《文中子辨》,《文史》第20輯,1983年,頁231—249。同類文章並見徐朔方《王通門人辨疑》,《浙江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段熙仲《王通王凝資料正訛》,《文史》第27輯,1986年,頁323—326。
不過筆者以爲,追求個性真實之外或更應當注重陳寅恪先生所説的通性真實問題。對於《中説》其書與王通事迹的懷疑,似乎不能成爲否定或者無視王通思想的理由。如仔細比對《中説》所論,不難發現其中所論並非無的放矢,尤其關於國家正統、政治改革的論説立意深刻,邏輯嚴密,自成體系,很難認爲是由他人拼湊而成。如從中發掘,還是能爲王通本人的不凡造詣提供依據。更何況王通講學實有其事,“續命河汾”弦歌不輟,“但開風氣不爲師”爲古今所稱頌。*龔自珍《己亥雜詩》,《龔自珍己亥雜詩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45;並參陳寅恪《贈蔣秉南序》,氏著《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62。因此王通事迹雖或有疑,但他曾通過教授學生傳播思想並不是無迹可尋。基於此,本文不欲再糾纏於王通具體事迹的有無確否,而是試圖通過《中説》的相關記載,分析其《續六經》之作與唐貞觀、開元“改撰”經典之關係,以證明他對唐初思想的啓發。
二 《中説》的意義與王通的《續六經》制作
唐以降記述文中子的論著不多,今《續六經》已散佚,某些現存本如《元經》多被指爲僞作,故研究文中子創作及其思想,比較集中的就只能是《中説》一書了。《中説》乃仿《論語》之作。據阮逸言“《中説》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阮逸《文中子中説序》,張沛《中説校注》,頁1。書中弟子們仿照孔子的稱謂直接稱王通爲“子”,其書性質和師生問答形式也頗類《論語》。阮逸並解書名之義曰:
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虚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説”者,如是而已。*《文中子中説序》,頁3。
二五、權衡、皇極、中庸都是經典中稱説中道的用語,而經典所言“中”也是事物處理、存在的適中之度和最合理狀態。“中”“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是符合規律性的認識,故能夠適應變化,順從道義,這也是《中説》一書所要宣揚的主旨。所以其弟子董常説:“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中説校注》卷八《魏相》,頁207。一切歸於大中,“中”的意念集中代表了王通的思想精髓。近人謝無量所謂“文中子學説,以執中爲要,故其書曰《中説》”。*謝無量《中國哲學史》,上海,中華書局,1916年,頁46。駱建人《文中子研究》也指出:“文中子之思想,蓋以中庸爲本,皇極爲歸,故《中説》一書,大中至重。”*駱建人《文中子研究》乙編第一章第三節《大中》,頁114。此一意念也見於王通論繼承周公、孔子之道:
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中説校注》卷二《天地》,頁58。
王通認爲自己是“紹宣尼之業”的當然繼承人。對於所説“折中”,阮逸解作“無位則修,而取中焉”。校注者張沛則進一步解釋説:“取正,以爲準則。《史記·孔子世家》:‘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將“中”或“折中”作爲經學最高標準或者至上境界,也見於文中子的其他論議。如《中説》記“子謂叔恬(王凝)曰”:“《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也。”阮逸釋“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之,皆約歸中道”。*《中説校注》卷三《事君》,頁85。又其論帝制説:“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中説校注》卷四《周公》,頁121。又如“子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中説校注》卷一《關朗》,頁253。
所以“中”或中道如就經學理論而言,實際上是代表着某種權衡之下的適度選擇,而執中、折中則包含着對錯誤的修改和糾正。堅持中道常常意味不守舊,而是面對新形勢、新變化采取一種新、故結合的原則。我們從《開元禮》的制作中可以看到這種努力,而王通的學説也是如此。雖然從《中説》一書中可以見到他對《六經》的師法,以及對三綱五常原則的遵循和强調,但是《續六經》顯然不是對古《六經》的重述或者單純解説。可以知道的是王通曾有“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的批評。他並且提出:“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中説校注》卷二《天地》,頁63—64。關於“九師興”阮逸注謂:“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可見他認爲由於各種學説黑白混淆、是非不分攪亂了正道,古《六經》反而由於文字殘毁及意見紛紜而導致了經文本身的流失或散落,對於以往的注疏,看來也是評價不高的。既不高就不會直接沿襲,更不會止步於前人論説而專究古典,通過以下的問答即可以了解王通《續六經》的宗旨:
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中説校注》卷六《禮樂》,頁165—166。
這裏的“續”《六經》,惟有《易》稱爲“贊”,而《詩》、《書》、《元經》、《禮》、《樂》分别稱爲“續”、“修”、“正”,既稱爲“續”、“修”、“正”,就不會不增不改,因而《續六經》當然不是古本《六經》的重複。而從其宗旨來看,也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通過“修”、“正”等不無糾正先儒釋經甚至經本身之意;二是除“申先師之旨”外,“存漢、晉之實”、“辯六代之俗”、“斷南北之疑”、“旌後王之失”等都明謂《六經》的内容是完全脱離了上古三代,真正以後世的治政興衰爲中心。其中“六代”用阮逸的解釋就是“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可知《續六經》關心旨在兩漢以降的中古,與前《六經》産生時代在兩漢以前乃至處處以三代爲準完全不同。
至於《續六經》各書具體内容,前人已有簡要論述。*見前引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隋唐卷》,頁28—29。但牽涉其形式體例及針對用意,這裏仍有必要略加梳理。而若依照其寫作方式不同,大體可分兩類。其一類是《續詩》、《續書》和《元經》。先以《續詩》爲例:
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雅》也。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之風。二曰《政》,續《國風》。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移俗,猶易俗也。三曰《頌》,續《周》、《殷》、《魯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享於宗廟。四曰嘆,續變《風》、變《雅》。以陳誨立誡於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嘆之,所以吟詠於家,諷刺其上,使達此變,以懷舊俗也。凡此四者,或美焉,嘉美之。或勉焉,無足嘉,則勉之。或傷焉,勉不得,則傷之。或惡焉,不足傷,則惡也。或誡焉,語他事,使聞之自誡。是謂五志。”*《中説校注》卷三《事君》,頁84—85。小字爲阮逸注。下同。
《續詩》的“四名”取代了《風》、《雅》、《頌》,但形式用意無差。文中子自言:“《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中説校注》卷三《事君》,頁85。而“五志”則表明其書作爲諷勸、抒情的用意也相同,所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中説校注》卷二《天地》,頁65—66。只是詩的時代變了。薛收明問文中子,“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而文中子回答是當“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中説校注》卷一《王道》,頁12。説明是纂集了晉宋至周隋的詩歌。文中子又言其《續詩》是“考諸《集記》”,此《集記》應即漢魏以來的前賢文集書記。*《中説校注》卷一《王道》,頁7。其各部分仿照《詩經》也自有用意,如説“《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中説校注》卷三《事君》,頁86。以“帝制”對“王澤”,《變風》、《變雅》乃示周室之没落,而《變化》、《變政》卻是因兩漢帝制之衰亡了。
又《續書》: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 曰制,制,命也。秦改命爲制,漢因之。曰詔,詔,令也。秦改令爲詔,漢因之。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而未形乎制詔者也。曰策,求直言而策慮之。大臣之義載於業者有七,曰命,爵命。曰訓,師訓。曰對,奏對。曰贊,襄贊。曰議,評議。曰誡,監誡。曰諫,箴諫。*《中説校注》卷四《周公》,頁120—121,下引王通語同。
衆所周知,《尚書》是由誥、訓、謨、誓、命、典等篇章組成的上古文獻和公文總集,《續書》在彙集典謨的意義上没有變化,只不過隨着時代的更替,改變和增加了文書的内容形式,但仍是刊録秦漢以後的君臣論説言事或公文典策。此即文中子所謂“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至於各種類型文書,也有不同的功用。如面對程元問叔恬的“《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回答是“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解釋“策”則是:“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命”則既是帝制時代君臣策畫的産物,也是王者君臨天下,自作天命的象徵。“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中説校注》卷五《問易》,頁129、130。
更值得一述的是模仿《春秋》的《元經》。《春秋》、《元經》在《中説》中往往並舉,兩者性質相類。所謂“《書》以辯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藴盡矣”。*《中説校注》卷八《魏相》,頁204。在諸經中《春秋》、《元經》負責“舉往”。“舉往”不僅是反映史事,更須將褒貶寄寓其間。按文中子的説法,《春秋》的意義乃使“邪正之迹明”,*《中説校注》卷一《王道》,頁8—9。《元經》自亦不例外。《元經》的紀事始於晉武帝去世、惠帝即位的太熙元年(290),包括前揭晉隋六代。王通認爲太熙是帝制被破壞之始,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中説校注》卷九《立命》,頁245。一無實權,所謂“帝之不帝久矣”,*《中説校注》卷六《禮樂》,頁154。故有“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興乎”的感嘆。當薛收問及“始於晉惠,何也”,王通以“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作答。*《中説校注》卷一《王道》,頁12。説明像《春秋》年代始於周平王、魯隱公一樣,《元經》始於太熙,也是爲了對不受帝王支配的亂世承擔褒貶之責,不過它所記述或評論的史事已經與《春秋》毫無關係了。
今存世本《元經》卷首薛收《元經原序》也引文中子稱“《春秋》,一國之書也”,“《元經》,天下之書也”及其關於正帝位和天命所歸的議論,*題王通撰,薛收傳,阮逸注《元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03册,頁831上。所引王通言並見《中説校注》卷八《魏相》,頁207,209。證明《元經》像《春秋》尊崇周天子權威一樣,是爲了明確皇帝時代天下正統之所在。今本雖被疑爲阮逸僞作,然至少體現書之原意。全書模仿《春秋》編年紀事,内有經有傳,傳題爲薛收作,對經所言事件或事物作出説明,證明經所取史料用意。所以正如論者所言,作爲史書《元經》並無多少特色和發明,但文中子著《元經》並不是真正想作一部純粹的史書,而是要用史事表達和傳遞一種正統的觀念。*李小成《文中子考論》第六章《〈元經〉真僞考》,引文見頁162。總之雖然存本的真僞不易斷定,但我們還是能從中了解《元經》的良苦用心。
以上三書,大抵是依照原來的經書形式體例,塞入後世的内容篇章,雖名爲經,但視野及内容所涉皆在中古。
另一類即《贊易》與《禮論》、《樂論》三書。*名見董常所言,《中説校注》卷八《魏相》,頁205。此三書的特色更多在於議論。其中王通對《易》用“贊”字,論者指出即對《易》作出新的解釋。*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隋唐卷》,頁28。或認爲贊意即頌,是宗關氏學而與關朗的《關氏易傳》有關。*李小成《文中子考論》,頁202—204。《中説》有見其談論《易》理的内容,如:
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臧,我思不遠。’”*《中説校注》卷四《周公》,頁122。
這是討論如何領會《易經》精神,及時而動,用於現實。又如:“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也是同樣的意思。又如:“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又如:“子《贊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中説校注》卷五《問易》,頁143、144、145。也都是對《易經》義理本身的新見和發揮,因此可以想見“贊”就是對《易經》基本精神與含義的闡發,是一種融會貫通式的理解,也是對真正古義的追求。其目的在於用《易經》的哲學原理來解決、處理精神層面的現實問題。
至於《禮論》、《樂論》,則二名最早見於《荀子》之《禮論》、《樂論》,*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一三《禮論》、《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346,385。内容是關於禮、樂生成來源、作用、原則及意義的解釋和説明,總可謂論禮義、樂義耳。《隋書·經籍志一》載有戴聖撰《石渠禮論》四卷,並有宋何承天《禮論》,以及徐廣、庾蔚之、王儉、賀瑒等的《禮論要鈔》、《禮論鈔》、《禮論答問》、《禮答問》等書;此外並有梁武帝和衛尉少卿蕭吉各撰《樂論》。*《隋書》卷三二,北京,中華書局,頁923,926。《宋書·何承天傳》稱:“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删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宋書》卷六四《何承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711。由此可見《禮論》、《樂論》之類書大約早已有之,於南朝形成一種禮書特色或者門類。從今天所見佚文來看,《禮論》結合相關的“答問”,多是對某種禮儀制度或者觀點議論加以論述和答疑,其中多引諸禮家不同見解,因此所關注者仍是真正的“禮義”,而不在解釋經文表面文字。如此或者也可以説南朝在章句之學之外,已經發展出另外一條以説理和議論爲主的獨特解經之路。
王通的《禮論》看來與之不無共同之處。雖然從名稱看,具體論何禮不詳,但顯然亦不是在解讀文字、章句上下功夫。上引文中子有“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語。又其言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以上分見《中説校注》卷二《天地》,卷六《禮樂》,頁57,153。幾處都無一例外地用了“正”字。其中“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阮逸解釋爲“後王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禮樂可以不正”,解釋爲“《禮論》、《樂論》,所以正之”;“正失”則釋爲“正禮樂沿革之文而已”。如此即知道王通續《禮》、《樂》的着眼點,與他的前面三書一樣,仍然是在後世、後王,且亦屬議論。而既然是“正”,即包括了對禮樂的重新理解,和後世錯用禮樂的一些謬論的批判。如他對於後世封禪禮有“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誇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和“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的批評,*《中説校注》卷一《王道》,卷六《禮樂》,頁21,165。就是試圖以古禮義以匡正現實。
另外從現有材料可知文中子重視以古《周禮》爲原則:“子居家,不暫舍《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中説校注》卷八《魏相》,頁208。可見是主張以《周禮》精神助興“王道”。他强調“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又指出“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向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辯上下,定民志”。*《中説校注》卷六《禮樂》,頁164。意謂治政必須與教化並行,而禮尤體現聖明和中道,能辨定秩序,是王道興盛的至高境界。所以當房玄齡問事君、使人、化人之道均答之甚明,惟問禮樂,則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又認爲禮樂是世道平安、和諧的産物,“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中説校注》卷一《王道》,頁26。所以禮不可輕議。*此可見《中説校注》卷三《事君》:“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頁74。在日常生活中,王通也刻意遵守禮儀規範。“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中説校注》卷三《事君》,頁93。“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中説校注》卷六《禮樂》,頁161。這些也都是屬於以古禮經義指導現實的内容。
因此從《中説》的字裏行間中,可以體會到王通雖處處遵循傳統,但無論於國於家,於公於私,關切的還是如何將禮樂之作與現實應用相結合,是一種批判現實的態度。《禮論》、《樂論》重義理的原則和其他續經一致,與原來章句之學的路徑完全不同。有一事或者可以説明,即王通本人對大儒劉炫的態度。劉炫與劉焯號稱“二劉”,曾師從熊安生,是北朝著名的經學家。孔穎達《五經正義》中,《尚書》、《詩》、《左傳》三疏,均以劉焯、劉炫二家爲本。但王通與之顯然並不相得。《中説》其一處言:“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没身而已,況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説校注》卷五《問易》,頁127。此處明謂王通對劉炫自矜其《易》學無敵的誇誇其談不以爲然。
另一處則更爲明顯:
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中説校注》卷四《周公》,頁111。
劉炫談起《六經》滔滔不絶,這很符合原來北學重視章句,追根思源、務求廣博的特色,此或即史言“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隋書》卷七五《儒林傳》,頁1706。當然劉炫本人也有受南學影響,過分追求文辭華麗的問題。孔穎達在《尚書正義序》中就批評過這一點。*孔穎達《尚書正義序》,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110。但從這裏看,王通對其學問的枝蔓繁瑣並不欣賞。他反對“榮華其言”,提倡學問“一以貫之”,可以知道所追求的確乎不是對各家義疏的熟稔和章句之學的淵博引用,也厭煩言語陳説的華麗繁複。唐長孺先生曾指出:“劉炫雖爲北人,卻屬於深染南學的經學大師,但王通對他仍重章句訓詁的治經方法不以爲然,表明王通的學風與北方的治經傳統相去更遠。”*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第四章第二節《學術思想》,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465。聯繫上述分析《禮論》重義理不重章句,我懷疑王通在學術上並不贊成北學,而受南學影響,或者説接受南學治學方式的成分較多。
前揭祝總斌先生文章提出王通學問重“道”與“德”是來源於《尚書》及僞孔傳,其學應受南方玄學系統之影響,而輕視“北學”章句訓詁,*祝總斌《關於王通的〈續六經〉與〈中説〉》,頁272—275,281—282。此或可爲祝先生的見解提供補充。不過在學派之外,王通似乎更重視對經學理念貫通性的認識和發揮,在於怎樣使之能與新的標準融合,對秦漢以後的帝制時代作出解釋和評價。且王通《禮論》(也包括《樂論》)很可能有諸多針對性的具體問題,其書(也包括《樂論》)的創新成分或更超過南朝的同類書目,而形成批判色彩更强而與時代並進的一種新學問。
綜上所述可以知道,《續六經》既稱爲“續”,形式、用意便與《六經》是相一致的。不過,它們既不是原上古經典的單純變體,内容也與《六經》没有太多關係。相反,在一定意義上,它們都可以説是“削去舊文,而以新事編之”。總之,《六經》於《續六經》雖有淵源,但後者不是前者的副産品,兩者完全不能看作是一回事。前人“新經學”的説法,可謂洞悉其思想内涵及時代底藴。從這個意義來説,《續六經》也可以説是對《六經》的“改撰”,它們是對古典原則的接受和具體内容的更新,是既舊且新、既古而“今”的新舊、古“今”結合體。進一步而言,本節最初所言文中子對中道的追求,也在經典的“改撰”中找到了落腳點。追求中道其實是追求變化,所以《續六經》可以説是通過“折衷(中)”、“改撰”修正古典,弘揚批判精神,無論它們最後的歷史評價是什麽,在當時的意義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 《續六經》的帝制正統觀與貞觀之治
《續六經》在形式、體例上完全取法《六經》,仿效之意甚明,但在内容上卻另闢天地。由於是討論王通著作與《類禮》的關係,我們必須知道《續六經》關心的對象、追求的目標是什麽。例如就《元經》而言,王通爲何對無人受理的六代史事並加褒貶,而以其“素王”之作承擔這一歷史評判之責呢?
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曆數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中説校注》卷一《關朗》,頁251。
《續書》、《元經》在文中子是知天命之書,“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無疑是他製作這兩部書的核心。其中“感帝制”一語可以説明帝制是王通最關心的命題。與帝制同時他也經常提到王道,有“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詩》《書》可以不續乎”的説法。*《中説校注》卷二《天地》,頁57。劉禹錫曾指出“在隋朝諸儒,惟通能明王道”。*《唐故宣歙池等州督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劉禹錫著,瞿蜕園《劉禹錫集箋證》卷三《碑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89。《中説》書首《王道》篇亦引其自語“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並述其六世祖江州府君以下之著作,相次爲《五經決録》、《政大論》、《政小論》、《皇極讜義》、《興衰要論》,一望即知無不關涉經世之論、帝王之業,故文中子言:“余小子獲睹成訓,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以上見《中説校注》卷一《王道》,頁4。表明所爲是受先人感召,而所謂王道或帝道就是其王氏一門數世所關懷和尊奉的中心。
那麽究竟何爲尊奉“王道”或“帝道”呢?此復見於其論《春秋》與《元經》:
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中説校注》卷八《魏相》,頁207。
中古世界是以皇帝爲中心。這裏所説“約諸侯以尊王政”和“徵天命以正帝位”,就是要建立帝王統治的權威,結合前文所述王通言“《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可以知道《元經》的期求首先就是要建立正確的帝位正統觀。
須知道這個帝位的正統觀並不完全以三代爲法。中古的王道即帝制,並不同於上古的“王道”,兩者的區分在王通曾特别予以强調:
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迹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薛收曰:“純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中説校注》卷五《問易》,頁140—141。
這裏王通指明帝制並非出自上古的王道,兩種帝王並非一個系統造就。後代帝王稱“帝”,與上古名同實異,已經没有了唐、虞三代“純懿”——單純美好的特質。但他不同意只有三代纔好,而是認爲事在人爲,帝道靠人道來發揚,“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將希望寄托於未來。
王通無疑是個現實主義者,從《中説》所見,他雖然稱頌周、孔,但並未動輒三代,所嚮往的也不完全是上古帝王的“純懿”之政。相反,就帝制而言,他最心儀的乃是兩漢。錢穆先生已談到其在政道治術上,不高慕唐虞三代,而惟寄情於兩漢,是不泥古而深通於時變者。*錢穆《讀王通〈中説〉》,頁11—12。其原因似乎不僅止於任繼愈書已指出兩漢“乃三代退而求其次”,還因秦的短命和殘暴使之被視爲中古皇帝制度的源頭。所以當薛收問及《續書》爲何始於漢的問題時,文中子的回答是“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中説校注》卷一《王道》,頁11。他又贊美兩漢政治,有“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舍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的評價。七制之主,即漢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七帝,認爲可與上古帝王相比:“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中説校注》卷二《天地》,頁56。王通稱美七制之主“有大功也”、“道斯盛矣”,*參見《中説校注》卷七《述史》,卷六《禮樂》,頁198,157。提出“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中説校注》卷一《關朗》,頁255—256。“舍兩漢,將安取制乎”?*《中説校注》卷五《問易》,頁133。認定兩漢之制纔是中古皇帝制度的楷模,是帝制時代已成就的基本軌範,拋棄兩漢,國家當無所適從。
當然在肯定兩漢制度之後,他還要面對中古國家曾經分裂的事實,樹立正統的旗幟,所謂“正歷數則斷南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中説校注》卷一《關朗》,卷六《禮樂》,頁251,165。也即《關朗》篇所説“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太熙已知是晉惠帝即位,皇始乃是後魏開國皇帝道武帝的年號。文中子是這樣定位道武帝所建北魏王朝的:
子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中説校注》卷五《問易》,頁149。
由原文及阮逸的注釋,我們很容易理解王通是將北魏視作正統而將中原作爲國土中心的,誰占據中原就是獲得了正統,這一點正是遵從其高祖晉陽穆公《政大論》的立場,也代表了王氏一族的“中國”觀。而北魏立國以前的晉、宋雖仍被作爲“正體”,但也只因當時中原無主,而且晉、宋還曾舉兵試圖統一中國。至於宋以後的齊、梁、陳在北魏已爲正統的情況下則被斥作“四夷”。特别由於孝文帝提倡漢制,完全實現了中華文化的代代相承,是爲正統的依據,北齊、北周則是當然的繼承者。這可以解釋爲何上文所言“六代”是晉、宋、後魏、北齊、後周和隋,也可以解釋何爲“尊中國而正皇始”。
與此同時,對於北魏大行漢化的孝文帝也給予如同兩漢“七制之主”那樣的評價。如説孝文帝“可與興化”,*《中説校注》卷二《天地》,頁68。又説“苻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中説校注》卷四《周公》,頁107。但他認爲尚不完美:“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中説校注》卷五《問易》,頁134。不得行穆公之道就是未能以中原爲中心建立統一的華夏帝國,但南北之“歷數”畢竟由此而定。相對而言,他雖然承認江東曾是衣冠禮樂所在,但認爲晉祚中衰終因“無人”,所以此後建立的政權自相篡立,不再奉其正朔。而《元經》也只是將晉以下五朝當作“棄先王之禮樂”的“中國之遺人(民)”對待,“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中説校注》卷七《述史》,頁183—184,下同。文中子並説明這是其父“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而當董常問及“《元經》之帝元魏,何也”時,文中子的回答也是:“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中説校注》卷七《述史》,頁181。作爲北地百姓,受其政權庇護,形成這樣的立場也很自然。
然而北朝的正統,不僅因兩晉的滅亡和北魏的占據中原,且因孝文帝的漢化統治而建。“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書》云: 天命不於常,惟歸而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中説校注》卷七《述史》、卷一《王道》,頁181、14。曾經的漢政權退出了中原的主位,轉而被胡族所占。但只要是德被黎民,即使統治者是戎狄,也是天命所歸而被百姓所不棄。這就是王通所提出“中國有一,聖賢明之”的“大哉中國”概念,*《中説校注》卷七《述史》,頁180—181。但無疑是對《春秋》漢族正統觀及相續的兩晉南朝正統觀的一大顛覆。
這一正統觀同樣給了之後的中原政權以正統地位。隋、唐二代接續北朝體系而建,無疑是這一正脈的延伸。*祝總斌先生認爲,《春秋》大義是尊王攘夷,但王通以僞古文《尚書》和僞孔傳提倡的“德”以“斷南北之疑”,“唐初,在否定魏、周、隋正統地位聲中,唐王朝依然堅持以魏、周、隋的後代爲‘三恪’,《續六經》、《中説》應該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前引文頁275—278,282—283。説到這裏,或許有人就會對王通的立場提出質疑,因爲王通雖然以北朝爲正統,在經學文化上卻並不以北學爲惟一標準,而是融入了南朝的學問方式,也就是南朝的禮樂。爲何如此?我以爲這是與王通心目中的帝國和王道有關的。建立中國者,應當是一統天下,對北朝正統地位的確立並不意味着對南朝文化的否定,相反兩者並無矛盾,因爲華夏的統一,不妨礙對南方漢文化的兼收並蓄。
還須申明的是,王通的正統不是三代帝王的正統,而是秦漢以降中古皇帝世界的正統。它有兩方面的意義: 一方面,這個正統觀建立了隋、唐兩代君主作爲統一帝國統治者的中心地位,給他們以傳承與改造禮樂文化的底氣和自信;另一方面,它藉助《續六經》確立了帝制時代的新標準,爲唐初君臣提供了諸多借鑑,也提供了進化和改良的範本。即不但肯定後來制度的現實性與合理性,而且以新的内容納入舊典,從而打造新經典,重建三代之後的新標準新秩序,此是中國大陸重新統一後所必須,采用方式卻是“新瓶裝舊酒”。無論如何,針對古《六經》的制作公然被稱爲“續經”,可以認爲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然而這樣做卻無疑打破了古經典的惟一性和權威性,某種角度上是對經典意識的一種挑戰,它所擁有的創新精神和元素正是“改撰”《禮記》的先聲。
也正是爲此,我們發現,將貞觀之治中君臣的某些做法與王通思想對照,即若合符節。例如爲什麽唐初君臣那樣熱衷於討論帝王之道,以至於唐太宗《帝範》一書,不但大談“人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人主之體如山嶽焉,高峻而不動;如日月焉,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歸往”的“君體”之重,也將“設軺樹木,思獻替之謀;傾耳虚心,佇忠正之説”作爲帝王增廣視聽、大臣拾遺補闕的要道。*唐太宗《帝範》卷一《君體》,卷二《納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96册,頁592上,602上。而玄宗時吴兢所撰《貞觀政要》則將“君道、政體”置於全書之首,並將“任賢、求諫、納諫”和“君臣鑑戒”放在重要位置。*吴兢撰,謝保成《貞觀政要集校·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其中求諫、納諫者也正見於王通所言。
子曰:“改過不恡,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中説校注》卷五《問易》,頁133。
這裏王通將忠臣事君的“盡忠補過”與帝王的從諫納諫置於極重要位置。所言與《帝範》、《貞觀政要》所反映的太宗刻意求諫和羣臣犯顔直諫的態度十分一致。此點似乎不是偶然。限於本文主旨和篇幅不擬一一討論,但有一點卻是要提請注意的,即人們常常提到的貞觀君臣曾對隋代暴政予以極大關注,討論隋朝衰亡教訓亦最多,應當與王通的衰世理論分不開。例如王方慶撰《魏鄭公諫録》有“對大亂之後大可致化”一條。内記魏徵針對“太宗論自古政化得失,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化”的看法不以爲然,提出“凡人居安樂則驕逸,驕逸則思亂,思亂則難化;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的一套邏輯,遭到封德彝等人“魏徵書生不識時務”的非難。魏徵對以“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化之而已”。結果太宗認同魏徵之説,遂“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契丹、靺鞨内附,突厥破滅,部落列爲編户”。於是太宗每謂侍臣曰:“貞觀之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王道。惟魏徵勸我而已,我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夷賓服。”*以上參見王方慶《魏鄭公諫録》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446册,頁180上,下。將衰亂之後行“帝王道”以致化的功勞歸於魏徵。
《貞觀政要》中也載魏徵對唐太宗關於“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的問題有“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爲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的回答,*《貞觀政要集注》卷一,頁14—15。其中談及王朝建業與衰亂的關係,與《諫録》相符。那麽這一看法是從哪裏來的呢?
這就不能不談到《中説》一書中文中子相關《六經》和衰世的言論。如“《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中説校注》卷六《禮樂》,頁173。又如“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中説校注》卷六《禮樂》,頁162。這些説法都歸結爲一點,就是無論古典還是他創作的“今典”,大都以朝代變亂衰亡爲起點,提供帝王借鑑,“義直而微,言曲而中”,可謂寄托了“衰世之意”。
那麽什麽是衰世之意?此可見王通與薛收的問對: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中説校注》卷一《王道》,頁12。
原來,所謂衰世之意就是要在“興衰之際”再三思索,總結教訓,找出興亡之由而行仁政。王通生逢亂世,經歷了隋朝由盛而衰的過程,應該很了解個中情由。他始則對隋文帝抱以希望,曾西游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文中子世家》,頁267。後逐漸對隋政權喪失信心,據説曾對魏徵批評煬帝,以爲“《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中説校注》卷一《關朗》,頁247。遼東之役興,文中子以爲“禍自此始”;*《中説校注》卷四《周公》,頁109。對當時“天下治船”和開鑿通濟渠的“御河之役”,也有“林麓盡矣”、“人力盡矣”的評説。*《中説校注》卷九《立命》,頁236,卷八《魏相》,頁208。不過文中子對亂世並不悲觀。如於蒲、陝聽聞遼東之敗,雖一面賦詩感慨,一面卻“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中説校注》卷五《問易》,頁142。按據阮逸注“《兔爰》之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六經》即所撰《續六經》。可見他認爲否極泰來,借亂世可以推陳出新、繼往開來,期待有人將他的續經之書發揚光大。也正是由此,當他得知隋煬帝在江都被弑的消息後,雖然已經“不豫”,卻仍“泫然而興”,發出“天其將啓堯、舜之運”的企盼之聲。*《中説校注》卷一《王道》,頁10。
由此,我們可以推斷貞觀中對於“君道”的研求及對隋代滅亡的總結,乃至對“亂世”的治理,恐怕相當程度是借鑑(至少是應和)王通的衰世理論和思路。今存世陳叔達《答王績書》就指出王通《元經》是在“中原版蕩,史道息矣”、“五裂山河,三分躔次”形勢下所興,而自己和王度(芮城)的《隋紀》和《隋書》,也是在此感召下而作。*陳叔達《答王績書》,《唐文粹》卷八二,四部叢刊縮印本,410册,頁543下。由此可見,王通《續六經》顯然是以現實爲中心爲出發點的,而其用心也爲其親友門生所領會和記取。雖然,對王通其人論者褒貶不一,或毁譽參半,對其學問事迹也提出質疑,但是如果比較現存《中説》與《魏鄭公諫録》、《貞觀政要》等書,就可以發現它們在思想上的貫通之處。那就是如何總結前代興衰治亂的經驗教訓,使“王道”——君道發揚光大,從而打造一個能夠締建中古“盛世”的帝君,形成一種畫時代的政治維新氛圍。從這一點説,文中子在皇權建設與治國思想方面對貞觀之治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而他所進行的經典改造和創新之作,都是爲達這一目標。因此在他的影響下,出現繼承性的經學批判論著也就決不是偶然的了。
四 魏徵《類禮》與貞觀禮制變革
回到《禮記》改撰與魏徵的關係上來。關於魏徵《類禮》,上文引《唐會要》已説明是根據戴聖所編《禮記》文本“乃删其所説,以類相從”。《舊唐書·魏徵傳》也言:
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爲《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重復,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思,數年而畢。太宗覽而善之。*《舊唐書》卷七一,頁2559。
對於魏徵的《類禮》,日本學者島一曾予以關注,他將此書的編纂置於貞觀初禮的修定與《禮記正義》關係的大背景之下,注意到孔穎達《五經正義》對經學傳統的繼承以及對鄭玄學説的堅持。並以廟制和藉田等爲例,認爲太宗和魏徵、岑文本君臣在治禮中提倡的“禮緣人情”以及多采王肅觀點的做法與《正義》相對立。而魏徵《類禮》的“以類相從”就是對孔穎達所指出的《禮記》“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問題的糾正。*引文並參孔穎達《禮記正義序》,十三經注疏本,頁1222—1223。認爲貞觀十一年(637)魏徵等修成的《貞觀禮》也和《五經正義》立場相反,而貞觀十四年成書的《類禮》即代表了魏徵對戴聖《禮記》及鄭玄錯誤的批判。他還特别注意到同年十一月魏徵、令狐德棻和顔師古等人關於喪服的討論和修訂,其中曾祖父、嫂叔、舅服等是對《儀禮·喪服傳》和《禮記》相關篇目的直接修改,魏徵等的上奏强調人情,代表了對《正義》的批判。其文還提出貞觀十六年王玄度注《尚書》、《毛詩》、《周易》等,並作《義決》,“毁孔、鄭舊義,上表請廢舊注,行己所注者”,*見《舊唐書》卷七四《崔仁師傳》,頁2620;《册府元龜》卷六六《學校部·注釋二》,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7276下。按《新唐書》卷五七《藝文志一》有王玄度注《尚書》十三卷、《毛詩》二十卷、《禮記》二十卷、《春秋左氏傳》(卷亡)及《周禮義決》三卷,頁1428,1430,1434,1440。是開始了對《五經正義》價值的全面否定。繼而指出貞觀十七年顔師古關於明堂制度的討論,針對當時的泥古之論所説“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彝則,尚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説,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事實上與之前魏徵主張的“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完全一致,*引文見《舊唐書》卷二二《禮儀志二》,頁852,851。都代表了對正統經學的批判。*參島一《貞觀年間の禮の修定と『禮記正義』》(上)(下),分見《學林》第26號,京都,立命館大學文學部,1997年,頁27—48;《立命館文學》549,1997年,頁665—698。
因此按照島一的觀點,即唐朝貞觀之際經學中已經出現了與孔穎達《五經正義》對立的學派和觀點,這一將經學批判中發生的單獨事件置於一統看待的做法無疑别開生面,也是很有啓發意義的。它表明以魏徵等爲代表,貞觀中已經有一種思想、甚至一股勢力,試圖突破一直以來遵從古典的格局,而建立對於經典的新理解新觀念,從而創造出時代的新篇章。筆者認爲,這一思想的變化無疑是唐代特有精神,是不容置疑的。不過,筆者並不贊成將魏徵《類禮》與孔穎達《五經正義》的立場看得過於絶對,畫分得過於分明。竊以爲唐朝經學的變化是有階段性的。雖然孔穎達仍采取疏不破注的原則,而未能打破舊義疏學的樊籬,但他畢竟大量引用了對立的觀點,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南北隔離的門户界限,即使他對不同觀點的諸多引用只是展示和擱置,並非是用來批判。但其做法與同時代賈公彦《儀禮》、《周禮》二疏(《禮記疏》已佚)專崇北學相比已有很大不同,而這一點正爲後來的變革打下基礎,對此筆者將在另文説明。當然孔穎達編纂《五經正義》的目的還是爲了實現經學的統一。高宗永徽四年(653)其書經再審訂後頒下。時長孫無忌《進五經正義表》也指出孔穎達是在“訓詁紛綸,文疏蹖駁,先儒競生别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之疑,莫祛五日之惑”的情況下奉敕修撰,於是乎“上稟宸旨,傍摭羣書,釋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亂,探曲臺之奧趣,索連山之元(玄)言,囊括百家,森羅萬有”。*長孫無忌《進五經正義表》,《全唐文》卷一三六,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3年,頁1375上,下。等於對經學義疏、門派進行了學術清理。正因爲如此,魏徵《類禮》如有對《禮記》及鄭玄的某些批判,就未必不借助孔穎達的成果。而唐朝科舉之所以始終使用《五經正義》,也是由於他在經學理論和文字解讀方面更爲公允和全面。客觀一點説,孔穎達的治學更接近傳統,更着重對章句和文字的理解;而魏徵等更注重義理,也更在意古典與現實需要的結合,這也是舊學和新學最大的分歧所在。
那麽爲何會出現這一新的理論關懷而取得突破,也即魏徵思想的直接成因又是什麽呢?對此,島一的文章没有交代。上文已經談到,將貞觀之治中的某些做法與王通思想對照非常合契,而這一點與魏徵等自不無關係。唐太宗曾將房、魏二人分别作爲貞觀前、後的最大功臣,以爲“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爲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貞觀政要集注》卷二《任賢》,頁63。王方慶《魏鄭公諫録》所收條目五卷共計一百條,最後一卷乃爲與魏徵相關之記事二十七條。《貞觀政要》中梳理魏徵的内容也極多,其中言君道政體者總二十四條,有其論説者約十二條;求諫納諫三十六條,有其論説或太宗提到他的有二十條;在“君臣鑑戒”的六條中,有魏徵論對的也占四條,各項分别超過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此外其他各篇與魏徵相關條目還有約五十、六十條之多,在《貞觀政要》中羣臣所占條目中比例最高。此雖爲開元中吴兢所記,但由此可見魏徵在刻意打造帝王盛業中的作用。
在《中説》的記載中,魏徵與王通交流甚多,似乎王通對其爲人頗爲欣賞,而魏徵則更將文中子直呼爲“聖人”。*見《中説校注》卷五《問易》:“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其“聖人”與“吾”對應,知即呼文中子。頁127。文中子與魏徵言談中也有“使民不倦”、“議事以制”之類的教導。*《中説校注》卷五《問易》,卷一《關朗》,頁135,250。據説魏徵曾宿文中子之家,“言《六經》,逾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中説校注》卷四《周公》,頁111。也即通過對《六經》的研習討論,認爲布衣王通纔是天地人間的不世出之才。
或認爲《中説》所載唐初重臣多爲王通弟子的説法很有可疑,但薛收、陳叔達、魏徵等與王通之關係卻不容否認。薛收作《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銘》言王通“天下聞其風采”,並自稱“收學不至穀,行無異能,奉高迹於絶塵;期深契於終古。義極師友,思兼親故”。*《全唐文》卷一三三,頁1338下。而王通之弟王績《答馮子華處士書》提及薛收《白牛溪賦》而嘆恨薛收、姚義早亡,同時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之説。*《文苑英華》卷六八八,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6年,頁3543下。白牛溪即王通家鄉和隱居所在,*見《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王公神道碑》,瞿蜕園《劉禹錫集箋證》卷三,頁89。可見至少房玄齡、李靖輩均與王家有過從,而與之相提並論的“吾家魏學士”應就是王通入室弟子魏徵。
不過《關朗》明謂王通弟子中,“杜淹、房喬、魏徵受《書》”而不是《禮》,*《中説校注》卷一《關朗》,頁259。文中子並不曾向魏徵傳授禮樂。《中説》一書後附“録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一文,*《中説校注》,頁270—271。記王通弟太原府君王凝訪問魏徵,徵因憶與諸賢侍文中子。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常)、薛(收)、程(元)、仇(璋)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於時有不平之色”。然而董、薛、程、仇均早逝,至貞觀中果有太宗召見,急於向羣臣討問經久之策事,房、杜等都無以作答。而魏徵雖以《周禮》和《詩》、《書》爲對,提出“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惟所施行”。但正如太宗所説,“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周禮與現實的結合無從落實,所以“會議數日,卒不能定”。此文最後説:“徵與房、杜等並慚栗,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可見不能解決令當世走向輝煌的禮樂問題,很令大臣慚愧,不知這是否對魏徵後來立意作《類禮》有所觸動。
無論如何,魏徵如果是王通學生,按其思路作《類禮》也很自然。有一點可以肯定,即魏徵恐怕確如《中説》所説没有專門研習過禮。《舊唐書》本傳説他“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爲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横之説”,*《舊唐書》卷七一《魏徵傳》,頁2545。也不像是受過經學門派的專門訓練。所謂“落拓有大志”、“縱横之説”的取向尤與之相反。故此他的著作就不大可能在章句細節上有太多的發揮,而應該是申述禮義,大言闡發占了主流。而且其書針對《禮記》,書名爲“類禮”,取其相類之意,這與王通的“續禮”,在立論方向上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使筆者懷疑,魏徵作此書是完全本着其師的思想路徑和既有方式而更有所推廣。
這裏再引《魏鄭公諫録》卷五《上〈類戴氏禮〉》:
《戴氏禮》並爲注解,二帙二十卷,上之。詔曰:“禮經殘缺,其來已久。漢代戴聖,爰記舊聞,古今所宗,條目雜亂。先儒傳授,多歷年所,咸事因循,莫能釐正。特進鄭國公徵,文高翰林,學綜册府,服膺典禮,有志討論。乃依聖所記,更事編録,以類相從,别爲篇第,並更注解,文義粲然。遂得先聖微言,因兹重闡,後之學者,多有弘益。宜付秘書,仍令繕寫,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本,並賜物一千匹。”*《魏鄭公諫録》卷五,頁203上—下。
《類戴氏禮》即《類禮》,這裏詔書的説法印證了前揭《唐會要》和《舊唐書·魏徵傳》的記載。本文前面曾提到王通有“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的評論,顯然認爲原先的傳注並没有真正理解經義,反而造成了經書本身的散佚和衰亡。詔書指出魏徵作《類禮》的着眼點是“禮經殘缺”和戴記的條目混亂,正與王通指摘相合。對前儒“咸事因循,莫能釐正”的批評,也與前揭王通“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吾於禮樂,正失而已”的意圖如出一轍。而魏徵的書顯然不僅僅改變了篇章結構。詔書“遂得先聖微言,因兹重闡”一句,可以解釋爲是對先聖微言大義按自己的理解重作闡釋和解讀,而絶非亦步亦趨地遵循鄭注。

事實上進入隋唐,經學思想發生方向性的變化也很自然。時代不能逆轉,恢復周禮既無可能,那麽創新就是惟一的出路。因此魏徵能夠做到和追求的,首先也只能是像王通《禮論》那樣。對禮義大加闡發,爲帝王之禮儀行事提供借鑑和依據。《貞觀政要·擇官》引《説苑》稱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六正其二曰“虚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貞觀政要》卷三《論擇官》,頁167。此“勉主以禮義”,魏徵是實行了的,《貞觀政要》言其在論政和諫的過程中提到《禮記》諸篇約有八處之多,此不但因其對《禮記》特别熟悉和重視,也表明他更在意發揮禮的真諦用於實踐。
其次即打破對於上古條框的限制,訂立當朝應用的禮儀規制。例如上述明堂之制,就是按照當世的建築格局,貫徹魏徵所説因事制宜的原則,只是明堂的設計,貞觀時似乎還是有阻力而未能完成,封禪最初也如此。上文説明,王通於封禪有“徒以誇天下”的批評。而當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惟魏徵切諫,以爲不可”。理由是“殫府竭財,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劉肅《大唐新語》卷一三《郊禪》,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96。又言“隋末大亂,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養之則至仁,勞之則未可。升中之禮,須備千乘萬騎,供帳之費,動役數州,户口蕭條,何以能給?”*《舊唐書》卷二三《禮儀志三》,頁882。可見魏徵仍秉承王通反對封禪的思想。不過,至貞觀十一年(637),“羣臣復勸封山,始議其禮”,“於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采衆議堪行用而於舊禮不同者,奏之。……太宗從其議。仍令附之於禮”。*《舊唐書》卷三三《儀禮志三》,頁883。因此最終封禪儀還是由房玄齡、魏徵等定,並被載入《貞觀禮》。史載此禮自設壇、器物到形制,多“依漢建武故事”,*《舊唐書》卷二三《禮儀志三》,頁882,884。這實際上也受王通遵法漢制的影響。貞觀十五年此禮再由顔師古等人“詳定”,因此雖然後來太宗封禪由於“彗星見”而未能成功,但畢竟是《貞觀禮》的一個創造。
當然定禮、改禮也包括用某些便於世俗接受的禮條取代原禮經中存在卻已經不合時宜的内容,即所謂“緣情制禮”。上述喪服的改制就是其中之一。這種改制兩晉南北朝其實已經開始,不過就事論事而並不對禮經傳注采取原則性的否定。貞觀的不同,是不僅針對鄭注,甚至也向禮經綱條直接開刀。從這一點來説,“緣情制禮”當然也不是魏徵等的發明,而是一直以來屈從現實,不按經典辦事的一種藉口。不過,現時制度往往受理論指導,從兩者發生時間的一致性來看,推斷貞觀十四年改革服制可能是《類禮》所設内容之一,恐怕也是無誤的。
這裏還有一處史料或許能對此服制改革的來源提供一些線索。《唐文粹》載有杜之松《答王績書》一首,談到“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别帖。想荒宴之餘,爲銓釋也”。*杜之松《答王績書》,《唐文粹》卷八一,頁537下。據《舊唐書·王績傳》杜爲刺史,乃王績故人,曾請績講禮而未果。*《新唐書》卷一九六《王績傳》,頁5595。其所言借《家禮》事在王績兩首答書中也提到,從後書知杜乃“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王並有回答。還提到“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録此篇附注,幸詳之也”。*王績《重答杜使君書》,《全唐文》卷一三一,頁1320下,1321下。此家兄御史當即王度,是其人對喪服也有研究。*《中説校注》卷三:“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注釋:“芮城府君,王通兄王度。”頁93。其文所釋内容雖不涉及嫂叔、舅服,看不出與貞觀改服之直接關係;但《家禮》爲王氏一族所有,其中“喪服新義”又是特色。所以進一步的問題是,其内容是否爲王通《禮論》所關注和吸收,並進而啓發魏徵作改革喪服之論呢?此尚有待進一步的發現和研究。
另外,結合元行沖對《類禮》及義疏的申述和評價,我懷疑《類禮》很可能還有涉及當時爭論焦點的郊廟一類内容,這是在討論《禮記》一書的《王制》、《大傳》、《祭法》、《郊特牲》等章節時不可少的。衆所周知,孔穎達完成的《禮記正義》雖然宗鄭,且以皇、熊兩家義疏爲基,但也在上述部分大量引述了王肅和南朝一些禮家學派之觀點。而魏徵領銜纂修的《隋書·禮儀志一》也在述南北郊祀之時專門言及兩大學派的不同。其曰:
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秦人蕩六籍以爲煨燼,祭天之禮殘缺,儒者各守其所見物而爲之義焉。一云: 祭天之數,終歲有九,祭地之數,一歲有二,圓丘、方澤,三年一行。若圓丘、方澤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圓丘之祭,終歲有八。地不通方澤之祭,終歲有一。此則鄭學之所宗也。一云: 唯有昊天,無五精之帝。而一天歲二祭,壇位唯一。圓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圓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謂之二祭,無别天也。五時迎氣,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皥之屬,非祭天也。天稱皇天,亦稱上帝,亦直稱帝。五行人帝亦得稱上帝,但不得稱天。故五時迎氣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則王學之所宗也。梁、陳以降,以迄於隋,議者各宗所師,故郊丘互有變易。*《隋書》卷六,頁107—108。
此一段話是對鄭王郊祀之學的總結。這裏雖因文章主題無須涉及其内容,但其言二者矛盾、差異較孔穎達《正義》更集中,更明晰。雖未偏袒哪一方,但點明了其時禮制衝突之所在,不知是否代表主持者魏徵本人之意圖。惟此非僅學術問題,實也關係統一之後的國家意識形態概觀,《類禮》不可能不就這一問題進一步立論且表達觀點,而他的主張可能比孔穎達更捨北從南。此雖未見確證,但元行沖曾在爲自己辯護的《釋疑》一文中,借述張融之論,指出“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玄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玄慮之失也”,*《舊唐書》卷一○二《元行沖傳》,頁3181。直接批評鄭玄的郊祀六天和感帝之説。这也很可能就是《義疏》自身對《類禮》内容觀點的發揮。所以在魏徵之後,許敬宗借《顯慶禮》的修撰進一步提出郊丘合一與一天説,此不過是經典“改撰”由來有漸而已。
總之,自隋至唐的經典改撰和思想變革是一長期的過程。有一點值得提出,即《中説》言王通曾有“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的預期。他解釋三十年即“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中説校注》卷八《魏相》,頁212。唐朝武德元年(618)始建,如按照王通的預言,貞觀十一年(637)以後,是唐朝走上“十年和之”的階段。“和”者即禮樂教化。《五經正義》、《貞觀禮》和《類禮》成書的年代恰恰都是在這十年中,與王通的説法相當接近,似乎是巧合,但實際上體現了一種規律。試想唐朝經過二十年的休養生息,朝政清平,四海晏然,對内對外都亟需要樹立强盛的帝國形象,故對於禮樂的期求也最爲强烈。如此我們可以理解爲何太宗君臣談論兹事如是迫切,也可以理解爲何有《類禮》著作和思想産生。從某種角度講,它們是王通《續六經》思想的翻版和實踐,也是中古社會演變的必然。不妨説,兩者的出現都奏出了時代的最强音。它們的出現告訴我們,由於上古經典日益顯現與現實脱節的一面,故打造中古“經典”另起爐竈的要求便應時而生,而當“改撰”思想和著作一旦出籠,時代變革的鐘聲也便同時被敲響了。
以上對王通《續六經》與貞觀時代“改撰《禮記》的先行——魏徵《類禮》作了討論,意在指出兩者在思想觀念上一脈相承的關係。有一點要明確,即隋、唐兩代在取得政權和政治改革的同時,統治思想也在發生極大的變化。即它們對上古經典的遵守和認同是建立在歷史發展的基礎上,而不是單純盲目的推崇。如此不但需要將中古國家區别於上古,建立帝制時代的“王道”正統觀和新標準,也需要建立對經典的新認識,實踐對經典終極理念、意義的追求,這就促進了對以往傳統經學的批判以及新撰“經典”的出籠。在這方面,王通的《續六經》與魏徵的《類禮》都僅僅是開始,我們將證明,它們啓迪了貞觀以後的經學爭議和禮制變革,以及特别是開元、天寶之際君臣的經典改撰之風。因此王通對中道的提倡,乃至唐代改禮所倡折衷觀念和標準,都是以改撰、革新爲基礎爲核心的。而且誠如以往學者所論,王通的精神還啓迪了唐後期韓愈建立的新道統和宋學。所以如果建立了王通與貞觀、開元改撰思想的聯繫,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找到隋唐之際思想變革的源頭。隋唐之初—貞觀、開元—中晚唐乃至宋代,便構成了中古後期思想發展的主線,其間的内涵也是士族社會向皇權獨尊社會轉變的一種思想回應。所以總的來説,經典和經典意識的變化,是隋唐之際的特色之一,它將引領國家和社會的變革走向更深更廣的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