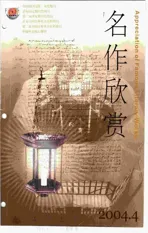探索肉体和灵魂的文学
——访美讲演稿(下)
2017-07-13北京残雪
北京 残雪
探索肉体和灵魂的文学——访美讲演稿(下)
北京 残雪
十、我一贯认为,冲突是推动实验文学生长的原始之力。没有冲突,生长就停止了。人性就是在冲突中发展壮大的,因为人性是一个矛盾体,矛盾的双方永远在角力中抗衡,这种冲突与抗衡提升着人的品质。当然,所有的艺术都是描述冲突的,但我认为我这种实验小说是将冲突发挥到极致而又有魄力,同时将操控力也坚持到极限的文学。在这种文学实践中,这两种力都同样具有无限性,经常要用杀戮来进行暂时的解决。这种表演性的文学时常达到惊心动魄的程度,但又并不导向对于人性的绝望,反而是导向无限的希望。当每个个体都自觉地建立起自己的矛盾机制,并通过学习文学来运用这种机制时,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具有理性与创造力,并焕发出勃勃生气。有理性钳制的冲突,以创造性分裂为目的的理性,这是我的实验文学的显著特征。无论小说中的冲突分裂是多么的触目惊心,那也是有理性机制在当中起作用的冲突和分裂,绝不是返回兽性或非理性。所以我的审美是一种清明、坚定,但又洋溢着饱满的肉感体验的审美。从哲学上来说,这种中西文化杂交的审美消除了经典宇宙观当中的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千年鸿沟,让一个浑然一体的大自然呈现出其真实面貌。因为这个特点,我的小说中出场的每一个角色都心怀一种“肇事”的欲望,他们卷入冲突,挑起冲突,在冲突中成长。冲突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需要躲避的事物,而是机运,是自由意志的操练场所,也是提升自由境界的基本方法。冲突来自于作品的核心矛盾,矛盾的发展又加剧着冲突,像浪潮一样一波一波地推动着作品不断展开,不断翻新,在一个又一个的高潮中趋向终极体验,这也许就是我拿自我做实验要达到的境界。我作为艺术家,是那种总是渴望极致体验的、不知疲倦的类型。我想,我的读者大概也是那种将创造当作人生的第一要义,愿意不断接受人生挑战的人吧。冲突既能训练我们大脑的逻辑能力,也能训练我们器官的灵活性,人的素质就是由这两方面构成的。如果你对自身的素质有很高的要求,就来从事这种高难度的文学阅读吧。这种文学不会令你失望,只会不断加强你的欲望,同时也加强你承受欲望冲击的韧性。
十一、我的实验文学是现存的世界文学中具有最大张力的种类,因为这种文学中矛盾的两极都被发挥到了极致,在读者看来就像是总在飞越鸿沟似的。创作中的作者必须时刻警惕着,绷紧那根创造之弦,不能有丝毫懈怠。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就如同推理小说与侦探小说一样造就它的读者,但它对读者的激发是一种另类的激发。因为这种奇异的张力,读者并不能轻易地找到它对自身的激发点,他往往要在似是而非的辨别和判断中长久地徘徊和等待,也就是吸收作品中发出的信息,让他的自我中的那两个部分交融与分裂,来促成某个新图案的产生。有时候,这种焦虑的持续甚至让一名读者产生痛苦的感受,而这种痛苦又并未让他获得他想要获得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读者最好选择暂时放弃,这是因为种种原因,他还没找到那种契合的方法,他有必要在加强各方面的素质训练之后再来尝试。这也是我的小说同推理小说的不同。这种小说是不能单凭脑力的发挥来进入的,读者的肉体,也就是情感性质料必须发动起来,并以他自己的创造来证实作者的创造,在与作品的互动中让作品得到延伸,所以我的实验小说的阅读实际上比它的创作要更难,它既需要读者在生活中有深厚情感经验作为底蕴,又需要读者具有广泛深入的对于经典文学的阅读探讨和钻研,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而想进入这种实验小说,就会遇到巨大的排斥力,在与作品的拉锯中败下阵来。有不少读者问过我这个问题:产生困惑是否就是阅读这种实验小说的主要感受?读者是否只要坚持在困惑中不退却,本身就是成功阅读的标志?我的看法是,困惑感只是阅读我的实验小说的过程中的主要特征之一,如果一名读者自始至终处在困惑中而没有任何升华,没能焕发出欢欣、明丽和幸福的感觉,那么他的阅读就是失败的,最好暂时放弃,待加强操练,提升了素质之后再来尝试。我的这个回答是基于我自己几十年阅读经典的经验,而且我已通过钻研发现,不少经典大师如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等人也是用类似的方法阅读。仅仅将阅读中产生的困惑感归于成功,不寻求谜底,不“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是萨特世界观中的缺陷对于现代青年造成的恶劣影响,因为他的那个“纯粹”的真理没有标准。像我的这种实验文学,你不寻求谜底的话,就永远体验不到作品中的张力和结构。看不到作品中的机制如何发生作用,就不可能与作品产生互动来开始你自己的创造,而只能站在外围说出一些支离破碎的感受,不成体系也同作品关系不大。如果想体验到作品中的张力,标准就是你自己在阅读过程中是否也产生了类似的张力,这种张力是否会随着阅读的深入而不断加强,又不断释放,并随着每一轮的释放升华到更强的二力抗衡的境界。没有体验到释放与升华,并在升华中清楚地看到小说中那个深层的、立体的结构,你的阅读就还不能称之为成功的阅读。在困惑中抵抗是过程开始时的必经阶段,这个过程有的人时间长,有的人时间短,但不论长短,所有的读者都应殊道同归,进入升华的幸福境界。像萨特那样以受苦当幸福的阅读,始终处于自虐的氛围中,已不是新世纪读者的理想追求了。我们追求的是在创造中享受,在克服难题中升华,并建构自己的理想事业。这样的阅读给人带来的不是纯粹的受虐和狭隘的自我欣赏,而是打开眼界,勇敢地在同别人的交流中丰富和提高自身的素质,在融入别人艺术的过程中自己也来当一回艺术家。如果整个纯文学阅读界能形成这样的风气,所谓“毁灭”的论调就不会再为大多数人所信奉了。
十二、我的实验小说的一大特征是它带给读者鲜明的“肉感”,这一点在同类的实验小说中恐怕是空前突出的。我想,这是因为我的世界观,我的终极设定都是倡导物质的缘故,物质就是质料体和生命体,我的小说处处让肉体和灵魂凝成同一个事物,所以肉体才能焕发出如此生动的力量。我在写小说时不光发动我的思维想象力,同时还发挥我的五官和肢体的力量,让感觉参与到创造中去。所以有不少读者说“肉感”是我作品的最大特点。我为此感到自豪。肉感即生命感,我是作为一名中国艺术家来创作的,我将我的民族的感性文化提升,又让这种感性同西方的理性融合,建构起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作品。这种作品,它是极其肉感的,与此同时,它又比西方的小说更为空灵。因为我的空灵是与肉感对比中的空灵,所以其透明度也许比某些西方小说更胜一筹。因为这个特点,读者在读这样的小说时,就必须探讨和掌握发动自己肉体的一套技巧。也许在冥想之际进入自己过去的情感经验世界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这种冥想不是单纯地回忆某些发生过的事件,而是重新再造你的记忆,让久远的记忆复活。在这个意义上,久远的记忆(主要是肢体器官的记忆)就是崭新的未来。那种记忆也许是一株叶落满地的树、一只棉手套、猫儿的一个眼神、一扇破旧的木门、一个油漆剥落的玩具、一张秀丽的白脸、一声惊恐的尖叫、长空中大雁鸣叫的余音、厨房里飘出的肉桂的香味、某种兽皮的触感、某类岩石的气味等,不论它们是什么,都是真切的生命记忆。作者将这类记忆储存在他的小说中,读者则需要依仗作者的记忆机制来开发他自己的记忆,直至这记忆成了作品记忆的延伸,作品便真实地存在了。单单从这个方面来看,也可以推论出这种现代主义小说是多么的依仗于读者的创造性来获得生命。双重的创造性对于肉体的发动有严格的要求。张力是什么?就是你的原始记忆在理性精神的追击之下能跑多远。被追击的记忆并非要逃离表演场所,毋宁说这是两股势力在表演超越的好戏。
十三、除了严密的逻辑性之外,我的实验小说的另一特征便是其毫无例外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由于这样的小说不存在所谓“题材”的问题,于是那些未能进入其境界的读者往往会说作者的叙事是“重复”“啰嗦”“无新意”,等等。而实际上这种实验小说对于他们所说的题材或描述手法的“创新”毫无兴趣,它感兴趣的不是表层现象的“新”,而是作为内核的宇宙观、世界观的“新”。在这个方面,我的实验小说可以说颠覆了以往任何时期的观念,并以其整体性显示出两种主要文化紧密结合的优越之处。我的实验小说在众多的作品中一眼就能被辨认出,就是以上所说的整体性的验证。很难设想这种文学脱离自己的风格,按照某些读者的期望去“创新”。因为在我眼里,那种表面层次的“新”其实是旧,是骨子里头的重复,而守旧和重复正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事。简言之,只有坚持自己创造的统一性,并将其风格和关注点发挥到最后,这才是真正的创新。如果有一天我改变了一贯的风格和叙事的主题,那只能说明我的创造力衰竭了,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脱离了我的实验文学。从一开始,我的创作风格就是在徐徐演变的,但那是整体性的演变,是“万变不离其宗”。不论这种实验文学与早期相比变化有多么大,它也是为着展示同一个终极理想在表演,它的终极追求是渐渐显露出来的,但从未改变过。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强大的整体性,它之所以比以往的经典哲学更有生命力,就在于这个整体性本身又是以它的绝对的分裂和突破为前提的。我的大自然是统一与分裂互为本质的矛盾。读过我的作品的人都知道,作品中的角色与角色,或角色与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势不两立,每篇作品中的矛盾总是要演绎到最后一刻,氛围中时常充满了杀戮的血腥味。但在种种的明争暗斗中,有透明的崇高的事物在闪闪发光。正因为有了那种事物,扭斗与分裂才不是盲目的,才无一例外地被导向升华的境界。
十四、我还要谈谈作品中的幽默感。很多读者都曾体验过我的实验小说中那种透骨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幽默感有某种契合(例如《堂·吉诃德》和《城堡》,等等),但又很不相同,因为这里是一名东方人或者说中国人在进行文学实践。幽默所包含的是批判精神,批判又寓于体认之中。每一批判就有一体认相伴相随。西方经典的幽默往往在体认这个阶段就停下来了,至少在那些大部头的作品的暗示中有停下来沉浸在冥想中的倾向,因为作者需要一个精神寄托。但我的实验小说中的幽默是一种魔性事物,这种幽默绝不最终停下来,反而要像中了邪似的一直转化和演绎下去。我的寄托,以及我给予读者的寄托就在这种幽默的实践本身之中。也就是说,批判越来越深入,体认越来越顽强,一轮又一轮,永无止境。这样,相对于西方文学中那种较为悲观的幽默,我的幽默更为积极,也更为振奋和自强不息。因为不论作者和读者,你幽默到底,你就获得精神的寄托与肉体的舒展,你如果停下来,那种自由感就消失了,你的快感取决于你的主观的努力和你的批判欲。而只有这种不知疲倦的批判欲,才会有崭新的建构。作为一名不信上帝的中国艺术家,我以实验小说为生命实践活动,将自己的命运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中,毫不松懈,从而以一种最有张力的幽默展示了艺术的理想境界。我的这种幽默感的获得来自于将两种文化的精髓都吸取到了艺术的内核之中,让它们在交融中分裂,在分裂中交融,从中生成出一种新型的、中西结合的处世态度。这种幽默中既有西方的进取精神,又有古老中国的人生智慧,应是21世纪世界文学中的新兴事物,其发展的前景也很广阔。从我多年的经验来看,由于我长年累月地努力学习和钻研西方的精神成果,使我对中国人的自我幽默这个领域得以不断开拓。没有西方精神作为参照,我不可能生成如此强韧、博大的自我意识。任何一种自我意识都只能通过“照镜子”来获取,异质的文化的“镜子”往往使“照镜者”受益最多。在21世纪里,也许这种实验小说的幽默人生观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追求,因为当今的时代要求我们有更为开阔的胸怀,更为务实的生活态度,更为积极的不懈的追求。而这种幽默是将人生变成自由表演的、可行性最大的模式。
十五、我的实验小说中对于生命体(肉体)的关注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强度。从最早的作品《黄泥街》《山上的小屋》《污水上的肥皂泡》等开始,人的肉体性感知就开始声张自己的权利,要与形而上学的精神平起平坐,并致力于划分出肉体世界的疆域。这个被前人所忽略了的黑暗中的存在在我的实验小说中迅速地建构起来,成为了不可抹杀的本质性的事物。不说话的生命体一旦与说话的精神结合,便促使精神替它喊出了千年沉默中蕴含的真理之声。我的早期作品就是这种试探、激发的产品。黑暗中有一个东西,它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基底,也许我们处于盲目之中不去看它,但它绝不放过我们,因为它就是我们自己。千年的等待是漫长的,但在整个人类史中也许很短暂。实际上,人的生命体从未完全沉默过,在千年历史里它在高层次的文学中不断发声,直至21世纪即将到来时,它才逐渐要汇成时代的强音。我的实验小说正是顺应了时代的这种精神,所以才能在三十多年里头从未有过灵感枯竭的时候,反而越战越强,将它的疆域不断地延伸,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黄泥街》等实验小说中,大部分读者所不习惯的那种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对话;那种令读者无法进入,只有与一条隐秘的信息相通才会恍然大悟的氛围;那种超脱怪诞的描述等,都是来自于这个黑暗中的生命体,它借我们的语言发声,同时又赋予我们的语言以生命的基底。它是一切自然事物的意义来源,它也为人的一切实践提供材料。同西方的某些经典小说形成对照,这种由生命体来唱主角的作品可以给人带来更大的自信,因为一切可能性都呈现在人的直观中了,人没必要躲躲闪闪,只要果断选择,只要启动肉体中的机制,整个世界就属于你。这样的英雄主义并非属于少数精英,它属于每个人。每个人,只要他体内的欲望没有死灭,他就能创造,并在创造中体验属于他个人的独特人生。肉体的潜力是可以无限发挥的,你不去发挥它,它就萎缩,你发挥它,它就保持活力。写作是这样,阅读也是这样。
十六、有不少读者认为,我的作品既多产重复,又好像没有什么严格的规范,写到哪里算哪里,结尾也很随便,时常不了了之,似乎无视读者的审美需求。持这种看法的读者大概还是从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于这种实验小说没有采取正确的立场,因而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吧。特殊的写作只能适合于特殊的审美观。我自认为我的审美观是对西方理论审美观的一场颠覆。我的实验小说确实不能按经典理论去规范,不如说它是对那种规范的打破。如果你怀着经典审美的期待来阅读这样的作品,那期待注定是要失败的。那么读者应不应该对这样的作品有审美期待,或者根本不应该有任何期待?我的观点是,当然要有期待。但这个期待不是像现实主义文学一样是一个较固定的范式,而应该是那种无法事先预测的新奇感、自由感。于写作、于阅读皆如此。作品如大自然本身一样徐徐展开,你在全神贯注中绷紧你的肉体与精神,你的肉体与精神里面都有机制,你渴望升华,你的审美期待就在这个升华之中,而升华又是通过突围来实现的。在紧张中突破,在凝聚中攀升,这就是这种小说遵循的规律,这种规律就是打破规律,是以打破来实现的规律。要时刻做好准备让自身有出乎意料的表现,因为只有创新才是大自然的意志。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操练中使自身变得强韧和灵活,而不是事先在大脑中构思出一个审美的模式来套作品。以肉体为基质的自然之美奇丽而多变,没有谁能有把握地预测它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因为一切都是即兴表演,因此阅读也必须有这种即兴表演式的跟进。肉体不运动、不表演,想单凭大脑的想象来把握作品是不可能的,而且这种方法也过时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实验小说的确是写到哪里算哪里,因为这位作者在写作之际已变成了大自然,一切旧有的规则全不在她眼里,她只关心一件事,就是在凝聚的质料当中突破,就是创造事物的新图型,所有的规则都被变通了,以便为这个目的服务。
十七、我想谈谈我的实验小说中所包含的一种新型的诗意。已经有读者指出过,我的小说中有很浓的诗意。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意?以早期的作品《黄泥街》为例,这个大中篇里面的描写充斥着粪便,垃圾,死鼠,烂水果,溃疡,地上的污水,空气中的黑灰等,能将这类描写看作诗意吗?在我的审美观中,这是可以的。我认为《黄泥街》就是一首很长的抒情诗。那是诗人的灵魂与肉体正在苏醒,开始奋起进行独立表演的景象。所有的生命感都复活了,人感觉到了环境的腐败,而这原始的腐败,正是孕育强大生命力的温床。我就是黄泥街,我要在腐败中翩翩起舞,表演人性的极致。这样的黑暗的、物质性的诗意,应该是时代的最强音。小说中有一个阴谋,那个阴谋是人性的狡计,也是大自然的预设机制之体现,为的是发动肉体进行那致命的一搏。虽然作为一部处女作,《黄泥街》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将表演一些什么内容,但那种强烈的诗的形式已充分显露了。它不同于西方的大部分歌颂纯精神的诗歌,它的境界有些类似于但丁的“地狱”境界,但更注重肉体的底蕴。这是一种中西文化交融、灵肉真正一体化的新型诗意——肉体也是诗,而且是诗的基质。阴谋就寓于肉体,从腐败中获得了强大生命力的肉体一旦崛起,就要开始肇事了。矛盾的机制以其特有的自由律奏演绎了这篇早期的朦胧诗歌。可以说在这第一部作品中,是作为诗人的本能启动了支持着写作的生命体的机制,几乎所有的场景和人物的表演都是依仗肉体的原始力来推动的。当然从一开始,我的这种生命体的冲动就同那些“本色作家”完全不一样,从这种感性冲动中可以体察到超强的控制力,就是这个理性控制力在冲动中掌握着诗的律奏。没有这个理性的参与,我的小说就不可能有今天这种整体化的景观,而只会是一些碎片。所以这样的小说对于读者理性能力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我的小说的抒情往往不动声色,时常通过深层的幽默来表现诗意。当读者如电光一闪似的领略了那种幽默时,她或他的阅读就已经进入了诗的境界。诗的境界就是自由的境界,现代人是在幽默中体验自由的,也只能这样体验自由,因为现代人是矛盾体,矛盾要在幽默中发挥。我的小说就是自我矛盾中对立的双方那种超强的张力的实践,它很像刀锋上的诗歌,需要高难度的阅读技巧。这种技巧不能单单通过冥思苦想来获得,而要在实践中训练器官与肢体的能力,让生命体的发动与思维相结合,这样才能获得。
我的幽默同现代主义文学一脉相承,是一种自我幽默,这种幽默与现实主义的讽刺完全不相同,它不是对现象的批判,而是在自我的对立面的抗衡中奋进。正因为这样,幽默才能同诗性精神融合——幽默即是诗。如果要问我的诗意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诗意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在于一种对于肉体自由的理直气壮的歌颂。在我的实验小说中,从腐败中诞生的这些卑微的小人物(而不是但丁的帝王、历史名人等)都具有形而上学的崇高特征,正是这些常常连姓名也没有的小人物在提升着人的精神层次,而他们所依仗的,就是那种与精神结合了的肉体的爆发力。这种灵肉互动的诗性舞蹈较之纯精神的诗性舞蹈来说,显得更有底气和韧性,其理想境界的纯度也在对比中加强了。这种诗的能量如同火山喷发,表明了文学新时代的临近。在连续三十多年的实践之后,我的实验文学还能越战越勇,这本身就验证了人的肉体在创造中的能量。肉体领域是一个无限的领域,它就是大自然质料体的延伸,属于我哲学的终极设定中的一方,所以我的实验小说的诗意都来自这个肉体。
十八、我的全部实验小说都可以看作一种新型的喜剧,并且我认为文学的新喜剧时代在新千年中正在到来。贝克特、加缪和萨特等人的悲剧时代已经过去了,人类虽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隐藏的转机已经初见端倪。世界并没有按贝克特等人所预料的,以及后现代主义所渲染的那样发展,而是有另一种规律在暗中起作用。我的实验小说在这方面走在前沿,这种小说从一出现就洋溢着一种新的时代气息,虽然这种事物还不为多数读者所认识,但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显示出自身的优势。这种小说的世界观与审美观与以往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拉开了距离,因为其内部具有矛盾机制,所以发展成了一种最具有建构性和积极性的文学样式。这是一种生长的文学,健康的矛盾机制使得它能不断自我完善,所以“毁灭”之类的后现代主义论调也为它所摒弃。能够自我幽默并幽默到底的文学,自然而然就具有了喜剧精神,叙事和行文当中会不断流露出痛快、狂喜、流泪的大笑、黑色的刻薄等现代喜剧的特征,这种喜剧精神带给人的不是彻底的绝望,而是不顾一切的奋起,与命运搏一把的决绝。总之,它是为加强我们的生存意志与自由意志而存在的。人必须建构起这种自我批判与自我生成的机制,才有可能冲破旧的经典主义审美的瓶颈,开拓出一片持续发展自我、建构自然事物的新天地。人不应停滞在古典精神的怀旧伤感之中,而应不断革新,致力于创造。作为自然界的灵物,这是我们肩负的义务。凡蔑视创新者,都将在未来的时代潮流中被甩下。既然世界是我们所建构的,它是否毁灭就有一半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这个主观意志也是大自然的意志。我作为一名艺术家,今天在此已看出了大自然的主观意志是要人活下去,让人去创造自由的新生活。我将这个预言以幽默的喜剧形式告诉大家,是在向人们指出一条自我生成、建构自然的创新之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会变得比以往更聪明,会生活得更愉快和充实。一个人,不论他的能力是大还是小,都有可能以幽默的喜剧精神来对待生活,这样他就会有目标,有追求的激情,难以坠入颓废情绪之中。贝克特式的绝望时代已经成了记忆,后现代主义也不过是人类思潮的一股支流,时代思潮的发展规律已隐隐显现出轮廓,而艺术家,作为最敏感的大自然的器官,往往能预见到历史的规律。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自身,又将自身与大自然连为一体时,我们或迟或早都会在实践中发现这条险峻的新生之路,它是挑战、诱惑,也是测试,它也会使我们在幽默的狂喜中创造性地回归大自然的怀抱。
(本演讲稿已经作者本人审订)
作 者:
残雪,当代作家。著有《五香街》《松明老师》《归途》《断垣残壁里的风景》《海的诱惑》《痕》《下山》等。编 辑:
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