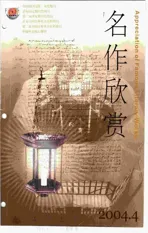梦境:被动的境遇与积极的策略
2017-07-13北京李建军
北京 李建军
梦境:被动的境遇与积极的策略
北京 李建军
梦境叙事是汤显祖在被动的写作环境里的一种积极的修辞建构,体现着一种自觉的写作意识和成熟的反讽精神。
梦境 象征 讽刺 修辞 现实主义
从文学精神来看,汤显祖无疑属于现实主义作家;但是,从写作方法来看,汤显祖的“临川四梦”,除了《紫钗记》大体上是用写实的方法创作出来的,其他三部全都是象征主义性质的作品,就此而言,他是用象征主义方法来写作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的象征主义写作既是被动的,又是自觉的。外在地看,作家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技巧写作,似乎纯粹是自己的事情——他完全可以根据具体的需要,来自主决定用哪种技巧和方法进行叙事和描写,就像他在走出家门的时候,可以自由地选择先迈左腿,或是先迈右腿。
然而,问题却并不那么简单。在一个异常的写作环境里,士人和作家常常被视为一群需要驯服的人。权力会以极其严酷的方式,例如,通过“文字狱”等恐吓性的手段,控制人们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有效地限制作家的叙事边界,规范他们的叙事态度和写作立场,从而获得它所需要的现实效果,实现它所设定的功利目的。所以,很多时候,作家在写作方法上的选择,完全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在技巧的背后,人们可以看见强大的皇权专制,可以看见意识形态诡异的面影。在一个极端形态的专制社会里,真正意义上的幽默和讽刺,是很难看到的;自由而充满个性的抒情和叙事,也是极为少见的。
真理是专制天然的敌人,真相是暴政最大的禁忌。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上都是以勇敢的精神追求真理的文学,以挑战的姿态批判现实的文学,以求真的态度发现和揭示真相的文学。所以,在任何专制主义的写作环境里,现实主义都是一种被敌视和压制的写作方法。也就是说,对现实无节制的粉饰和赞美,是允许的;对琐碎私人生活的近乎无聊的描写,是允许的;玩弄形式主义的“叙事圈套”,也是允许的,但是,真实而客观地叙述苦难和描写真相,却是绝不允许的。
于是,身处艰难境遇的作家,便开始寻找一种安全而有效的方式来写作。每当缺乏最起码的写作安全和表达自由的时候,那种朦胧、含混甚至晦涩的写作方式,就成了许多作家无奈的选择。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在鲁迅看来,这是在英国才有的事情,“古来只能‘道路以目’的人们是不敢的”。于是,许多中国的作家,便只剩下了“瞒”和“骗”两件事可做。可以避开“瞒”和“骗”的老路,从而“分途异治”的办法,大概就是做梦了,即在对梦的象征性叙事中,隐蔽性地完成自己的批判性叙事。
就写作环境来看,就像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所讨论过的那样,明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存条件,无疑是很恶劣的,甚至比蒙元时代的写作环境还要糟糕。
元代的专制统治也很黑暗和严重,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很低,在宋末谢枋得的描述中,是居于社会最底层的:“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其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也,今之儒也。”但是,作家和艺人的自由空间,却要大得多。元代统治的八九十年间,几乎没有搞什么“文字狱”,“只是偶尔闪现一下文祸的影子”,最后也都不予深究,不了了之。
正因为钳制较松,文祸较少,所以,在元代的散曲和杂剧中,才会有尖锐批判现实的锋芒。有的作品,将讽刺的矛头,直接对准最高统治者。例如,《窦娥冤》第三折中“滚绣球”就这样唱道:“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天”和“太阳”这样的意象,从来就是最高统治者的象征。关汉卿如此痛快淋漓诅咒天地,属于严重的“犯上”行为,如果放在明代或别的暴虐时代,他的下场一定会很悲惨。
相比而言,明代社会的思想天空就要黑暗得多,文化生态环境就要恶劣得多。那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前现代社会。它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野蛮和血腥。自由和尊严在这里没有太大的生存空间。理性被奴性的绳子紧紧缚住。用理性的眼睛看世界,用理性的头脑思考生活,用理性的尺度分析和评价生活,都是不允许的。然而,做梦是可以的,醉生梦死,花天酒地是可以的。清醒的生活是危险的,但混沌的生活是安全的。迷离惝恍的梦境,就是混沌生活的象征。汤显祖之所以始终以梦作为自己的叙事内容,就是因为,作为一种不明朗的事象,梦可以被象征化,可以被转化为一种安全而积极的叙事策略,正像汤显祖研究专家郭纪金所指出的那样:“翻开汤显祖的作品集,可以发现包括诗、文、赋、书札、传奇在内的许多作品都有梦幻描写。其中传奇和诗写梦最为突出。”汤显祖喜欢写梦境,写梦境中的奇人异事。梦境中事,子虚乌有,容易打马虎眼,总不至于轻易被按上“诽谤”的罪名,砍了脑袋。
然而,醒着做梦,并不简单,而写梦中之事,也很不容易。
按照19世纪心理学家杰森的解释,梦的发生和内容,似乎并不神秘:“梦的内容往往决定于梦者的人格,决定于他的年龄、性别、阶级、教育标准和生活习惯方式,以及决定于他的整个过去生活的事件和体验。”这显然是一个传统的理性主义释梦者的观点。弗洛伊德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他将分析的解剖刀,探入人的潜意识领域,并将“力比多”当作人的一切行为的最终根源,因而,所谓“梦的内容”,也就不过是“欲望的满足”而已。谚语中问:“鹅梦见什么?”回答:“玉米。”在他看来,“梦是欲望的满足的全部理论都包含在这两句话中了”。他还说,“任何梦都由利己主义的动机所驱使”。而作家的梦,则纯粹是“白日梦”;作家的作品,则“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时代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和代替物”。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也许很深刻,但也很狭隘。因为,人不是鹅,也不只需要“玉米”,成年后,也不总是在继续做童年的梦;而且,更重要的,除了“欲望”,人还有更庄严的思想,更深刻的痛苦和更伟大的诉求。
就汤显祖自己的经验来讲,做梦纯然是一个情感活动,按他的话说,就是“梦生于情,情生于适”。他在《赴帅生梦》的序中说:他的师友帅惟审梦见他来,便在梦中聚饮,由于汤显祖穿着官服,帅惟审就拿了唤作“山巾”的便帽让他戴,结果不大不小,刚刚合适。后来,他们果真见面,帅惟审果真送他“山巾”,山巾他戴着果真合适:“不差分寸,旁客骇叹。”他写了一首很长的诗,记录了这次梦里梦外、虚实相契的美好经验。
总之,用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汤显祖的创作动机和他的作品所表现的主题。因为,在汤显祖的戏剧叙事世界里,梦是一种修辞工具,而剧中人所做的梦,也不过是一个形象体系,一个包含着叙事者的理性设计和修辞目的的形象体系罢了。也就是说,汤显祖笔下的梦,不是本能意义上的“欲望”之梦,并不是对人物的含混梦境的简单记录,而是一个智性的叙事建构和自觉的修辞选择。他要通过对梦叙事的文本建构,来表达自己的生活理念,来曲折地反映自己时代的现实情状,进而实现反讽和劝谕的双重目的。
3)操作严格,人员素质要求高。为保证仪器设备达到理想的性能和精度水平,必须严格规范操作流程。因此,操作这些仪器设备的人员必须要求专业素质高,不仅要懂操作,还需懂得技术,有理论基础。任何不按操作流程操作、超负载、超速设置等的违规行为轻则造成设备损坏,重则影响生命财产安全。
从“临川四梦”的题材来源看,这四部作品全都取材于传说或唐代的传奇——《紫钗记》取材于蒋防的小说《霍小玉传》,《南柯记》取材于李公佐的小说《南柯太守传》,《邯郸记》则取材于沈既济的《枕中记》,《牡丹亭》也与陈玄祐的《离魂记》有点关系,总之,没有一部是直接从当下发生的现实生活中获取写作资源的。然而,这些貌似离奇的鬼蜮故事,却不并虚幻,而是具有丰富的隐喻性,每每使人联想到人间,引发人们的现实性想象。汤显祖在《紫钗记题词》中说:“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芝、曾粤祥诸君,度新词与戏,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词梓之,明无所与于时也。”这里的所谓“是非”和“讹言”,就是其现实性的一种曲折反映。
如果我们从写作风格流变的角度,对汤显祖的四部戏曲作品进行深入考察,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就叙事策略和写作方法来看,汤显祖四部剧作的写实性越来越弱,但是,它们的批判性和现实感,却也越来越强。如果说,《紫钗记》是正剧——“霍小玉能作有情痴,黄衣客能作无名豪,余人微各有致”,《牡丹亭》是悲喜剧——杜丽娘死而后生,虽历磨难,但最终花好月圆,诸事顺遂,那么,《南柯记》和《邯郸记》就大体上可以被视为讽刺剧。它们完全是对现实生活的隐喻性展示,内中充满了尖锐的讽刺和辛辣的嘲笑。
在《南柯记》和《邯郸记》这“后二记”里,几乎全写梦境中事。“人生若梦”,汤显祖赋予这句感叹以更丰富的社会内容。不仅“人生”如梦,而且,一切貌似正大庄严的东西,都无不虚无如梦,荒诞如梦,可笑如梦。汤显祖用“梦境”消解了“神圣帝国”的虚假而夸张的庄严性,否定了帝国中那些傲慢而贪婪的人,嘲笑了蝇营狗苟的虚妄和可笑。透过作者所建构的象征主义的事象,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个社会里,到处都是庸俗和龌龊的人,很少见到高尚和有尊严的人;就精神生活而言,这个社会的人们,并没有摆脱动物性,几乎个个都是欲望的奴隶,都以攫取金钱、名望和利益,作为自己人生的全部目标。米尔斯基说:“果戈理的作品并非客观的讽刺,而是主观的讽刺。其人物并非关于外在世界的现实主义漫画,而是对其内心活动的反省式讽刺描摹。”一切象征主义的讽刺文学,大体上都属于这种主观的讽刺,本质上都是对人物及其时代精神状况所做的“反省式讽刺描摹”。它是主观的,但却是一种积极的策略和自觉的修辞,本质上是真实和深刻的。
在“前二记”,即《紫钗记》和《牡丹亭》里,皇帝还扮演着一个调停者的角色,会在最关键的时候现身,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威,伸张正义,解决问题。例如,在《紫钗记》里,刘节镇就在最后宣读了皇帝的诏书:“皇帝诏曰:朕惟伉俪之义,末世所轻;任侠之风,昔贤所重。每观图史,在意斯人。若尔参军李益,冠世文才,惊人武略,不婚权艳,甚晓夫纲。可封贤集殿学士、鸾台侍郞。霍小玉怜才誓死,有望夫石不语之心;破产回生,有怀清台卫足之智。可封太原郡夫人。郑氏相夫翦桐叶而王,择婿显桃夭之女。慈而能训,老益幽贞。可进封荥阳郡太夫人。卢太尉徒以势压郞才,强其奠雁,几乎威逼人命,碎此团鸾。宜削太尉之衔,以申少妇之气。其黄衣豪客,援钗幽淑女,有助纲常;提剑不平人,无伤律令,可遥封无名郡公。呜呼!凡赞相于王风,皆扬名于白日。受兹勑命。钦哉。”于是,大家“跪听宣读”,皆大欢喜,叩头谢恩。即使《牡丹亭》也未脱此套路。
然而,到了“后二记”里,皇帝就不再被捧得这么高了。不仅如此,作者还将这些最高统治者置于被批判和讽刺的位置,多有讽刺和批评。这说明,随着人生经验的丰富和对现实认识的深入,汤显祖已经不再把那些平庸的皇帝,奉为伟大而智慧的神明。
总之,汤显祖的梦境叙事,是一种自觉的修辞建构,充满了丰富的文化意味和社会内容,包含着尖锐的批判精神和深刻的主题意蕴,值得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和阐释。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0页。
②③胡奇光:《中国文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第90页。
④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8页。
⑤江西文学艺术研究所编:《汤显祖研究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383页。
⑥⑦⑧⑨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页,第115页,第129页,第441页。
(10)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等译,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11)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31—432页。
(12)(13)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8页,第1558页。
(14)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页。
(15)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600—2601页。
作 者: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编 辑:
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