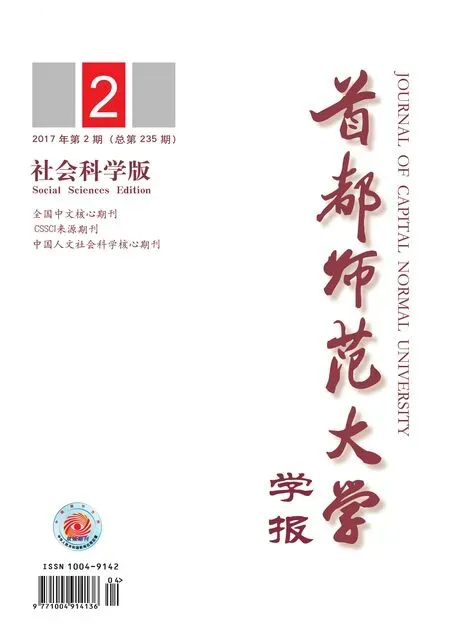晚明西方传教士学术传教的策略与实践——以高一志为中心的考察
2017-06-28王申
王 申
学术传教是晚明西方传教士在华布道的重要策略。既往研究多侧重学术传教的内容[注]代表性的论著有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7-744页),在“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框架内介绍了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内容;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89-1290页)系统讨论了“明末天主教输入什么‘西学’?具有什么历史意义?”;还有冯天瑜《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在华学术活动》(《江汉论坛》,1979年第4期)、樊洪业《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黄见德《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和李志军《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版)等相关著述,都是从科技和人文两方面讨论学术传教带来了哪些西学知识。和特点[注]刘耘华认为学术传教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以事“理”作为论辩的出发点和主要依据;二是主动依附于儒家,并拿儒家词汇作为阐述天主教义理的依托,以期相互说明(《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的学术传教策略及其文化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伍玉西考察了华人在学术传教中扮演重要作用的特点(《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1552-1773)》,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而针对学术传教发展过程及问题的研究主要从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开创之功[注]代表性著作有邓恩(George H.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和孟德卫(David E. Mungello)著、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等,指出了利玛窦等人开创学术传教的贡献。和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对前者的继承[注]庞迪我延续了利玛窦学术传教的路线,代表性的研究有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的反对[注]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和夏伯嘉《天主教与明末社会:崇祯朝龙华民山东传教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均指出龙华民对利玛窦路线的脱离。也有学者认为“龙华民与利玛窦表面龃龉的背后,是前者在传教史的整体中对后者的直接深化与继承,两者路线之间的转换,又可视为双方在谋求传教的‘均衡’运作”(柴可辅:《晚明耶教“民间布道”之考察:龙华民路线的新定位》,《文史哲》,2015年第6期)。展开,忽视了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注]以往学者对高一志的研究侧重他引进西学,主要有金文兵《高一志与明末西学东传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和许苏民《正义即和谐:晚明西方政治哲学的东渐——以“西学治平四书”为主要文献依据的考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而对于他在传教方法上的贡献少有涉及。。本文试图以对高一志所著“修齐治平”系列书籍的分析为中心,考察他从背离到执行学术传教的过程和借实学概念诠释天主教义理的策略,并指出这种传教方式对以后来华传教士传教活动产生的深远影响。
高一志1566年生于意大利,曾用汉文名王丰肃,后改名高一志,字则圣。1605年首次来华传教,因南京教案(1616-1617年)被驱逐出内地。1624年二次入华前往山西传教,期间,他与当地士人合作编刊汉文西书,将天主教化的西学介绍到中国,促进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播,客观上将西方学术介绍到中国。1640年卒于绛州。在高一志所编刊的汉文西书中,“修齐治平”系列书籍所占比重甚大,而学界关注不多。笔者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影印本查得“修齐治平”书籍《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注]《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仅收录后三卷,前两卷影印在《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王宜温和》、《王政须臣》、《治政原本》、《治民西学》[注]《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缺《治民西学》卷之下,可参考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学文本——50种重要文献汇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治民西学卷之下”所收录之部分。计六种。[注]学界一般将后四种合并称之为《治平西学》。
一、高一志从背离到实践学术传教
采取何种方式在中国进行传教,以西班牙籍的桑彻斯(Alonso Sanchez)为代表的耶稣会士主张武力传教[注]桑彻斯称:“我和罗明坚的意见完全相反,我以为劝化中国,只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借重武力。”引自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导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而罗明坚(Michael Ruggier)、利玛窦却主张和平归化。罗明坚、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后,发现书籍对传教来说十分重要。利玛窦指出:“书籍可以到达神父们无法到达的地方,而这个国家,文字比语言能更好地传播我们的圣教,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们的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效力。”[注]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03-104页。因此,刊书传教成为至上的选择,在中国“所有的宗教也是依靠印成的书籍来传播推广,而并非以当众布道或者传授教理的形式”[注]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354页。。同时,“中国人可以随便在家中印制书籍,相当自由,也相当方便”[注]利玛窦著,文铮译,梅欧金(Eugenio Menegon)校:《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第365页。。于是便有了罗明坚编刊《祖传天主十诫》、《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等,开创了耶稣会士在华刊书传教的先例。刊书传教包括两方面,一是刊刻天主教的教义书,二是刊刻西学书籍,后者我们称之为学术传教[注]学术传教指的是传教士为了迎合中国士人对西方学术的需要,通过编刊西方世俗知识的书籍,搞好与中国士人的关系,以求得传教机会的传教策略,这既体现了学术性又具备传播教义的色彩,即知识与教义相结合的传教方法。它是刊书传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上促进了西学在华的传播。。1595年,利玛窦编译《交友论》的刊刻是传教士在华学术传教的开端。[注]朱维铮指出:“利玛窦在肇庆便开始改绘并用中文译注的世界地图,起意必得罗明坚乃至范礼安许可自不待言,而直接目的在于取悦地方长官,并非借学术传教。”见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而《交友论》的编刊,是利玛窦“不得不把著书重点由西教要理移向西学入门”(朱维铮语,同上,第88页)的成果。利玛窦去世后,传教士之间围绕着学术传教与公开宣教进行争论,以庞迪我为代表的传教士主张继续进行学术传教;龙华民却主张公开宣讲福音,进而引发了传教士内部不同传教方式的论争。“耶稣会内部相当于一部分人对于借助传播科学知识为契机来宣传基督福音的做法持有异议。”[注]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第275页。张氏在书中举了龙华民和熊三拔的例子,认为龙华民直到编刊《地震解》时候,才有所转变,而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也是在徐光启的劝说下才参与科技活动。甚至1615年耶稣会中国和日本传教会的省会长瓦伦廷·卡瓦略(Valentim Carvalho)颁布严厉的公告:“禁止使用利玛窦的传教方法,教授数学和哲学的工作也被禁止了。神父们只能专门宣讲福音。他们必须拒绝与修订历书有关的事情,即使是皇帝特别颁布了圣旨也不行。”[注][美]邓恩(George H.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原文收在Daniello Bartoli. 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La Cina. Terza parte dell’ Asia, 安卡拉1841年版,Ⅲ,第232-233页。
1605年,高一志首次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在南京传教期间,他刚开始深居简出,随后的一段时期却公开宣教:
私置花园于孝陵卫,广集徒众于洪武冈;大瞻礼,小瞻礼,以房、虚、星、昴日为会约。洒圣水,擦圣油,以剪字贴户门为记号;迫人尽去家堂之神,令人惟悬天主之像。假周济为招来,入其教者,即与以银。记年庚为恐吓,背其盟者,云置之死。对士大夫谈,则言天性;对徒辈论,则言神术。道路为之喧传,士绅为之疑虑。[注]徐昌治编,夏瑰琦校注:《圣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年版,第78-79页。
高一志等人公开宣讲福音的举动,引起了部分官员的不满,以至于发出“祖宗根本之地,教化自出之区,而可令若辈久居乎?”[注]徐昌治编,夏瑰琦校注:《圣朝破邪集》,第79页。的呼声。1616年爆发教案,高一志等人被驱逐出内地,抵达澳门。在澳门期间,从事于编撰后来印行之汉文著作,并教授神学两年,任学校教习一年。[注][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92页。1624年得以重返中国内地,便进入山西传教。期间,高一志积极与当地士绅合作,编写刊刻汉文西学书籍,根据笔者的统计,高一志在华编刊汉文西书18种,至少15种1624年后(二次入华后)刊刻,8种在绛州刊刻,具体见表1。[注]数据的主要来源是这些文献的影印本和相关书目,包括《天学初函》、《天主教东传文献》、《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续编》、《东传福音》、《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第一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国国家图书馆网站、CCB-Database以及陈伦绪、徐宗泽、费赖之、古郎等人为天主教文献编写的书目等。
由表1可见高一志在华编刊汉文西书的概貌。我们可以按照内容将这些书籍分为宗教和学术两类,其中学术类包括《则圣十篇》、《童幼教育》、《励学古言》、《寰宇始末》、《斐录汇答》、《譬学警语》、《空寂格致》、《达道纪言》、《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西学》十一种,宗教类有《教要解略》、《十慰》、《圣母行实》、《天主圣教圣人行实》、《四末论》、《神鬼正纪》、《推验正道论》七种。从数量上看,前者远超后者;从时间上看,前者多撰写或者刊刻于南京教案之后,即高一志在澳门、绛州期间,尤其在绛州时,大量学术著作被刊刻,也包括少量的宗教类著作。这与南京教案爆发前的高一志形成鲜明的对比。如前文所述,1615年中国和日本传教会的省会长瓦伦廷·卡瓦略正式下达严厉禁止在华传教士传播和介绍西方的数学和哲学思想的命令,高一志在此后的几年里反而从公开宣教转入学术传教,体现了传教士个人的意志和经验在传教中所扮演的角色。高一志对学术传教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不认可到认可的过程,而这种态度的转变与其自身的经验密不可分,是对公开宣教失败的反省和纠偏。
二、学术传教与晚明的实学风气
在对晚明实学或者西学的研究中,以往比较强调以历算、舆地、水利、军事为代表的科学的实学地位和经世价值,而较少关注以“敬天爱人”为核心的天主教伦理作为实理之学的经世内容和意义,西学中的天主教义理与实学的关系还未得到很好的阐释。[注]关于这一问题,学界前辈已经做出具有启发性的探讨,比如: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曾提及“基督实学”的概念,在对杨廷筠的思想行为的研究中,钟氏曾指出后者对“实学”具有不同的见解,即认为天主教伦理也是实学。(钟鸣旦:《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在孙尚扬与钟鸣旦合著的《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一书中,两人也重申了这一观点。(孙尚扬、钟鸣旦:《184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3页)也有学者认为,明末徐光启等人肯定天学,将天学说成实学,是从正人心、救社会这一经世需要出发。(刘志军:《西学东渐与明清实学》,第40-41页)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研究都是建立在中国士大夫对这一解释模式的认同或者再解释的研究上,而忽略了西方传教士如何以实学诠释天学、以迎合当时士人的实学价值取向。对天主教义理如何实学化这一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揭示晚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途径和方式。

表1 样本构成
实学的研究曾经在学界风靡一时,诸多学者各有解说。一般认为,实学的高潮在心学衰落之后。[注]张显清:《晚明心学的没落与实学思潮的兴起》,《明史研究论丛》(第一辑),1982年,第307-338页。李宪堂指出明清实学具有七个层面的含义:“在知识的对象和范围层面上,与注重个体知识积累和人格修养的‘小学’相比,重在实践中探求治国理民之道——比如富国强兵的举措,世风人情的化导、山川形式的规划等等——的经世致用的‘大学’,为实学,可称为‘实功’之学;在知识领域的形而上层面,针对佛道两家大而无当的玄言妄说,切于现世人生的、有关天道性命的学问,为实学,可称为‘实理’之学;在真理探求的路向方面,针对默坐冥想、或高谈阔论的空浮习气,主张在事中求理且达于民生日用的用世之道,为实学,可称为‘实事’之学;从行和知的关系方面,针对墨守师说、记诵章句的教条学问,注重践履和实行的自我成就之道,为实学,可称为‘实行’之学;在知识的内容层面,针对天道性命的抽象义理,讲求有关农兵工商等实用技术的学问,为实学,可称为‘实用’之学;在实践和致知的方法层面,针对直达本源、当下现成的王学,主张由本体而功夫的程朱之学,为实学,可称为‘实本’之学;在经典阐释的方法层面,针对凭空裁断、据臆发挥的学风,强调求音问义、析事考典、追求经典本义的致知之道,为实学,可称为‘实证’之学。”[注]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晚明实学蔚成风潮,同时具有以上各个方面的含义。这种理解上的宽泛性使“实学”接纳“天学”成为可能。
在这种实学高涨的氛围中,西方传教士找到了参与中国文化讨论的突破口和发挥的空间,即迎合实学的需要,编刊西学类的书籍。当利玛窦发现中国士人重视友谊、热衷交友,便作《交友论》,将西方的友谊伦理观介绍到中国;为了满足社会对历算、农业、天文等技术知识的需求,一大批技术性的著作相继译出。这些知识似乎并不构成中西之间文化交流的障碍,但在天主教义理层面的介绍,要困难的多。
传教士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天主教的义理介绍给中国,以求得更多的人归信,这是他们来华的主动力。根据以往的研究,天主教义理的传播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探求天主教的义理与早期儒家的共同点,比如利玛窦所编刊的《天主实义》;二是迎合部分人崇“实”风气,将天主教伦理妆扮成实理之学,满足有志士人医治道德伦理衰退、重整社会秩序的期望。在第一个方面,学界已有较多的研究,第二方面以往多关注中国士大夫认天学为实学的层面,而忽略了传教士如何修饰天学为实学。高一志借助实学的概念去诠释天主教的义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他借助实学介绍天学,拉近天主教与儒家文化的距离,寻求两者之间的认同,同时拓展实学的内容,将晚明士人对实学的追求引领到对天主教的信仰上去,也客观上促进了西学在华的传播。这种诠释方法使中西文化的沟通成为可能,对晚明以降西学的介绍具有范式意义。即传教士将天学或者西学诠释为实学,将天主教义理和西学知识一并传入中国。这有助于解释在传教士所编刊的许多看似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主题的书籍中多有天主教义理的介入的原因,传教士的使命感和中国的现实状况,共同构就了西学知识与天主教教义相结合的西学文本。
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强调:“天学以道德为本。而道德之学又以识天主、事天主为本,有为于此学之学为实学、益学、永学;无为于此学之学为虚学、废学、暂学而已。”[注]阳玛诺:《天问略》自序,李之藻:《天学初函》(第五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2630-2631页。在阳玛诺看来,天学以道德为本,乃为实学。张铠指出,“庞迪我参与中国的科学实践活动‘最主要的是使相当一部分中国士大夫认为“天学”即是“实学”,从而愿意进一步了解基督教的教义,甚至由此而归信了天主教。’”[注]张铠:《庞迪我与中国——耶稣会“适应”策略研究》,第282页。可见,西来传教士以“实学”解“天学”的策略具有一定程度的内在认同性,他们多主张通过迎合部分士人的实学观念去解构天主教的义理,借此传播天主教。
三、高一志“修齐治平”书中所阐发的天主教实学思想
修齐治平是儒家安身立命、成己成人的大学之教,儒家政治思想的总纲领。传教士要中华士人接受教义,必须见诸身心,故主动将教义与修齐治平之学相对接,以便表现出天主教化的修齐治平之学与儒家学说的一致性,甚至超越后者。高一志称修齐治平之学为“义理之学”或“义礼之学”:
所贵义理之学者:曰身、曰家、曰国。人生非止为己生也,兼为家国。然必为己,而后可以为家国也,则身之先修焉必也。盖诸实学,由内及外,由近及远。修身者,剖诸义理、诸德之源也,正邪善恶之界各识所当趋、所当避焉;进而齐家,有居室生殖畜养之事,各识所当取与弃焉;进而治国,有王公、群臣、兆民之宜,各明所当从与戒焉。[注]高一志:《修身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9年版,第19-20页。
高一志把修齐治平之学描述成一种次序性的实践伦理,具有实学致用的功能,强调人不能只为了自己,还要顾及家族和国家,包含着修己、成人,进而为家国的次序,与中国所讲的儒家学说达到高度一致。与高一志同时期来华的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也将西方的“厄第加”(Ethics)学说解释为“修齐治平之学”。[注]艾儒略说:“修齐治平之学,名曰厄第加者,译言察义理之学……”详见艾儒略:《西学凡》,李之藻:《天学初函》(第一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40页。可以说,他们都是在借助儒家的话语去传播天主教化的西方思想观念。
在所著修齐治平书籍中,高一志借助学术传教的方式,通过“实学”诠释“天学”的手段,使天主教的伦理道德以实学的面目呈现,比较注重强调天主教伦理的德性。天主教将德性分为超性德性与伦理德性,其中“超性德性是以天主及天主的完美特性为对象;而伦理德性则是以人及其他造物为对象”[注][德]白舍客(Karl-Heinz Peschke)著,静也等译:《基督宗教伦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85页。。超性德性,主要指的是“信”、“望”、“爱”三德;伦理德性,以“智”、“勇”、“节”、“义”为主:“圣盎博罗修将这四种德性(智、勇、节、义)称为四枢德,因为他认为这四种德性是整个伦理生活的枢纽。圣托玛斯把四枢德视为所有伦理德性的总纲与总目。”[注][德]白舍客著,静也等译:《基督宗教伦理学》,第385页。可见,天主教不仅重视超性德性的意义,还将伦理德性置于重要地位,既关注人对天主的尊崇关系,又重视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天主教的德性论包含着出世与入世两方面的内容,其中对世俗的关怀与儒家的伦理观产生了共鸣。高一志通过这一共同点打通西方的厄第加学说与儒家学说的关联,并将其实学化。
高一志在行文中突出“德”的地位。他强调超性之德,认为统治天下者若要治理好百姓,首先要做到尊奉天主,天主是人的本原,其所立宗教当是人所应当归宿的正道。这相当于在世俗之外,设立一种外在的神秘力量,人们要对这个称作天主的力量保持敬畏和信仰,获得这种超性德性,要做到“信、爱、望”三德。这三德赋予了天主至尊至善的地位,将天主教的信仰观念推介给中国士人,冀图宣传天主教是实实在在的实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实理已经不同于中国儒家所倡导的实理。中国士人关注的是切于现实世界的学问,而天主对他们多是想象的存在。表面上来看,士人的追求与天主教的义理是不相关的,前者多诉求于现世问题的解决,后者钟情于信仰中的天主,但是高一志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将信仰天主变成一种可供操作的程序化的行为,信、望、爱三德规定了信仰天主的仪式,这种程序保证了信仰落在实处,相较于佛道两家大而无当的玄言妄说,便具备了实学性。对程式化实用性的追求,是晚明部分士人实修实学的一个重要表征,部分士人对外在约束的需求已经凸显出来,这个时期流行的功过格也可说明这一点。
高一志重视以“四枢德”为核心的伦理德性,同时把智德放到四枢德的首位。晚明的空谈学风助推社会危机之后,一些士人便开始重新考虑知识的价值,他们广求一切知识资源,去充实空洞务虚的学术,重智是当时实学风气的一个重要特征。发挥多种知识资源的作用,有助于为实学的致用功能奠定基础。正如余英时先生指出:“阳明之后,因王学末流虚言‘良知’,尽废学问,引起学者不满,所以渐渐有人出来重新强调‘道问学’的重要。”[注]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98页。道问学的价值取向使知识的地位得到提升,进而呈现知识与经世的关联,学术的致用功能空前加强。
高一志在强调智的同时,也提出了智德的养成之法,认为智德的养成需要加以训练,智以性生,以习成,要通过“问、读、试、反是”四个环节去习行,“多问、多读、多试,不容一废者也。反者,反身察行之得失者也”[注]高一志:《修身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142页。。这种方法正迎合了实学所具有的“实行”特征,即“从行和知的关系方面,针对墨守师说、记诵章句的教条学问,注重践履和实行的自我成就之道”。[注]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宋代以来,知与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程朱以天理为灯烛,故先知而后行;阳明灵明内具,故知行合一;王学末流则打着知行合一的旗号率性而行。阳明所开拓的知行合一的境界,给传教士们留下了可供渗透的空间,正如朱维铮所提出的:“在阳明所开拓的思想空间内,更易于接受西方所传入的天主教学说。”[注]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第74-80页。
高一志认为义德主诸宜于物,万事主义,包罗甚广:“义德之大功二:率人于巨务,使志邦国之宜,不违公制,谓之公制之义;率人于细事,使均齐彼此之出入,不违正宜,谓之相施之义。”[注]高一志:《修身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205页。义德规定了治天下者的行为,君主要注重仁和义,“以仁善事天主,以义善使国民;以仁修己,以义治物;以仁施惠,以义施刑;以仁为父政,以义为师;以仁尽其情,以义尽其职。仁而无义则政懦软,义而无仁则政厉虐。仁而义义而仁,方政谓有实据,自足保矣”[注]高一志:《治政原本》,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438-439页。。君主既要爱慕天地真主,又要有爱人之德。而爱慕天主在君主之上,因为君主的地位由天主所赋予。这与中国传统的天子在天下的地位是不相符的,但这种将天主纳入到君主“仁”的对象的意义,将中国对苍莽之天的崇拜落实为天主,为天主存在以及应当受到尊奉提供了合法性。其次,要爱世人,关怀百姓,因为这些也是爱天主的表现。同时,君主还要遵守法度,赏罚有道,要亲政主务,不可荒废朝政,这种仁义相成、德性互补的做法与儒家所倡导的内圣外王之道具有某种同质性。但高一志在君主之上赋予一个天主的位置,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这反应了高一志与中国士人实学观念的差异性,至少多数中国士人不会轻易承认有一个教主驾驭在君主之上,而这种差异恰恰是传教士所急于宣扬的。
高一志不仅将修齐治平学说以实学化论述,而且明确提出相应举措,可称之为实功之学。他指出若要国家富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建立以实学为主旨的学校教育,做到:“凡有学问者是宠是举,无学者是置不用,乃学无不将立焉……国中多立学院多宣学师,令民中凡有才有志者任游受业焉……国中多立益书之寓室,以应学者之广用也……非独遍集益书,则无益而非善者必禁之严也。”[注]高一志:《治民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492-499页。为了解决邪书流毒于世、阻碍实学的道路,高一志介绍了西方的书籍审查制度,“吾西诸国立司以查书籍,即凡于道于节、于正政法不和者,必禁不令刊行。凡值私刊私行者,必焚诸市,兼究其工人矣”[注]高一志:《治民西学》,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一册),第500页。。统治者要重视国家建设,必以法律治民,法律的制定要谨慎,有所为有所不为,改变法律要慎重,不可随意变更;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让民众有交易之义,不相互欺诈;要有富民思想,让民众发展生产,禁止奢华,使他们积累财富;关心贫民阶层,在中国引进西方的慈善机构;税收要适度,注重公平,不可过度与民争利;要净化民间风气,鼓励民众和睦友爱,严禁赌博和邪淫。这些举措正迎合了晚明有志之士励精图治的讲实学、建实功的愿望,此即“重在实践中探求治国理民之道——比如富国强兵的举措,世风人情的化导、山川形式的规划等等——的经世致用的‘大学’”[注]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这种讲求修齐治平并能提出具体措施的学说为天学带来巨大的声誉。[注]比如:韩霖所著《铎书》征引了《齐家西学》中大量的语言和思想,作为在地方上宣讲圣谕六言的文本。
值得指出的是,天主教所倡导的“德性不是以人性为中心,这和那些将自我完善为伦理行为的终极目标的伦理观形成鲜明的对比。基督徒的德性以基督为力量源泉,并将基督视为德性的最终目的”[注][德]白舍客著,静也等译:《基督宗教伦理学》,第383页。。而儒家伦理是以自我完善为前提,通过自我完善,将实现对社会的贡献为最终目的。这两者本身存在一定的沟通障碍,而高一志采取的以实学诠释天学的方法,弥合了这种冲突,选择了它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即天主教化的修齐治平学说中所包含的实功、实理、实行思想。这为天主教义理与儒家伦理的联结找到了融通点。
总之,高一志将西方天主教化的厄第加学说与中国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相联接,通过实学观念解释天主教的义理,冀图部分消解后者与儒家学说的差异,减少天主教传入中国的障碍。他试图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引入到天主教化的伦理观念上,在中国传统伦理之上安奉一个天主,将天主教介绍到中国,说明晚明来华传教士在将天主教义理实学化的过程中,对儒家学说既有迎合联接,又有增补。高一志所强调的实学在于通过信奉天主教的伦理使人们的道德臻于至善,并渗透到家族、社会与国家之中。这种实学观念给予当时苦苦追寻实理、实学以求正人心、挽救社会危机的部分士大夫新鲜感。
四、学术传教所激起的影响
由于受个人知识、家庭背景、社会关系、时代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不可否认,明清之际有部分士大夫对天主教的义理持排斥态度,[注]晚明出现了《破邪集》之类的反教文献可证;方以智也提出:“万历季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载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页。而本文所探讨的是天主教义理所激起的正面反应。
高一志在绛州的活动引起了绛州知州雷翀的注意,他称前者为西儒,在雷翀看来,高一志“修身事天,爱人如己,以教忠教孝为第一事,上自圣天子,贤宰相,莫不敬礼之;以致缙绅、学校诸君子,尊之如师傅,爱之如兄弟。百姓从其教者,皆化为良民,其有功朝廷大矣!”[注]参见郑安德编:《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第三卷第二十四册,北京大学宗教所内部出版,2003年版,第27页。有学者认为,雷翀的支持乃是出于引耶入儒的现实考量,希图通过以儒学为主神学为辅的地方教化模式,来应对明末社会所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注]金文兵:《明末地方教化“引耶入儒”的现实考量》,《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3期。换而言之,雷翀接受天主教化的思想是由于后者具有实学的倾向,能够实现经世致用的目的。
同样,以“敬天爱人”为核心的天主教实学思想,也被韩霖所接受。据黄一农考证:“韩霖在《铎书》的字里行间,除提及自己所撰的《救荒书》外,还曾多次直引如高一志的《齐家西学》、《修身西学》、《童幼教育》、《达道纪言》、《神鬼正纪》,以及庞迪我的《七克》、艾儒略的《涤罪正规》、罗雅谷的《哀矜行诠》等耶稣会士的著述。”[注]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韩霖《铎书》对高《齐家西学》、《修身西学》的直接征引,说明高一志所介绍的厄第加学说的直接影响。
“敬天爱人”思想成为《铎书》的主旨,韩霖主张:“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敬天为第一事。”[注]韩霖著,孙尚扬、肖清和等校注:《<铎书>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其次要孝顺父母,然后是君,再次是师。将中国传统中的天、地、君、亲、师之次序,变为天主、父、君、师。天主主宰一切,父母的地位高于君主,这一新思想对传统伦理秩序的颠覆,给传统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冲击。我们现在虽然难以考察这种新观念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晚明社会,但从长时期来看,还是有助传统伦理观念向近代的转型。天主、父的地位高于君,有助于打破对君主的崇拜情结,瓦解君主的权力基础。高一志所传播的天主教思想的影响深度由此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高一志所介绍的天主教实学观念使部分中国士人认识到:天主教化的修齐治平之学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可供操作的实理,有助于解决晚明所面临的社会问题。雷翀将其视为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途径,韩霖寄希望于它能维护地方教化。同时,这些学说也冲击着中国传统的伦理秩序,客观上促进传统思想的转型。
由学术传教所引发的实学诠释天学的策略,打开了天主教在晚明传播的新局面,正如前文所述,这些思想被雷翀、韩霖所接受,并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去,其中韩霖成为天主教教徒,这些中国士人通过自己的交际圈去拓展天主教的空间。他们纷纷出资、出力帮传教士编刊书籍,这里面既包括学术书,也有相当部分的天主教教义书。李之藻甚至将《天主实义》、《灵言蠡勺》等教义书与《七克》、《交友论》、《泰西水法》等等二十种书籍共同结集编成《天学初函》丛书。随着这些书籍的编刊和流传,天主教思想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由于书籍的长效性,即便在禁教时期,天主教思想的传播仍然没有间断,也由于部分书籍所具有的学术性,官方一直给予保留合适的地位,以至被收入《四库全书》。甚至一度引发了晚清来华传教士追寻重刊晚明汉文西书的热潮。[注]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设法弄到了一整套罗马天主教的中文书籍,天主教传教士所建立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重刊了大量晚明的汉文西书。
学术传教为晚清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式,即坚持学术传教的立场,迎合中国的实际需求,满足士人的期待,通过实学诠释天学的策略,将天主教学说实学化。1840年代以后,晚清面临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晚明相比,实学展开的面向有所差异,但经世致用的核心理念却没有变。士人们期待新的思想资源有助于在大厦将倾时力挽狂澜,而当时来华的传教士思考如何因应现实进行传教。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刚开始采取了刊书传教的策略,刊印了大量的基督教的宣传品,但很快导致了非基督教的敌意,为了更好地传教准备,他从1880年至1884年,“花了将近一千英镑用于购买书籍和仪器”,这些书籍除了宗教书籍外,还包括“天文学、电学、化学、地理学、自然史、工程学、机械学类;医药学及各类产业学;名民族的历史;亚洲文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那时,每一册都用锡金装着,价值30先令);《钱伯斯百科全书》;等等”。[注][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后来参与中文报纸的编辑,发表关于中国改革的建议;筹建山西大学、并在上海成立翻译部,为山西大学准备教材。[注][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196、292、293页。他还与蔡尔康合作翻译了《泰西新史揽要》,参与广学会的翻译活动。可见,传教士在晚明与晚清遭受到同样的困境,寻求解决的办法也多是通过学术传教的方式赢得中国士人和官方的信任,进而打开传教的局面。[注]尽管晚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保障传教权的条约,但这并不能促成西方宗教在华的传播,唯有获得精神上的信任和文化上的理解,才能铺就通往信仰基督的道路,这是传教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从晚明到晚清,传教士所采取的学术传教的立场、实学诠释天学的策略,构成了传教士在华“适应策略”的主要内容。而晚明时期所建立的传教策略与实践,为以后传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树立了范式,甚至影响到今天基督教(天主教)在华的活动。对中国社会而言,它客观上促进了西学在华的传播,为近代社会转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