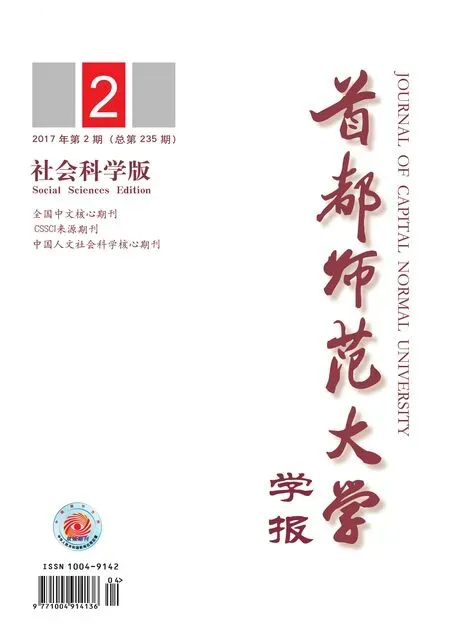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验证及修正:以典型职业群体为例
2017-06-28石长慧王卓妮
石长慧 王卓妮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刻板印象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认知图式,它是对某一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的特质、品性和行为的固定化或模式化的看法和信念。[注]Hilton, J. L. and von Hippel, W. Stereotyp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6, 47: 237-271.最初对刻板印象的研究聚焦于“人们对某一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是什么”,研究者普遍采用形容词列举选择法(卡茨-布莱利法)来确定目标群体的特征,由此形成对该群体的刻板印象。[注]Katz, D. and Braly, K. Racial stereotypes of one hundred college students.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33, 28 (3): 280-290.此后,研究者开始关注导致刻板印象的动机驱力与心理过程,以及刻板印象的社会学习和社会强化机制等,对刻板印象产生的原因、影响因素和后果等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探索。[注]王沛:《刻板印象的社会认知研究述论》,《心理科学》1999年第4期,第342—345页; Gilbert, D.T., Fiske, S.T., Lindzey, G.(eds).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4th ed). Boston:McGraw-Hill, 1998:357-411.
近年来,关于刻板印象的研究又重新开始关注刻板印象的内容。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刻板印象的内容结构维度,[注]Anderson, C.A., Sedikides, C. Thinking about people:Contributions of a typological alternative to associationistic and dimensional models of person percep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1,60:203-217; Edwin, P, Hub, L. In-group favoritism and the reflection of realistic dimensions of difference between national stat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nationality stereotyp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999,38:85-102.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菲斯克等人提出的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SCM)。该理论模型认为,虽然个体对不同社会群体成员有着不同的刻板印象内容,但是这些内容可由热情(warmth)与能力(competence)两个维度所概括。其中,热情是对知觉对象的意图感知,具体包括友好、值得信任、助人、真诚和道德等方面;能力则是对知觉对象实现该意图的能力状况的感知,具体包括智力、效能、技能和创造性等方面。[注]Fiske, S. T., Cuddy, A. J. C., Glick, P., & Xu, J. A model of (often mixed) stereotype content: Competence and warmth respectively follow from perceived status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6), 878-902; 佐斌、代涛涛、温芳芳、滕婷婷:《热情与能力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9期,第1467—1474页。
SCM模型提出了四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假设[注]Fiske, S. T., Cuddy, A. J. C., Glick, P., & Xu, J. A model of (often mixed) stereotype content: Competence and warmth respectively follow from perceived status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6), 878-902; Cuddy, A. J. C., Fiske, S. T., V. S. Y. Kwan, et al. 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across cultures: Towards universal similarities and some differenc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9,48:1-33.:(1)双维结构假设:认为可以通过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来区分群体,从而确定各类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2)混合评价假设:认为大部分群体的刻板印象是混合的,即群体在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的评价方面存在显著差异。(3)社会地位假设:认为群体的社会地位可以预测刻板印象。具体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地位与能力呈正相关,“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能力也越强”;二是竞争性与热情呈负相关,对于与本群体有竞争关系的群体,通常会被认为缺乏热情,或者说,在热情维度上会被给予较低的评价。(4)群体偏好假设:认为在热情和能力两维上,人们对于自身所属群体(即内群)会存在给予更高评价的偏好,即呈现内群偏好(ingroup favoritism);相应地,会给予外群体较低的评价,即产生外群贬抑(outgroup derogation)。
SCM模型在不同群体、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研究中都得到了广泛的验证,[注]佐斌、张阳阳、赵菊、王娟:《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理论假设及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1期,第138—145页。显现出很好的文化普适性和群际关系预测性。与此同时,它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刻板印象内容的维度问题。学者们认为,刻板印象的内容不只由能力和热情双维度组成,可能还有其他诸如道德、社会性等多种维度。[注]陈晶、佐斌、周少慧:《5~16岁儿童对中国人的评价与喜好研究》,《心理科学》2004年第4期,第833—835页; 郑健、刘力:《大学生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内容与结构》,《青年研究》2012年第4期,第35—44页。虽然菲斯克等人认为SCM模型中热情维度的内涵已经包括了道德,[注]Fiske, S. T., Cuddy, A. J. C., & Glick, P.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social cognition: Warmth and competenc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7,11(2), 77-83.但是学者们仍然发现,道德的重要性足以使其与能力和热情的其它内涵相并列,而成为刻板印象内容的第三个维度。[注]Leach, C.W., N. Ellemers, and M. Barreto. Group Virtue: The Importance of Morality (vs. Competence and Sociability) in the Positive Evaluation of In-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ersonality,2007,93(2): 234-249; Brambilla, M., Rusconi, P., Sacchi, S., & Cherubini, P. Looking for honesty: The primary role of morality (vs. sociability and competence) in information gather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1, 41(2), 135-143.此外,SCM模型仅仅局限于发现事实,没有对刻板印象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解释,这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注]高明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修正与发展:源于大学生群体样本的调查结果》,《社会》2010年第5期,第193—216页。
自SCM模型提出以来,我国也开展了一些与之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综述性文章,介绍了SCM模型的产生背景、理论假设与相关研究;[注]佐斌、张阳阳、赵菊、王娟:《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理论假设及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1期,第138—145页;佐斌、代涛涛、温芳芳、滕婷婷:《热情与能力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9期,第1467—1474页;管健:《刻板印象从内容模型到系统模型的发展与应用》,《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4期,第845—851页;汪新建、程婕婷、管健:《解析群际偏见——基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认知神经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173—180页。第二类是借鉴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对特定的社会群体包括独生子女[注]包蕾萍:《中国独生子女刻板印象:结构、来源和后果》,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残疾学生[注]刘嘉秋:《师范生对残疾学生的刻板印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和日本人[注]张燕、高红梅、王芳、许燕:《北京学生对日刻板印象及3·11地震后的情绪和援助意向研究》,《心理学探新》2013年第3期,第225—233页。等刻板印象的考察;第三类是关于SCM模型理论假设验证的实证性研究。其中,管健和程婕婷对SCM模型的前三个假设进行了验证,认为SCM模型对我国的社会群体有很好的预测作用,热情和能力可以作为考察中国人刻板印象内容的两个基本维度;[注]管健、程婕婷:《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确认、测量及卷入的影响》,《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年第2期,第184—188页。高明华则发现,我国大学生对典型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的感知和评价围绕“能力-道德”两个维度展开,且相对于能力,道德居于更主导的地位;另外,人们并不是对每个维度上的内群体都存在内群偏好;[注]高明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修正与发展:源于大学生群体样本的调查结果》,《社会》2010年第5期,第193—216页。郑健和刘力通过考察大学生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内容,发现“热情”与“能力”维度并不在其中,因此认为,刻板印象内容模型在我国不具有普适性。[注]郑健、刘力:《大学生对农民工的刻板印象内容与结构》,《青年研究》2012年第4期,第35—44页。
总的来看,目前国内关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研究还较少。同时,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关于SCM模型在国内是否具有普适性,学者们还存在较大的争议。此外,目前国内关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验证性研究还存在研究程序问题。无论是管健和程婕婷的研究[注]管健、程婕婷:《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确认、测量及卷入的影响》,《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年第2期,第184—188页。,还是高明华的研究[注]高明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修正与发展:源于大学生群体样本的调查结果》,《社会》2010年第5期,第193—216页。,都是以大学生作为评价主体(被试群体),且样本较少,尽管在他们的研究中,研究者都要求大学生被试推断社会中大多数人(而不仅是自己)对于某一群体的评价,但是样本的单一性仍然使得对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验证大打折扣,无法推论到社会公众的总体。另外,在被评价群体的选择方面,二者的研究都是通过评价主体自由列举的方法来收集被评价群体。它的优点在于增加群体的多样性,但是其弱点在于被评价群体在成员身份之间具有很大的重叠性,如两个研究中都被列举为被评价群体的老人、女人、富人、大学生等群体成员完全可能交叉。这些群体在热情和能力双维中的分布,在应用到具体的现实群体成员时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在不存在成员身份重叠的群体中进行验证。[注]佐斌、张阳阳、赵菊、王娟:《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理论假设及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1期,第138—145页。
鉴于上述关于SCM模型的验证性研究存在的缺陷,本文提出并试图回答的研究问题是:在我国,SCM模型在以社会公众为评价主体、以典型职业群体为被评价群体时是否能够得到验证?本研究尝试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并对刻板印象内容模型进行验证及修正。
二、研究假设
关于刻板印象的内容到底由几个维度构成,目前国内外的研究都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本文沿用SCM模型关于刻板印象内容包括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的理论框架,对前述SCM模型的后三个假设进行验证。此外,笔者还将验证与SCM模型相关的关于修正刻板印象的相关假设。
(一)关于混合评价假设
有学者认为刻板印象可以划分为纯粹型刻板印象和混合型刻板印象(又称矛盾型或补偿型)。所谓纯粹型刻板印象(pure stereotypes),是指社会群体在两个(如热情和能力)或多个评价维度上处于相同的位置,例如,认为能力强的群体其热情程度也高。而混合型刻板印象(mixed /ambivalent/complementary stereotypes),是指社会群体在两个维度上被给予相反的评价,呈现出“此高彼低”的特征。[注]高明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修正与发展:源于大学生群体样本的调查结果》,《社会》2010年第5期,第193—216页。如前文所述,菲斯克等人认为,人们对大多数群体的刻板印象属于混合型,[注]Fiske, S. T., Cuddy, A. J., Glick, P., & Xu, J. A model of (often mixed) stereotype content: Competence and warmth respectively follow from perceived status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6), 878-902.由此我们得到假设:
假设1:个体对大多数群体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一高一低”的特征。
(二)关于社会地位相关假设
菲斯克等人认为,群体的社会地位可以显著预测其能力值,而群体的竞争性可以显著预测其热情度。[注]Fiske, S. T., Cuddy, A. J., Glick, P., & Xu, J. A model of (often mixed) stereotype content: Competence and warmth respectively follow from perceived status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6), 878-902.由于数据所限,本文只检验其中社会地位是否能预测能力的假设。需要说明的是,在SCM模型的验证研究中,菲斯克等人用声望、经济成功和教育三个观测变量整合为整体上的“社会地位”变量来预测能力。而此前的许多研究表明,教育和经济成功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注]李春玲:《文化水平如何影响人们的经济收入——对目前教育的经济收益率的考查》,《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64—76页。因此,用声望、经济成功和教育三个变量来合成“社会地位”变量可能不是很好的选择。根据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声望、收入和权力是划分社会阶层的三个核心指标。[注]Bendix, Reinhard. Max Weber: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因此,本文选择用声望、收入和权力三个观测变量来分别验证它们对能力的预测性。由此得到假设:
假设2a:群体被感知的声望越高,其获得的能力评价也越高。
中医学认为,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病理基础是痰浊和瘀血,因此治疗中常常贯彻活血化瘀和祛痰消浊。护心康主要具有消痰散结和活血行瘀的作用,在临床冠心病的治疗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研究发现:护心康对痰瘀阻络型冠心病具有较好的疗效,能有效改善心绞痛的发作症状和心电图表现[9];同时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10]。护心康可以降低冠心病患者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和sICAM-1水平[11],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是判断炎症的灵敏指标,其表达下降可以降低单核细胞分泌炎症因子;血清sICAM-1含量降低可以减少炎症反应导致的细胞黏附,护心康通过降低二者的表达,减轻炎症反应,延缓冠心病的发生发展。
假设2b:群体被感知的收入越高,其获得的能力评价也越高。
假设2c:群体被感知的权力越大,其获得的能力评价也越高。
(三)关于群体偏好假设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为了抬高自己所属群体的身价和提高自尊,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人们会争取把自己编入较优越的社会群体,并对群体内成员给予更积极的评价,表现出内群偏好;同时内群体成员会贬抑外群体,将负面的评价给予外群体,表现出外群偏见(outgroup bias)。[注]Hogg, M. A and Abrams, D. Social Identificatlons: 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在菲斯克等人的研究中,内群偏好表现为评价者在热情与能力维度上对内群体的评价分值普遍高于其他群体,而外群偏见或外群贬抑表现为对外群体能力与热情的评价中至少有一个维度的评价分值会明显低于内群体。由此我们得到假设:
假设3:个体在热情与能力维度上对内群体的评价分值普遍高于其他群体。
(四)关于刻板印象修正假设
此假设与群体偏好假设直接相关。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划分群体的维度是多种多样的,根据不同的维度,如年龄、性别、民族、职业等,我们可以区分出多种不同的内外群体。因此,内外群体的边界是模糊、动态的,而不是固定的。根据群际接触理论,群际偏见源于某一群体对另一群体缺乏充足信息或(和)存在错误信息,而群际接触则为获得新信息和澄清错误信息提供了机会。因此,群体之间的接触有利于减少群际偏见,对外群体被美化或被丑化的刻板印象起到“修正”作用,[注]Ben-Ari.R, Amir.Y.Intergroup contact,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change in ethnic attitudes. In W.Stroebe, A.W. Kruglanski, D.Bar-Tal, M.Hewstone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Berlin:Springer,1988:151-165甚至找到认同,在其他维度上形成新的内群体。由此可以推论,群际接触会修正人们对于外群体的刻板印象。据此,本研究在SCM模型假设的基础上,得到了刻板印象修正假设:
假设4:经常接触和从不(或很少)接触被评价群体的两类个体,对被评价群体能力与热情维度的评价会存在显著差异。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于由中国科协委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于2011 年7-10月实施的“我国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公众形象调查”项目。本次调查在综合考虑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各地区的人口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选取5个地区,在每个地区的市区和一个下辖的农业县/县级市的农村地区进行抽样调查。这5个地区分别是:北京、泉州、郑州、荆州和兰州。在城市,课题组随机选取社区,而后在社区中采用等距抽样方法选择家庭户,在家庭内用Kish表选取出受访者进行面访;在农村,课题组随机选取村庄,而后在村庄内按建筑物画图编制抽样框,随机抽取家庭户,进行入户问卷调查。所有调查对象均要求在当地连续居住3个月以上且年龄在18周岁以上。调查共回收问卷4843份,其中有效问卷4659份,有效回收率为96.2%。最后汇总统计时均按当年各地区的人口规模和城乡人口比例对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调查样本的构成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构成
(二)研究方法
在问卷调查中,我们要求被调查者对11个群体的特点在Likert5点量表上进行评价。1-5分表示该特点由弱到强,例如“1”代表“能力很差/非常不热情”,“5”代表“能力很强/非常热情”。为了减轻调查对象的疲劳感,我们把问卷分成了A、B两类,每类包含7个群体,其中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三个群体在两类问卷中都出现,另外8个群体分两组分别出现在A、B卷中。最后回收的A卷为2441份,占52.4%;B卷为2218份,占47.6%。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混合型刻板印象
依照SCM模型的典范研究程序,[注]Fiske, S. T., Cuddy, A. J., Glick, P., & Xu, J. A model of (often mixed) stereotype content: Competence and warmth respectively follow from perceived status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6), 878-902.我们首先在群体层次上对各群体的能力与热情得分值进行分析(见表2)。如表2所示,11个群体中以科学家的能力得分值为最高(4.16),文体明星的能力得分值为最低(3.23)。以记者的热情得分值为最高(3.42),公务员的热情得分值为最低(3.18)。总体而言,11个群体的能力和热情得分值都大于中位值(3),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将其称为高能力高热情群体或社会优势群体。
我们以群体为单位,用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比较各群体能力和热情得分值的差别。从表2可以看出,除了技术工人的能力得分值略低于热情得分值之外,11个群体中有10个群体的能力得分值都高于热情得分值。进一步分析表明,在11个群体中,有7个群体的能力-热情评价在P≤0.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1个群体在P≤0.0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只有3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不显著。由此可知,在群体层次上,假设1得到验证,即大多数群体的刻板印象属于混合型。

表2 群体层次的能力与热情得分及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注:上表第二、三、四列分别为每类群体的能力和热情得分值以及能力得分均值-热情得分均值。第五列和第六列为技术工人群体评价的每类群体的能力和热情得分值。*P≤0.05,**P≤0.01,***P≤0.001,下同。

图1 聚类分析图
我们进一步采用系统聚类法对11个群体的能力和热情得分值进行聚类分析,选择组内联结法为聚类方法,结果显示:11个群体可以聚成四类。第一类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相对而言,可以称为高能力高热情群体;第二类为军官、民营企业家、记者和医生,可以称为高能力低热情群体;第三类为中学教师、技术工人和农技推广人员,可以称为低能力高热情群体;第四类为公务员和文体明星,可以称为低能力低热情群体(见图1)。
在类别层次上,我们同样通过配对样本t检验方法比较了各类别的能力和热情得分值的差别。统计结果发现(见表3),四个类别的“能力”和“热情”均值都有显著差异,都是能力大于热情,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由此可知,在类别层次上,假设1同样得到了验证。

表3 类别层次的能力与热情得分及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二)社会地位对能力的预测
为了验证社会地位变量对能力的预测作用,本研究同时分析了群体层次的数据(即对11个群体的数据分别进行分析)和总体层次的数据(即11个群体合并后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见表4),在群体层次上,11个群体的声望、收入和权力评价,在P≤0.05的水平上都与能力评价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在对能力的预测方面,声望和收入对能力的预测力高于权力。
本研究同时发现,社会地位变量对热情也有预测作用。在对热情的预测方面,11个群体中,全部群体的声望与热情评价在P≤0.05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除了技术工人之外,其他10个群体(91%)的收入与热情评价在P≤0.05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有8个群体(72.7%)的权力与热情评价在P≤0.05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在对热情的预测方面,声望对热情的预测力高于收入和权力。

表 4 社会地位对能力和热情的预测作用
注: 表中百分比表示在11个群体中两变量之间显著相关(P≤0.05)的群体比例,群体层次上的r表示两变量有显著相关的群体的平均相关系数。
总体数据显示,声望、收入和权力评价,无论对于能力评价还是热情评价,都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综合群体层次和总体层次的分析结果可知,社会地位与能力评价存在显著正相关。群体被感知的声望、收入越高,权力越大,被感知的能力值也越高。假设2a,2b,2c都得到了验证。
(三)群体偏好
在本部分的研究中,我们从全体被调查者中选取出职业为技术工人的群体为评价主体来检测群体偏好假设。如表2(第五列和第六列)所示,技术工人群体对内群体的能力评分值为3.27,排在11个群体的最后一位;对内群体的热情评分值为3.43,仅低于农技推广人员(3.45),排在11个群体的第二位,且与农技推广人员之间的热情评分差值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技术工人群体对内群体的评价存在两个极端,即在能力维度上对内群体的评分最低,而在热情维度上对内群体的评分最高。这一发现不同于SCM模型所提出的个体在热情与能力维度上对内群体的评价分值会普遍高于其他群体的观点,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
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在于,在菲斯克等人[注]Fiske, S. T., Cuddy, A. J., Glick, P., & Xu, J. A model of (often mixed) stereotype content: Competence and warmth respectively follow from perceived status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2(6), 878-902.和高明华[注]高明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的修正与发展:源于大学生群体样本的调查结果》,《社会》2010年第5期,第193—216页。的研究中,评价主体(被试)都是大学生群体,他们是受着高等教育、年轻热情有活力的“天之骄子”,无论是自我评价还是被他人评价,他们是在能力和热情维度上都会得到高分值的社会优势群体。因此,他们在评价内群体时在能力和热情维度上都给予高分值,可能是一种客观的评价,而不能简单视为一种对内群的“偏好”。而本研究中的技术工人群体,相对于其他10个群体,在社会中并非处于优势地位,甚至处在社会劣势的位置,因此他们对内群体至少在能力维度的评价,可能更接近于客观,没有出现“偏好”的现象。
事实上,本研究的发现更支持朱斯特等学者提出的系统正当化理论(system justification theory)[注]Jost, J. T. and Banaji, M.R. The Role of Stereotyping in System-justif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False Consciousne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4,33(1): 1-27.,即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其中的成员同时表现出内群偏好与外群偏好(outgroup favoritism)。[注]Jost, J. T. Outgroup Favoritism and the Theory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An Experimental Paradigm for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uccess on Stereotype Content. in Moskowitz, G. (Ed.), Cognitive Social Psychology: The Princeton Symposium on the Legacy and Future of Social Cognition.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 89-102.弱势群体成员在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能力维度上会给社会优势群体更高的评价,表现出外群偏好;而在与社会经济地位不相关的其他维度,如热情、道德等维度上则表现出内群偏好,以平衡自身在社会经济地位维度上对内群体的消极性社会认同。[注]Mullen, B.;Brown, R. and Smith, C. Ingroup Bias as a Function of Salience, Relevance, and Status: 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2, 22(2):103-122; Jost, J. T. and Burgess, D.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Group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Motives in Low Status Grou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0,26(3):293-305.通过在与社会经济地位不相关的其他维度上得到补偿,弱势群体接受并顺从了既存社会系统的分配与安排。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的假设3没有得到检验。而对于SCM的内群偏好假设,我们认为或可修正为:社会优势群体的成员,在热情与能力维度上对内群体的评价分值会普遍高于其他群体,表现出内群偏好,社会弱势群体的成员,对内群体在能力维度上的评分会低于其他群体,表现出外群偏好;而在热情维度上的评分会高于其他群体,表现出内群偏好。
(四)刻板印象修正
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询问“你的家人、亲戚、朋友或熟人中,有没有人在从事以下工作”这一问题来测量被调查者是否经常接触被评价群体。[注]在这里我们将家人、亲戚、朋友或熟人中“有”视为“经常接触”被评价群体;而“没有”则视为没有(或很少)接触过被评价群体。严格说来,即使家人和亲戚中有被评价群体,被访者也可能没有或很少接触过他们;而相应地,即使家人、亲戚、朋友或熟人中没有被评价群体,被访者也可能经常接触被评价群体,如频繁去医院看病而经常接触医生群体。因此,这里只是一种非严格的、近似的划分。然后用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比较经常接触与没有(或很少)接触过被评价群体的人,对被评价群体在能力和热情维度上评价的差别(见表5)。从表5可以看出,在能力维度上,在11个群体中,只有对技术工人能力的评价,经常接触的人高于没有(或很少)接触的人,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其中9个群体的能力评价,经常接触的人打分低于没有(或很少)接触的人。总体而言,对6个(54.5%)群体的能力评价,经常接触的人与没有(或很少)接触的人存在显著差异。

表5 各群体能力与热情得分及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注:上表第二、三列分别为家人、亲戚、朋友或熟人中有被评价群体和没有被评价群体的人对被评价群体能力的评价,第四列为两类人能力评价的差值。第五、六、七列为相应的热情评价及差值。
在热情维度上的评价则表现出非常不同的状况。在11个群体中,对其中7个群体的热情评价,经常接触的人打分高于没有(或很少)接触的人,且其中对5个群体的评价差异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总体而言,对6个(54.5%)群体的热情评价,经常接触的人与没有(或很少)接触的人存在显著差异。
综合对能力和热情维度的评价可知,对于大多数群体来说,经常接触与没有(或很少)接触该群体的人,他们对该群体在能力与热情维度上的评价会存在显著差异,假设4得到验证。我们认为,经常接触某个群体,会形成对该群体的客观认识,因此,对于大多数群体而言,群体之间的接触确实有利于减少刻板印象。但是这种“去刻板印象化”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修正机制。对于本研究中的社会优势群体(如科学家、医生等)而言,经常与人接触会让他们在能力维度去神秘化,削弱人们对他们能力的拔高和美化;而在热情维度上,无论是社会优势群体还是社会弱势群体,经常与人接触会让群体显得更加亲和而友好。
五 结论及讨论
本文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以城乡居民为评价主体、以典型职业群体为被评价群体,对刻板印象内容模型进行了验证及修正。本研究发现,SCM模型关于混合刻板印象评价和社会地位可以显著预测群体能力的假设得到验证,即大多数群体的刻板印象属于混合型刻板印象,群体被感知的声望越高、收入越高、权力越大,其获得的能力评价也越高。但是SCM模型的内群偏好假设没有得到验证,本研究认为该假设可以修正为:社会优势群体的成员在热情与能力维度上都表现出内群偏好;而社会弱势群体的成员在能力维度上表现出外群偏好,在热情维度上表现出内群偏好。在SCM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还验证了刻板印象修正假设,发现对于大多数群体而言,群际接触确实有利于减少刻板印象,对外群体被美化或被丑化的刻板印象起到“修正”作用。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之前国内外的大多数研究,大多以大学生为评价主体,而本研究则以城乡居民为评价主体,这样避免了群体的单一性所导致的SCM模型适用范围的局限。而正是通过选择以技术工人群体为评价主体,本研究发现了与SCM模型不同的关于群体偏好的新的假设。当然,这一假设是否成立,有待于未来更多研究的验证。
本研究另外的独特之处在于,选择典型的职业群体为被评价群体,避免了之前的研究中被评价群体的成员在身份之间存在交叉和重叠的缺陷。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本研究的11个被评价群体中大多数群体和之前的研究一致,有较大的典型性,但是选取群体的方法仍然稍显随意。此外,在研究程序上本文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比如对于“是否经常接触被评价群体”这一问题,可以问得更为直接而具体。
此外,在理论演进方面,菲斯克等人在SCM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SCM与群际情绪、行为反应相结合,发展出了刻板印象-群际情绪-行为趋向系统模型(BIAS Map,偏差地图)。[注]Cuddy, A. J. C., Fiske S. T., & Glick, P. The BIAS Map: 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92(4): 631-648;管健:《刻板印象从内容模型到系统模型的发展与应用》,《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4期,第845—851页。而我国学者指出了这一模型对社会结构(包括社会地位与群际竞争性)加以操作化方面存在的缺陷,改之以地位感知与合法性表征为基础,尝试把偏差地图模型修正为心态地图模型。[注]方文:《中国非信徒和基督徒的心态地图比较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第61—74页。无论是偏差地图模型还是心态地图模型,其适用性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加以验证。本研究由于数据所限,没有纳入评价主体对于被评价群体的情感取向及行为趋向,因此无法对其进行验证分析。这是将来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开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