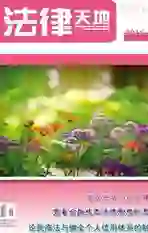《商标法》第63条的理解与反思
2017-06-19何江龙
何江龙
摘 要:我国知识产权法是否引进适用惩罚性赔偿讨论很有争议,而2013年修订的《商标法》第63条作出了立法上的回应。本文对其所涉及的赔偿模式、倍数赔偿、法定赔偿及与《专利法》第65条、《著作权法》第49条的关系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梳理,以期能够发现我国的知识产权赔偿上存在的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倍数赔偿;法定赔偿
201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模式和要求,在原来的赔偿模式上进行了相应的增加和修改,并且新增了惩罚性赔偿,这样与我国的现行的《专利法》第六十五条和《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有很大程度上的切合性,但又有所不同,尤其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提出,条文的背后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上述三条文都是关于知识产权侵权的赔偿问题的规定,而且商标法改变了原来的选择性侵权获益赔偿模式而适用了补充性侵权获益赔偿模式,与一些学者之前关于赔偿模式的主张有所不同①。这两种赔偿模式都属于补偿性赔偿的下位概念,区别仅在于被侵权人是否享有选择权,即受害人是否可以在实际损失和侵权收益之间做选择,而三个法条的高度统一看出立法者旨在让当事人获得补偿,而非惩罚侵权人,这与私法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精神相契合。
然而,我们所谓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惩罚并非公法意义上的惩罚,这儿的惩罚性仅指赔偿大于损害的情况。对于侵权获益大于实际损害的情况以及法院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裁量的情况皆有可能赔偿大于损害,尽管一般情况下侵权人的所得可能会低于被侵权人的所失,如小偷窃取一部手机后变卖,其所得远远低于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但是注意到这里的实际损失是需要证明的,而在知识产权领域,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往往是很难证明的,所以其证明的实际损失也是很低的,而且侵權人的所得相对比较容易证明,故而其所证明的实际损失常常会低于其所证明的侵权获益。所以可以说把侵权获益作为赔偿的基准是具有惩罚性质的,而且对侵权人利益的剥夺本身也是一种惩罚,但与公法意义上的惩罚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商标法》第六十三条和《专利法》第六十五条都规定了倍数赔偿,学者大多认为这是惩罚性赔偿模式,其一、在适用条件上,实际损失和侵权获利都难以确定才能适用该规定。但是,根据统计,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是按倍数或者法官自由裁量来判的,而真正能确定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的案件很少,因而决定了知识产权侵权在我国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社会需求。其二、倍数的基数是该专利或商标的“许可使用费”,然而,怎么确定该许可使用费呢,显然,这只是对于那些已经许可使用过的专利或商标而适用的,对于未许可的专利或商标,只能作许可使用费不能确定的情况来处理。而外国则有别的一些做法其实我觉得我国也可以借鉴,如美国在许可使用费的计算中就设计了虚拟谈判法、结构法和分析法等,其中所考虑的各种因素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比较赞同虚拟谈判法,假设专利权人与侵权人在侵权发生时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自愿达成的令双方都满意的许可费数额。当然,把这种思路应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中亦无不可。
再者,新《商标法》还新增加了一至三倍的赔偿模式,这是《专利法》和《著作权法》中没有涉及的,这种制度的引进和群众的呼声是相关的,在关于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相关的近几年的博硕士论文和大量的期刊中,笔者们都赞同引进倍数赔偿模式,并且从经济学、法理学、社会学等各个角度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当然这种惩罚性赔偿的模式是有适用前提的,核心是主观恶意,也即是说之所以惩罚是因为侵权人的恶意,这很显然突破了传统私法的补偿性赔偿理论,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制度引进的合理性——侵权人之所以明知故犯,一方面是高额利润的诱惑。另一方面是侵权人理性的衡量,当侵权收益大于成本(包括机会成本)的时候,商人也就都会选择侵权,这样不仅达不到立法目的,也损害社会的发展。而适用惩罚性赔偿则大大增加了其机会成本,侵权可能性就必然会减少。
然而这种模式是否完全合理呢,就我国当前的知识产权侵权而言,绝大部分是没有独立研发能力的小微企业,甚至是个体工商户、家庭作坊等,他们的经济实力薄弱,如果按许可使用费的倍数赔偿,许多专利或商标的赔偿额都是惊人的天文数字,那么这些侵权人无力也不可能赔偿,即使其倾家荡产。那么这样的判决便失去了执行力和公信力,这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对于大企业而言,赔偿那些“白菜价”的许可使用费的一至三倍的赔偿额只是九牛一毛,完全达不到惩罚的效果。所以如何规定,如何适用还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最后、对于法定赔偿金的规定,三个条款都做了相应的规定,但数额幅度略有不同,《商标法》是三百万元以下,《专利法》规定是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著作权法》则是五十万元以下,我们看到在《商标法》未修改之前也是五十万以下,专利法之前没有规定,著作权法一直没变。共同点是三个都规定了上限,不同的上限表示其价值判断的不同,但在信息革命的今天,把软件归为作品,然后确定上限50万还是否合适,我们知道的如三星、微软、谷歌、腾讯等等涉及软件的案子的标的都是过亿了,而对于上限之设定,目的是避免天价赔偿案,尤其是赔偿基数就很高的案件,再乘以倍数,结果明显不合理。
而不同的是只有专利法规定了下限,我们知道知识产权的侵权诉讼案件时间长,成本高,难证明和计算等,而司法实践中的许多知识产权侵权的判决赔偿数额很低,以致出现了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我很难相信如400元、240元的赔偿能填平受害人的损失,更不用说惩罚性了。故而我个人认为对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设定下限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商标法》第65条的修改可以说是我国知识产权赔偿模式进步的一个体现,然而对于上述所涉的几点问题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有必要在立法中进行完善也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当然,也需要结合社会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具有一定的法律价值。
注释:
①孙国良《知识产权侵权获益赔偿的立法模式的选择—以现行法为分析对象》一文中明确肯定了选择模式而否定了补充模式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