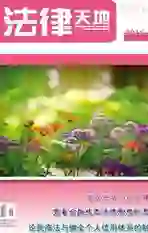违法收益性质研究
2017-06-19纪文哲
摘 要:违法收益这一名词并不常见的在学术讨论或者司法实践中出现,但这种法律现象却由于涉及到财产权利的归属而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及明晰化的处理。违法所得投资收益,是指行为人利用通过违法或犯罪行为获得的经济性利益进行投资而获得的财产性收益。对于赃款投资收益的性质,学界有“犯罪所得说”,有“合法收入说”,也有“折中说”。基于法的安定性、成本考虑,应当以“折中说”为依据判断违法收益的属性。
关键词:违法收益;违法所得;投资收益
《刑法修正案》(九)中体现的犯罪化趋势代表了刑事政策的扩张主义倾向,刑法的全面干预表现出其以一般预防为主的重刑化价值导向,这种思维模式也将对犯罪收益的处理制度构成较为深刻的影响。立法上的犯罪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立法实践活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严”也在犯罪立法的趋重化中有所彰显,对于犯罪收益的处置也应当有所体现,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也将有所裨益。违法所得的构成既包括其原生所得,也应当包括其衍生所得,这种衍生所得可以行为人包括利用违法所得的天然孳息、法定孳息以及利用违法所得经营获得的财产性利益,这种衍生利益即可视为违法收益,对于违法所得的经营行为,可以是投资于房地产等的直接增值行为,也有可能凝结合法劳动而进行服务业等活动的经营,对于上述违法收益性质认定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及实践性意义。
一、违法收益的概念
概念作为一种法律工具,在解决法律问题中必不可少,要想清晰理性的思考法律问题,严格的法律概念不可或缺。①由违法所得作为来源投资所取得的收益本身是一种具有多重概念特征限定的名词,因此并不是一个具备法律明确特征与地位的术语,我国立法并没有对此收益的含义进行明确的界定,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对这类收益的界定也是莫衷一是。
完善立法制度往往需要对于违法收益概念外延的厘定,有学者指出,通过对违法所得增值和经营而获得的利益就称为违法收益。②笔者同意这种观点,违法收益是指犯罪分子通过违法犯罪行为所直接或者间接取得的财物作为投资或置业的资金来源获得经济性利益,是一种获取犯罪收益的方式,在不存在混同投资行为的情况下应当采取刑事追缴手段予以处理。将犯罪收益界定为通过犯罪直接或间接获得的财产,具体包括替代收入、混合收入与利益收入。如果违法收益中存在来源于替代收入、混合收入与利益收入的犯罪资金来源,则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继续作为犯罪收益而存在。
二、違法收益性质认定
对于违法收益的性质,学界具有不同观点,有犯罪所得说,有合法收入说,也有折中说。
(一)“犯罪所得说”学者观点及评析
由于“只要刑罚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可以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既得利益的丧失”,这也是持“犯罪所得说”③学者理论的主要出发点。持“犯罪所得说”的学者从“无人能从犯罪中获益”的原则出发认为,赃款投资收益属于犯罪所得,应当一律没收,而且如果将赃款投资的收入部分或者全部合法化,将不利于犯罪的预防。笔者认为,持犯罪所得说观点的学者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充分关注到刑法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并且明确了认定犯罪所得的对象问题就要正确理解没收程序所要保护的法益,然而为上述理论观点忽略的事实在于违法所得投资行为往往具有循环性和延续性,如果不加限制的一律加以没收,则在理论上和程序运作上都将产生一定的问题。理论上来讲,随着行为人经营活动的延续,资金不断注入,由于运作资金和金融资产本身的复杂性,来源于犯罪所得的部分将难以区分,一刀切的追缴没收难免波及合法收入,从而损害其他合法财产所有人等的利益。程序运作方面,由于上述资金链条的复杂性,司法实际操作工作将由于举证难度大和利益多重性而不易进行,更加深了实务工作的困境。
有些持“犯罪所得说”的学者认为,只有对违法所得积极没收才可以对犯罪分子产生威慑作用,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并不绝对。从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可以探知,个体会做出通过违反法律获取个人财产的选择。对于持风险中立观点的违法者而言,只要预期收益高于犯罪成本,其从事的犯罪就是有利可图的,而这种成本是由其获得的刑事制裁所决定的。因此,最优化的刑事裁决应实现处罚设置和被探知可能性的最优组合。鲍尔斯的著作验证了如下观点,违法所得的没收降低了行为人对在违法活动中获取收益的可能性的预期,因为他们发现,只有在非常规的情况下其违法活动才能不被察觉。④当然,也有学者通过数据研究表明,对违法所得的没收也许会导致更多犯罪的发生。其进行分析得到的数据结果的原理如下:他们对已被察觉到的违法财产获得者给出下列两种选择(a)降低犯罪预期的收益(b)扩大用于规避被察觉到违法所得的有利条件。在(a)的结果下,其对犯罪的扩张化起到了直接消极的影响。在(b)的结果下,对行为人的规避行为起到了直接的积极影响,由于犯罪与犯罪规避是具有互补性的,规避的程度将会基于以下原因提高:当(b)对犯罪具有足够强烈的非直接影响,其对由(a)造成的对犯罪负面直接影响产生过度补偿的效果。因此,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其认为,如果潜在的违法者可以通过规避活动影响其被察觉到违法的可能性,对违法所得的没收未必会对犯罪构成威慑力,相反,其反而会提高犯罪率。⑤因此,虽然对违法所得的追缴是一种必然,但最终对犯罪分子的威慑应当基于多种原因,而对于犯罪规避行为的刑事规制也是其中可行的方式之一。
(二)“合法财产说”学者观点及评析
有学者指出,对于行为人现有资产扣除违法所得后的经营收益,属于其合法诚实劳动所获得,应视为其合法财产并予以承认和保护,进言之不能予以没收。该学者也对犯罪预防的质疑从合宪性的角度给出了解释,其认为,行为人通过合法诚实劳动获得的财富,都应当予以法律上的认可,这也符合宪法有关财产权规范的基本目的;犯罪预防应以确认和维护公民合法权利为基础,如此其也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可⑥。并且在合法经营诚实劳动的情况下,通过合法劳动而取得利益,已经不再具有孳息的属性,而应视为通过劳动而取得的合法财产,不应当再进行没收。⑦也有学者指出,犯罪分子的错误行为与获益之间并不是直接必然的法律上因果关系,其获益的原因是其投资行为,但是对于收益的追缴无法无限延伸至其投资收益,只应当对其现有财产进行适当没收即可。需要惩罚的是为收益创造条件的犯罪行为而不是因此获取的投资收益,因此,刑事责任的追究是必要的。⑧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接收违法所得投资公司经营发展的稳定性而言,通过公司法优先的理念性指导,有利于维护其他股东、债权人合法权益和市场交易安全,从而也消减了公权力直接对“股份”进行“追赃”的权力滥用情况,在现实执行中更具有可行性。
(三)“折中说”学者观点及评析
持折中说的学者认为,如果行为人将犯罪所得投入正常的生产经营,生产经营活动不仅仅是资金的投入,还包括其他资源投入,此种情况下的收益主要也不是由犯罪所得直接产生,不能轻易归纳为犯罪所得收益。⑨也有学者指出合法的投资、经营活动应当与犯罪所产生的利益存在因果关系即可。但是,具体认定收益数额上,应当扣除行为人投入的合法因素,如将犯罪所得进行投资,所获得的利益应当扣除其所付出的劳动价值。⑩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在行为人利用犯罪所得投入合法劳动的情况下取得的收益,应当在扣除劳动所具有的价值后,再进行没收或追缴,而不是完全作为合法财产进行认定。这种劳动价值的具体扣除可以设定相关标准进行扣减。
笔者赞同折中说学者的观点,笔者的最终观点在于以利用违法所得首次经营获得的收益为限进行追缴,但必须扣除行为人所投入的合法性因素,而在利用首次经营收益循环获得的收益由于逐渐脱离了犯罪所得的孽根性,则不再作为犯罪收益进行追缴。这种合法性因素可以包括投入的合法收入,行为人投入的劳动价值等。不过折中说的观点并未对于利用合法劳动投资收益继续经营的循环收益进行探讨,即犯罪人再次利用上述收益投资经营而获得的收益以及如此循环而获得的收益。对违法所得的投资是行为人有目的性的对其资产进行增值的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是通过房地产的投资或出租增值,也可能通过金融途径使得财产增值,如股票或债券,还可能通过自行创办公司企业等的活动进行。在不存在经营劳动的附加的投资行为,其实现的财产增值未脱离犯罪收益的范畴,只是一种毒树之果的延续,而凝结经营劳动活动的投资行为在大量民事属性附加的情况下,使得违法所得的性质大大改善,其投资行为产生的收益即应当作为合法财产予以保护。不过折中说的观点并未对于利用合法劳动投资收益继续经营的循环收益进行探讨,即犯罪人再次利用上述收益投资经营而获得的收益以及如此循环而获得的收益。
三、结论
本文讨论的违法所得投资收益,是犯罪分子通过违法犯罪行为所直接或者间接取得的财物作为投资或置业的资金来源获得经济性利益,是一种获取犯罪收益的方式,在不存在混同投资行为的情况下应当采取刑事追缴手段予以处理。如果违法所得投资收益中存在来源于替代收入、混合收入与利益收入的犯罪资金来源,则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继续作为犯罪收益而存在。本文的核心论点之一在于厘清违法所得投资收益的性质,对此,笔者分析认为,违法所得投资收益是否应当予以追缴的界限应在于是否存在合法经营,如只是不具有经营性质的无风险投资行为,由于其并未切断违法所得与其转化形态的直接联系,违法所得收益的显存形态只是违法所得的一种转化形式,对其追缴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根据赃款投资的不同方式,其具体的追缴处理制度也不同,本文倡导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在是否存在合法经营附加的条件下,讨论不同情况下涉案财物的处置。例如哪些情况下的追缴应当有所限缩,追缴的财物归属何处,涉及复杂民事问题的情况应当通过怎样的法规进行完善,需要在更多、更深入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总结。
注释:
①Boden Heimer. Edgar. Jurisprudence : 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 of the law[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326.
②刘伟,时延安.《违法所得和违法收益》,《中国检察官》,2007年第2期,第37-39页.
③[意]贝卡里亚.《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
④Bowles, Roger, Michael Faure, and Nuno Garoupa. “Forfeiture of Illegal Gain: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5.2 (2005): 275–295.
⑤Tim Friehe. A Note on the Deterrence Effects of the Forfeiture of Illegal Gains. Review of Law & Economics. Volume 7, Issue 1 (2011):118–124.
⑥时延安.《刑法规范的合宪性解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75页.
⑦时延安.《违法所得没收条款的刑事法解释》,《法学》,2015年第11期,第127页.
⑧李和仁,张利兆,张炳生,张兆松,潘申明,倪爱静,王志胜,曾祥生.刑事司法如何面对国企转制中的资本“原罪”问题[J].人民检察,2009,10:29-35.
⑨孙国祥.《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理若干问题研究》,《人民检察》,2015年第9期,第14页.
⑩陆建红,杨华,曹东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15年第17期,第21页.
作者简介:
纪文哲(1991~),女,汉族,山西大同人,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