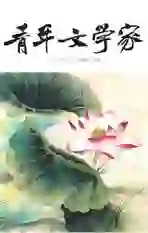朱熹中和新旧说理论之辨析
2017-06-17罗琼
摘 要:朱熹关于中和新旧说理论之辨析,古今学者均畏于浸漫其中。究其原因,大抵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割裂了朱熹各阶段之研究成果,混淆了如胡宏、李侗等前贤对朱熹的影响,而忽视了朱熹的自我理论创新。朱熹在不断潜研过程中,从乾道二年的“丙戌之悟”,直至乾道五年的“乙丑之悟”,完成了自己否定之否定的理论总结,由“中和”旧说向“中和”新说发展,这是我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十分值得后世学者的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中庸;中和;主静;主敬;丙戌之悟;乙丑之悟
作者简介:罗琼(1973-),女,福建尤溪人,尤溪县朱子文化研究会文博馆员,大学本科学历,研究方向:朱子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5-0-02
一、中和说的缘起
“中和”一词出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致中和”,则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于和谐境界,它是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中庸章句序》)朱熹在序言开篇就点出:之思先生为何要撰写《中庸》呢?他担心道学因历时久远失其真传。原来中庸在经书中出现,那就是《论语.尧曰篇》中引《尚书》中的“允执厥中”这句话。这是尧来传授舜的,舜又拿“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四句话传授给禹。实际上尧的一句话已经把中庸的精神概括无余了,而舜增加了三句话,原来是用来阐明尧的一句话的。
道南学派一脉从杨时到罗从彦再到李侗,都非常注重《中庸》的“中和”学说,并用“工夫论”解释《中庸》,以静来体验“未发”。“学者当于喜怒哀乐之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龟山文集》卷四)“某曩时从罗先生问学,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一及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知,退入堂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李延平集》卷二)朱熹受业于李侗,朱熹也曾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朱文公文集》卷四十—)
由于“体验未发”需要在静中进行,所以罗从彦、李延平都强调终日静坐。而朱熹对“终日静坐”一类的体验之学持怀疑态度。“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或问:延平先生何故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求所谓中?曰:只是要见气象。陈后之曰:持守良久,亦未见未发气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这里,又差从释氏去。”(《朱子语类》卷一0三)延平去世后,大概也正是从这个时候,朱熹开始认真地思考,并且身体力行延平“默坐澄心”的教导,突然对“未发已发”问题有了自己的崭新认识。
二、朱熹中和旧说观
朱熹早年师从延平李侗,李侗赠送《中庸》一书,要求其体验“喜怒哀乐未发”之旨。可惜,朱熹所谓的体验尚未达成效果,延平先生就去世了。此时的他感到自己不够聪慧,好像是一个无家可归之人。后来他追述这段拜师过程道:“余窃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张栻)得衡山胡氏(胡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余以所闻,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耳。自此不复有疑,以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朱文公文集》卷七五《中和旧说序》)
后来,朱熹得到了胡氏之书,又与曾吉父[1]论及已发未发问题。他的论述恰恰又与朱熹观点一致,因此他益加自信。虽然朱熹感到程子的观点与自己的认识有不一致的地方,那可能是原作已经失传而不可信。但是,平常和人谈及这个问题,“则未见有能深领会者。”(同上)由此可以发现,“已发未发”这个命题,历史上的前贤达人都没有提出过令人信服的结论。实际上朱熹的最新见解是体现在他和湖湘学派张栻的几次通信之中,其对中和的观点是:
以体用关系来解释“未发”和“已发”。“未发”是寂然之本体,“已发”则是流行发用。“未发”要借“已发”来显现,在“已发”之外别无所谓“未发”。因此,“未发”和“已发”之间不能用时间(“拘于一时”)或空间(“限于一处”)关系来界定。 “未发之前”或“未发之时”是不存在的,所有对“未发”的了解都必须借助于“已发”。“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李延平集》卷四)既然“未发之前”或“未发之时”是不存在的,那么“危坐終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如何,而求所谓中者”,(同上)非惟无意义,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所以只能从“已发”者来指其“未发”者,涵养和察识的关系也必须调转过来:不是先涵养后察识,而是先察识后涵养。
“钦夫(张栻)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朱文公文集》卷二四)此时的朱熹已与师说“所见不同”,倒跟湖湘学说的观点相近了。朱熹在回忆中和旧说时说:“中庸未发已发之义,前此认得此心流行之体。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遂目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朱文公文集》卷六四)可以看出,朱熹的“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观点是受程颐的影响,且在与张栻会晤之前,便已经有了这样的感悟。同时,在与张栻的交往中,发现胡宏也有相接近的看法和观点,这更加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了自信。但在这种思想的转变过程中,湖湘学派的张栻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这一年是乾道二年(1166年丙戌),朱熹37岁,故而,后人将其称之为“丙戌之悟”。
三、朱熹的中和新说观
乾道五年(1169)乙丑初春,朱熹与蔡元定(季通)讲学时,忽然悟到“中和旧说”原来“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当”,而且“日用工夫全无本领。”即用“敬”和“双修”思想从读二程著作,从全新角度独创“中和新说”,标志着朱熹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升华。
所谓“中和新说”是区别于“中和旧说”而言的。原来朱熹以《中庸》未发之旨,令静中体验未发气象分明,不能尽心于此,反以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体论来解释《中庸》的已发未发说。他把《太极图说》的“太极动而生阳”看成天地喜怒哀乐的已发,而“二气交感,化生万物”看成人和物喜怒哀乐的已发。因此,《中庸》的未发已发不仅指人的性情而言,而且指宇宙演化的动静过程。朱熹总是从客观性和本体性即“理”的方面解释《中庸》之说,认为天地、人物及人之性情已发未发,受此统一天理说支配。而《中庸》的未发已发特指人的思维情感而言,其自身并没有本体论的意义,这不能不说是朱熹的一大发明。
朱熹的“中和新说”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已发未发》一文中,它有哪些特点呢?其意义在于:
新说是以“心兼未发、已发而言”,避免了旧说可能导出“未发之前无心”的谬误,同时,新说更加的严密,将未发作性看,心为性之体,情为心之用,心统性情,解决了心、性、情在心性理论体系中的定位问题。这就是“心统性情说”。
从工夫论上看,朱熹的中和旧说“直以心为已发”,因而之强调“动时省察”,而忽视“静时涵养”的工夫。新说则以“未发”为“思虑未萌、事物未至”时的心态,平时持加涵养之功,使无人欲之私以乱之,至其发时而无不中节,方是日用本领工夫。“毕竟求之未发之中,归之主静一路。”朱熹并未回归于李侗,走向“主静一路”,而是上溯于程子,以“主敬”为“圣门之纲领”,以为“敬”字通贯动静,无论静时涵养、动时省察,皆可持以“敬”字工夫。“持敬”既通贯动、静,就不必特别强调未发、已发的分别了。未发、已发完成心、性、情的定位,但它并不在心性理论结构中占据位置。这就是朱熹由对恩师李侗的“主静”观到对圣贤之学再创新的“主敬”观发展阶段。“故程子之答苏季明,反复论辩,极于详密,而卒之不过以‘敬为言。又曰: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若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盖为此也。”(《文集》卷六四)
朱熹曾经把“丙戌之悟”称为“中和旧说”,那么,乾道五年(1169)乙丑的这次总结自然就是“乙丑之悟”的“中和新说”了。总的来说,中和“新说”与中和“旧说”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本体上看,旧说认为“未发为性、已发为心”,而新说则认为“未发和已发都属于心”。
第二,从工夫上看,旧说主张先察识而后涵养,在已发处用功。新说则认为涵养在先、察识在后。
朱熹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定论,是朱子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四、结语
关于中庸已发未发的命题,历史上争论已久,至于最终的结论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我们今天重新发现朱熹对这个问题严谨的科学态度以及不懈的穷研精神,能给我们哪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中庸》之书朱熹早年受之于李延平,而对于喜怒哀乐之未发已发一问题,中间屡经曲折,经年累月,始终往复于心中,相互讨论于师友之间,其辛苦体会,反复疑信之过程。一代大贤严谨治学的精神,尤当为有志儒学研究者所注意和学习的。
其次,关于已发、未发问题,朱熹先接受了张栻的观点。随后又对心为已发之旨产生了怀疑,从而提出性體情用,心统性情之说。他的“乙丑之悟”又反过来影响了张栻。在论辩中,张栻提出的“心主性情”的观点被朱熹接受,并成为朱熹“心统性情”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张栻后来则基本接受了朱熹的观点,放弃了前说。
第三,关于察识与涵养问题。张栻主张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得到了朱熹的认可。但不久后,朱熹认识到张栻的观点缺少前面涵养的一截工夫,主张应先涵养后察识。在随后多次辩论中,张栻认识到自己观点的不足,却也不认可朱熹的先涵养后察识的观点,又提出涵养、省察相兼并进,以涵养为本的思想。直至后来,朱熹进一步提出涵养与察识交相助,从而使他们之间的观点基本达成一致。
注释:
[1]曾吉父:即金履祥,亦称僧吉甫,字吉父,婺之兰溪人。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书,即能记诵。比长,益自策励。及壮,知向濂洛之学,事同郡王柏,从登何基之门。基则学于黄榦,而榦亲承朱熹之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