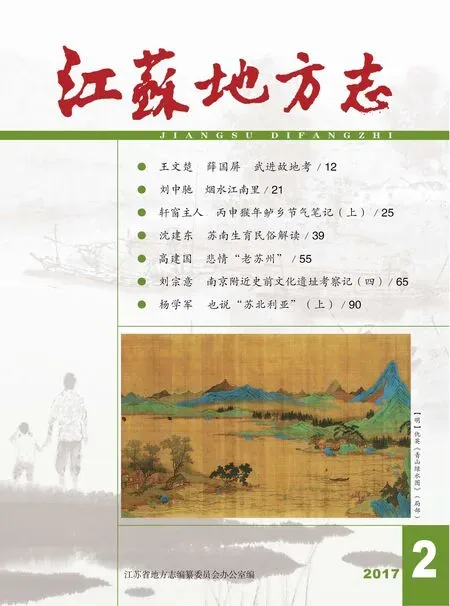也说“苏北利亚”(上)
——一个男孩眼中的劳改农场
2017-06-09杨学军
◎ 杨学军
也说“苏北利亚”(上)
——一个男孩眼中的劳改农场
◎ 杨学军

最近读了一本书,书名叫《苏北利亚》,作者于疆。
书写得不错。作者那平实的表达、幽默的语言和温而不火的情绪,比较适合我的口味。不过,真正吸引我一口气将其读完的根本原因是:书中所记述的“苏北利亚”——江苏最大的劳改农场及其前身苏北沿海地区五大劳改农场,是我人生最初成长的地方!
一
于疆,本名江宇,旅美作家。祖籍江西永新,1954年毕业于上海市市东中学,同年考入南京工学院电力工程系,四年级时被错划为“右派”,其后22年在苏北劳改农场度过。1982年赴美,做过餐馆杂工、电工、电气工程师和GWC工程公司总裁,2004年退休。业余写作以散文和文学评论为主,曾获第十五届联合报文学奖。担任过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和名誉会长。
《苏北利亚》里所记述的,就是他在劳改农场的那段“悲惨离奇荒诞”的牢狱生活。编者在“内容提要”里这样介绍:
《苏北利亚》是一部个人回忆录,也是一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实录,记述作者作为一名大学生“右派”,在苏北集体农场中度过的二十多个春秋,如何一步步从理想主义者变成现实主义者。对当年的极“左”路线,作者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其中,有关生活、劳动、教学、恋爱等等故事,都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离奇荒诞,惊心动魄,极具传奇性。
作者在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苏北利亚基本上是大有农场、东直农场、新荡农场、民生农场和潮河农场等五大劳改农场结合成的,涵盖了从废黄河到灌河口的广袤海涂。”
需要补充一点,书中的后半部分还涉及由上述五大农场迁徙合并而成的洪泽湖监狱。这个坐落在洪泽湖畔的被当地人称作“车路口”和“农场”的监狱,与原来的五个劳改农场有着承接延续的关系,故而在于疆的笔下也被称为“苏北利亚”。
面对这样一本“身边人写身边事”的书,即使是为了探知作者“写得像不像”,我也会认真地读一读。
匆匆读罢,心灵受到震撼,但脑海一片空白。奇怪的是,我非但未觉着清醒,反而觉得原先熟悉的一切正在变得陌生,甚至恍若隔世。
作为从同一块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对于这块苍凉而神奇的土地,于疆的认识与我差别之大,超出我的想象,尽管他的认识比我深入也深刻得多。
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我几乎没有为洪泽湖监狱这个被我称作故乡的地方写过一个字,这与我每年二三十万字的写作量很不相称。但这并非意味着,我对这块土地就完全没有感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禁锢的圈子里生活久了,把周围的一切都神秘化了,及至今日,回望过去,神秘的浮云依旧飘飘忽忽没有散去。我不否认,依靠模糊的印象去追忆描述甚至塑造那些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人和事,不是没有勇气和动力,而是根本就没有能力。虽然那里埋藏着父辈们的创业历史,孕育过我和小伙伴们的童年梦想,也发生过鲜为人知的却关乎共和国安危的故事……
实际情况是,在这个农场(监狱)建立初期的1956年,父母在黄海之滨生下了我。9年后,为适应战备需要,我们随着农场举家迁到了洪泽湖畔。又4年后,对那里的一切还没形成完整的印象,我又跟随父母离开了。
而于疆则不同,1957年冬天他踏上这块“神奇而荒凉”土地的时候,虽然仅有20岁,却已是身着白色西装风度翩翩的大四学生了。彼时的他,应当完全具备独立充分的认识和思考能力。他经历了一个“犯人”从被捕宣判到接受劳改的全过程,时间跨度长达22年之久!我至今弄不懂《苏北利亚》编者所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实录”的真实所指——是作者22年的“被改造”,还是铁窗下的“自我改造”或“逆改造”?“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22年的“改造”使于疆获得了独特的视角,而视角的独特又衍化成创作手法上的独特,这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端倪。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到了大洋彼岸后才成为作家,而他在苏北劳改农场的牢狱生涯,则成了他丰厚的生活积淀和创作源泉。这一切,是一般作家无法比拟的。
实话实说,我还是蛮喜欢于疆的作品,当然也包括在网上能看到的他的其它作品。单就这本书而言,其中诸多故事和细节我觉得还是真实可信的。与其说是喜欢,不如说是理解和信任。这部作品不是小说,自然不应该有虚构的成分。出于对其人格尊重和信任,我没有理由怀疑他创作动机和诚意。他的作品固然悲怆凝重,但也不失诙谐幽默,即使是在嬉笑怒骂揶揄责难之间,也很难找到恶意中伤信口雌黄的痕迹。应该说,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一个蒙冤者的挣扎、抗争和隐忍,领略了一名批判者的尖锐、执着和思辨,也感知了一位作家的学识、中庸和良心。我不止一次地拷问自己:假如身陷囹圄的人是我,我会在这22年中如何生活、认识和思考?在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和反思后,我又将在新的舆论环境中如何发声?40多年前,我跟随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父母下放农村,在十分悲凉和近乎绝望中生活了4年。时至今日,我能否淡然地认为,心灵上的那道伤痕已经完全弥合?
说到伤痕,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与我和“右派”都有关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我老舅,上海某工厂工人身份的工会主席。当年因为同情厂里的某个“右派”,他也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往青海某工厂监督劳动。22年后,同去的“右派”纷纷平反返沪,而老舅的事却无人问津。他向有关部门申诉,答复令人震惊而又毋庸置疑:“经查,你是工人身份,不属于抓右派的范围,档案里也无右派结论。你到青海属正常调动,因此也不存在平反和返回上海的问题。”天哪!顶着“右派”的帽子在青海呆了22年,竟然是“正常调动”?!这个结果,简直比当初被抓了“右派”更可怕!老舅如五雷轰顶,从此以酒浇愁,最后郁郁而终。老舅到死也不知道,他这个不是右派的“右派”身份,还影响到诸多亲属。我姐姐1971年报考海政文工团没被录取,主要就是因为有这一层“社会关系”。说起来让人啼笑皆非,我父母作为管理“右派”的干警,而自己的弟弟却也是“右派”!“同是天涯沦落人,相'怜'何必曾相识。”自家的窘况和老舅的遭遇,也许是我理解于疆的重要原因。
当然,理解不等于赞同。
二
读于疆的书,我是有心理铺垫的。在此之前,我早已读过从维熙、张贤亮等人反映右派牢狱生涯的诸多作品,读过省委党校同学张晶描写新一代狱警生活的小说《总矫正师》,读过父母的老战友谷万江、卢水银两位前辈的回忆录,还参与了《洪泽湖监狱志》的后期审稿,再加上有限的亲身经历和父母的回忆,自以为对苏北劳改农场历史乃至我国劳改事业的发展史多有了解。但我毕竟还没有读过像《苏北利亚》这样一本与本人最初生命轨迹高度重合,与父辈“创业战斗”经历几乎平行,以右派“改造蒙难”历史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因而,我对于疆及其作品产生兴趣是顺理成章的。相信与我有着类似经历的人,也会很自然地成为这本书的读者群。
当《苏北利亚》成为畅销书后,就很快在苏北乃至江苏的劳改干警(他们当中有许多跟我一样被称为“警二代”)中引起强烈反响,一些与于疆(江宇)有过接触的人士,努力拼接还原他牢狱生活的片断,重新标定这个当年的“右派分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在我的记忆中,应该与于疆有过一面之交。
1976年初夏,我在洪泽农场医院实习期间,到相邻的场运输队看望一位亲戚。当时,亲戚正在与一名“场员”(劳改劳教留场就业人员)讨论什么技术问题。由于干部要会客,那场员知趣地走开了。亲戚指着那名场员的背影告诉我:“这人是个大学生,技术和理论都是一流!”据了解,当时运输队的场员中,只有于疆一名大学生。由此不难推断,我见到的那位无疑就是于疆。相隔时间过久,我已无法回忆出于疆的长相,甚至说不清他是否戴着眼镜,也就更难将当年的场员“理工男”与今天的著名作家等同起来。冥冥之中,只感到命运之手的存在。这是闲话。
再说于疆的作品。《苏北利亚》不仅很有读者,还在评论界掀起了波澜。有学者这样评论这部作品:在劳改农场,“人的尊严被蹂躏,被践踏。对思想违逆的惩罚,须经受野蛮的体力折磨,而目的是从精神上摧垮,从肉体上消灭。这是中世纪野蛮的暴行,其实也曾在我们的国土上演。”
果真如斯所言?
对此,我不想简单地回答是与不是。无论我怎样回答,都可能引来争议。
几十年来,我国的劳改劳教制度一直就是一面“金银盾”:从不同的角度看,其结论完全不同。即便如此,这面“盾”依然长期存在,并依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我的父辈们,则是以锻造这面“金银盾”为起点,开始了自己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漫长生涯,开始了“我为监狱献青春,献完青春献子孙”奇异人生。正是有了他们和于疆们的存在,才有了关于“苏北利亚”的故事和传说。
奇怪的是,在接触于疆作品之前,我并未听说过“苏北利亚”这一称谓。是我孤陋寡闻么?我问过许多在苏北劳改农场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同学,他们竟也表示闻所未闻。揣摩再三,窃以为这一称谓多半是于疆成为作家后加工提炼出来的,就像他在另一篇作品中将犯人子弟戏称为“犯二代”一样。否则,右派改正已30多年,怎么这一后来成为畅销书名的地名绰号,却一直不为人所知?这不是当事者们有意保守秘密,便是他们莫名其妙地集体失忆了!
何谓“苏北利亚”?
作者的本意和我的猜测大约是一致的:它源自俄国的流放之地“西伯利亚”。
众所周知,从乌拉尔山脉到太平洋之间,有一片现在仍属于俄国的辽阔土地——西伯利亚。由于地处边远且环境恶劣,其一直是沙皇帝国的反对者们的流放之地。无论是以穆拉维约夫为代表的十二月党人、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民粹派分子、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还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的早期领袖以及他们的家属,都在这里经历过与世隔绝的流放生活。十月革命后,西伯利亚又成为苏维埃政府集中惩治敌对势力的地方。曾在西伯利亚被关押了八年的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无情地揭开了西伯利亚神秘的面纱,向世界揭露了集中营摧残人性杀戮生灵的真相,展示了红色阴影下的黑暗,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了如此特异的历史轨迹,西伯利亚这一称谓,也就自然地成为寒冷、残酷、血腥甚至死亡的代名词。于疆的作品把地处苏北沿海地区的劳改场所比作“苏北利亚”,其象征意义可想而知。
假如我们按照作者的意图,试着把“苏北利亚”与“西伯利亚”之间划上等号或相似号,是否就意味着,新中国的劳改事业等同于沙皇当局的流放制度?换言之,是否因为西伯利亚曾流放过革命领袖列宁,而苏北劳改农场关押过一批“右派分子”,就可以把两地相提并论?再者,于疆们在接受“劳改”的过程中,除了备受冤屈之外,是否还饱尝身心摧残和肉体折磨?而在这块土地上付出汗水、热血和青春的管教人员,是否也成了狰狞可怕、无恶不作和臭名昭著的酷吏?回答上述问题,肯定又面临一场争论。当然,如果作者只是为了追求视觉效果——让人一看到“苏北利亚”,就立即产生目睹西伯利亚的凄凉阴冷、残酷血腥场面的感觉,则另当别论了。
在此,我不得不心悦诚服:作者的目的达到了。
在于疆作品的评论者看来,一名亲历冤狱达22年之久的知识分子,能够在痛苦、歧视、屈辱下生存下来已属万幸,倘能写出一部得到多方接受的反映监狱生活的文学作品,则更是难上加难。对此,我自然没有异议,甚至对作品中个别细节甚至部分情节的失真,也依然表示能够谅解。
但不可否认的是,标题和书名,历来是文章和著作的灵魂,有着鲜明的导向性。也就是说,其引领着读者欣赏或排斥的方向。况且,单凭这部作品的“自己写自己”,就已经在真实性上先得一分,作者似不应枉对读者的信任。本来只是一部书的书名问题,看似无关紧要,如若将其进一步发展为一个地名或一种社会现象的代称,就带有明显的贬义和偏见了。
人们不禁要问:在黄海之滨组建劳改农场,难道只是为关押那些“心怀报国之志却惨遭冤狱的知识分子精英”?或者说,这间劳改农场本来就是冤狱成灾草菅人命之所在?果真如此的话,说这里是“苏北利亚”似乎也不为过。
这一问题,牵扯到对我国劳改制度及其实施情况的整体评价,似乎不用我来作答。但是,这个问题还是让我纠结不已。正是怀着一颗纠结之心,我才尝试着去叩开了那扇封闭已久的、隐藏着诸多历史秘密的监狱大门。
三
20世纪50年代初,为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全国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加上土改运动的“斩获”,一批批“地富反坏军警宪特分子”和其它“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被投入监狱。一时间,各大中城市和县城的监狱看守所人满为患,亟须组建一批能容纳并教育改造众多罪犯的场所。于是,地处黄海之滨的“华东军政委员会苏北新人农场”应运而生。
新人者,将罪犯改造教育成新人之意也,这表明了组建这个劳改单位的真实目的。
“新人农场”自1952年6月开始筹建,初为总队(地厅)级建制,隶属于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首任政委兼场长是红军干部姜文章(后兼任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农场实行总场(总队)、分场(处)、大队(科)、中队四级管理体制,干部们按部队职务套入相应职级岗位。农场领导机构成立后,又先后从华东公安部、华东公安部干部学校、华东军政大学教导团(整建制,农场干部的主体)以及浙江、福建支队等单位调进干部1900名。干部中“老八路”居多,老红军还有喻国兴、徐福生等好几位,于疆作品里提到的女红军王文珍也在其中。这批先于犯人进入农场的干部,会同从当地滨海县临时招募的25000余名民工紧急奔赴海滩,拦海筑堤,修桥铺路,搭建临时工棚。
两个月后,17000余名罪犯陆续进入。
再两个月后的10月1日,新人农场在欢庆建国三周年的鞭炮声中正式宣告成立。
几年后,于疆等“右派分子”进入农场时,新人农场继更名为建设农场(划归江苏省)之后,并在1956年被拆分为东直、新荡、民生、潮河、大有等五个农场,在押犯人总量虽大幅减少,但总体规模有所扩大。
于疆所到的是东直农场(原一分场),对内称江苏省第一劳动改造管教队。
还是说新人农场。这个可容纳两三万人的大型劳改农场,在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从组建到正式成立,只用了四个月时间!其中的艰难困苦,不是今人可以想象的。在其最初三年,被后人称之为“黄海之滨拓荒”阶段,作为农场最艰难的一节,被写入“场志(《洪泽湖监狱志》)”。
尽管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被问起何时最苦最累最令人难忘时,硕果仅存的“老管教”们仍异口同声:建场初期。
毋庸讳言,在共和国的历史中,1959至1961的这三年,是可以与饥饿、灾荒、疾病和死亡同日而语的。有关这三年的文学作品早已充斥文坛,关于这三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争论也一直持续至今。于疆的这三年,正是在我家所在的农场里度过的。他在作品中,用了较多的篇幅,把这三年作为最阴冷黑暗、最刻骨铭心的阶段来加以描绘。不管他怎么说,就“苦难”而言,在苏北劳改农场这个特定的地域,这三年也许真不能与建场初期的那三年相提并论。
这里,不妨以人的生存必需之“衣食住行”为例,将前后两个三年作些许比较:
先说“衣”。
军人出身的管教干部们,都是穿着军装来到农场的。别看这黄土布军装新的时候还有模有样,可洗了几水之后,就像纸一样白,像纸一样薄,再加上汗水、雨水、泥水的不断侵蚀,整日盐渍斑斑,看上去像披了幅“世界地图”。稍一用力,“地图”上就会被扯开一道或几道口子,宛如弯弯曲曲的国境线。烈日炎炎之下,女干部们多被安排在室内工作,男干部们要在野外带工,被热浪烤得恨不能赤膊上阵,但碍于警容风纪又不敢造次。一个季节的衣服穿不到头便完全没了“图像”。到了冬季,按照南方标准配发的棉衣被褥,根本抵御不了海滩冰冷天气的侵袭。白天,人们还可以通过大幅度的活动自行取暖,到了晚上,就统统成了“团长”。若是遇上寒流肆虐,又都成了“冰棍”。
干部们窘态如此,犯人的状况便不难想象。彼时,还没有统一的囚服,犯人们大都穿着从家里带来的衣服。或长袍马袿,或粗服短袿,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跟干部们一样,犯人们最难过的也是冬天。单薄的衣被无法御寒,许多犯人便采集芦花装填到棉衣的夹层里,其保暖原理类似今天的羽绒服,但其御寒能力自然远不及后者。
当时,农场正进行紧张的水利施工。在严寒的淫威下,水利工地的流感也趁势大面积暴发,其它传染病也不甘示弱跟风而至,病患者一度突破千人,局部冻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当局先是减轻劳动强度,最终不得不实施全员撤退。可是,人虽撒下来了,不等于解决了御寒的问题。为确保全体犯人安全过冬,经华东公安部出面斡旋,紧急调运了大批棉花布匹,为急需的犯人补齐衣被。与此同时,一座规模较大的被服厂也在农场应运而生。在此之后,每当犯人入狱之际,他们都会领到统一配发的服装和棉被。服装是黑色的,有明显的标志意义,就是于疆说的他平反返回南京时穿走的那种。服装被褥的问题解决了,因缺衣少被的原因而导致冻伤事故的情况也就基本杜绝。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