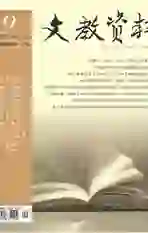浅析康德对笛卡尔 “我思” 范畴的发展
2017-06-08吴梅梅
吴梅梅
摘 要: 笛卡尔的“我思”范畴只具有自身抽象的同一性,本身并不包含对物质性对象的综合,且他的论证以观念的演绎进行,可抽象的逻辑与物质性对象之间是存在鸿沟的;康德的先验统觉范畴首先承认“我思”的存在,之后通过“我思”对杂多表象的综合,最终得出“我思”的综合的同一性。因此,康德的“我思”是综合着表象杂多的“我思”。表象象杂多源于物自体,物自体并不可知。
关键词: 我思 先验统觉 康德 笛卡尔
笛卡尔的“我思”可以说是自我意识的活动,在这种自我意识的活动中,并不涉及对象性活动的具体内容,他以观念的演绎论证了我、上帝与物质性东西的存在,最终从上帝那里寻求一切的终极根据,未对理性与上帝进行明确的区分。
康德发展了笛卡尔的“我思”范畴。“我思”在康德这里易名为“先验统觉”或自我意识,已不同于笛卡尔的只具有抽象统一性的“我思”。于康德而言,“我思”是自我意识在认识活动中所产生的能够伴随所有其他表象却不能被任何其他表象伴随的表象,包含对直观杂多的综合,直观是先于一切思维被给予的,这恰恰是笛卡尔的只具有抽象同一性的“我思”范畴所不具备的。那么,杂多表象的来源是什么?康德认为是物自体,物自体仅可以被思考,却不可知。在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中,康德对人的理性能力进行着考量。“人的事实,乃是‘理性的事实(fait de la raison),理性在其有限的存在中,要不断地去存在(àêtre)。于是,康德就规定了那唯一哲学命题的意义:‘人是什么?三个从属性的问题都潜在地解释着这一问题,这三个问题即:‘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1]
一、笛卡尔的“我思”范畴
在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我思”是笛卡尔认识论的起点,也是主线。在关于“我在”、上帝的存在与物质性东西的存在的过程中,“我思”其实是一以贯之的。在对“我在”的论证中,“我思”即为“我在”;在对上帝存在的证明过程中,笛卡尔以观念的演绎为基础证明的;在对物质性东西存在的过程中,笛卡尔是以“我思”进行论证,以上帝的存在为根本的基石做最终的说明。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在第二沉思中提出的著名命题。什么是“我思”?“我思”是“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2]。什么是我?在第二沉思中,“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3]。“我思维多长时间,就存在多长时间;因为假如我停止思维,也许很可能我就同时停止了存在”[4]。结合“我思”与“我”的定义,“我思”与我其实是一个东西。思维多久,我就存在多久,假如我不思维,那我就不存在。那么,“我思”与“我在”是直接同一的。“‘我思就是‘我在,‘我之思与‘思之我也是一体的”[5]。“我思”与“我在”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在第三沉思中,笛卡尔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他写道:“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把这个观念放在我心里,就如同工匠把标记刻印在他的作品上一样。”[6]“这个观念”指上帝的观念,上帝的观念是上帝先天赋予我的,言外之意,笛卡尔先天地承认上帝的存在。从上帝的观念出发,他进一步讲到,上帝的观念是蕴含着完满的客观实在性的,给予我上帝的观念的原因一定至少形式地或卓越地蕴含着同样完满的客观实在性,这个原因只能是上帝,因此上帝存在。笔者认为,首先,笛卡尔用上帝的存在证明上帝的存在;其次,一个包含着完满的客观实在性的观念无法从逻辑上必然地得出现实中一定有其载体;最后,用包含完满的客观实在性的观念论证上帝的现实存在,该客观实在性是空洞的,因为它里面并不包含与现实存在相应的任何物质性的东西。
在第六沉思中,笛卡尔对物质性东西的存在进行了论证。在对物质性东西进行论证时,笛卡尔通过“我思”与上帝的存在相结合论证。首先,他再一次明确定义“我只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而没有广延”[7],于是,作为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我”只能接受和认识可感知的观念,以观念为中介论证物质性的东西的存在。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想象与感觉是思维的模型,也可以说是思维的一部分。“在我心里有某一种受动的感觉功能,也就是说,接受和认识可感知的东西的观念的功能;可是,如果在我心里或者在别人心里没有另一种能动的功能能够形成和产生这些观念,那么这种受动的功能对我来说就是无用的,我绝对使用不上它。可是,既然我不过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那么这种能动的功能不可能在我心里,因为它并不事先根据我的思维,而那些观念也绝不经我协助,甚至经常和我的意愿相反而出现给我;因此它一定是在不同于我的什么实体里,在那个实体里形式地或卓越地包含着(如同我以前指出的那样)客观地存在于由这个功能所产生的观念里的全部实在性”[8]。作为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我”无法能动地产生物质性的东西的观念,因此它不是来源于“我”的内心的;同时,这些观念呈现于“我”绝不由“我”的意志自由选择,说明产生物质性东西的观念的实体是独立于“我”的。笛卡尔全然纯粹地在用逻辑对物质性东西的观念进行推演,以此得出一个物质性的实体的存在。可是,他的物质性的观念并未包含任何物质性的东西,纯粹是在自己的“我思”中构想的,因此,无法真正证明客观实体的存在。上帝“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倾向性使我相信它们是物体性的东西送给我的……因此必须承认有物体性的东西存在”[9]。在关于该实体是否是物质性的东西时,笛卡尔再一次将上帝拉入自己的理性范围之内,指出是上帝使“我”相信物质性东西的存在。那么物质性东西的存在的最终根据是上帝,而上帝对于笛卡尔而言,毋宁说是先天存在的。笛卡尔从“物质性东西的观念”出发,逻辑地推导出一个客观实体的存在,最终使上帝成为客观实体存在的根本依据。这样的证明是纯粹的逻辑演绎与使上帝为理性服务的过程,不能真正证明客观实体的存在。
因此,笔者认为,在笛卡尔“我思”的自我意识活动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我思”,在自我意识活动中只是观念的演绎,并不包含杂多表象(借用康德的概念),仅与自身抽象同一;二是對于笛卡尔而言,上帝是先天存在的,在论证的时候,笛卡尔最终会将上帝拉入自己的理性范围之内,请他成为一切的根源。
二、康德的“先验统觉”范畴
什么是先验统觉?“‘我思必须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因为否则的话,某种完全不可能被思考的东西就会在我里面被表象出来,而这就等于说,这表象要么就是不可能的,要么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无……但这个表象是一个自发性的行动,即它不能被看作属于感性的。我把它称之为纯粹统觉,以便将它与经验性的统觉区别开来,或者称之为本源的统觉,因为它就是那个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由于产生出‘我思表象,而这表象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所以决不能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随”[10]。先验统觉又被称为“我思”、自我意识、纯粹统觉与本源统觉。“我思”是自我意识在意识活动中产生的表象;“‘我思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说明“我思”的普遍必然性,也说明此时得到的意识是经验性的意识,经验性的意识(经验性的统觉)伴随着不同的表象,本身是分散的;“这个表象是一个自发性的行动,即它不能被看作属于感性的”,说明“我思”是从理性出发的,也是本源的;“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说明“我思”是在对表象综合的基础之上所获得的自身的同一性,综合是将“一个表象加到另一个表象之上”。此即为康德的先验统觉的完整的定义,具有普遍必然性、自发性、本源性、综合性与同一性的特点。
统觉范畴包含三个方面:一是统觉自身的自发性、本源性;二是知性对直观杂多的综合;三是统觉自身完全的同一性。其中,知性对直观杂多的综合是统觉自身获得同一性的基础,这恰恰使得康德的同一性不再是自身抽象的同一性。正如康德自己所言,“直观中被给予的杂多,有关此杂多的统觉的完全同一性包含着对表象的综合,且只有通过对此综合的意识,统觉的完全同一性才是可能的”[11]。
首先,承认先验统觉的自发性是知性对直观杂多综合的前提,必须承认有先验统觉的存在,先验统觉不是感性的,而是理性的,且是从理性自身出发的,是本源的——“我思”源于自我意识,“我思”本身即为自我意识。
其次,统觉的统一性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知性对直观中被给予的杂多表象的综合。知性是先验统觉的逻辑能力,“能够先于一切思维被给予的表象叫作直观”[12],综合是“一个表象加到另一个表象上”,在此处即为“联结”,“联结是一个知性行动,我们将用综合这个普遍名称来称呼它”[13]。综合或联结是主体的知性将一个表象加到另一个表象之上,它是在主体中进行的,不是在客体中进行的。综合的逻辑进程是先承认“我思”的存在,之后“我思”伴随一切表象,将一切表象都容纳在“自我意识”之中,“我思”再对这些表象进行知性的联结,最后“我思”在对“我思”所伴随的这些表象的综合中,在对综合的表象的分析中,“先验统觉”获得了自身的同一性。
统觉的同一性是指“我思”在对杂多表象综合之后,从杂多表象中获得的自身综合的同一性,同一性的定义是A=A。统觉的分析统一是以某一种统觉的综合统一为前提的。“一个应被设想为各种不同的表象所共同的表象是被看作属于这些不同表象的,这些不同表象本身除了拥有该表象外还拥有某种不同的东西,因此这个表象必须预先在与其他表象(即使只是可能的表象)的综合统一中被想出来,我才能在它身上想到使它成为conceptus communis(共同概念)的那种意识的分析的统一”[14] 。也就是说,“我思”首先存在,其次能够伴随所有其他表象,之后使一个表象加到另一个表象之上,比较分析,发现“我思”一直在每一个表象之中,最终得出“我思”的同一性。由此可以看出,统觉的同一性是包含着杂多表象的综合的内在的统一。
这里就涉及了另一个问题,即杂多表象的来源问题,康德认为是物自体给予的,而物自体仅可以被理性思考,本身却不可知。在此处,笛卡尔与康德面对着同一个问题,即关于无限的存在的问题。尽管笛卡尔将上帝引入自己的理性之内,康德明确将物自体劃出自己的理性范围之外,可是他们都各自承认上帝与物自体的存在,可言之为无限的存在。
三、康德对笛卡尔“我思”概念的发展
康德的先验统觉的统一性包含了知性对杂多表象的综合。杂多表象借助于感性被物自体给予我们,之后知性对直观杂多进行综合(联结),可知性作为先验统觉的自发性的逻辑能力,不具有感性直观的能力,因此需要借助一个中介,即生产的想象力。生产的想象力亦称为先验的想象力,“它是思维用其先天固有规律——范畴综合感性材料形成知识的能动的心理机能”[15]。由此可见,先验想象力既有知性的特征又有感性的特点,可以成为联结感性与知性的桥梁。先验想象力是以先验统觉为基础的。如此,知性通过先验想象力对直观杂多进行综合,获得统觉的同一性,即统觉的原始的综合统一,同时说明知识是何以可能的。
然而,笛卡尔在他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我思”本身并没有任何物质性的东西掺杂其中,只具有抽象的同一性。因此,康德的包含着对直观杂多的综合的统觉相对于笛卡尔的“我思”范畴是一个发展。
笛卡尔将物质性的东西的来源归为上帝,康德将杂多表象归于物自体,无论是上帝还是物自体,二人皆认为它们是存在的,且是我们有限的理性所难以完全认知的。不同的是,笛卡尔使上帝为自己的论证服务,康德则对理性的认识能力进行批判,对理性与物自体做了区分。
参考文献:
[1]贝尔纳·布尔乔亚,著.邓刚,译.德国古典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6.
[2][3][4][6][7][8][9]笛卡尔,著.庞景仁,译.第一哲学沉思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9,28,56,85,87.
[5]居俊、张荣.先验统觉的思想物抑或物自体?——康德先验对象概念歧义之辨[J].世界哲学,2015(9).
[10][12][13][14]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89,89,88,90.
[11]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247.
[15]崔巍.先验哲学中的想象力学说[J].吉林大学,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