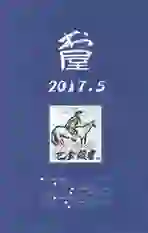此总理的耳光与彼总理的下跪
2017-06-05赵刚
赵刚
一
这一记耳光,注定要她付出沉重的代价,被判入狱一年,不得保释。因为这记耳光打的不是普通人,而是扇在了总理脸上,并且还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但是,这记耳光也使她与“耳光事件”迅速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让人们记住了1968年11月7日这历史性的一刻。
那一天是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大会,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库特·基辛格正在台上口若悬河地发表演讲,台下听众一个个全神贯注聚精会神。这时,突然有一位妇女迅速闯入会场,从讲台一侧快步走到基辛格身边,二话不说,扬起手臂,朝他的脸颊扇去。
正在台上演讲的基辛格猝不及防,一下子给打懵了,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保安们见势不妙立即扑了上去,死死地扭住了这个女人的胳膊。这时就听见这位妇女不断高喊:“纳粹!纳粹!纳粹!”此时,会场一片哗然。
打总理耳光的这个女人是西德记者贝娅特·克拉斯菲尔德。事后,她对采访的记者说:“打耳光的时候,我知道他的贴身保安就坐在第一排,我是从他后边走过来的,所以他们没法朝我开枪,但那时候我所有的注意力都在怎么使这个行动成功,直到打完,我也没感到害怕。”她说,自己是以年轻一代的名义打这个耳光的。在她看来,二战结束后仅仅二十年,一位曾交了十二年纳粹党费,并且被美军在路德维希拘留所关押了十八个月的纳粹分子,竟然当上了联邦总理,这是德国的耻辱。
贝娅特·克拉斯菲尔德的这记耳光虽然打在西德总理库特·基辛格的脸上,但却在德国人民的心理上产生了巨大反响,这一记耳光,开启了德国社会的反省进程,由此将反思大屠杀与纳粹罪行的行为由极少数人的见解变为举国上下的共识。就在“耳光事件”后不久,1969年初,联邦总理库特·基辛格连同当时的总统吕布克(在第三帝国时期,曾在一家设计过纳粹集中营的建筑公司中工作),在德国人民的反对声中黯然下台。
二
历史是复杂的,总是呈现出不同的侧面与多样性,并非是想象中的非黑即白。对纳粹德国的深刻反省确实是战后德国的一个伟大的行为,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但这种反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个由集体遗忘到全民觉醒的曲折过程。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可以赞赏克拉斯菲尔德的这记耳光打得痛快淋漓,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深入到当时德国的背景分析,就不难发现历史复杂和曲折的一面,不难体会到德国人民所走过的悲怆抑郁的心路历程。
战后德国满目疮痍,荒芜衰败,民生凋敝。城市四周遍布腐烂的尸体和恶臭的污水,到处是炮火摧毁的断壁残垣,河床上倒塌着断为两截的桥梁,高速公路被坦克碾压得支离破碎,工厂被占领者拆毁得七零八落,铁路被轰炸得残缺不全……学校里的儿童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未成年的少年混迹于街头,男孩们聚众闹事打架斗殴,女孩子们则描眉画眼做起了皮肉生意,他们的父母们整日穿着断底的靴子和开裂的工服拼命地勞做,甚至连昔日的富人也不得不奔走于大街小巷,去餐馆和酒店里端盘子洗碗,打扫卫生以维持生计。
战争虽然结束了,取代死亡恐惧的是生活的潦倒和前途的迷茫。哪里可以搞到食物?哪里可以找到工作?明天又该如何生活?这一切,对于绝大多数德国人来说不仅难以预料,而且槁木死灰,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也都噤若寒蝉,眼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活下去。
当时,盟国占领军为了配合“非纳粹化”审查,规定每个德国人在领取食物配给证之前,必须要进行纳粹罪恶史的再教育,通过组织观看达豪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纪录片,让德国人了解犹太民族是如何被纳粹迫害并遭受屠杀的。多年后,曾有作家对此回忆到:“在放映机忽明忽暗的光亮下,我看到电影从一开始放映,大多数人就将脸背过去,那样直到放映结束。如今我在想,这些转过去的脸就是当时千百万人的态度……既伤感又麻木。”在这样的情景下,人们越来越沉默,纳粹曾经的罪恶也似乎消失在沉默之中,面对饥肠辘辘,面对穷途潦倒,德国人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和兴趣去反省过去。
与此同时,战后欧洲所发生的许多骇人听闻,至今仍令人不齿的的事件,也给战后德国人民的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并且为德国的“非纳粹化”进程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1945年5月德国战败之后,在德国境内以及曾经被纳粹统治的占领区,多次爆发了报复德意志人的骚乱。据史料记载,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的居民任意殴打德国平民,“在这场民族清算的狂潮中,德意志族的妇女和儿童成为了最主要的牺牲品。德意志妇女被吐口水,剃光头、剥光衣服并在身体上画上纳粹党徽标志,被强迫赤身裸体在街头排除障碍,甚至当众遭受强奸。德意志的儿童有的被从楼房抛出来摔死在街头,有的被塞进盛水的马桶中溺毙。狂怒而放纵的人群把大批德意志居民从家中驱赶出来,把他们两个或三人为一组用铁丝捆起来推进伏尔塔瓦河,尸体顺流而下被冲进易北河。两周后,人们从易北河中竟打捞出上千具尸体。据德国战后统计,在捷克发生的这次大规模复仇中,共有三万德意志人被杀死”。“在今天的德国和波兰的奥德-尼斯河边界线以东的地区,曾经有三千三百个战前属于德国的城镇和村庄发生过群众性迫害德国平民事件。在南斯拉夫居住的近二十万德意志族人中,约十六万人在战后被关押进集中营,其中被杀害、折磨致者死达五万人。”(朱毅维:《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世界国际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294~295页)
在柏林发生的暴行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在苏军进军柏林期间,约有一百九十万妇女遭受到了苏军士兵的强奸,其中一百四十万人受害于在德国东部的逃亡途中,五十万人受害于后来的苏军占领区。苏军攻占柏林后,共计十万名柏林妇女遭到了强奸,其中百分之四十的人被多次强奸,近一万人被强奸致死”。把以上两个数字加在一起,被苏军强奸的德国妇女约合计二百万人。这个数字被联邦档案馆和柏林档案馆的历史统计资料所证实。在被强奸的人群中,有十二岁的孩子,还有八十岁的老人。仅仅在“1945年4月27日到5月4日期间,苏军在整个柏林掀起了一阵强奸狂潮”,每天有上万名德国妇女遭到蹂躏。
在战后初期的平民暴力和苏军强奸高潮过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欧洲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民族大清洗,而清洗的对象就是刚刚投降的纳粹德国统治下的德意志的普通百姓。
二战期间,希特勒为了达到民族扩张的目的,实施了所谓“生存空间”计划,纳粹德国在兼并奥地利,进占苏德台,以及侵略波兰之后,数以百万计的德意志人进入了被占领区。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为了激励苏联对德作战,英、美两国承诺,在打败德国后,同意将波兰的一半领土彻底划归苏联,波兰由此而丧失的领土则由战败的德国补偿。在这个没有主权国参加的对波兰主权和领土问题的裁决过程中,英、美、苏三大国领导人还对移民作出明确的计划:波兰居民要离开被苏联占领的领土,西迁至新划定的波兰国界;德国人不仅要从被德国侵占的波兰领土上迁出,还要从划归波兰的原德国领土上搬走。1945年8月波茨坦会议上,英、美、苏三大国达成“确定把德意志人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驱赶出去”的共识。“战争一结束,有关国家当局就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驱赶一切德国的和德意志族居民。在最野蛮和最混乱的驱赶初期,往往是限他们在几个小时集中,而后赶上闷罐车或令其步行回到德国的边界之内。被驱逐的德国人和德意志族人与战争末期逃避战火的七百万难民挤在德国各占领区,局面极为混乱,一度甚至引起饥荒。死于逃亡和被驱逐路上的人数无法统计,估计要十万计。美国《时代》杂志当时用‘欧洲从历史上最恐怖的战争过渡到最可怕的和平这样的话来形容当时的形势。1946年10月,《纽约时报》的报道评论道:‘这种大范围的迁移和实施是历史上无可比拟的。谁若直接经历了这种恐怖,谁就会毫不怀疑这是对人类的犯罪。历史将会给予它可怕的报复。”“截止到1947年10月11日‘遣返行动行动正式结束,从前德国东部领土上被驱逐或逃亡的德国人为七百一十万人,从波兰中部地区被驱逐的德意志族人为一百一十万人,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驱逐的为二百九十万人,从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被驱逐的合计为七十万人”(朱毅维:《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世界国际出版社2010年11月出版,296~297页)。
二战后,将近一千二百万德意志的老百姓再一次遭受到新的折磨,他们扶老携幼,拖家带口,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在不到两年内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迁移,其中所遭受的坎坷与苦难是后人无法想象的。
刚刚摆脱了希特勒暴政的人们采取了比纳粹毫不逊色的暴行来对待敌对国的平民百姓,在欧洲历史上书写了同样的极其黑暗却鲜为人知的一页。正像英国作家基斯·罗威在其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的《野蛮大陆》一书中所描述的:法律和秩序荡然无存,因为那里没有警察,没有法官。在某些地方,是非对错似乎再无意义。人们自谋生路,无视所有权,财产只属于那些足够强大的人,以及那些为了保住财产不惜豁出性命的人。男人们手持武器,在大街上游荡,肆意抢劫他们想要的东西,女人们不论阶层,不論年纪,为求食物,为求庇护不惜出卖肉体。那里没有礼义廉耻,那里没有伦理道德,只有生存高于一切。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古稀之年的阿登纳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出任了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后又四任其职,执政长达十四年。在此期间,他表现出卓越和非凡的领导能力,他不仅具有德国人特有的原则性与严谨性,而且具有非常睿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政治谋略。他清楚,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下,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还是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对战后的德国都疑虑丛生,都恨不得把这个在不到二十年时间内就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让数千万生灵涂炭的民族死死地踩在脚下,不给它有翻身害人的机会。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任何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是不会立即采取让本国人民向占领者悔罪的做法,因为一旦提出这样的要求,不仅于事无补,反而适得其反火上浇油,造成更加对立的民族矛盾和冲突。阿登纳明白,对于联邦德国政府而言,首要的是重建家园,让人们重燃生活的勇气,唯有此,德国的复苏和振兴才有可能。在当时的情况下,活下去就意味着团结起来向前看,意味着要暂时忘记过去的仇恨,意味着德国人一段时间的集体失忆。
三
作为一名务实、精明的政治家,阿登纳认为,为了使一个混乱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恢复到某种程度的正常状态,关键是人才,特别是那些具有能力、有经验和业务专长的人才。但他所面临的困窘是,这样的人才不是死于纳粹集中营或流亡海外,就是由于反对纳粹政权而受到迫害,多年赋闲在家而丧失了工作能力,真正符合条件的恰恰是那些参加过纳粹党,现在还在接受审查的前纳粹分子。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阿登纳政府采取了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策略,缓和“非纳粹化”的压力。为此,阿登纳发表声明:“大多数德国人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1949年和1954年联邦众议院两次通过了赦免纳粹分子一般罪行的法案,1951年又通过了恢复1945年被撤职的原纳粹官员职位的法律。在阿登纳时期,大批原纳粹高级文职官员因此得以重返政府机关。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西德政府的十七位部长中,就有八人曾经在纳粹政权中担任过领导职务,或者是担任过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中的负责职位的人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西德司法界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前纳粹分子多达九千余人。
在东西方冷战加剧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也逐渐失去了彻底清查纳粹分子的兴趣。面对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咄咄逼人的压力,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迅速扶持西德政府,将其发展成为西方阵营中的实力成员,在欧洲防务上发挥作用。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分属两个不同阵营,其政治和经济制度、价值观念和意志形态完全对立的的东德与西德,在对清算纳粹罪行的问题上,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集体失忆”的做法。东德政府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产生希特勒的土壤,因此纳粹分子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西德;而西德政府则由于建设经济强国的需要,也对“非纳粹化”轻描淡写。总之,两边的德国人都仿佛在“揣着明白装糊涂”,蒙着眼过子日,表面上庸庸碌碌,忙于解决温饱和追求富足,实际上将清算纳粹罪行的责任搁置脑后。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开始转变。在经济社会迅速繁荣之后,“战后的一代”也逐步成长起来了。1961年在以色列举行的对“艾希曼审判”,1963-1965年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审判”,将清算纳粹暴行重新带入了公众视线。在这个意义上,贝娅特·克拉斯菲尔德所打基辛格总理的一记耳光,就成了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
1979年春,深刻揭露纳粹战犯灭绝犹太人的美国影片《大屠杀》在德国上演,立即掀起了一股反省战争、清算战犯的浪潮。影片在德国各地放映,观众达二千万,几乎占了联邦德国成年人的一半人数。首映之后的当晚,就有一万二千封信、电报和明信片寄到广播电台,同时,电台和电视台还接到五千二百个电话。对影片持赞同态度的占百分之七十二,反对的仅有百分之七点三,观众中有百分之五十八要求这部电影重新放映。许多生于战后的年轻观众在信中表示,觉得自己身为德国人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德国公众对于大屠杀的反思、清算纳粹的罪行是全方位的,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窥见一斑。1940年出生的画家乔晨·戈兹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屠杀犹太人的罪恶,他不辞辛苦地奔波在德国四处,一个一个地寻找犹太人的墓地,查找死者的确切姓名。戈兹发现,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每造访一座坟墓,祭典者都要在墓上放上一块石头。戈兹受到启发,于是和他的学生在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监狱所在地萨布肯镇的街道上,将铺在路面的石头挖出来,并在每一块石头上刻上他所寻找到的犹太人墓地的名称,以及发现时的日期,然后,再將这些石头字面朝下埋回原处,作为永久的纪念碑。几年来,戈兹和他的学生一共掘出一千九百二十六块石头,并一一刻写后放回原处。为此,他们还在路口安放了一块铭牌——“无形的警示”,提醒来往的行人,就在他们每天行走的脚下,深埋着无数被纳粹残害的犹太人的冤魂。
在德国各处都会有各种形态的“警示碑”,例如柏林市中心的“警示碑”就竖立在几家最热闹的百货公司对面,告诉每天从它面前走过的游人,这里曾经是纳粹集中营的所在地。在德国,人们已经将保留纳粹集中营的遗迹视为一种反思大屠杀的神圣责任。
四
1970年12月7日,一场大雪刚刚过后,潮湿阴冷的华沙上空彤云低锁。在凛冽的寒风中,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向犹太人死难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他伫立凝视着一幅幅受难者浮雕,突然,勃兰特双膝跪在死难烈士纪念碑前冰冷湿漉的大理石板上,大声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这个既不在访问日程安排内,事前也没有任何征兆的突然举动震动了世界。
就勃兰特本人而言,此时虽身为联邦德国总理,但因在纳粹统治时期从事反法西斯的活动,被希特勒政府剥夺了国籍,被迫流亡海外,直到1957年才刚刚恢复国籍。按理说,作为一名饱受纳粹迫害而且反法西斯的斗士,由他来承担德国法西斯的罪责似乎显得有些不公平。正像有的国外媒体所言:“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了。”波兰的媒体当时是这样评论的:“作为反纳粹战士的勃兰特这一跪,使德国真正地站起来。”
1973年,勃兰特在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谈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我问心无愧,而且我认为把纳粹的罪过归咎于我国人民和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发动二战的战犯去承担。尽管我很早就离开德国,但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出任德国总理后,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那天早晨醒来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能只限于给纪念碑献一个花圈。我本能地预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尽管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献完花圈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这就是下意识吧?”
勃兰特超出国宾礼仪的惊人之举不仅使在场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和记者们为之动容,而且感动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当一名记者采访当地的犹太人:“你们恨德国人吗?”回答同样令人感动:“不恨,因为德国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民族。”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安妮·费兰克,当年仅是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曾惨遭强暴,又被剃了光头,换上黑白条的囚衣关进了集中营,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在集中营里,她目睹了纳粹摧残人类文明的种种暴行——电刑、绞刑、枪杀、剥人皮、炼人油、用活人打靶、毒气屠杀等等。1944年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这座欧洲最大的人间地狱,安妮·费兰克曾亲眼看到从仓库里搜出的四百多公斤人发、九百多公斤人皮、一千二百多公斤人油。战后,安妮辗转来到华沙定居,并结婚生子。当得知勃兰特总理来华沙赎罪的消息时,她百感交集,热泪盈眶,特意派小女儿莎莎为勃兰特献上象征和平的法国黄玫瑰。勃兰特接过鲜花,含泪亲吻了小姑娘的面颊,连声道谢致歉,并祝福安妮夫人健康长寿。
在对纳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中,德国知识分子承担了重要的使命,他们绝不仅是简单地就事论事,把所有罪责统统归咎于希特勒,一骂了之,而是从哲学、宗教、文学、史学、基督教神学的高度及德国文化的根源,反省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原因。
对于纳粹罪责和大屠杀的反思与批判,首先是责任问题。而在德国人眼中的责任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在当时的欧洲道德又是一个宗教问题,而宗教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一个信仰问题。循着这样的逻辑思路,在对希特勒极权专制的批判中,德国知识分子寻根溯源,他们认识到,“纳粹分子扮演的角色原本是上帝扮演的角色”。由此看来,中世纪基督教中的神权政治与纳粹的极权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
为什么说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同纳粹主义如出一辙?首先,它们都旨在确立某种终极真理,并形成终极真理与强权暴政的神圣同盟,它们都图谋通过所谓的终极真理达到对人的思想实施绝对控制,让服膺专制、畏惧暴力的观念深入到人类灵魂之中,以实现对社会的全面专政,对人的全面控制。其次,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它们都妄图对思想进行审判,对言论进行封锁,不惜用残酷至极的方式摧残、凌辱、虐杀自由的心灵,它们最不能容忍精神多样性和思想自由,为实现属于它们的终极真理,都采取了用铁血暴力征服一切的手段。最后,它们所干的这一切,又无一不是在神圣与正义的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将凶残的兽性和腐败的贪欲发挥到极致。它们都宣称自己拥有真理且道德高尚,是一群让人仰慕的代表民意的政治精英,它们极力宣扬,整个社会必须由它们这些高于普通人的特权阶层才能实现统治,这个团体在中世纪是主教、神甫、修道院的僧侣,而在第三帝国则是纳粹党徒、冲锋队、党卫军、盖世太保。
正像有的西方学者所分析的:“只要有极权主义和普通人,就有恶。”西方极权主义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在第三帝国复活,纳粹主义能够猖獗一时,其重要原因是来自人类心底里的最黑暗的本能冲动——无尽的贪欲。只要人类存在,这种本能冲动就会存在,并成为极权主义的心理動因,而纳粹主义就为这种心理动因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存在,提供了最为适用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基础。
毫不夸张地说,当人类的贪欲膨胀到试图垄断世界的一切资源,包括垄断人类的精神在内时,或者说试图通过奴役人类的心灵来拥有整个世界时,隐藏在人的生命深处的贪欲便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心理起点和专制暴政导火索。
1988年11月10日,就在“水晶之夜”事件发生五十周年之际,德国联邦议会主席詹宁格亲自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在西德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在讲演中他指出:“1933年-1938年,在德国无疑发生了一场真正的革命:把一个法治国家变成了一个罪恶甚嚣尘上的‘国家,把一个国家变成了一种工具,并以这个工具,毁灭了正常的法制与民族规范,从根子上摧毁了本应具有存储国力和保护民族精粹功能的国家体系……许多德国人心甘情愿地受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蒙蔽,不打算拒绝它的诱惑。许多人以事不关己的态度,眼看着罪行在身边发生。许多人甚至卷了进去。我们有没有犯罪?有没有觉得心上不安?这是每个人必须做出解答的问题。”
詹宁格博士的发问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是丧失了思考、放弃了权利、失去了自尊的德国人民造就了希特勒。与此同时,在纳粹的暴政高压下,德国人民无法左右自己的生活,知识分子屡战屡败,反对派无能为力无所作为,于是,面对极权专制,德国民众选择了精神上任人阉割,政治上任人玩弄,生活上任人摆布,沦落为“沉默的大多数”。
战后,虽然美军在西德境内对普通德国人曾以表格登记审查的方式进行了“非纳粹化”,但当时德国民众的抵触情绪非常强烈,对纳粹的罪恶历史多采取沉默与回避的态度,“非纳粹化”运动也因此半途夭折。尽管有少数人,例如德国杰出的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曾大声疾呼:凡是不曾以实际行动制止纳粹党上台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人,均应对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承担责任。但这种深邃的见解,在当时并不为人所接受,而卡尔·雅斯贝尔斯本人却不断地遭受到人身攻击。
由此可见,清算纳粹的罪行离不开德国人民的觉醒和参与,因为“历史不属于政治,也不属于政府”,它属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