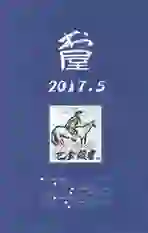关于鱼儿和飞鸟的记忆
2017-06-05疏延祥
疏延祥
我总认为,对村庄有完整记忆的人是有福的。每一个村庄都有比较完整的生态,每一个村庄都有丰富的民俗风情和各种性格的人物。对于后者,往往是小说家创作的土壤。比如沈从文的湘西也是由一个个类似村庄的单位组成,莫言山东高密东北乡是以一个夏庄镇河崖平安庄为主体构成的。小说家的小说既描写人,也写物,写生态景观,动植物也是他们写作的对象,但写人是他们主要任务。一些散文家尤其是农村走出来的作家描写家乡,自然离不开物,如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就有不少物的描写,但这种对物的描写是和村庄环境、人联系在一起的,以村庄生态为主体,把各种虫,各种鱼,各种鸟单独拎出来,而且一类一类的,单独成书,不说中国当代文学少见,现代也少。韩开春先生以自己曾经生活(现在还时常回去)过的苏北平原废黄河边上一个叫作时庄的小村子为对象,写自己亲密或接触过的虫、鱼、鸟,写虫的部分结集为《虫虫》,写鱼的部分结集为《水精灵》,写鸟部分结集为《雀之灵》,皆写得趣味盅然,值得一读。
关于《虫虫》,我已写过评论,这里想谈谈后两部作品的感受。
有村庄,就有各种各样的鱼,从农村走出或仍在农村生活的人对它们都有记忆,甚至有故事,但把它们写成一篇篇文章,就既要有生物学知识,也要有生花妙笔。比如,对于时庄的“屎黄屁子”,开春知道它的学名叫“鳑鲏”,这种鱼依靠河蚌代孕,同时也将河蚌的幼子钩附到自己的鳃或鳍上,生出一个个被囊,把幼虫包裹起来,直至小河蚌独立生活才会从它身上脱落。这种生物学知识几乎遍及开春三本写物之书,在我看来,这是高大上,正是它们和一个又一个独属于开春的个人记忆的组合,才使得这几本著作丰富多彩,有着独特的价值。
对于鳑鲏,开春是在时庄汪塘获得感性记忆的,认识了它,开春母亲大人叫他淘米,他不再感到枯燥,常常把淘米箩放进塘中,再端出水,就能捉到几个,而当周老师告诉他,这是一种非常有爱心、对子女极其负责的小鱼后,韩开春更爱它们了。
对于鳑鲏,我有家族记忆,也有个人记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农村食物贫乏。我们那儿靠近圩区,鳑鲏非常多,一次我大姐捞回一脸盆小鳑鲏,此物长不大,以拇指大居多,无法逐个挤出肝脏泥巴,母亲只能用脚踩后洗洗就煮,结果吃了一碗,吐得要死。
我大概八九岁时就认得鳑鲏,能用捞鱼工具时就捞过它,十七岁时在河里以罾为具,以“糠食”(炒过的米糠)为饵,捉过一些稍大鳑鲏。因为这些美好回忆,阅读开春写鳑鲏的文字,我觉得我们心是相通的。
“桃花流水鳜鱼肥”。对于“鳜鱼”,大家都知道是美味,臭鳜鱼,恐怕都吃过,不少人也能将这种鱼与张志和的词联系在一起,但亲手和亲眼看到它们出水的人可能并不多,尤其是生长在城市的人。我上高中时跟着小舅去公社鱼塘偷鱼,那天,我是参加学校浇油菜劳动的,劳动结束回家,小舅提着打鱼的网,遇上我,让我跟着他。在公社鱼塘,小舅很快捞上条鳜鱼,让我放进粪桶里,此时看塘人已经向这边跑来,小舅要我带着鳜鱼跑,这条鱼一斤多,第二天舅舅在集市上卖了,得了一块多钱,当时生产队一天工分只有三毛钱,那时,我知道鳜鱼真贵!
鳜鱼,在时庄叫“季花鱼”,韩开春将它和时庄有人不会撒网,还有白胡子老爷爷讲的“季花鱼精”的故事,李大华子在汪塘里捕获一条斤把重鳜鱼的故事,还有鳜鱼昼伏夜出的习性,以及它刺人有毒,童子尿可以解毒等等组合在一起,韩式关于鳜鱼的美文便诞生了。
1979年,我看过越剧《追鱼》,鱼精的美艳令少年的我怦然心动。对于反派蚌精,我已没有记忆了,作为同代人的开春却有。河蚌成精,那是神话传说。真正的河蚌,农村几乎每个水塘都有,我们那儿人都看不上它,没有人吃它,孩子们觉得好玩,洗冷水澡时顺带从水底泥中抓上几个,回来用蛮棰捣碎硬壳,鹅鸭争抢。
时庄人与我们一样,不吃蚌肉,两地不同省,有几百公里路程,乡风如此相同,也是一奇。读韩开春《河蚌》,我喜欢“夏日游泳的时候常能于脚底下摸上几只,沉甸甸得像块石头,我不太喜欢它的模样,青黑的铠甲,沾满污泥,即使洗净,也是貌不惊人,没有鱼的灵动,甚至不若田螺,有着优美的螺旋”这样朴素且有感情的文字。
河蚌有着坚硬的壳,人凭力道,即若大人,也奈何不了。我小时也像开春,想掰开一窥究竟,终是失败。但它不是锤子、石头的对手,一用这些,它细白的肉就暴露无疑,不过,韩开春因此不仅想到“鹬蚌相争”,还联想到“外强中干”这样成语,对于这种文学联想,少年的我似乎缺少如此发达的文学细胞。
对于鲤鱼,我也是打小熟悉,我是不善捕鱼之人,从未捉过它。有一年,祖父要我到五公里外的杨湾镇买鱼,告诉我要一斤以上,结果我买回了一条一斤多的鲤鱼,但祖母说,鲤鱼是发的(指有炎症的人不宜食用),不宜于祖父的支气管炎,不过鱼还是煮了。我知道“鲤鱼跳龙门”的故事,但不晓得鲤鱼又叫“龙鱼”,隐约记得越剧《追鱼》与鲤鱼有关,一查,果然由王文娟饰演的鲤鱼精正是《追鱼》主角。韩开春告诉我们,黄河鲤鱼非常有名,《诗经》就有记载,“岂其食鱼,必河之鲤”;《洛阳伽蓝记》也说“洛鲤伊鲂,贵于牛羊”。
历史上有过不食鲤鱼的群体和禁食鲤鱼的朝代。读书人不吃鲤鱼,吃了鲤鱼,哪能跳龙门呢?孔家人不吃鲤鱼,因为孔子有个儿子叫孔鲤,生孔鲤时,鲁昭公曾以鲤鱼作为贺礼赠送,此子因此得名。
禁食鲤鱼的朝代是唐代,“李”和“鲤”同音,幸好朱元璋沒有这样干,否则,有明一代,都不能吃猪肉了。
“卧冰求鲤”,年画“年年有余”,鲤鱼是中国文化的符号。关于这些,韩开春娓娓道来。
还有北方人叫黑鱼、南方人叫“乌鱼”的乌鳢,学名“鲶鱼”(安庆人叫“鲢胡子”)、黄鳝、泥鳅、刀鳅、老鳖、鳊鱼、银鱼、螃蟹、小龙虾、青虾等这些散发出乡土气息、极其平民化的鱼类,韩开春都有故事。其实,大多数读者对它们也有温馨记忆,只不过我们少韩氏彩笔,也没有他那样勤奋,愿意花时间把自己与鱼的琐碎、片断记忆写出来,与人分享。
鸟同人一样是温血动物,自古以来即受到人类喜爱。中国有漫长的笼养鸟的历史,诗词和书画涉及鸟的很多,很早就有《禽经》这样的著作,可以说,中国是鸟文化发达的国家。诸如“东飞伯劳西飞燕”、“劳燕分飞”的“伯劳”和“燕子”;像《格物总论》云:“莺,黑尾,嘴尖红,脚青,遍身甘草黄色,翅及尾有黑毛相间。三四月鸣,声音圆滑。”这和今天的鸟类图鉴描述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而王维的“阴阴夏木啭黄鹂”、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更是开启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美学想象。韩开春《雀之灵》涉及二十七种鸟类,所幸的是,笔者都认识,而且除了“布谷”和“鹩哥”,其他二十五种我都在野外观察过,我也读过鸟类学家、中国鸟类学的奠基人郑作新写的关于鸟类科普文章。当然,我们不能说《雀之灵》超过古代的《禽经》和郑老写鸟的文章,但由于开春写鸟融入了自己的乡土经验,便有了自己的特色。比如他亲眼在乡下大伯屋后看过伯劳吞食麻雀,这种“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绝杀,留存在韩开春脑海里,如今再写出来,就使得他对伯劳有相当的发言权。
《水精灵》、《雀之灵》属于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丛书的两本,正如封面上所写,它能引导孩子“在童年的天空中自由飞翔”,是真正原创的大自然文学著作,对孩子们有启蒙意义。正如刘先平先生所说:“大自然文学的首要任务是引领孩子们认识山川河流、花鸟虫鱼,从发现生命形态的千变万化、构造的无穷奥妙……大自然的丰富多彩开始,进而感悟生命的伟大,热爱生命,尊重生命,热爱自然,保护自然……”。韩开春这三本大自然文学著作(还有《虫虫》)不仅适合孩子读,也适合大人读。只要你去阅读,你会发现树影斑驳的村庄,有一个追逐飞鸟、鱼儿、虫子的小小韩开春身影,那也是儿时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