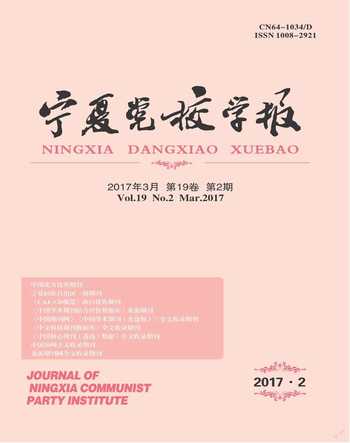马克思的幸福观及其现实启示
2017-05-30张海滨李琳
张海滨 李琳
摘要:对于人的现实幸福的思考,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主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人的角度出发,深入地思考了“什么是幸福”,“工人现实的不幸的根源何在”以及“如何实现人的最终的幸福”这样三个问题,清晰地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思想逻辑。深入挖掘和把握马克思的幸福观,对于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以幸福为核心的发展观,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幸福观;中国梦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也是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反复思考的一个哲学命题。对于人的现实幸福问题的不懈求索,也是贯穿马克思一生的思想主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思考幸福问题的一部代表作品。在《手稿》中,马克思透过对异化劳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和共产主义的深入思考,深刻地回答了有关幸福的三个核心问题,即什么是幸福,现实的人的不幸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实现人的现实的幸福,搭建了马克思幸福观的基本思维框架。深入研究和把握马克思对于幸福问题的思考,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来说,无疑具有极强的反思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幸福的前提是对人的本质的深刻把握
什么是幸福,这是所有思考幸福问题的人必须首先回答的一个问题。幸福是人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是人对自我的一种价值评价,人们对于幸福的讨论始终是围绕着人来展开的。因此,思考“什么是幸福”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对于“人是什么”的回答。人的定义,决定着对于幸福的理解。《手稿》中,马克思对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思考,主要是从人的类本质的角度出发。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类存在物,这种类特性是人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人具备了把握自身类本质的这种能力。“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白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类本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在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过程中,不仅满足了生理本能的需要,更是将自己的思想、审美赋予对象世界,最终导致了对象的人化和人的对象化。人只有在这样的生产活动中才彰显自己的本质,体会着“人”的幸福。
然而,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使得劳动不可避免地陷入异化状态。异化劳动的存在使人丧失了自己的类本质特征。在异化劳动过程中,人被迫退回到仅仅满足生理机能的动物的劳动层次上,劳动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在这样的劳动中,人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人只有在不劳动的时候才是快乐的,而劳动的时候则是不快乐的。在《手稿》中,马克思运用异化劳动的概念来详细地描述了工人在劳动中所体现的悲惨和不幸。这里,马克思不是用肯定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于幸福的理解,而是用否定的方式告诉世人,什么叫不幸,现实的人只有实现对于异化劳动的扬弃,才能完成对于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实现真正的彻底的幸福。
二、幸福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辩证统一
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篇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考试的论文中,马克思就写到:“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可见,当时的马克思就已经在个体命运和人类整体命运的辩证思考中去理解幸福了。《手稿》中,马克思从工人异化劳动的事实出发,重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下,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所呈现出的紧张矛盾。
马克思看来,在私有财产制度下,个人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之间往往呈现一种对抗状态,即我的幸福即他人的不幸。奴隶主和贵族们的幸福是建立在奴隶——一种被当做会说话的工具的辛勤劳作基础之上的。封建主们幸福的奢华生活同样建立在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勤耕作之上。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抗状态则达到了顶点。资本家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象征,追求利润和财富成了其最大的幸福源泉,但这种幸福却是建立在工人巨大的劳动付出和悲惨的现实境遇基础之上的。资本家越是感到幸福,工人越是感到不幸。对于工人而言,生活的贫困使得一切精神上的享受成为不切实际的奢侈品,“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对于资本家而言,物质上的满足只能激发他们无尽的贪欲,而丧失了对于美的追求和享受,这种幸福恰恰是人的自由的丧失,是人依然无法摆脱“为物所役”状态的真实写照。因此,在异化劳动过程中,工人和资本家全都丧失了自我,工人的解放运动即共产主义的实现,解放的就不仅仅是工人自身,而是包含资本家在内的全人类。因此,一个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幸福,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全社会的幸福,是个体幸福与社会的、集体的幸福的有机统一。
三、幸福是在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中完成的
马克思的幸福观不是建立在抽象的、以纯粹的理性思辨的形式展开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而是立足于现实的具体的人,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的角度出发,在历史过程中把握幸福的含义。因而,从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的立场,从实践的、历史的角度,而非抽象的、逻辑思辨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幸福问题,是马克思区别于之前所有思想家的关键所在。
从历史唯物主義的立场出发,马克思认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幸福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不可能从抽象的概念中去寻找和定义,也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上独立地得到实现,归根到底,它是要受到现实的生产活动的制约和支配。人的自由的、有意识地生产活动,又是在历史过程中展开的。所以,幸福只能是在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中得到实现。
立足于现实,马克思具体考察了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生活状况,并最终找到了工人不幸福的最大根源——私有财产制度下的异化劳动。所以,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而言,幸福的实现必然是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而异化劳动的扬弃就是扬弃以私有财产制度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这里,马克思通过对共产主义的科学阐释表达了他的幸福观:幸福不是抽象的、静止的,更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对应的理想状态,幸福就是改造现存的一切不合理的现实制度的具体的、历史活动。
四、马克思的幸福观的当代启示
首先,树立幸福的发展观。工业革命的爆发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张,作为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核心内容的工具理性也随着资本的流动,被深深地植入了广大民众的头脑之中。然而,这种工具理性除了使现代社会的生产更加富有效率之外,并没有能够带领人类走出“为物所役”的困境。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和机械化,非但没有将人类带向通往幸福之路,反而越来越走在资本的奴役之路上。伴随着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日益商品化、标准化、模式化和强迫化,作为人之本质力量确证的劳动行为越来越多地失去自己的主动性、丰富性以及自足性。马克思在《手稿》中的思考,本质上是可以被看做是对于以工具理性为代表的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反思,不仅仅是针对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同样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如果仅仅停留在生产力无节制的扩张与发展上,就难以摆脱异化劳动所带来的幸福困局。因而,生产力的进步只有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对于幸福最高的价值尺度的时候,才可以避免重蹈發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所以,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原则的幸福发展观,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历史优越性。
其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实现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有机统一。2013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回信中谈到:“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碍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人生理想融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完整统一。中国人自古就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深刻地表达了将个人幸福服务于民族大业的价值关怀。这一点与马克思在类本质中体现个人幸福的观点有着天然的契合。中国梦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统一于伟大的民族复兴实践之中,实现了个人与国家命运的统一,理想的幸福与人民现实的幸福的内在统一。
最后,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的幸福观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因为只有在那里,人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是,共产主义“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因此,共产主义不是静态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在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下的“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只有不断地深化改革,让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于民,才能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幸福红利,才能让更多的人坚信共产主义信念,在永无止境的历史实践中体验人生的幸福。
责任编辑:查徽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