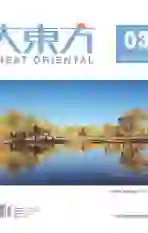萧红《生死场》的女性书写
2017-05-30玛伊莱·艾麦尔
【摘要】:《生死场》,生和死连缀起了全书的主题,生育、妊娠、临盆,这些只有女性才能经历的事情在萧红笔下是纯粹的苦难是无从选择的。萧红站在女性的角度,揭示了在男权社会中孤独无助的女性形象,生活在无爱并压迫的环境中的女性,生活的困苦,还要作为男人们的“同谋”,正像她自评“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关键词】: 萧红 生死场 女性
对于萧红的认识最初来源于《黄金时代》的演绎,也多听过她与萧军和端木的情感纠葛,《生死场》是我第一次阅读萧红的作品,带给我的震撼是十分强烈的。作为“奴隶丛书”之一,萧红对于人性、人的生存和死亡进行了深层探索,我始终认为,女性作家在观察和描写这个世界时有男性作家无法达到的敏锐和细致,萧红从女性身体的角度表达了对生死、对男性以及对民族国家的理解。《生死场》的帷幕由一头在大道边啃榆树皮的山羊挑起,接下去的一句是:“城外一条长长的大道,被榆树打成荫片。走在大道中,像是走进一个荡动遮天的大伞。”
一位在生活中饱受困苦的女作家以她犀利的观察把她自身的生命图示和农村生活图示以近乎残忍的描写展现在我们面前,生死场的前十章的“生”、“死”主要以女性的身体为依托来表现,萧红笔下的女性形象多是动物性的,她们生活在无爱的环境中,怕男人、怕流言、所有的女人都像“是在父权下的孩童般怕自己的男人”,成业的嫂子说:“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 “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作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地服从。”女性们在男权社会下是无力反抗的,从出生起便是这样”,萧红幼时便是这样,父权在她的家庭是权威的,她笔下的女性总是低贱的、麻木的,这种被压抑的情感已经埋在内心深处,在潜意识里我认为萧红是对男权有着隐性崇拜的,生死场里的女人们,一方面妥协于男权一方面在潜意识里为男权服务,作为自己男人的同谋。他们低贱麻木的让我在初读时有些难以接受,但是正如萧红自己所说; 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生死场所表现的正是在故乡乡村男权压抑下的卑微、困苦和愚昧。她笔下的女性都是悲惨的。打鱼村最美丽的月英,性子温和,却过着悲惨的生活,半夜透出哀楚的声音,丈夫的虐待使她在说话时只有舌尖在转动,被砖块围起的月英身下已经腐烂生蛆,她的美貌也早已不复存在,“她像一只患病的猫儿,孤独而无望”。
萧红的一生颠沛流离,却一直在反抗,不断地逃离,出走,漂泊,从呼兰到哈尔滨,之后北平、青岛、上海、东京、武汉、西安、重庆、香港,为逃婚、为求学、为自由、为独立、为疗伤、为写作、为温暖和爱……虽然一路伤痕累累,历经战乱。却也难以求得安稳和平的写作环境。《祖父死了的时候》中写萧红在和父亲的打斗中生活,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我”是小孩,以及父亲对于新娶的母亲的态度,萧红早早地就看到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与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压迫和痛苦,“我到邻家去看看,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是怕舅父”这不正是生死场中打鱼村的女人们么?她们的血肉之躯不断被侮辱、被践踏、被撕裂、被损毁、被牺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自己经历过的生育经历都在生死场中得到了描写。萧红把女人的生育称为“妇人们的惩罚”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由生到死的命运,无从选择,不管是身体还是命运。所有的女人都被男人摆布,没有愿不愿意一说,不仅要承受生育之苦,还被看作是自己的罪过。五姑姑的姐姐快生产了,光着身子爬在土炕上的尘土中挣扎。丈夫醉酒归家,差唤她拿靴子,未应,嘴里骂着“装死”,拿起长烟袋就打了过去。“每年是这样,一看见妻子生产他便反对。”一夜苦挣苦扎仍然生不下来,丈夫又进来了,兜头浇下一大盆冷水。“大肚子的女人,仍漲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地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每当看到这样的描写,我开始是震惊和愤怒,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任何一个女性都无法接受这样的描写,生育是多么伟大而神圣的事情,让我不禁怀疑即便是麻木贫贱的男权主义乡村,竟然对于女性践踏到了这种地步么?然而,“孩子终于生下来了,死婴。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浸着血。”又让我觉得这就是刑罚,如此残忍又血淋淋的刑罚。每一个女性的个体的痛苦被放大,那么所表现的就是普罗大众的痛苦,不仅仅是女性,不仅仅是打鱼村,整个中国的乡土社会都要受到批判。即便如此,萧红的叙述方式还是让我花费了一些时间去接受,不同于我想象中的清高淡漠,萧红的写作似乎可以用残忍来描述,贫瘠的土地,受到压迫的女人,生育的痛苦,以及后面日本的入侵,生不能安安稳稳的生,连死都身不由己的死。混混沌沌的一生,没有一丝幸福。金枝即将临盆仍然被迫满足丈夫的欲望,初生的女儿被亲生父亲摔死;即便刚烈如王婆,丈夫要搞“镰刀会”她教丈夫用枪,她可以说出“孩子死,不算一回事”可到了冬天,还会想起她三岁的女儿和经历过的痛苦;“在王婆服毒下葬时全村女人借机放声一哭,因为她们的一生可哭的机会并不多,心里再苦,平白哭起来,是要被骂挨打的,而她们可哭的痛苦却太多”;生活如此艰难却连流泪的机会都少有,是何等的不幸与苦难。妇女们除了肉体的痛苦,精神上也饱受痛苦。即便是未嫁人之前的金枝和成业之间都没有爱情,爱情这个因素在萧红的《生死场》中似乎消失了,大多度作品即便并非以爱情为主题,也多有爱情线索,女人是在无爱的环境下生存的,没有爱情,甚至没有对爱情的憧憬和向往。
参考文献
[1].萧红.生死场. [M] 京华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玛伊莱·艾麦尔 (1994-),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人,中央民族大学2013级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宗教学专业本科生。
(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