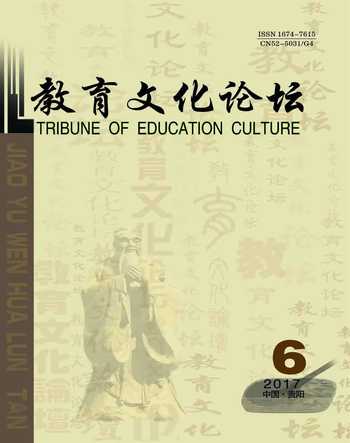对李端棻规训后学的学术性考证
2017-05-30余文武
余文武
摘要:作者将追求近代化的李端棻作为规训后学的主体来对待,其核心问题在:其规训的对象是否明确无误,其规训的内容是否鑿凿有据,其规训的效能是否明效大验;研究主要采用历史文献法,厘析既往研究中的可信史料,剔除旧有文献中的不根之论,以期采获李端棻规训后学与诱掖后进的旁引曲证。
关键词:李端棻;规训;后学;学术考察
中图分类号:G40-09;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6-0125-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6.026
作为身在体制内却站出来挑战旧体制的第一人,李端棻被梁启超称为是“二品以上言新政者一人而已”的晚清重臣。他曾替康有为代递《上清帝第五书》,曾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改革派进入晚清中枢的密荐者,曾上呈《请推广学校折》和《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两个重要奏折,曾在戊戌变法的紧要关头取代守旧派大臣出任礼部尚书,曾在归隐后创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师范学堂之一——“贵阳公立师范学堂”, 曾与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之流同列“松筠十君子”……可是,李端棻为何做出以上离经叛道之举,从京师清流派成员一跃而成维新派干将?就此,多学科学者均在潜精研思其间的个中道理。不过,他慧眼擢拔梁启超又反受其广譬曲谕的多方开导,他跟出使东洋的黎庶昌与出使西洋的张荫桓相视莫逆,他在数十年的若干学政任上奖掖后进再而罗致人才,以及蛰居贵阳与乡贤毕力同心而共赴事功的殊勋异绩,是作者见猎心喜的学术旨趣。
“规训”一词语出社会学家福柯,具有纪律、惩戒、训练、学科等多重含义,也是教育学研究的概念。在此文中引作学术训练,特指先知先觉率马以骥、同志同僚能者居先的姿态,对于后学之政治上的引领与学问上的提点之意;后学即学问居于人后之后进学者。论文假定李端棻自入仕起即获得日就月将般的学问进步,以一个精明强干的开明政治家形象示人,拥有旷达不羁的胸襟、高明过人的思想与才德兼备的品格,在多地的学政任上对莘莘学子三薰三沐,尔后重任在肩仍勉力对同道同僚发蒙解惑,再而借助学堂讲堂力行金石良言的教化之功,其道德文章与嘉言懿行足以成为当朝当世的楷模。作者将审读事关李端棻规训后学与知识生产的材料,作李端棻研究文献的“文籍先生”,规避之前盲信的单文孤证,考证李端棻规训后学、诱掖后进、开办新学与著书立说的史实,采获其导德齐礼之有案可稽的凿凿证据,为李端棻研究领域开出信而有征的学术意见。
积学待时与宦海交游
李端棻幼年六岁时失怙,其母独自承担阿保之劳。随后,跟随其叔父李朝仪研习四书五经,在积微成着的铺垫之后,随即向其舅父何亮清领受科举之教。因此才有梁启超的“京兆公(李朝仪)以圣贤之教率其家……公终其生立身事君,大事凛然不可犯,一如京兆公” 一说,亦表明李氏家族的先人的确有言传身教的道德示范。李端棻晚岁亲自讲与其表弟何麟书,称“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此亦可增加其领受家教的确凿证据。为细察其积学待时的史实,有必要在此悉数呈现李端棻于艰辛幼年时目不窥园的笃信好学之表现。道光二十九年(1850年),时年17岁的李端棻进入其舅父何亮清执教的贵山书院,跟随这位日后的翰林院编修学习帖括词章(应试的道德文章规范),何亮清对执弟子礼的外甥颇为器重,曾赞叹朝经暮史的李端棻:“苾园忠孝之忱根于性生,异日必能为国家尽瘁”; 其舅父出仕四川之后,李端棻再赴京投其叔父李朝仪门下,李朝仪视李端棻为己出,以一喷一醒的推动督促,使李端棻对《诗》、《书》、《经》、《史》博识多通,其学业进展亦呈杆头日上之势。
咸丰三年(1851年)弱冠之年李端棻即补博士弟子员(秀才),咸丰十一年(1861年)顺天乡试中举人,同治二年(1863年)会试连捷成进士,选庶吉士后入翰林院任编修。由是,在以道学吏治闻名于世的李朝仪和奉行经世思想的何亮清的双重“熏影”之下,以及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等理学家的器重之中,李端棻在学问与志业上白日飞升,期许着一个“君圣臣贤”的政治舞台。除却短时间担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之外,李端棻的宦海生涯主要与科举密切相关,值得晚清教育史研究者倾耳注目。同治六年(1867年)典试山西,同治九年(1870年)分校顺天试,同治十一年(1872年)出督云南学政,光绪四年(1878年)丁忧期满入京,迁监察御史,因叔父李朝仪擢升顺天府尹,李端棻按例回避,重返翰林院,擢升内阁学士,光绪十五年(1889年)以内阁学士典试广东,光绪十七年(1891年)典四川乡试,光绪十八年(1892年)任会试副总裁,光绪二十年(1894年)复典山东乡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8月授为礼部尚书”。 这其间得以领有与朝野人物在政治上此唱彼和、在交谊上诗酒唱酬的人际交往优势,为其荡平宦海风波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此亦是我们管窥其获致同侪学问规训的径路。
与出使过外国的同僚交往,为其提供览闻辩见的通道。比如遵义沙滩人黎庶昌曾在光绪初期受命出任西欧四国参赞,历时6年之久,游历欧洲10国;李端棻在其拜会时询问西洋情形,再阅读其手稿《西洋杂志》,两人声气相求。又如与“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黄遵宪交往,黄遵宪早年随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复任驻美国旧金山领事,之后又随法英比意四国公使薛福成出使英国任参赞,再而赴任驻新加坡总领事;李端棻与之会晤于北京,伺机了解国外的森罗万象。 日后随新出史料,还可以再度证实李端棻受欧风美雨沐浴的铁案。
与出仕的黔中籍官员交往,领受前辈有风有化的教诲。李端棻进京入翰林院任编修之后,其叔父李朝仪彼时颇得朝廷重用,先后在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等地出任知府,忙着行兵布阵、防御捻军, 其叔父单刀赴会敌军帐内说服叛将的胆识,对曾居李朝仪家中的李端棻,在立身处世上给予耳熏目染般的显著性影响。李端棻丁忧守孝期满返京途中,特地绕道成都拜望在四川任总督的乡贤丁宝桢,领受耳提面命之教;丁宝桢智杀总管太监安得海而名满天下,在治理黄河、海防建设、革新盐政等方面颇有伟绩丰功,李端棻视其为轨物范世的榜样。
从同治二年(1863年)入翰林院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遭免官流放,李端棻从政35年之久;在朝纲不振、国势衰微的情形之下,于少年时代磨砺以须,心慕手追叔父李朝仪的道德人生,在寒窗苦读中藏器待时;于青年时代砥节砺行,精诚团结诸多朝野志向高远的同道,为江河日下的旧中国尽一份学子才力。由此,还可以开掘若干李端棻与近代名人的交游故事,从中探察他们为询谋谘度而焦思苦虑的史实,以及在政治上的桴鼓相应之势。譬如,与贵州学正严修的过从,支持其开设经济特科,以达到“培养天下人才来治天下事”的目的;与同榜考中进士、同事供职于翰林院编修的张之洞,抨击朝政、坚持甲午海战的主战立场;之外,联袂翁同龢、识拔梁启超、荐举康有为等,均是值得行思坐忆的大事象。
“宦海交游”可列为窥察李端棻规训同僚的视角。李端棻仕宦生涯35年,与政客文人有良好的交谊,有如清流派干将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宝廷、邓承修、黄体芳、张楷、邓庆麟、邵积诚等,与李端棻合称“松筠十君子”,他们在济世匡时中砥节砺行;之后,李端棻名列帝党集团,与翁同龢、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长麟、张謇等因高情远致而道同志合;此外,还与廖寿恒、张荫桓、谭继洵、陈宝箴、黄遵宪、丁宝桢、黎庶昌等相知有素而惺惺惜惺惺。 此交代意在说明其领有的交谊圈子,为其在位从政奠定了坚实的人脉根基,并得以呈现其学问规训的对象与范围:每有奏折呈递朝廷,总有同僚八方呼应,成为其思想观点的奥援;同僚与之论学多有抵牾之时,因其精密详备的观点立场而折服:
一则李端棻有扎实的学问功底与精深的考证功夫,能指陈晚清颓废不振、病痛百出的时弊;二则李端棻之陈述能彰显问题意识,能一语中的地指明甲午海战之后晚清政治的破局之策;三则李端棻有通权达变的襟怀,并非一味地“尊古抑今”,而是强有力地 “申故抑今”。规训本身不限于师长对于弟子,还有道德知识的“掌控者”对于“后知后觉”的知识规训。李端棻对于同僚的规训,于今看来,形式上别具一格,内容上确切不移。
规训后学与诱掖后进
若以规训理论来审察李端棻的实教从学,难以尽喻其口讲指画的学科规训,亦未见其事关专才孚育的专门理论析出,因为晚晴时局给这样一位政治家的重任是辅佐朝廷、力挽困局,李端棻年富力强之时在“金口木舌”的教化事业上的用功当有新出史料来佐证。故我们探察规训后学与诱掖后进的真相,要从其参与的里程碑式的大事件中管窥其创造化育的思想脉络。
1.呈遞奏折。《请推广学校折》的全名是《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折》,是一份影响中国近代社会教育体制的重大纲领,它力主变革陈旧的教育体制,提出新式学堂创建的具体措施。这份奏折的写就,是李端棻“念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的危机意识使然,其建言内容不仅涉及变革学校教育的建议,还大胆建倡设藏书楼、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重大举措,以此发展晚清困厄中的社会教育。如果说《请推广学校折》是一份启蒙朝野思想界的宣言书,那具体的被启蒙对象都是谁?作者认为朝廷的执掌者(皇帝)和权力的掌控者(重臣),民间儒士乡绅和地方各级官员,以及近代学校教育的拥趸者均在之列。其中,在设藏书楼的事宜上最具格局与眼光,提出陆续译出西学,制定发挥图书价值的利用规程,譬如由印书局将西学书籍分送各省,使天下学子“得以自勉于学,无为弃才矣”;再次,在开设书局的问题上颇具前瞻性意识,他感叹先前的西学译著“详于艺术而略于政事”,为达到助益治国、审察时局的政治目的,他郑重建议在京师设立大译书馆,分类译出最利于“增益见闻广开才智”的西学经典;至于广立报馆则更见李端棻规训世人的思想,他声言报纸对于开启民智传播资讯的重要性,即“在上者能措办庶务而无壅弊,在下者能通达政体以待上之用”,从而达到其“识时之俊日多,于国之才日出” 的政治目的。
2.选贤使能。 论文的考察重点不在李端棻对于同党同僚的规训,因为作者尚在收集晚清与其相关人物的不可多见的史料。相反,李端棻在学官位上二十余年,担任云南学政、主持山西乡试、分校顺天大试、以内阁学士身份主持广东乡试、主持四川乡试、任会试副总裁等主考官,其主考对象就是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有不教之教的训育便利;其荐举的名士名流,亦颇得其不言之教的道德濡化。李端棻在戊戌变法前,就曾向光绪帝力荐康有为,维新派遭受弹劾之际,他又举荐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入值懋勤殿,可见其称贤荐能的气度;在礼部尚书的任上,他向朝廷保举严修、耿保贤、崔朝庆、宋梦槐、程先申、熊希龄、唐才常、戴修鲤、曾习经、徐勤、欧矩甲、韩文举、夏曾佑、汤寿潜、寿富等维新派人士十六人,亦足见其爱才惜才的胸怀。严修在贵州学政任上,明令开设经世致用的课程,增加英文、算学、格致(物理与化学)等课程,赢得“经世学堂”的名号,后来严修自美国考察归来还创办天津南开大学;唐才常在“戊戌变法”期间,在湖南创办算学馆、南学会、群萌学会、《湘学会》和《湘报》,组织“自立军”,还在武昌发动“勤王讨贼”;熊希龄在时务学堂任提调,延聘梁启超为中学总教习、李维格为西学总教习,与谭嗣同在长沙创设延年会,认为兴学之本在师范,联合湘绅倡议整理湖南全省的书院;夏曾佑与梁启超、谭嗣同过从甚密,在天津与严复创办《国闻报》,宣传西学、鼓动变法、援引西方学说,形成“民智决定论”的文化史观…… 以上提及的四个人物,均为艰危时世之伤心蒿目的仁人志士,其人其事当是李端棻规训后学而生发效用的重要凭据。
3.学堂讲课。退居贵阳之后,李端棻参与学堂主讲、学堂创建、课程教学,用近代先进的学科知识训练学子,开启了贵州文教振兴的先河。李端棻回贵阳几日便欣然受聘于贵筑经世学堂,出于对老先生高山景行的仰慕,贵州书香世家子弟聚集在其周围,朝斯夕斯地领受老先生的桃李之教。其中,最突出的六位青年才俊是姚华、唐尔镛、王仲旭、任可澄、何麟书和桂伯铸,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贵州乡试的前六名,日后在贵州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均有不俗的事功。 有学者称李端棻经受“欧风美雨”的吹沫,熟谙西方教育制度与教育典籍,譬如卢梭的《爱弥儿》、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培根的《论事物的本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包尔生的《伦理学》等名著, 当然,这种经由读典而致的理论储备本是文人积学的基本功,李端棻晚岁在贵州经世学堂主讲西学内容,加之1903年撰写的《普通学说》,可以推断其所具备的西学功底足以推动西学知识的散布,明证就是李端棻曾专题主讲“卢梭论”、“培根论”,并大力宣介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
4.兴办教育。李端棻参与兴办教育至少有两个维度的表现,一是《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的通过奏折来提出教育改良意见,即经由改革课程来改造传统的书院以达到办成新学堂的目的,这是思想层面参与兴办教育的例证;二是在学官任上和避居贵阳之后的身体力行,受聘经世学堂山长,参与乡绅儒士的办学活动,并积极撰写《政治思想》、《国家思想》等文献来唤醒世人, 这是实践层面参与兴办教育的例证。之后,李端棻在贵州鼓动有志之士办教育,使华之鸿、任可澄、唐尔镛、于德凯和何麟书等参与兴办新式学堂,成为李端棻思想“最快与最彻底的接受者和实施者”(何克勤语),数年间年几百所贵州各类学校有如雨后春笋,深刻地影响着贵州各类教育的历史进程。譬如,贵州陆军小学培养的学生,在辛亥革命的历史大潮中,打响贵州巡抚衙门的第一枪;贵州通省公立学堂更是延揽人才,成为因材施教的教育重镇, 并促成近代教育体制在贵州的落地生根。他支持学子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运动,有利于贵州知识阶层的觉醒,为清末贵州教育改革的兴起,储备了“先锋式”的人才。其教育主张演变为教育实践,在贵州的具体表现就是:改书院、推广学校、改良经世学堂、发展官书局、选派游历。其中,选派游历有力地表明了李端棻借此来规训学子的孚育思想,他认为设置同文馆、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等,有其规训人才的局限性,那就是受其书斋的拘囿,李端棻毫不客气地指正其弊端在于“未遣游历”。故李端棻在贵阳避居之后亲自促成1905年春夏78名学子出国深造,秋冬73名學子赴日留学,这些学子中的绝大多数日后归来成为振兴贵州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
知识规训与思想启蒙
著名教育学家瞿葆奎撰文称,学者陈鸿祥所著《王国维全传》一书中“王国维1904年曾任教的江苏师范学堂是全国最早的管办师范”有误, 因为李端棻在1902年创办的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以及张之洞在1902年创办的湖北武昌师范学堂、陈宝琛在1903年创办的福建全闽师范学堂、张謇1903年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南通)、袁世凯1903年创办的直隶保定师范学堂等才是中国晚清最早的一批“官办师范学堂”,均在1904年端方创建的江苏师范学堂(苏州)之前创建。陈述这段学案的意义在于,声明李端棻创办的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具有中国近现代教育上的“先驱”价值,它不但有践行《请推广学校折》之教育主张的地方回应动作,而且有对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学制规定、教习聘请、生员资格、学习内容、专业分科、毕业待遇及经费来源等具体问题的落地生根。在李端棻的切实领导之下,创办群体勾勒了一个官办师范学堂的体制轮廓,并推行现代学校教育的规训制度,以期实现李端棻提出的“十年之后,贤俊盈庭,不可胜用”的教育目标。
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乃私人集资筹建,但校牌却以“公立”示人,学堂宗旨宣称:“以忠君爱国为本源,教授中学以上诸学课”;开设的课程有:“日文、化学、博物、万国历史、中国历史、万国地理、中国地理、地文学(兼天文学)、生理学、算术、代数、几何、法制学大要、国家学大要、国际公法大要、教育学、图画学、体操学”;考试评点方法为:“学生在学期间,实行学期试验、学业试验、卒业试验三种。成绩以‘评点方式核定,每科以二十点为得点。其得点各科平均不达三分之一者,为不及格。”学生守则为:“要求学生充其固有之良知良能,以为学而又必忠信、笃敬、持重、廉耻,与同学互相砥砺。如有一品行不正,才学浅劣,前途无中学教习之望者;二徒知放议时事,怠于讲习者;三屡犯堂规,悛悔无望者。经教习与总理副办会同商议命其退学。” 从上述章程的具体内容可见,办学者在作育新人上的良工苦心,我虽不同意秋阳判定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相当于大专层次的办学水平,但其开展知识生产与培养新人的学科规训制度,实是有案可稽的现代学校规训制度的典范。
彼时因八股文废除而代之以论说文,在实质性地参与规训后学的月课中,足见李端棻的思想开明,譬如他第一次月课即以“卢梭论”为题,第二次月考则以“培根论”为题,第三次月考再以“朋友相处,常常自己的不是,方能感化他人的不是说”为题,颇有开通黔中风气、提携后进的教育意图,至于阐发的民权自由思想则是其规训后学的实质内容。 诚然,李端棻没有像开缺回籍的翁同龢那样一蹶不振,相反以其病势尪羸的身躯成为贵州维新变法的一面旗帜和贵州经世学堂、贵阳公立师范学堂等宣传新学、规训后学的一员干将。譬如在学堂对于卢梭《民约论》中的“天赋人权说”与自由平等思想的散布,在私宅对于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进化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的宣讲,着实影响了一批青年才俊。在师资匮乏的情况之下援引日籍教员岗山源六,后又因其殴辱学生而遭到李端棻等人的强烈抵制,并将事件原委函寄在日本横滨主编《新民丛报》的梁启超,李端棻在整个事件中的态度坚定,其立身处世的风格堪为规训学子的鲜活道德内容。
李端棻一生虽无著作等身,但有值得教育学者关注的高文大册,譬如传世译著《苾园诗存》和《普通学说》,均被认为是研究李端棻的珍贵史料,《苾园诗存》由其表弟何麟书辑录成书,其存诗多为晚年对家国寒心销志的情怀,但亦可见他从帝党官僚转向维新派的人生大变故中,身怀经邦论道之情与出以公心之意地勉力规训后学的心理历程。譬如,在《应经世学堂聘》中,他借山长之位称述自己的离经辨志之教育抱负:“帖括词章误此生,敢膺重币领群英。时贤心折谈何易,山长头衔恐是名。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乍拥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 再如《学术思想》中,他感喟维新变法给教育以时至运来的转机,指正“虚空”之学误国误民,推出炼石补天的金石之计:“早知素习尽虚空,志积维新日有功。目的胡为犹惝恍,心思毋乃欠昭融。素王学术无今古,黄种灵明胜白棕。宗旨看真须取法,何妨时势造英雄。”
《普通学说》是李端棻规训思想的最集约式的表达,其刊印初衷在于帮助无条件入学的寒门子弟自学新学基础。李端棻在这个6400字的单行小册子里的修辞立诚是什么?李端棻做了如下陈述:“还乡以来,瞬将二载,睹吾乡人士未尝不思为学,而或蔽或偏,莫能自拔,不揣固陋,竭其所知,以与为学,诸君共求进取之途,著之于编,以共众览”,“自严范孙编修督学以来人始知学,至于今日空疏如故,不喜西学者固无论矣,即号知西学者亦只从数种报章少开知识。即而扣之,不特专门之学未之有也,即寻常之普通知识亦未之前闻,甚至本国地理、历史,不论新学旧学悉应通晓者亦多相对茫然”, 表明李端棻欲借为学的基础——“普通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以规训黔中学子的动因,全10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图书的途径与目的:救时和穷理;第二部分讲普通学说的分科:理化生、政法经、史地、博物与伦理;第三部分讲彼时中国教育改革的阶段与区分,启发黔中学子奋力直追东南士大夫的“兴学”创举。全书犹如匕首投枪,击中黔中教育的要害,同时亦显示李端棻接受东洋西洋之现代科学的自我规训格局,在国势衰微之时借力规训后学以大展经纶的政治谋略。
作为帝党官僚的李端棻与时俱化,渐变成为资产阶级的维新官僚,从其一生借力“教育与政治”之双向径路的救国强国的政治诉求中,足见其美人香草般的赤子之心。他不仅奥援维新变法的志士仁人,而且规训有志于学的四海学子;为学为文有高明远见,为官任上则行不苟合,作育人材更是有风有化;李端棻不仅是反哺故土的黔中乡贤,更是扶危定倾的华夏榜样。
李端棻乃科举出身,深知科举取士的利弊,故其改变时局的动因和举措具有其自身体会良多的“困厄感”使然,他深知不可再延续坐而论道般的僵化培育模式,而需抢占孚育“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的教育制高点。而他一生的教育实践表明,其规训自身与规训他人的自觉自识都很强烈,他为当世与后人所铭记,有其历历可辨的规训和潜移默运的教化这两个层面的铁案来佐证。
参考文献:
[1]李端棻.普通学说[A].贵阳城北官书发行所,1903.[Z].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室藏.2017.
[2]李端棻.苾园诗存[J].贵州文献季刊,1937.
[3]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Z].
[4]清史稿﹒李端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7.
[5](民国)贵州通志﹒李端棻传[M].
[6]康有为.祭故礼部尚书苾园李公文.1907.
[7]梁启超.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Z].1907.
[8]秋阳.李端棻传[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
[9]钟家鼎.李端棻评传——兼论维新官僚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10]罗文荣.梁启超与李端棻[J].读书,1985(4).
[11]方登学.慧眼识拔梁启超的礼部尚书李端棻[J].炎黄春秋,1995(6).
[12]史继忠.李端棻举才[J].贵州文史天地,1998(4).
[13]张新航.李端棻及其所著《普通学说》一书[J].贵阳文史,2005(4).
[14]龍炘成.北京大学奠基人李端棻[J].文史天地,2008(4).
[15]张立程.西学东渐与晚清新式学堂教师群体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6.
[16]冉海霞.晚晴清流派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5.
[17]李瑞锋.戊戌维新与北京的会馆[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6.
[18]杨菲.晚清贵州书院改制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3.
[19]黄士嘉.晚清教育政策之研究(1862-1911)[D].台北: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1992.
[20]曾重凯.晚清科举废除后传统士人的动向(1905-1926)[D].台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1995.
[21]陈泽恺.黔人端棻(新编历史京剧剧本)[Z].贵州京剧院,2014.
[22]顾久.我们为何要重提李端棻[J].贵阳文史,2010(6).
[23]刘学洙.李端棻:一部改革者的大书[J].当代贵州,2016(1).
[24]刘宗棠.维新之艰兮,公缔其始——纪念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120周年[J].贵州文史丛刊,2016(4).
[25]李良格,李良筑.贵阳李氏家谱(第三稿)[Z].北京大学档案馆藏,2017.
[26]马筑生.李端棻研究史料(未刊)[Z].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