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鲁布革:不忘经典,造物未来
2017-05-30
鲁布革,一个被阐释了30年的经典项目。
她是中国现代项目管理的策源地,是项目管理教材中必然出现的名字。
2017年7月,本刊专题报道组从烈日下的北京出发,前往进入雨季的云南,重访鲁布革水电站,找寻那些时间无法抹去的辉煌。
本期《项目管理评论》精心策划推出“纪念推广鲁布革经验30周年专题”,以期站在现时语境,透过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光谱,铭记经典,造物未来。
鲁布革,一个被阐释了30年的名字。
作为布依族语地名,“鲁布革”意为“山清水秀的寨子”;作为中国现代项目管理策源地,鲁布革是实践的起点,也是历史的经典。
在没有手机、没有IT系统、不知AlphaGo为何物的年代,鲁布革水电站建设项目(下称“鲁布革项目”)造就了多个“第一”:中国第一次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国内第一个引进世界银行贷款的工程建设项目,首个土木施工国际招标项目,首个采用合同制管理的项目,首次引进监理制度的项目……
1987年8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题为《鲁布革冲击》的长篇通讯,由此,鲁布革水电站项目引起广泛关注,影响深远。
鲁布革经验究竟是什么?也许现已无人能全盘言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历史的证据中,找寻现时语境下中国现代项目管理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的线索。
2017年7月,《项目管理评论》记者从烈日下的北京出发,前往进入雨季的云南,重访鲁布革水电站,以期鉴古知来。
最前沿的山沟
从罗平火车站租车前往鲁布革,一路时而入云端,时而过洼地,直至滇、桂、黔三省通信商发来消息,才知已到“鸡鸣三省”的结合地——鲁布革。
鲁布革水电站在一片深山峡谷中,峭壁千仞,飞涛入川,声振雄浑。遥想当日徐霞客所言“破崖急涌,势若万马之奔腾”,果然并非妄论。
陪同我们的是云南大学教授汪小金。20世纪80年代,正值年少的汪小金见证了中国项目管理的生发。
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鲁布革项目迎来大好机会。为了解决资金困难,推动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改革,1981年,国家决定为鲁布革项目申请世界银行贷款。
1984年,世界银行贷款协议生效,鲁布革项目获贷款1.454亿美元,挪威王国政府赠款9000万挪威克朗、澳大利亚政府赠款790万澳元,另有少量世界银行软贷款、加拿大政府赠款。
获得这些外资后,一个新型的项目管理机构——鲁布革工程管理局(下称“鲁管局”)正式成立,鲁布革项目全方位改革开放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此时,年仅20岁、大学刚毕业的汪小金已被分配至此,一干就是10年,直到鲁布革项目通过国家验收。
汪小金表示,第一份工作就在穷乡僻壤,“起初是不甘心的,但鲁布革这个窗口,能看到很多值得学习的先进东西。”
顺着山路登顶,到达昔日鲁管局办公室所在地。这里云雾缭绕、雄奇清幽,“早看日出云海,晚看日落星辰”。漫步川流山峙间,不禁有问道游仙、举天地万物的遐感。
景象虽似世外,生活却无从逍遥。
“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的,”汪小金回忆,“用石头砌一些简陋的小房间,就成了领导们的住处。我们那时住在贵州、吃在云南、望着广西。”正是这些“小房子”成了鲁布革冲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鲁管局是根据世界银行贷款要求设立的项目管理机构。鲁管局成立之前,由云南省电力局(下称“电力局”)、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下称“十四局”)、昆明水电勘测设计院(下称“昆明院”)对鲁布革项目“三足鼎立,分权而治”。鲁管局的出现,直接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布局。
愤怒、谩骂、哀怨……这些情绪背后,是对未知的不安。当时有“段子手”调侃:“鲁管局这个‘小轮子必将被十四局、昆明院和電力局这三个‘大轮子碾得粉碎。”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还得感谢杨局长。”汪小金说的杨局长,是他“心中最伟大的项目经理”、鲁管局局长杨克昌。
“杨局长的思路很好。他一开始没有用行政手段让大家接受鲁管局,而是先做出业绩,潜移默化地让大家理解和接受。鲁管局和相关单位之间良好合作,是鲁布革项目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鲁布革项目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还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国家对鲁管局的顶层设计非常到位。国家授予了鲁管局“总管”鲁布革项目的权力。这种总管,就是现代项目管理方法中特别强调的“整合管理”。任何项目都必须设立一个对项目成败承担最终责任的总管团队,这一点是不会过时的。
要落实总管的权力,并不容易。由于鲁管局和十四局、昆明院都没有合同关系,如果仅以合同为依据,他们完全可以不配合工作。在各单位都致力于为国家建设做贡献的前提下,鲁管局用开明的态度和服务的精神,赢得了大家对鲁管局的理解和接受。中国人文环境的特殊性,也造就了中国项目管理的魅力和优势。
“别看这里是山沟,但它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方。鲁管局的整合管理,在今天仍非常适用。”汪小金感慨。
大成冲击波
如果说鲁管局是“来自内部的刺”,那么外国承包商则是“来自外部的矛”。内外夹击,推动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改革。
鲁布革项目之前的水电建设,采用由政府指定国内施工单位自营建设的管理体制,经过一次次实践固化,已形成由上至下的思维惯性。
根据世界银行要求,鲁布革项目引水隧洞工程采用国际竞争性招标。日本大成建设株式会社(下称“大成公司”)一举中标,而早已驻扎在鲁布革现场的十四局,开标后第一轮即惨遭淘汰。
这对十四局是一次惨烈的冲击。正如报告文学《鲁布革阵痛之秘》(作者:汤世杰,李鹏程,《花城》1988年第5期)中写道的“我们就像一位带着嫁妆、坐着花轿、兴冲冲赶往婆家的新娘,可到了那里一看,新郎竟娶了别人。”
据汪小金介绍,“大成公司到鲁布革后,首先的冲击就是报价太低了,只有8400万元人民币,而我们的标底是1.4亿元人民币。十四局的人员和设备已在鲁布革现场,而大成公司还要从国外调。他们靠什么?管理好,浪费少!”
据鲁布革项目亲历者、昆明院副总工程师曹以南回忆,大成公司的现场管理很到位:“他们的工地干净、整洁、有序,你根本不用担心会踩到钉子。他们浇出来的混凝土会反光,照得出人影,手一摸光溜溜的。”
当年的工长徐运汉,在《情满绿水青山》(黄河水利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写道:“(大成)公司很注意工人的技术培训,每个工人发一张钻孔布置图,各人的钻孔范围基本上是固定的。每次爆破以后都要让钻手看看效果,有没有超、欠挖。如果超挖过大,日本人就帮你分析找原因,多次纠正不过来,那就不叫你干了。”
台车工陈石益这样描述大成公司的“管理经”:“核心就是围绕项目,用经济手段激励工人干活,一个是收入和掘进任务挂钩,再是考核计算简单明晰,每人每天收入多少,人人心中都清楚。”(《腾身却放我向青云里》,作者:陈昌云,工人日报,2015年8月3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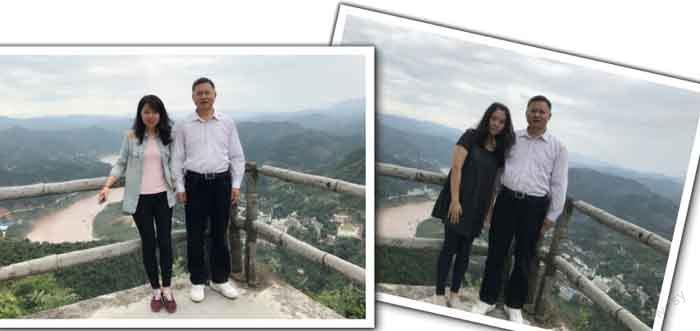
一方面,大成公司用30多名来自本部的管理人员和400多名来自十四局的工人,引水隧洞工程的进展高歌猛进。另一方面,十四局承担的首部枢纽和地下厂房工程,进度严重拖后,直接威胁到按期截流和按期投产。这种鲜明的对比,刺痛了十四局员工,也刺痛了许多中国人。
活生生的差距,把十四局逼上新起点。他们渐渐明白,问题的根本不在技术和设备,更不在工人,而在管理方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沿用的行政成建制管理方法,已经不适用于做水电建设工程。为此,十四局开始积极学习大成公司的管理经验,主动进行管理方法的改革。
相关资料显示,十四局成立了厂房工程指挥所(相当于项目部),实行所长(相当于项目经理)负责制,组建精干的施工队伍(相当于项目团队),实行科学管理。结果是,劳动生产率成倍增加,提前四个月完成厂房开挖。
市场思维的启蒙
世界银行给鲁布革项目贷款,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建设资金不足,而且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鲁布革项目聘请了三个国际咨询团(组),负责为项目提供技术指导、管理指导、人员培训等事宜。可以说,国际咨询团(组)的到来,引导了鲁布革项目全面与国际接轨。
鲁布革项目的三个咨询团(组)是:特别咨询团,由四位著名的国内外专家组成,负责对工程设计和施工的决策性咨询;挪威咨询组(AGN),负责对地下厂房工程进行技术和管理咨询;澳大利亚雪山工程公司咨询组(SMEC),负责对首部枢纽和引水隧洞工程进行技术和管理咨询。
专家们一到鲁布革,便经历了与大成公司相似的“待遇”。一些人埋怨,以前那么多工程都干過了,还需要问别人吗,太丢脸了!
“原来我们做项目,由领导带一组人到山头,用手指一比画就把方案定了,没什么道理可讲。”在世界银行中国贷款项目顾问、清华大学教授吴之明看来,这种“原生态”管理方式正是十四局受冲击的主要因素。
相关资料显示,三个咨询团(组)对工程设计和施工优化提出的建议,经我国技术人员吸收消化、实施之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节约了工程投资3600万元,约占项目总投资的2%。
咨询团(组)带来的效益,当然不局限于经济效益,更传播了新的设计思路、施工思路、管理方法。例如,鲁管局该如何按国际通行的方式与大成公司打交道?如何与世界银行打交道?这些步骤都是在SMEC的指导下顺利进行的。
在鲁布革项目施工现场,AGN和SMEC许多次为中方人员开展培训,内容包括工程技术、合同管理、项目管理和电厂运营等方面。参培人员来自电力局、鲁管局、昆明院、十四局和其他相关单位。这些培训对提高我国工程技术和项目管理水平作用深远。
世界银行对培训经费的管理方式也值得借鉴。作为鲁布革项目现场培训的受益者之一,汪小金向我们介绍,在世界银行贷款、挪威和澳大利亚赠款中,都含有数额不小且必须专款专用的人员培训费。世界银行代表团检查项目进度时,会专门过问培训工作的情况。此外,鲁管局也拿出大量的办公经费,投入员工培训。
据吴之明介绍,鲁布革项目结束后,世界银行意识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和国际规范接轨,于是成立“经济发展学院”(Economic Development Institute,EDI),通过项目经理师资培训(Training of Trainer,先培养一批项目管理教师,再由这些教师培训项目经理)积累人才。
在市场经济思维未深入实践,甚至“项目管理”四个字还没明确提出的时代,一个待脱贫的山沟在“外力”作用下,渐次融入开放、人文、规范的国际语境。
过渡时期的经典产物
自《鲁布革冲击》发表后,学习鲁布革经验成为热潮,尤以建筑业为典型。鲁布革经验,是在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好形势下,由国内外众多单位和个人共同创造的。
1987年10月,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劳动人事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文,要求建筑施工企业试点推广鲁布革工程管理经验,采用“项目法施工”。
“从鲁布革冲击的出现到‘项目法施工的提出,是鲁布革经验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汪小金认为,“项目法施工的提出,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虽然现在已经不太使用这个词了。”
“从‘项目法施工的提出到正式引入‘项目管理这个术语,可看作鲁布革经验形成和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作为鲁布革经验的主要内容,业主责任制、招标承包制、建设监理制被广为宣传。同时,不少业内专家开始思考更深层的概念——工程建设项目管理。”
1988年10月,以鲁布革项目为背景的《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教材极有可能是我国第一本全面讲述项目管理的著作,它把鲁布革工程管理经验与国际项目管理学科进行了较好对接。
“从1989年初到1994年8月,是鲁布革经验形成和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鲁管局主动按项目管理的要求对内部机构设置进行了实质性调整,整个项目顺利竣工并通过国家验收,世界银行对鲁布革项目进行完工后评价,以及鲁管局全面总结鲁布革的项目管理实践。”
1994年8月,鲁管局精心编写的《鲁布革水电站建设项目管理的实践》一书,由水力发电杂志社出版。这本书以改革开放为主线,以项目管理为主体,全方位、多层次地记述了鲁布革项目的建设历程。
几经辗转,我们拜访了时任鲁管局副局长周醒钟。周局长自称“水电建设退休老兵”,而他记忆中的“战友”,多半已不在人世。受某电站项目风钻刺激,老人家听力渐失,如今靠手写和人交流。
由于无法辨别声响,周局长的嗓门有些大。谈及鲁布革,他一语中的:“鲁布革项目是过渡时期的过渡产物,好在过渡出了比较好的结果。”
鲁布革实践是在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中进行的。彼时,电力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和产权改革还没起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实质性转化的阶段,鲁布革项目推动了中国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由感性冲击向理性沉淀、操作层面向制度层面、局部实践向整套方法的过渡。
未完成的旅途
1987年,与中国刚步入现代项目管理阶段同时,南澳大利亚大学开设项目管理专业,PMI发表题为《项目管理知识体系》的研究报告,世界正将项目管理发展为方法、学科和一整套职业资质规范。
隨着PMI《项目管理知识体系指南》、IPMA《项目经理能力体系》等规范标准的引入和推广,高等院校项目管理硕士研究生专业的开设,多个项目获得IPMA的项目大奖,我国项目管理的专业化、职业化、制度化程度渐与国际接轨。
本次报道筹备期间,我们在微信平台发布问卷,收集大家对鲁布革的兴趣点。一些项目经理还发来工作中面临的问题,如:甲、乙关系超越项目合同本身;前期销售方案项目可行性未经验证,存在先天性缺陷;缺乏制衡的项目治理结构;项目的决策者经常不是项目经理,而是项目经理的领导……
这些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说明我们在“反向格义”的同时,仍然比较欠缺“创造性的会通”。
鲁布革水电站建成后,大坝回水形成“小三峡”风景区,山水相映,气象万千:雄狮峡、滴灵峡、双象峡,高峡出平湖;玉带湖、腊月湖、弯子湖,三湖夹腊山。烟江叠嶂中,隐约可见开门迎客的布依族民宿。今天的鲁布革,除了水电站,还有时下正热的文旅项目。
置身青云徘徊的鲁管局旧址,虽然人事皆非,但得以阅览人与自然合力而生的造物美学,不禁感慨一代开拓者的盛炽年华。
“我有时还会梦见他们,那些和我一起在鲁布革工作过的人。”回程的火车上,汪小金深情地说道,似乎那些熟悉的面孔正浮现在他的眼前。鲁布革,随着隆隆的火车渐行渐远,却让我们无法忘却……
回顾经典,是为了创构自身的经典。梳理鲁布革的历史光谱,并非要将所谓经验装饰性地代入现时,而是以它为参照系,拓展中国项目管理的新的可能。
从“知物”到“造物”,我们仍在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