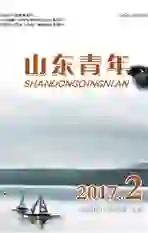中国情法之辨
2017-05-20郭于会��
郭于会��
摘要:前些年,“亲亲相隐”制度引起学界大讨论,被当成封建糟粕为人们所诟病,但这种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价值规范不正彰显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之处吗?本文试图从“亲亲相隐”制度谈起,通过分析“家国同构”的忠与孝,延伸至现代社会,探讨当今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亲亲相隐;道德;法律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以情为本的国度,一切皆离不开情:“人之常情”是情,“盛情难却”是情,“通情达理”是情,“风土人情”也是情……而众多情中,亲情里的“亲亲相隐”制度源于先秦,贯穿我国法律发展的始终。先秦有“子为父隐”,汉代有“亲亲得相首匿”,民国有“对亲属不得提起自讼”等规定,“亲亲相隐”作为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而有别于西方之法。然而,法律的第一原则——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揭示了法律作为刚性的、铁面无私的“规矩”,要求人们公平、公正、公开地对待人和事。那情与法到底该如何取舍呢?许多学者的观点不一而足,因此情法之辨在我国一直经久不衰。下面来谈谈我国语境下的情与法。
一、“情”与“法”之涵义解析
首先,“情”指人之常情,也即伦理道德,涉及人的内心向度。在我国,“情”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家国同构”中的“家”,如对长辈的孝敬之情,同辈间的手足之情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此情的表现。扩展至整个社会,“情”更多通过道德行为外化出来,“道德是非强制性地调节社会关系的规范”,以善恶为评价标准,主观性较强,因为善恶没有具体的准则来衡量哪种行为是善,哪种行为是恶;也没有具体规定某一行为到哪种程度属于善,到哪种程度就变成了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所说,“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①他把善作为行为的目的,而我们把善作为评价行为的尺度。后又提到“幸福作为最高善”,那关于什么是幸福,又没有具体的标准。“不同的人对于它有不同的看法,甚至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也把它说成不同的东西……”②并且他不遗余力地列举各种属于善(德性)的东西:勇敢、节制、慷慨、诚实
……最后说:“善事物有两种:一些是自身即善的事物,另一些是作为他它们的手段而是善的事物。”③由此可知,善并非无定论,但要界定善与恶,把握“适度”却很难。因此,如何衡量“情”,如何判定亲人间的“情”合乎人之常情的“亲亲相隐”,又是难上加难。
其次,“法”即法律,是国家机构制定的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外化为具体的条文规范,以强制性措施来规定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有明显的导向性。“法”毋庸置疑就是“家国同构”中的“国”。“法”时常给人以冷冰冰的印象,内容多是禁止性规范,多以否定口吻来规定人们不准做什么,为人们设置了一个框架,框架内的行为合法,越界的行为非法,明确指出对与错的边界。
由此看来,“情”与“法”在形式或内容上都难以达成共鸣,甚至针锋相对:道德以人内心的主观信念为出发点,外在形式多为社会习俗,是软性规定;法律以社会普遍意志为出发点,外在形式多为客观公正的规章制度,是硬性律法。然而无论是不讲情面的“法”,还是人之常情的“情”,本质上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具体来讲,情理上的“善”其实就是价值判断中的“应该”,“恶”就是价值判断中的“不应该”。而法律把哲学上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融为一体,即“对”与“应该”是同义的,“错”就等同于“不应该”。因此“情”与“法”就统一了。
二、“情”与“法”之关系辨析
从古至今“情”与“法”并非水火不容。但在古代,道德法律化趋势更明显。传统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家道德中的“亲亲相隐”制度。
汉董仲舒推行“独尊儒术”措施,开始了儒家伦理和传统法律融合的进程。“情”在先秦时期,表现为孔子提倡的“仁”,主要重视人与人相处的规范。“先秦伦理主要是一种宗法伦理、家庭伦理,但也初步显示政治伦理的色彩。”④两汉时期,“情”最突出表现为“孝”,极大促进了“亲亲相隐”制度的发展。统治阶级提倡以“孝”治天下,推行“举孝廉”制度,且不论这种将“情”硬化为“法”的做法对子女而言有道德绑架之嫌,单讲其后果就危害极大。在此影响下,以法令形式颁布养老令,孝文化促使子女极度维护父权,进而使父母拥有极大的权力,以致最终形成亲亲得相首匿法。以情入法,以孝制法,显然将“情”极端化了,说明“情”对传统法律产生的影响之大。“法”是“情”的实现形式,这里的“情”已经异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情”主要表现为“礼”,情法融合的特色就是以礼入律。晋律首立丧服制度,对违反丧服制度尊卑之间的行为进行量刑。由于统治阶级多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缘故,对长不孝即为对国不忠,这样就把礼与法交融起来。在这种融合中伦理道德与传统法律是不对等的状态,“情”居于主要地位,对“法”有深刻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涵盖甚至吞噬了“法”;而传统“法”居于弱势地位,沦为维护封建道德的工具,被动受到“情”的熏陶。至此,“道德法律化”、以“情”为“法”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这种源于血缘的“情”重于源于公理的“法”,因此“亲亲相隐”制度也就顺理成章地盛行直至近代。
随着现代社會的发展,“情”与“法”转变为高要求与底线的区别——道德是教导人做好事,法律是要求人不作恶。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里的“人人平等”就暗含着“法不容情”的意味,不论是陌生或熟悉,不论敌人或亲人,都必须抛弃一切“情”按照事先制定好的制度来依“法”行事。加之作为四端之情的恻隐之心似乎越来越缺乏,人们变得越来越冷漠。施韦泽曾说“道德的大敌是麻木不仁”。2010年河北省高院研究通过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中关于亲人举报即可减刑的规定虽既不合情也不合法,但从侧面说明了“法不容情”已经到了一种极端地步。由此看来,当今“法”的地位高于“情”,“法不容情”优胜于“亲亲相隐”。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不断变化发展。人是有感情有温度的,满足正当情感需求是必要的,因此不可能存在不容情的“酷法”。法律是底线的道德,随着人们道德素质的提升,法律道德化是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三、“情”“法”冲突之我见
法律关注的是人的行为后果,道德更多关注人的内在追求与主观动机。因此二者必定会存在一定的冲突。刘云林老师曾在《公民情感的法律确认》中指出,“人的本能要求人们以家庭和亲情为重,信赖家庭,依赖亲情。”⑤而法律却规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面对这两难境地,该如何抉择?
在我看来,道德与法律应该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法律必须是有人情味的法,而非冷冰冰的条令;道德应该作为法律的基础和补充,为法律指明方向,净化人的内心世界。二者都是维护公平正义,“亲亲相隐”为了家庭和睦,是人的本性要求;“法不容情”为了社会正义,是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构筑法治社会时,要高度重视伦理道德的应有地位,处理好“亲亲相隐”与“法不容情”的关系,使“硬性的法”内化为“软性的情”。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②同上,第9页.
③同上,第15页.
④刘绍云:“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理论学刊》,2003年第6期,第33页.
⑤刘云林:“公民情感的法律确认:立法伦理的应有视域”,《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4期,第39页.
[参考文献]
[1]刘云林.公民情感的法律确认:立法伦理的应有视域[J].伦理学研究,2007(4).
[2]刘绍云.儒家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J].理论学刊,2003(6).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