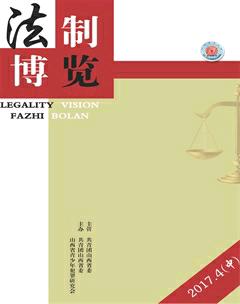论负担行政行为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2017-05-20黄文瀚
摘要:对于负担行政行为违法,通说的观点认为行政机关可以随时予以撤销、废止,信赖保护原则于此不适用。理由是负担行政行为既然对人民不利,那么撤销不会发生即得权和信赖保护的问题。然而,这种通说仍有例外,如果当事人现有负担被更不利的合法处分所取代,或者是当事人遵守先前的处分内容,已消费和处置标的物,以致无法或很难回复。这两种情形出现,撤销先前的负担行政行为会使人民处于更不利的境地,由此来看,负担行政行为中仍然存在信赖保护的利益,既然存在信赖保护利益,并且符合信赖保护原则的构成要件,就应当援引信赖保护原则予以保护,不论该行为受益还是负担。
关键词:负担行政行为;信赖利益;行政法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11-0008-03
作者简介:黄文瀚(1993-),男,汉族,江西抚州人,华东交通大学,2015级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学。
一、负担行政行为概述
在中国,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有效运用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所产生的法律行为。以行政相对人是否是特定的相对人为标准,我们通常把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但为了更好的认识行政行为的特征,我们还可以更具体的分析行政行为的效果、合法等特征以及运行机制,并加以辨析。
(一)负担行政行为和授益行政行为
以行政行为对于行政相对人所产生的效果为标准,可以把行政行为分为负担行政行为和授益行政行为。负担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实施的对相对人予以不利益或侵犯相对人权益的行为。例如对当事人的罚款、行政拘留等等。授益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实施的为相对人确立、确认权利或法律利益的行政行为。例如行政许可、行政确认某种身份资格等等。台湾学者对于两者的关系还有进一步的论述:“凡对相对人产生设定或确认权利,皆属授益处分;又废弃对相对人不利的负担处分,该废弃本身对相对人有利的,其亦属受益处分”①“凡对相对人产生不利效果的,无论是课于其作为、不作为或者忍受义务(如征兵),或者变更、消减其权利或者法律上的利益(如撤销许可),乃至拒绝其授益之请求(如拒绝申请)的前述的消极处分,俱为负担处分”。②在程序设定上,负担行政行为较为严格,而授益行政行为更为宽松。
然而授益和负担本身对于不同的个体来说感受是不一样的,一个行政行为实现的效果也不是单一的,往往有多重的效果。例如相对人向行政机关申请抚慰金2000元,行政机关最终只批准了1000元,另外1000元被驳回。对于相对人而言,批准的1000元显然是受益。然而剩下驳回的1000元没有实现相对人期待的利益,因而又具有负担性质。授益性行政行为中对当事人产生受益效果,但也可能对第三方产生负担效果。在行政法中,前一种情形属于混合效力的行政行为,后者被认定为第三人效力的行政行为。对负担行政行为和授益行政行为的分类,与行政法的一系列问题相联系,其中就涉及到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问题,关于这一点,后文會进行详细阐述。
(二)负担行政行为与违法行政行为
在我国的行政法实践中,违法行政通常指行政主体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通常违法行政的形式有:无权或者越权行政、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滥用职权,程序违法等。违法行政行为产生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曾说过:“世上不法之事莫过于执法人自己破坏法律。”③执法者的行为违法对于相对人的利益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一般而言,行政主体的违法行政行为会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但是也不尽然。例如行政机关违法颁发行政许可,虽然行政主体是违反行政行为,但是对于行政相对人并没有产生负担,而是受益的。由此可见我们并不能把违法行政行为等同与负担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行为是以合法为标准认定的,而负担行政行为是以对相对人产生的效果来判断的。两者常有重合但并不包含,负担行政行为倘若违反的是道德,即使我们认为这个行为是不合理的,但并没有触犯法律规定,也不能认为是违法的,这也是行政行为中合法性与合理性冲突的一个表现。
通过对上述概念的阐述,我们认为行政行为的成立应当具有以下三个要素:
第一是具有法律认定的行政主体的存在;第二是运用了行政权力,做出了对相对人的行政行为;第三是确实对行政相对人造成利益损害的负担效果。
二、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中的运用
所谓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极其管理活动已经产生信赖利益,并且这种信赖利益因其具有正当性而应当得到保护时,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变更这种行为,如果变更必须补偿相对方的信赖利益损失。由此可见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有两个关键:一是是否存在信赖利益:二是这种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信赖保护原则肇始与德国行政法院判例,经日本和台湾的学习、发展、传播,我国的《行政许可法》最早将信赖保护原则引入,现如今信赖保护原则已成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根据国内外行政法的理论研究,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主要有四个要素:(1)信赖的对象是行政主体或者得到授权的行政行为;(2)行政相对人却有实际的信赖;(3)行政相对人不仅产生信赖,并且以此信赖为预设而进行了其它行为;(4)信赖利益合法且保护之利益大于撤销之利益。与此同时法律对于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还做了几点排除:(1)行政行为本身是由行政相对人通过胁迫、贿赂等不正当方式产生的;(2)行政相对人对于重要事项隐瞒或者不正确描述;(3)行政相对人应当知道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是违法的;(4)行政行为有显著的重大的错误;(5)行政机关预先保留了变更权。
从政治哲学角度而言,任何政府的存在基础是民众的认同和信赖,政府行为不保护民众的认同和信赖无异于自毁其身。④在行政行为没有重大瑕疵或者严重损害第三方和公共利益时,应当尽可能的保护信赖利益。对于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在行政法的适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负担行政行为理论与信赖保护原则的矛盾与冲突
联邦德国宪法、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大陆对负担行政行为并没有设置任何限制,缘由是负担行政行为既然产生负担,那么这种不利的消除对于人民来说是受益的,且之前的负担处分并不会产生信赖利益。但是这种考量并不细致,我国台湾的学者提出负担行政行为是否必然排除信赖保护原则值得商榷。例如在司法实践中,行政相对人被行政机关处以了10万元的行政罚款,不久后行政机关根据掌握的最新证据,改变原先的处罚,判处罚款20万元。如果当事人因为信赖了第一次处罚的决定,把自身财产10万元以外的部分处分了以至于行政机关无法执行,那么面临的可能还有罚款以外的处罚。分析这个例子,行政主体作出的第一次处罚显然是个负担行政行为,但第二次处罚造成的负担比之前的更加重。
诚然行政机关在这个处罚中是有过失的,但是行政相对人对第一次的处罚也产生了信赖,并以这种信赖为预设作出了其他的处分行为。我国现有的原则是一事不再罚,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有理由相信行政机关对其做出的处罚是终决,第一次的处罚产生的相信或者信赖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有关的学者对于负担行政行为的排除信赖保护原则提出了两点例外:(1)由于对人民更不利的合法处分所取代;(2)行政相對人由于遵守处分内容,已消费或者处置标的物,以致无法或很难回复。这两种情形下,撤销行为将使人民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因此看来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很有必要。
2003年8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可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2004年3月,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将信赖保护原则扩大适用于所有的行政领域,明确指出:诚实守信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行政机关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律程序不得撤销、变更已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其他法定事由需要撤回、变更行政决定的,因依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相对人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予以补偿。然而我国行政实践中一直不注重信赖保护原则,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处于强势地位,“有错必纠”和“公共利益优先”等观念仍然是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信赖保护原则还没有被行政主体深刻的认识并指导于实践。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随意变更的情况仍然不少见,负担行政行为是否要改,如何改等问题成为行政主体的难题。如果这个负担行政行为是违法行为,那么这种有错必改会带来其他的后果或许是行政主体未曾细细考量的。
四、冲突矛盾的协调与平衡
负担行政行为中,行政主体对负担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变更与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发生冲突时,冲突双方的地位往往并不对等,行政相对人由于各种原因在和行政主体的对抗中处于弱势地位,强大的行政权很容易侵犯到弱小的信赖利益。负担行政行为如果有瑕疵,那么法律允许行政主体有自我纠错的权力,但必须同时兼顾其中的信赖保护利益,尽可能在职权行为和信赖利益中保持平衡。
在世界范围内很少有对负担行政行为中信赖保护的规定。但是借鉴和吸收信赖保护原则在其他行政领域保护规则,也有着指导作用。
(一)对负担行政行为的变更进行限制,如果负担行政行为是违法行为,那么负担行政行为的变更应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于有明显和重大违法的情形应宣布无效;二是轻微程序违法但对相对人的实体权益没有重大影响的,进行补正即可;三是一般的违法情形可以灵活转换。《德国行政程序法》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完善。通过对负担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变更作出限制,避免小错大纠而引发的一系列信赖保护利益损害。
(二)对负担行政行为的撤销进行限制,负担行政行为的撤销通常不会对相对人的利益造成损害,但是应当明确如果撤销行为确有造成更大负担甚至危机社会公共利益的,这种撤销应当慎重考虑,对于撤销行为应当予以限制。
(三)除斥期间的限制,行政法中少有除斥期间的论述,除斥期间常见于民法,指法律规定某种权利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如果不在此区间行使权利,则预定期届满便发生该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但原来的法律关系继续有效。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为行政主体行使对生效行政行为进行变更、撤销设立除斥期间与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间行使救济权一样,行政主体同样应该有时限的要求。对于时效的设置,对于稳定社会现有的信赖关系产生重要的作用。⑤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都有对行政行为变更、撤销的除斥期间设定。对负担行政行为中信赖利益的保护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四)信赖利益的救济,信赖利益一般包括既得利益和期待利益。但是在负担行政行为中并不存在对于当事人的受益,在负担行政行为中,行政相对人没有得到利益但存在对于受到处分后没有更大负担的信赖,这种无加重处罚的信赖对于受罚的行政相对人来说可以归纳为一种期待利益。对于行政主体变更、撤销负担行政行为加重了行政相对人负担的行为,行政相对人可以在行政途径和司法途径寻求保护,行政途径包括行政复议和行政申诉,司法途径主要包括行政诉讼。在国家赔偿法中还可以增加对信赖利益的赔偿规定,以便通过行政诉讼方式来保障正当的信赖利益。
负担行政行为中存在的信赖利益长期没有得到关注和重视。以至于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的纠错机制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其中小错大纠的做法严重影响了行政相对人的合理信赖。任何一个人都有理由相信行政机关不会进行二次处罚,这种期待或者是信赖是合理的,并且以此为预设进行的相关活动就会涉及到信赖利益。法律赋予行政主体主动撤销或者变更违法和不当的行政行为主要是为了自我纠正和息诉止争。然而我国法律对于行政主体的这种变更甚至撤销并没有完善的限制措施,当负担行政行为生效后乃至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行政主体的这种变更或者撤销就会既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影响到法的安定性。对于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也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从而降低行政行为的公信力。因此将信赖保护原则引入负担行政行为很有必要,这种信赖利益的保护不仅仅是作用于行政相对人,也保障了行政主体自身的权威和行政行为秩序的稳定性。
[注释]
①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M].台湾: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572.
②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22.
③Der Zweck im Recht,Band 1-2,Leipzig 1877-1883<法律中的目的>(共两卷).
④张树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⑤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25.
[参考文献]
[1]张树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章志远.行政撤销权法律控制研究 [J].政治与法律,2003(5).
[3]冯举.纠错行政行为与信赖利益保护 [J].中州学刊,2006(5).
[4]黄学贤.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研究 [J].法学,2002(5).
[5]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6]胡建淼.行政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7]应松年.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8]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罗豪才.现代行政法制的发展趋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0]翁岳生.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11]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一、二)[M].台北:台北三民书局印行,1999.
[12]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M].台北:台北三民书局印行,1980.
[13][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